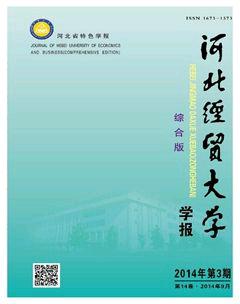從“養生”到“逍遙”的莊子之美
張振飛 張勝南
摘要:莊子是一位有極強現實關懷的浪漫主義者。為了結束當時人們的倒懸狀態,莊子通過含弘光大的思想系統和汪洋恣睢的語言文字,提出了由養生到逍遙的懸解之路。他的理論旨趣在于實現個體逍遙進而人人得以自由,最終達到天下大美的狀態。而他順道而行、靜觀默賞的自然美正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
關鍵詞:倒懸;養生;逍遙;自然美;莊子;道家;理想人格;浪漫主義
中圖分類號:B2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573(2014)03-0022-04
莊子具有藝術化生命情調的逍遙游人格理想是基于自然本真并指向自由的。為解倒懸的時代困惑,莊子主張順任自然的養生之道:自然之道由物及人,人性之美盡在于真誠無偽的順道而行。莊子以“游”的姿態對待人生,面對現實的殘酷,提倡心靈的超越,他懷著一種無奈、悲痛的心情為解世人之苦超然而與道游,為世人樹立了游心的逍遙自由之榜樣。
一、懸解而朝徹
莊子思想的著力點,應是“懸解”,《大宗師》中說道的: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人所謂懸解也。從此點出發莊子多言養生,意圖將生命提升至逍遙的境界,如此言語往復之間,便生發出了莊子的美學思想。正如方東美先生所言:“道是蘊藏在莊子《逍遙游》一篇寓言之中之形上學意蘊。”[1]這樣一來,我們便可沿尋莊子從“養生”到“逍遙”的文字略窺其道體思想之一二。然而,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因此莊子認為若想達到懸解的目的,勢必得接觸那些有結之物。《知北游》有言: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如此短短一生,“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可見于此生而活之人,大多哀戚不已,不知何所從。又《田子方》云: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可見人于此生當中最大的悲哀莫過于身生心死:生卻不知己所以生,不知其生之價值和意義,忙忙碌碌卻不知何所來、何所從、何所往,如此則妄有一副軀殼,反倒為之所困鎖。
莊子正是有感于此,才認為人必須超越現況,這種超越并非在于軀體安置的現實,而在于心境,即心靈的超越。在莊子看來,若心靈死寂,即便是軀體再怎么完好都沒有意義。在此點審美上,莊子是大異于常人的。《德充符》中的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哀駘駝, 跂支離無脤和甕盎大癭這些人個個丑陋殘缺非常,然而他們無視自然稟受,與物為一,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并且與德為友而內德充足,因此遠比世俗所謂的美人更美。以至于孔子、子產、惠子與他們相比都無不汗顏。在此,莊子以他夸張的語言所呈現出的強烈視覺落差意在向我們說明,外表遠無法與內心相比,所以內心的超越對人生而言要比現實中色相聲貌、功名利祿的滿足更加有效。這種對形體的超越,提示人們應該把注意力放到內心和德性上面來。莊子撰出五個形體殘缺不全的畸形丑怪之人,表現了道家的一種獨特的行殘而德高的道德觀。這種深含遺形忘精、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的“德”之審美標準,不可不謂是莊子美學思想的一大創舉。
如此看來,處于“倒懸”狀態的人,即所謂的“倒置之民”,大都“喪己于物,失性于俗”(《繕性》),并且,他們顛倒于俗思之中而不自知,“囿于物而不知返”(《徐無鬼》),還在迷途之中“以物易其性”(《駢拇》)。如此身為物役、心為物役,殘生傷性,以身殉物,喪失了生命的最高價值。
二、任自然之養生
面對外物之勞役、軀體之榮辱、生死之哀苦,莊子提出了他超越于此的養生思想。《達生》中直接批評道: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行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可見,養生絕不可以從身體層面做起,從這一點可看出,莊子對后世道家以修丹煉藥執著于長生不死的觀點根本是反對的。其所提倡的則是:“形全精復,與天為一”(《達生》)的養生之道。蓋身體發膚乃父母所生,而稟與天道,于人則無從變其本質,因此只能從精神層面著手進行改造,以求達到復歸自然并與之融渾一體的境界。
在操作方法上,莊子的養生思想首先是從道出發而衍生的處世方法。《大宗師》中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
其《天道》篇中則將盡言天道、帝道、圣道。《在宥》篇亦言:無為而為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這與《老子·二十五章》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無所差異。蓋可知,莊子是宗法于天以及其背后的自然的。《養生主》中講“緣督以為經”,強調順循天然正中的道以為常法,則可看做莊子順道而行的總章法。
從莊子的道之本意出發,可知必須忘情釋智、順應自然。莊子的“游”是物我同一、情景交融的游,是超越于行和知的精神絕對自由,“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建立在齊萬物、一死生的基礎之上的。
心齋、坐忘便是體道的不二之法。《人間世》中莊子借顏回與仲尼的一問一答,道明“心齋”: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而所謂“坐忘”,即《大宗師》中所言: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道,是謂坐忘。
心齋與坐忘的目的便是虛靜。在此過程中,需要做到“喪我”而成吾,也就是說從形態我和情態我的層面上升到泯物我的狀態,即實現“吾喪我”。如此則“參日而后能外天下”“七日而后能外物”“九日而后能外生”境界日益提升,最終達到“朝徹”之境,而后能體道“見獨”,之后便可以無古今、入于不死不生的破生死狀態。只有虛靜之后,才能夠化解一切仁義禮樂之束縛,讓自己重新回歸到自我之本真狀態,忘卻了生死,從而“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最終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大宗師》)的齊萬物之境界。
循道則能夠“技近乎道”。正如《養生主》中庖丁解牛故事所言,做事情時應當“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強調順循自然,處于己虛,通過實踐之訓練,累久而熟,方能夠游于無有,不為外物傷身,如此才能越“官知”而行“神欲”達到“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的自由境界。另有“宋元君將畫圖”“津人操舟若神”“佝僂者承蜩”“呂梁丈夫蹈水”等故事,都揭示了技藝必須依循事理本身的自然之道,順道而行才能夠超越技術的物質性、功利性而進入自由無阻的境界。這一點被后世廣泛應用于藝術創作當中,尤其山水國畫,更見其離形去知、獨與道游的高深境界,此足可見莊子思想對美學的重大啟發作用。
從莊子所言之道的體用出發,則有其無為的思想。《外物》中莊子說道: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言:“莊子誠然是無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2]就像在“象罔得珠”(《天地》)中所表明的那樣,尋求大道不能依靠聰明、言辯,而恰恰是要以無為自然為宗,破除“迷于知”“困于文”的境況,即在實踐當中不再受到來自自身欲求和外界事物的誘惑和壓迫,純任自我,順其本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知北游》)。
可見,正因為道體虛無,不可問、不可見、不可言,所以順道而行只能是無為。自然之道可體而不可說,得道的圣人之所以有本于天地長養萬物的功德,并且能通曉萬物自然變化的道理,就在于他能夠觀察體會天地的自然變化,渾然與天地為一,雖然無為,卻是在順應天道而無所作為,因此無所不為。
除此之外,莊子的養生思想尤其重視守氣全神這一方法。清人宣穎云:“蓋神者,人人具足,不知養之,則生而昏,死而散;知養之,則生而湛然自得,死而與化為體。此莊子惓惓欲養生者之必養神也。”[3]足可見養神之于養生的重要作用。正如“梓慶削木為 ”這則寓言所表明的那樣:梓慶削木為 , 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臣將為 ,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達生》)。
若為一事,需以不傷物性為第一要義,包括不傷己之本性和外物之本性兩方面。而后方能守氣全神達到“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的境界,如此才能達到巧奪天工的效果。再如望之似木雞的斗雞,之所以能夠使“異雞無敢應”而德全,就在于它重視養氣,摒除了虛浮的傲氣和無旺盛的斗氣。
不難看出莊子的養生之方是在道體至虛的基礎上,從純然任性、無為而無不為和守氣全神等方面著手,從而達到的一種破生死、齊是非、泯物我的心靈超越之效果的不二手段。在達到心靈超越的同時,也就實現了莊子所言的逍遙游的人格理想。
三、游心之逍遙
莊子的逍遙是詩性的逍遙,因為在提出人的生命安頓的道路上,他的養生方法是直指心靈超越的而非現實的,因此又可以說是一種藝術性而非道德性的境界。這種境界不同于那個時代仕人知識分子所普遍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實現功利性價值的同時實現解救世人于倒懸之態的觀點,更沒有為天下蒼生奮不顧身而請命的偉大抱負。在這一點上后世對莊子頗有微詞,認為他沒有現實之擔當而使其心靈超越之說流于虛無。
然而莊子的逍遙是否真如流俗所言,是虛無的浪漫主義嗎?
首先,莊子著筆之時秉持的是一種無奈的悲痛。他看到了人生于世的短暫猶如白駒過隙,看到了生命的短中又有諸多痛苦,人們苦惱于生死、是非和物我之間,被物、文、知等一系列周遭的環境迷困著,在其中忙忙碌碌無從逃脫。如此的生命不可不謂之悲劇。而莊子極欲解除人這場悲劇,可是,現實的無望卻使他無法實現心愿。若言莊子無現實之擔當那么其甘受其清貧而不仕,以為人們解脫之榜樣的那份巨大付出又當作何解釋?
這種付出絲毫不亞于賢人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的安貧樂道,寧為漆園吏而不為千金相位所動的莊子言堯讓天下于許由,以及不甘為衣以文繡、食以芻叔的大廟之犧牛,寧愿做《秋水》中曳尾于涂中的烏龜,而不愿做僅為一副骨架而藏之于廟堂之上的神龜。對惠子誤以為自己要奪其相位的看法不齒,他自比為鹓芻鳥,對鴟得腐鼠嗤之以鼻。出仕為官一方面根本有損于莊子絕對自由的目的,更為重要者乃是這樣一來莊子便不可能對最大多數者的生命有共同體驗,更不可能現實地為生命之最大多數找到出路。如此為蒼生請命不知是不是一種偉大呢?
其次,莊子所提倡的,是一種量力而行的睿智: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人間世》)。
若不然,則猶如如關龍逢、比干之流,只因好名而得身死的下場,更為可悲的是他們以死換來的只是芳名流傳,而對其赴死獻身的目的卻絲毫無益,更無奈于夏商被后來者推翻的命運。
此外,令獨有一番風骨的莊子難以忍受而斷了他出仕以救人的念想的,更有當時宦途風氣。秦王有病召醫。破癕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列御寇》)。所以,莊子對待出仕的態度是: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生不仕(《秋水》)。司馬遷作《史記》時引此句以描述莊子人格,足可見莊子思想當中以出仕為官為不屑的情結。
再次,莊子的絕對自由并非是只關一己之私的“自私”之學。在這種注重獨善其身超然獨化之境之中,若人人獨化則全部獨化,如此何來“自私”之言呢?這種不為建功立業之一己之私而達到匡正世道的胸懷,豈是那些以匡正世道為實現一己之私的手段者所能比的啊!因此可以說,莊子的濟世之方,乃是世人各自養生獨善其身而逍遙,進而消融掉一切外化之阻礙,人人朝徹而天下大化。如此宏大的思想體系恐怕無人能與之比肩了。
再談莊子逍遙游的理想人格。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逍遙游》)。
蕓蕓眾常通過以上所提之養生之道,可以漸漸接近這種理想人格。其表現即為: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刻意》)。
圣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而游乎塵垢之外(《齊物論》)。
圣人之所以能夠得道是因為他們能隨自然變化而運動,其死離人世則隨萬物的變化而變化;他們不從事瑣細的事務,不追逐私利,不回避災害,不喜好貪求,不尋求道的緣由;沒說什么又好像說了些什么,說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沒有說,因而遨游于世俗之外。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
忘我的至人用心猶如明鏡,他能夠做到物去不送,物來不迎;物來自照,不留藏妍丑之境。
古之真人,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大宗師》)。
可宗而師之的有真知之人,無動于生死,無拘無束,不忘生命之源,守而不失;不尋求歸宿而一任自然。受生之后常自得,忘其死而又復歸于自然,不以欲心背自然之道,不以人為助天命之常。
因此可見,莊子的逍遙乃是純任自然的絕對自由。這種貌似無關他人的逍遙游,正是在引導世人之整體進入一種人人逍遙、天下大美的境界。
四、靜觀默賞之自然美
正如莊子在“輪扁斫輪”(《天道》)的故事中所講的那樣,輪扁的高超斫輪技藝,之所以不能傳給其子,就是因為他的斫輪之技只能意會,不可言傳,因而他“行年七十而老斫輪”。莊子認為:“大道不稱,大辯不言”(《齊物論》),若為強言,則已不為道;可以言傳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
強求而為,只能是管窺蠡測、邯鄲學步,根本無關道體之真。因此,莊子所言之道,在體而不在得,體有深淺、正偏而得則有多少和得與不得之別。若不知無用以為用的道理,逆其天性而為之必然適得其反。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渾沌之地,渾沌代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應帝王》)。可見天地本身所具有的美即自然之美才是真正的美。世間一切方圓曲直皆為自然天成,未經雕琢的美才是美的極致。《刻意》曰: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
由此可見莊子美學,力主自然,追求本真。處于倒懸狀態的人,若不能做到純任自然、虛己順時,去掉矜能炫知之心而急功近利地一味地傷害自然之道,必然陷入萬劫不復之境而不能自拔。從這一點出發可以知道,莊子所主的獨與道游的逍遙游人生乃是一種包含藝術化生命情調的姿態,如同與惠子的“濠梁之辯”之將物融于“我”當中,《齊物論》中亦言: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如此物我兩忘的“物化”之藝術境界和審美情態絕非常人所及,這也體現了莊子任意游走于天地物我的絕對自由狀態,也正是這種至高博大的認識境界奠定了莊子詩性的逍遙游之基礎。
莊子自然美的體悟亦不外乎此道理:“自然之美表現于無言,莊子乃由大自然的默察中而引申其無言之美。”[4]莊子的美學思想是由其“道”生發而來,其中又多含有“無為”的思想因素,既然自然美是由莊子于無言之處體自然之道而獲得的,那么對莊子美學的體悟自然也不是強求可得的,因此對莊子自然美之美學思想的體察方法應以“靜觀默賞”為不二之方。就莊子的廣博思想和任意的文字來說,沒有什么已成之法能夠依循來學習,因此只有順從他的思想展開的方法,重在體悟而非他所抨擊的知識性的學習,才能夠較為真切地體悟到莊子的美學所在。所以,唯此靜觀默賞之中,我們才能默默地體會出莊子那份胸懷蒼生、包羅萬象、翰宏天下、冥思精進的自然之美。
綜觀莊子思想之整體,我們不難發現,他含弘光大的思想系統和汪洋恣睢的語言文字是一種飽含現實關懷的展開,為解救世人于“倒懸”,他甘愿放棄一切可得富貴榮華的機遇,生活在最大多數的貧苦大眾當中,從養生到逍遙,不僅在文字上,更在個人的生命實踐上,向世人展示了逃離于亂世的出路。同時,在這條出路上,自然而然地展現出來的是一種獨與道游、真誠無偽、靜觀默賞的自然美。
參考文獻:
[1]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M].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3:242.
[2]袁謇正.聞一多全集·莊子編[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5.
[3]陸永品.莊子通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277.
[4]陳鼓應.莊子淺說[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8:69.
責任編輯、校對:杜 瑩
Abstract: Chuang Tzu is a romanticist who expressed strong concern of reality. To end people's state of hanging by the feet at that time, Chuang Tzu proposed a solution from health preservation to peripateticism through his coverall ideological system and uninhibited language. His theory purport is to realize the individual liberty, so as to obtain everyone's freedom, eventually to achieve the big beauty of the world. And the natural beauty of following the rules and calm appreciation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is idea.
Keywords: hanging by the feet, health preservation, peripateticism, natural beauty, Chuang Tzu, Taoists, ideal personality, roman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