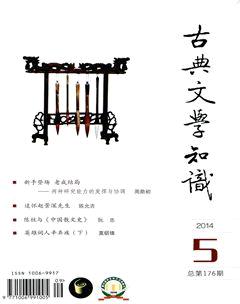從筆記體提升為小說品格
周先慎
這篇小說取材于林四娘的傳說。關于小說本事的記載,據有學者考證,在清初康熙年間,現已發現的就有七八種之多。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有兩種,即王漁洋《池北偶談》中所載和林云銘的《林四娘記》(在張友鶴《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和任篤行《聊齋志異全校會注集評本》中均有附錄)。兩家所記,都是閩人陳寶鑰在山東青州任職期間,于官署中與林四娘鬼魂交往事,雖然人鬼關系密切程度不同,但都未涉及性愛。而對林四娘的出身和行跡,兩家所記卻有很大的不同。王記大致內容是:林四娘乃明末衡王朱祐寵幸的宮嬪,不幸早死,殯于宮中。因國破,王府荒毀。后閩人陳寶鑰任青州觀察,林四娘鬼魂借居延客,并與主人宴飲賦詩,述及宮中舊事時悲不自勝。臨別時贈詩一卷,文中錄七律一首,情詞凄婉。林記卻與衡王無涉,林四娘乃明末江寧府庫官的女兒,其父因虧空庫銀而下獄,四娘與其表兄相謀營救,同住數月而不及亂。父出獄后疑其有私情,女竟投繯以自明清白。因與陳寶鑰為福建同鄉,有桑梓之誼,故鬼魂現身陳署中。初為厲鬼,面目猙獰,攪擾公署,陳之仆人、標兵二千及請來驅鬼的神巫均不能敵。后改異面目,變為一國色麗人,日與陳歡飲賦詩,親狎備至,唯不及亂。鬼女還助陳處理許多公私事務。喜做詩,所著多感慨凄楚之音。林記最后還說,故事是陳寶鑰親口向他所述,并囑他記錄下來的。
或許就是這個原因,方舒巖在蒲作《林四娘》文后加了一段評語,就以林云銘所記為實。他在引用了林記關于林四娘死因的一段話后說:“(蒲作)與此迥異。聊齋豈傳之非真耶?”“傳之非真”的批評從反面啟示我們,蒲松齡并不是單純記錄聽來的奇聞異事,而是根據他對生活的體驗和認識,對原始素材進行了藝術的再創造,使之從傳聞故事的真實,提升為具有小說品格的藝術的真實。
作為一個小說家,蒲松齡著重的不是講故事,而是刻畫人物。他極有可能還接觸過更多的林四娘的傳說,但從小說的內容來看,王、林兩家的傳述他應該都有所聞,而且是作為主要參考的。他雖然采用了林四娘出身衡王宮嬪之說(這一點非常重要,是小說悲凄情調的主要依據),但從作品中林四娘向陳寶鑰自明,并在隨后證實自己身為“處子”,又聲言“一世堅貞”來看,與林記中她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而投繯的情節,似也有一定的聯系。不過,蒲松齡在進行藝術提煉的時候,顯然更看重林四娘工詩的特點和內心難以排解的悲情,尤其是王記中所述她在詩中所傳達出的亡國破家之恨。以此為基礎,蒲松齡對林四娘這個形象有一個明確的定位:一個風雅的女鬼,一個多情的女鬼,一個懷抱家國之恨的凄哀的女鬼。經過藝術的概括和集中,他把這個在當時士人中傳聞很廣的故事,由筆記體的散漫蕪雜的敘事,寫成了一篇藝術上很集中、很精致,思想上充滿悲情并具有一定的歷史內涵的小說。
蒲松齡根據形象塑造和思想表達的需要,大刀闊斧地刪削了兩家記述中諸如厲鬼攪擾公署、助理公私事務以及借館延客等內容,而集中到寫女鬼與陳寶鑰之間的戀情上,借助這一特殊的關系,深入地揭示出林四娘這個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內心世界。
小說一開篇,除了介紹故事發生的地點青州和男主人公閩人陳寶鑰外,單刀直入,直接描寫人與鬼之間發生的戀情:“(陳公)夜獨坐,有女子搴幃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夜兀坐,得勿寂耶?”“長袖宮裝”,伏下文女子的出身和經歷。而夜間突然來一女子,而又容色“艷絕”,在當時民間的觀念中,就意味著可能為“非人”,故下文說“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此時公之所“好”,顯然是因其容貌之“艷絕”。而下文寫陳大膽地“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這是第一次寫女鬼用到一個“雅”字,是概括地也是初步地寫其內在的文化素養。而這時繼“好之”之后寫陳公的“大悅”,就該主要是傾慕其精神氣質之風雅了。接下來寫兩個人的性愛,雖然寫得較為直露,但因為有這樣從容貌到素養都令陳公欣喜作為基礎,因而雖近于俗,也還俗不傷雅。而以后的描寫,不管是從男或女哪一面來講,都發展成了真正的愛情。值得注意的是,從“緩裳”開始,整個過程都是陳公主動。女鬼雖然“意殊羞怯”,卻并無反抗,而是半推半就,表現得相當從容大方。小說通過具體的描寫,證實了女鬼自稱為“處子”和“一世堅貞”并非虛言,說明她在人世時確實是一個清白的女子。故下文寫她對陳公說:“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明確地提出愛情的要求,就不僅是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值得同情的。
二人相處,小說著力描寫的是女鬼“風雅”的修養和悲凄的情懷。“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這是第二次對女鬼用上一個“雅”字。相談中,知道她精通音律,“能剖悉宮商”,并“工于度曲”。這是具體地描寫“雅”的內容。于是“公請領一雅奏”。這是第三次用到“雅”字。這都是作者有意通過敘述語言,一再重復,對女主人公的文化修養所做的點染。接著寫這個女鬼對傳統技藝的掌握和理解,進一步揭示出她的精神風貌和文化素養。音樂是她“兒時之所習”,卻又以“久矣不托于音,節奏強半遺忘”作為托詞而婉拒陳公的請求。陳公“再強之,乃俯首擊節”。這是寫她的“多情“。這情是對陳公的,是第一個層面;她的多情還有更深的層面,就是歌唱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深摯的家國之情。這一層,是寫得更有深度,也是更為感人的。她“唱伊涼之調,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為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為亡國之音,使人悒悒。”令歌者和聽者都為之酸惻而泣下的,就是這“亡國之音”。這時女鬼的回答,表現了她很高的藝術修養,她說:“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這是寫她對音樂藝術的深刻理解和精辟議論。這里在字面上沒有再用“雅”字,但卻在更深的層面上寫出了她的修養和眼光,亦即她的“雅識”。作者的高明之處在于,寫她的風雅修養,同時也就表現了她的“多情”,而這“情”既是對陳公的,更是對故國的。這情,因她的風雅而得到了更動人的表現:風雅鬼女和多情鬼女是融合在一起的。
下文擴大到寫女鬼與陳公家人的關系,由此而深化了對她身世與感情的描寫。因為家人竊聽,“聞其歌者,無不流涕”。但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因而“勸公絕之”。公不聽,因問其身世,這才引出對女鬼不幸遭遇的敘寫。“女愀然(二字寫內在悲情的外化)曰:‘妾衡府宮人也(照應前文“長袖宮裝”的描寫)。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為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疑畏,即從此辭。”這里講到她的不幸遭遇,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王漁洋所記是“不幸早死”,這里卻改為“遭難而死”。雖然遭受何難并沒有說明,但熟悉南明抗清歷史的人,都了解衡王朱祐曾經抗清,失敗歸順后以謀反罪被殺,那么林四娘的遭難也必與此相關;二是對陳公表示若遭“疑畏”立即告辭,從她的善良,也見出其為深于情者也。陳公問她宮中之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式微”之痛,至于“哽咽不能成語”,小說的用語雖然含蓄隱微,但鬼女心中飽含的亡國破家之痛,還是非常明顯的。而她對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乃因“思終身滄落,欲度來生”的解釋,所傳達出的深沉的凄哀,也正好能與此相呼應。
為了寫出她臨別時飽含家國之痛的贈詩,就先寫她能評詩、吟詩、做詩,以為鋪墊。“每與公評詩詞,瑕則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她是否工詩,回答說:“生時亦偶為之。”卻又以“兒女之語,烏足為高人道”為由,婉拒陳公的索贈。這些,也都是同時寫她的風雅和多情兩個方面。
三年后,女忽慘然來告別。告以冥王因她生前無罪,死后又不忘誦念佛經,便使她投生到王家。別時二人“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為哀曼之音,一字百囀;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后曲終,飲不能暢”。雖然臨別時,兩人難舍難分,一“愴然”,一“淚下”,但她所唱的這支歌,如此低回哀婉,哽咽難繼,卻是男女間的戀情所難有的,多半還是前面提到過的那種“使人悒悒”的“亡國之音”。在這里,她的風雅和多情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強調。
前面寫陳公索詩而女婉拒,此次“長別”,卻主動“率成一章”奉獻給陳。然后“掩袖而去。公送諸門外,湮然而沒”。林四娘所獻的這首詩,將個人的悲慘遭遇與亡國之痛結合起來,“深宮”、“故國”、“殿宇”、“海國”、“漢家”云云,與明末清初那段特定的歷史時期聯系起來,所表現出的民族感情,是既深沉而又相當鮮明的。蒲松齡將林四娘的形象寫得如此凄美,并給予深切的同情,應該說,其間也是寄托了作者本人的民族感情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新書架
《蘇詩補注》
本書是清初學者査慎行窮畢生精力編撰而成,編次上首開蘇軾集50卷之規模,又開清人補注蘇詩之先河,廣征博引,注釋詳明,解釋詩旨,考辨詩題,保存蘇詩自注,功績尤甚。在宋元以來注釋蘇詩的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查慎行的注釋中,補錄了新刻本中刪削的施、顧原注,并駁正了分類注中的大量訛誤,同時對史籍中有關蘇軾的舛誤之處,也做了駁正。同時,該書保存了大量的蘇軾自注。查氏闡釋詩旨,考辨詩題,注釋所涉人物與地名,尤為翔實。查慎行的注釋,還在系年、補遺、辨偽方面,取得了重要實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