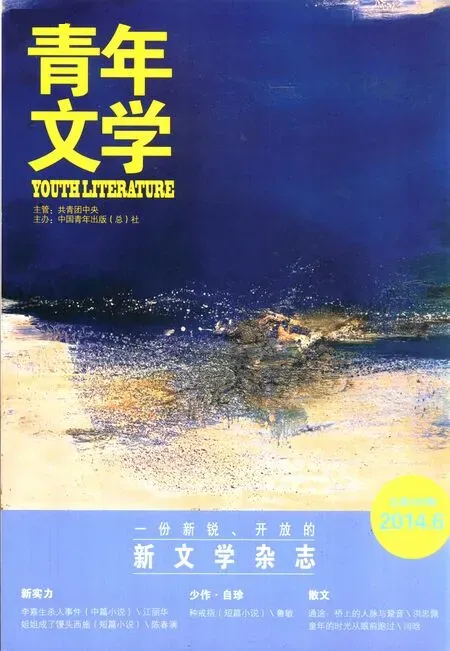姐姐成了饅頭西施
文/陳春瀾 [短篇小說]
付萍十七歲那年,是一九七八年,也就是國家恢復高考的第二年,這年春節過后不久的一個星期天,家里突然來了個陌生的中年男人,中等個、圓臉、微胖,模樣和爸爸差不多,只是爸爸的臉白,這個人的臉黑。付萍想:爸爸和這個人,像自己蒸的饅頭,爸爸是堿小時的饅頭,這個人是堿大時的饅頭。
付萍那時剛學著蒸饅頭,凡事都能聯想到饅頭問題。在她眼里,世界上最難的事莫過于蒸饅頭,只有把發好的白面揉進不多不少正好的堿面,出鍋的饅頭才能又大又白又耀眼。但那耀眼饅頭的榮光,屬于母親,不屬于她,她蒸的饅頭不是堿大就是堿小。她覺得媽媽是世界上最精明的女人,沒有一件事辦不利落。
黑饅頭的來人走后,母親讓白饅頭的父親上街去打醬油。然后把付萍從另一個屋子喊出來,母親偷偷瞅了她一眼,看見她手里還拿著書,邊走邊看,母親在心里輕輕地嘆了口氣,說:“萍萍,你去替人考一次試吧。”低著頭說話的母親不看付萍,看著手中正在織的毛衣。付萍也不看母親,她盯著自己的書看,邊看邊問:“替誰?啥考試?”
“替一個鄉下遠房親戚的孩子,就是今年的高考,別的,你就不用問了。”母親終于說出了最難說的話,她長出了口氣,仍然埋頭織毛衣,好像織毛衣才是全天下最當緊的事。
付萍手中的書“啪”的一聲落到地上。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搖著母親的胳膊問:“媽,那我怎么辦?”
“你學習那么好,晚考一年怕啥!”
在最近的一次家長會上,付萍的班主任老師朗聲宣布:像付萍同學,現在就完全可以回家睡覺去了,不用擔心,到考試那天醒來去考就行。深受鼓舞的母親,把頭抬得高高的,回家就教付萍蒸饅頭。母親用蒸饅頭的悠閑盲目地展示了她和班主任老師同樣的感受,他們對付萍高考這件事是一百個放心、二百個信心滿滿、三百個底氣十足。母親相信付萍今年能考上大學,明年照樣能考一個更好的大學。
“替考可以,復讀一年,我不愿意。”付萍對母親說,“如果那樣,我情愿待在家里蒸一年的饅頭。”
母親說:“不用你蒸,你不想復讀,那就在家里自學一年,明年再考,反正這個替考的事,媽就給你做主了,不去也得去。人活在世上,有多少事是你想做的呢,媽還想當皇后,每天有人侍候著,什么也不用做,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可是,能行嗎?別人不清楚,你還看不見。媽每天不僅趕死趕活地去上班,還得帶你和你弟弟,供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尤其是你,小時候最能鬧病,隔幾天跑一趟醫院,媽帶你這么大容易嗎?媽不懂大道理,但知道你學習好,也不是一生下來就學習好,也是大人這么多年苦心培養的結果。媽就求你這么個事,你還不答應媽,現在翅膀還沒硬了,就不聽大人話了,將來考上大學有了本事,媽說話更是……”
付萍低著頭,聽著母親的數落,看著地上掉的書也不去撿。她雙手抓著上衣的一角機械地揉搓著,揉得手都疼了,母親的主意還沒變。母親的決定不是衣服,是鐵板釘釘兒,她揉不動。在母親一浪高過一浪的哭訴中,付萍走到母親身邊,接過她手中織的毛衣,放在床上,抱住母親的肩膀安慰道:“媽,你別生氣了,我去替考。”
付萍不敢和母親硬頂牛,大事小事,對與錯都得聽母親的。母親有心臟病,母親說是生她時落下的病根。付萍想求父親,她不想替別人高考,她要自己考自己的。可是,父親在這個家里做不了主。再說,父親重男輕女,對弟弟管教的多,對她的事干涉的少。不論大小事,都是一句話:問你媽去,你媽覺著好就好。
老師是付萍能想到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尤其是班主任老師對她最好。第二天早上,付萍背起書包就要去學校,她想老師有辦法讓母親改變主意。可是,母親根本不給她翻牌的機會,更不會讓她把替考的事捅給老師。她還沒走到門口,母親就從后面扯住了她的書包帶說:“今天你就不用去上學了,一會兒我就去學校,和你老師說,你得了傳染病。”
母親在醫院掛號室工作,開個假病假條對她來說,不是什么難事。她拿著一張“急性傳染性黃疸型肝炎”的診斷建議書,找到了付萍的班主任。班主任無奈地搖頭:“真是太遺憾了。”母親點頭:“可不是,得病不由人啊!”
高考前一天,母親領著“病中”的付萍,坐了八個多小時的火車,來到了遠離省城的一個偏遠小縣城。一下車,付萍就看見那個黑饅頭男人憂心忡忡地出現在站臺上。他問母親:“怎么就你,孩子不肯嗎?”母親把身后的付萍一把拉到了他面前。他伸手就去拽付萍背上的包,要替付萍背。付萍往旁邊緊躲了兩步,冷著臉說:“謝謝叔叔,我自己行。”他尷尬地縮回手,扭過頭和母親說:“那我帶你們去住的地方。”
他在前,付萍母女在后,三個人沉默地走進了一家小旅館。住的地方安排好后,他要帶她們一起去外邊飯店里吃飯。付萍說:“媽,我不餓,要去,你去。”母親說:“那就算了,我們在火車上吃了,明天還要考試,你走吧。”黑饅頭男人再沒說什么,臨出門時把一張準考證放在了桌上。
準考證上照片是付萍的,名字不是。母親指著這個陌生的名字叮囑道:“萍萍,記住,從明天起,你就是鄭好,有同學和你說話,你就指指嗓子,什么話也不要說,趕緊躲開。”
母親多慮了,進考場前,除了那個討厭的黑饅頭男人,沒有一個人和她打招呼。進了考場,更沒人搭理她。倒是付萍幾次想站起來,和監考老師說,這個準考證上的人,不是我,我不是鄭好,我是替考的付萍。可是,她不敢,她不能壞媽媽應承下的事。媽媽說了,要像給自己考一樣好好地考。還放了更狠的話,今年若是故意考不取,明年你也別想考自己的。
三天的高考,很順利地結束了。黑饅頭男人把她們母女送到了返程的火車上,列車員最后一次催送客的人下車時,付萍看見,站在過道里的黑饅頭男人動作麻利地從身上掏出一百元錢,俯下身來,用討好的口氣和坐著的她說:“給你的。”
黑饅頭男人手里拿的是第四套人民幣里面值最大的一張,去年才出的,也是付萍見過的最大的錢數。她想拿上,攢起來買個錄音機,可是,她怎么能拿他的錢?她不是為錢替考的,是為了母親。如果是為錢,多少錢她都不愿意。她故意把頭扭過去,看著車窗外。
車窗外的小站臺,在晚霞的映照下,呈現出一派沒心沒肺自得其樂的神情。在這種喜洋洋的神情里,有不多的幾個送客男女,稀稀拉拉胡亂地向車上的人招手。他們這一招手,差點把付萍的眼淚招出來。想到不久之后,身邊這個黑饅頭男人也會這樣興沖沖地和遠走高飛的鄭好招手,付萍就覺得這個小站臺真是豈有此理,叫什么名字不好,為什么偏偏叫“下馬塔站”,好像專為嘲弄自己似的。沒有她付萍的下馬,能有鄭好的上馬?
黑饅頭的男人下車不一會兒后,車開了,付萍又把目光轉向車廂內。車廂里,陸續有人從包里往出掏吃的干糧,也有人端著杯子到車廂連接的地方去打水。母親有點討好地和付萍說:“他特意給咱們買了肉蓉方便面,兩毛五一包呢,還有一只帶包裝的燒雞,打開就能吃。”
“我不餓。”付萍聲音很低。
母親瞅了付萍一眼,想說什么強忍住沒說,彎腰拿出另一個包,那里有她們來時從家里帶的麻花和散裝的泡面,她給付萍泡了一碗,把麻花掰開泡進面里說:“好好吃飽,咱們還有明年。”
考完最后一門那天,母親把標準答案遞到她手里:“萍萍,幫人幫到底,送佛送到家。你估個分告訴人家,人家也踏實,咱們走得也安心。”付萍保守地估了一下說:“按去年的標準,超重點大學的線應該是沒問題。”母親聽了安心地笑了。母親如釋重負的神情讓付萍感到說不出的傷心,傷心的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來年的高考。
在等待明年高考的日子里,母親沒有讓付萍在家蒸饅頭。九月份開學前,付萍的班主任老師幾次上門勸“康復”的付萍回原校插班再上一年高三,付萍不愿意。老師又把她介紹到了另一所學校,正好,小付萍一歲的弟弟付杰也在這個學校讀高三,學校索性就把姐弟倆放在了一個班。校領導拿著付萍的進校測試卷,對推薦她的原班主任老師說:“謝老同學割愛,弟弟就很優秀,想不到,姐姐比弟弟更優秀。”
付萍和付杰上了同一所學校,最高興的人是父親。他把兒子叫到跟前說:“姐姐能和你一起學習,是你的福氣,姐姐不是別人,有問題不要自己在心里悶著,要多問姐姐。”母親也把付萍叫到跟前叮囑道:“你是姐姐,你要多幫著點弟弟。”付萍笑了:“媽,你和爸怎么了,我也是去當學生,又不是去當老師。”
付萍嘴上這樣講,行動上對付杰可是一點沒保留,姐弟倆每天白天一起上課,晚上就在一個桌上臉對臉共同學習到深夜。畢竟付萍是又上一次高三,更多的時候,是她帶著付杰一起學。
都以為姐弟倆雙雙考入名牌大學是十拿九穩的事,誰料,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行。就在高考的前三個月,家里突然又來了陌生人,這次,不是一個,是一群,他們是父親單位的領導和同事。母親顯然沒有接待群體來訪的能力,她手忙腳亂、語無倫次,完全沒有了去年面對黑饅頭男人的那份從容。她說,快,快去學校,把付萍和付杰都接回來。
付萍做夢都沒想到,在那個萬物蓬勃向上的四月天里,她的命運又一次急轉直下。那天下午,正上化學課,教室的門被突然推開,教導處主任走了進來,他用極其溫和的聲音把付萍和付杰同時喊了出去。付萍和付杰領會錯了主任的溫和,倆人往出走時,臉上都掛著天真爛漫的微笑。付萍在前頭走,付杰跟在后頭,付萍回過頭來笑著招呼付杰:“快點,要不,有好事全讓姐搶了。”說這話時,付萍哪里能想到,等待他們姐弟倆的是父親意外去世的消息。
父親是煤礦的技術員,死于井下冒頂事故。“人死不能復生。不管老付是怎么走的,走了就走了,重要的是活著的人還得活。”父親單位的領導這樣勸母親,母親點頭,她心里清楚,同樣是活,先前想好的活法就得跟著變。到山砍柴,到河脫鞋,走到那步就得說那步的話。打理完父親的后事,母親把礦上給的二百六十元撫恤金,鎖到箱子里。然后,把付萍和付杰叫到跟前說:“你們姐弟倆商量一下,誰去考大學,誰留下來頂替你爸去上班。反正,這個指標不能白白作廢,它是你爸用命換的。再說,你爸走了,媽現在只能供一個,不說供不起,就算供得起,媽身邊也不能沒個人照應吧!”母親把該說的話說完后,嘆口氣,倒在了床上。
付萍站在當地,咬著下嘴唇,半天不說一句話。她想自己要是能重生一回就好了,讓付杰當哥,她當妹。可是不行,付杰一落地,頭上就有她這么個姐姐,不說大一歲,就是大一分鐘也是姐姐啊!姐姐是最疼弟弟的,姐姐怎么有臉和弟弟爭。可付萍想起母親去年對她說的話“你學習那么好,晚考一年怕啥”,她的心就放不到肚里,心不踏實,人就會亂說話,所以,她不說話。
付杰和姐姐挨著站著,也咬著嘴唇,也不說話。付杰不說話,付萍不怪他,小的時候,付杰貪玩,不愛學習,沒少挨父親的打,被父親打怕了的弟弟從小就不愛說話。其實,付杰是在等著付萍先開口。小的時候,家里有了好吃的,母親總是給他倆平均分配,一人一份。付杰總是狼吞虎咽,先把自己的一份消滅掉,然后,就直著眼睛看著姐姐吃,姐姐這時總會主動再勻一半給他。從小到大,付萍沒有不讓著付杰的時候,付杰想讓姐姐再讓自己一回。
姐弟倆的沉默惹惱了母親,她坐起來,用手拍著床,聲淚俱下:“都不說話,好,你們都去奔自己的前程吧,都不用留下來陪我這個無依無靠的媽。”說完,母親用頭撞著墻:“干脆我也死了算了,省得活著當你們的累贅。”知女莫如母,母親是哭鬧給付萍看的,她知道付萍一向心軟,禁不住她這么折騰。
果然,和付杰并排站在當地的付萍,一步沖到床上,把母親從墻邊拉回到床上躺下。然后,身子靠墻面朝母親坐在床上。在家靠娘,出門靠墻。現在,娘不讓她出門,娘也出不了門,出不了門的娘撞墻是假,要靠她是真;父親走了,她就是娘的墻。付萍探過身子,拉起母親的手,扭頭看著付杰,說:“小杰,我留下管媽,你去高考。”說完,付萍起身下床,走回自己的房間。再出來的時候,手里拎了一大堆書和作業本,當著媽和付杰的面,她把書和作業本一把火全燒了。
因為父親是工傷,付萍的工作解決得很順利,短平快,不到一個月,付萍就退學上了班,她被安排在礦上最大的職工食堂。大食堂分工明確,付萍選擇了面案,負責做各種面點,山西人愛吃饅頭,付萍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蒸饅頭。揉饅頭的活兒,她不討厭,從小就喜歡,只是那時是自己覺著新鮮好玩,跟著母親在家瞎起哄。現在是命運對她的安排,日復一日的生計,天天都得干。想到自己沒準得蒸一輩子饅頭,付萍常常笑著笑著就笑不出來了。
看著落寞的付萍,母親給她打氣,行行出狀元,淘糞工時傳祥,還能和劉少奇握手,受毛主席接見。咱好好蒸饅頭,肯定能蒸出大氣候。其實,在母親的心里,她并不想什么大氣候,她只想付萍能安安分分地守在自己身邊。她越來越老了,她的身邊沒了男人,不能再沒有付萍。不在自己身邊的孩子,再有出息也指不上,蒸饅頭的付萍才是留給自己的依靠。
付杰的高考成績出來后,付萍看著付杰的成績單,驕傲地想,自己到底是姐姐,她去年給鄭好考的分怎么也要比弟弟今年的分高,至少也能高出二十多分,可惜,分再高也沒用,沾光的人是鄭好。付萍問母親:“媽,你說那個鄭好去了大學,人家就發現不了照片和人不一樣嗎?”
母親不吭聲,母親又在織毛衣。織了一會兒,母親放下毛衣,認真地勸起了付萍:“萍萍,別想那么多,媽就從來不愛想過去的事,過去的事再想也沒用。替考這事兒過去就過去了,不用老說。這就好比送到別人家的孩子,就是人家的了,你不用老惦記的。一個人一個命,興許,就該著人家上那個大學。再說,上大學也不見得有多好,畢了業天南地北的還不知分到哪里,媽想見你一面都不容易。你想,你爸爸單位怎么著也是個國營大單位,沒準,上了大學還分到集體單位呢。”
付萍想不到自己隨便問的一句話,引出了母親這樣一番扯不清的大道理。付萍說不過母親,也怕母親,這怕里其實有一半是付萍的孝順,她不想傷母親的心。母親常說,孝順孝順,沒有順哪來的孝。從此以后,付萍再不敢在母親面前提鄭好兩個字。
母親的眼界沒有那么寬,你就是讓她望穿雙眼,也望不到幾年之后大學畢業的鄭好,根本沒把國營和集體放在眼里,她揮動著付萍給她裝上的隱形翅膀,跟著八十年代的出國風潮,飛越了國門,在一家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供職。鄭好的天空越來越遼闊,遠遠不是每天低頭蒸饅頭的付萍抬頭就能望到的天空。
付杰上大學走的前一天晚上,付萍悄悄地對弟弟說:“小杰,姐想求你一件事。”付杰面有愧色,他對付萍說:“姐,我知道你心里難過,你能上個比我更好的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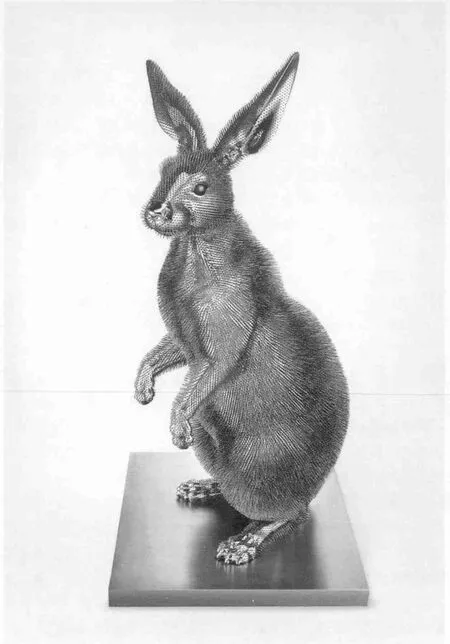
一向柔軟、溫暖的皮毛哪兒去了?面對近十五萬根“縫衣針”重構的金屬兔,碰觸棘手,溫存不在,堅硬、冰冷、刺痛、距離……藝術家以獨具創新的語言表達了對自然生命的悲憫與敬畏、對人類惡行的反思與控訴。名稱:千針萬痛作者:解勇材料:不銹鋼、縫紉針姐姐成了饅頭西施
“小杰,你誤會姐了,你是咱們家唯一的男孩,我當姐的,愿意讓你好。姐是想求你到了大學后,幫姐找個人,這個人叫鄭好,媽說是咱們家的遠房親戚,姐去年就是替她考來著,要不,姐現在都大二了。姐去年考的那個分肯定能上了北京的大學,你不知道姐多想去北京念書,可惜,再高的分,也是替人家考下的。不知道她到底上了哪所大學,有沒有因為穿幫被學校退回去。”
想起母親的千叮嚀萬囑咐,只要你不說,這事永遠不會被人發現。付萍也千叮嚀萬囑咐弟弟:“小杰,你悄悄地幫姐打聽,姐已經這樣了,只是好奇,沒有禍害人家的意思,你不要讓人發現,找到也只是把她現在的情況告訴姐就行了。記住,千萬不能讓媽知道這件事。”
付杰不敢報北京的大學,報了云南大學,付杰指著地圖告訴母親:“離太原有兩千多公里,得坐好幾天火車,還得到西安中轉。”
“那我要有個三長兩短,你哭也哭不回來。”
付萍安慰母親:“媽,報的時候,你不是說好男兒志在四方,再說,不是還有我在你身邊嗎?”
“得虧有你。”母親說這話時,更覺得不讓付萍考大學是對的。母親勸付萍,知足常樂,蒸饅頭也沒什么不好,風吹不著,雨淋不著,不愁吃不愁喝。要是放在一九六〇年,能在食堂上班,還不把人羨慕死。
付萍不語,心說,都快八十年代了,還翻六十年代的老皇歷?現在,誰羨慕的不是大學生,報上都把大學生稱作“天之驕子”,她也想當“驕子”。可惜,人們眼里的她不過是個“饅頭西施”。所以,母親的話,付萍不愛聽。她愛看付杰的來信。付杰每次給她的信,她都平平展展地收起來,看著信封底下大學的落款,就好像自己上了大學一樣,頗為自豪。有次,她揚著手里的信和食堂的姐妹們說:“我弟弟從大學里寄來的。”一個菜案上的女孩,很不屑地當眾譏笑她:“有什么可顯擺的,再好的大學也是你弟弟的大學,又不是你的,你不是和我們一樣,就一個食堂做飯的。”
付萍收起信,收不起的是自己對大學生活的那份由衷的向往。每天晚上回到家,付萍都要把付杰的信顛來倒去,看上一遍又一遍。從付杰的來信里,付萍看到了諸多可以點燃她的新名詞,她記住了階梯教室、大課、男生公寓、女生公寓、學生會和社團,還有老鄉會等。看到了老鄉會,付萍又在信里特意問起了鄭好,可付杰的回答是:“姐,還是找不到,也許她就沒敢上,也許她上了,已經被退回去了。”付杰的信里,從來沒出現過鄭好兩個字,付杰總是寫她怎么樣,她怎么樣。付萍突然覺得中文很有意思,如果交談的雙方談到一個人,從不用名字稱呼這個人,而是一直用代詞他或她,這樣,無形中,就把被指的這個人和他們之間的關系指遠了,一下就指到了千里之外。她笑了,弟弟還是和她親,也長大了,學會安慰姐姐了。
付杰是一九七九年上的大學,一入學就通過老鄉會幫姐姐打聽鄭好,可是,問到的人都說不知道。那時電腦稀缺而金貴,像舊時王謝堂前燕,別說飛入尋常百姓家了,就是在大學也不多見,更沒有互聯網,打聽人的途徑又窄又有限。就在付杰絕望地以為有負姐姐重托的時候,那個讓他踏破鐵鞋無覓處的鄭好,得來全不費功夫地和他不期而遇。付杰大四那年寒假,送同屋的一個同學去飛機場,在機場的候機廳里,同學突然被一個看上去很體面的高個男人拍了一下肩膀,然后,同學一回頭,四目相對的同時,倆人就擁抱到了一起。抱了一會兒,那個男人指著他問:“這是……”
“我的大學同學,一個寢室的哥們兒。”
那個男人伸出手,和付杰禮節性地握了一握,又轉身笑著和同學說:“一會兒,我也介紹你認識個人。”說著,他朝剛從洗手間走出來的一個女孩頻頻招手:“快過來,鄭好,遇上發小兒了。”
聽到叫“鄭好”,付杰的心“咚”地跳了一下,再一看,整個人也差點跳起來。付杰看著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的鄭好,不覺倒吸了一口冷氣,細長的身材,細長的臉,細長的眼睛,小巧的嘴,天,這不是付萍,我的親姐嗎?
這個和付萍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孩子,聽完對付杰的介紹后,微微點頭,輕輕一笑。這個微笑讓付杰確定,眼前這個人絕對不是他的親姐付萍。付萍不是這樣的做派,在家鄉蒸饅頭的付萍,不會這么含蓄地微笑,這是見過世面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性女人才有的淺笑,淡定、自信,還有那么點不顯山不顯水的神秘。
在家里陪母親的付萍,也不會出現在機場,付萍沒有坐過飛機,就是火車也只坐過一次,那就是替鄭好高考那次,那是付萍出門最遠的一次。鄭好老家那個小縣城,也是付萍到過的最遠的地方。
付杰忘記了自己怎么和那個男人,還有挽著那個男人的鄭好道的別,他迷迷糊糊地目送著鄭好挽著那個男人的胳膊幸福地通往安檢口,他突然十分想念姐姐。此刻,付萍在干什么呢?是在彎腰和面,還是低著頭揉饅頭,或者是把揉好的饅頭正一個一個耐心地擺往籠里……付杰突然覺得心里堵得慌,他問同學:“你那發小兒剛才是不是說,那個女孩子叫鄭好?”
同學愣了一下,看著神情恍惚的付杰開起了玩笑:“付杰,你小子是不是看上那個鄭好了,一見鐘情啊!你可勸住點自己的癡心妄想,我那發小兒自己已不簡單,老子更不簡單,我們從小住一個大院,他爹是我爹的老上級。你沒聽他剛才說,鄭好是他大學的同班同學,下個月就要結婚嘛。”
付杰凄慘地一笑:“我知道我是誰,不過看見鄭好,想起一個人。那個人可沒她的命好,本來能考上大學,可陰錯陽差總是考不成。”
他問同學:“你那發小兒是哪個大學的?”
“北京對外經貿大學。”
付杰心中甚是感慨,付萍果然把鄭好送到了北京。付杰那年寒假回家的時候,特意繞道北京,專程去了一趟北京對外經貿學院。幾經周折,付杰找到了鄭好的一個同鄉。沒錯,鄭好的老家就是姐姐說的那個叫下馬塔的小縣城,也就是說,鄭好肯定是付萍替考的那個人。真相終于在付杰的心里大白了。怪不得能替考,原來付萍和鄭好她們是一對雙胞胎。
付杰從北京回太原的路上,心情沉重,一點也沒有完成任務后的釋懷,看來,謎底原比他和付萍想的復雜。之所以他有一個親姐,而不是兩個,付杰能想到的思路是鄭好出生不久后,就被父母送人了,后來父母為了彌補他們把鄭好送人的愧疚,才讓付萍去替她高考。付杰覺得在告訴付萍真相之前,必須先征得母親的同意,因為對母親來說,付萍和鄭好,手心手背都是肉。
付杰提著行李,直接去了母親工作的醫院。他直截了當地問母親:“我是不是有兩個姐姐?付萍是不是雙胞胎?”母親吃驚地看著付杰。付杰任性地又喊了一聲:“媽。”這一聲“媽”讓母親放心了,看來付杰知道的并不多。母親鎮定地回答:“不要胡說,這話和我說說還行,千萬不能和你姐瞎說。”就像父親從來不打罵付萍一樣,母親也從來都是由著付杰。付杰習慣了在母親面前的任性,他固執地追問母親:“媽,你和我說,是,還是不是?”
“不是。你快回家休息,媽還要上班。”
付杰沒心思休息,他拖著行李來到了付萍的食堂,母親的態度讓他生氣,他偏要把這一切告訴付萍。當付杰突然出現在七八米寬的大面案前時,穿著白圍裙的付萍舉著兩只面手,細長的眼睛笑成了一條縫,她想拉付杰的手或者拍拍弟弟的肩膀,可因為手上沾著面粉,什么都做不了,付萍只是憨憨地笑著說:“付杰,你回來了,是不是沒拿家門鑰匙,你吃飯沒,快坐到外面凳子上,姐給你打點飯。要不,先喝口熱水。”
看著興奮得滿地打轉卻不知做什么才好的付萍,尤其是她那滿臉沒有修飾的憨笑,付杰突然決定忘掉那個機場里和眼前這張相同的面孔,他不能讓鄭好的淺笑傷害或打擊到付萍的憨笑,母親說得對,不能和姐姐瞎說。世界上長得一樣的人多著呢,但能處處讓著他,這么疼他的姐姐就付萍一個。付杰眼睛一濕,決定放棄考研。他和付萍說:“姐,我是專門來告訴你,你準備明年的高考吧,我一畢業就分回太原,你去考大學。”
付萍愣了一下,趕緊高聲把話岔開,她怕同事聽到付杰說的話。她已經把弟弟保送研究生的事說出去了,弟弟是她在同事中最大的驕傲。至于付杰讓她考大學,那是不可能的,媽怎么舍得放她走。這沒影的事,讓同事聽到不好,別人會說她好高騖遠,不安心工作。付萍著急地搖著兩只沾滿面粉的雙手,用胳膊肘把付杰推了出去:“付杰,有話咱回家再說。”
那天晚上,付萍和付杰又像在高中時一樣,面對面地爭論了一夜。付杰勸付萍:“姐,你能考,過了年你才二十二歲,補習幾年的同學也有你這么大的。”
“不是我年齡大與小的問題,我說的是你的問題,你保送了研究生不上就是半途而廢。這不是小時候分蘋果吃,你有一個,我就得有一個。你知道姐,就算再好的東西,姐也愿意都給了你。這是你一輩子的大事,說好的讀研,怎么能說變就變?你是不是怕媽不供你?姐供,只要你能上,你上到博士,姐都供。”
在另一個屋子織毛衣的母親,聽見付杰讓付萍明年再考大學,心想:這個付杰,上了幾年大學也沒長大,想起一出是一出。我可不要兒子來管,我還怕受兒媳的氣呢。就算你能孝順我,可誰敢保進門的兒媳是個什么樣的人。想到未來的兒媳,母親腦子里突然蹦出一個新的想法。
付杰說得對,鄭好就是她的女兒,二十多年前,她生下付萍和鄭好這對雙胞胎一年后就和前夫離婚了,她帶走了大鄭好三分鐘的付萍,不為什么,就因為付萍那時比鄭好能鬧病,付萍那時叫鄭萍。她改嫁給付杰的爸爸后,付萍才又隨了付杰他爸的姓。
讓姐姐付萍替妹妹鄭好考,也是沒辦法的辦法,鄭好在繼母手里太受制,她這個親媽聽一次就哭一次。高考前,前夫找上門來,想讓付萍替鄭好考,鄭好學習不如付萍,只有付萍替考才能保證把鄭好送到外地的大學,遠離繼母。母親當時沒多想就同意了。誰也沒長后眼,誰能想到第二年,付杰的父親,好端端的人,說不在就不在了!付杰雖說不是她生的,但卻是老付家留下的唯一的根。為付杰念書的事,老付活著時沒少操心,現在,老付走了,她這個做后母的能讓付萍去考、付杰不考嗎?
為此,母親一直覺得虧欠著付萍,可一直也想不出個補救的辦法,現在見他們姐弟倆都能這樣為對方想,就有了把他們一輩子拴在一起的心思,反正紙里包不住火。看來付杰已經知道了付萍和鄭好的身世,不然,他不會家也不回就去問她。孩子們都大了,有些事瞞是瞞不住的,還不如她這個當媽的早為他們拿了主意。這樣不但拴住了付萍,就是付杰飛得再遠也會飛回自己的身邊。她進老付家的門時,付萍一歲八個月,付杰才七個多月,起先,兩個孩子一起吃她的奶,一邊一個,后來付萍斷了奶后,付杰吃到五歲上學才斷的奶。如果付杰能做她的女婿,真的比付萍找了任何一個毛頭小伙子都稱她的心。
有一天,母親趁付杰不在,把付萍又叫到跟前,這次,她沒有打毛衣,她幾乎是趴在付萍的耳邊說出了自己的打算。聽母親要讓自己和付杰親上加親,結為夫妻,還有前面說得一大堆亂七八糟,付萍呆住了。“媽,這怎么可能,根本就不可能,簡直是天方夜譚。”她目光呆呆地看著母親,完全被母親過去的突然復雜化搞暈了,她覺得母親不應該離過婚,那個黑饅頭男人也不應該是她親爸,付杰也不應該還有一個死了的親媽,她不想讓自己和付杰有這么亂麻一團的家庭背景。
付萍一直覺得她們家是單純而美滿的,一個親媽,一個親爸,還有一對親生的姐弟,這就是她成長的家。就是父親走了,這個家依然有三個最親的親人支撐著,溫暖而堅固。現在,母親用真相打碎了它的堅固,它像玻璃做的房子一樣不堪一擊,說倒就倒,變成一堆特別容易傷人的碎玻璃碴兒,付萍的思緒在這堆碎玻璃碴兒中小心地躲來躲去。
她想起了小的時候她牽著付杰的手和院里的小伙伴們一起玩藏貓貓,付杰膽小,總是要和姐姐藏到一處,而游戲規則是各藏各的,為這,小伙伴們幾次不帶他們姐弟倆玩。后來,付萍就自己不玩,讓付杰跟他們玩,她把付杰藏好后,她就站在不遠的地方給付杰站崗放哨。想到付杰的膽小,付萍覺得說什么也不能讓這一地的碎玻璃碴兒扎到弟弟,如果不告訴他,這個家就是缺了父親這個角,其他三個角在他心目中也會永遠像水晶一樣晶瑩剔透。
母親老了,她得提醒母親,能不說的就永遠不要說。知道得多,痛苦就多。付萍問母親:“媽,小杰知道這些嗎?”
“媽怎么會傻到先和他講,你畢竟是媽親生的。”
“那就千萬別和小杰講。”付萍說,“就像你不讓我問你鄭好的事一樣,我們永遠也不要再提過去的事了。如果小杰知道,你不是他的親媽,我也不是她的親姐姐,那小杰會受不了的,他在這個世界上,豈不是一個親人都沒有了。”
付萍想起埋了父親那天,小杰哭著和她說:“姐,從此我們就光有親媽,沒有親爸了。”這句話讓付萍多會兒想起來,多會兒就會像刀割一樣的心痛。她和母親表態:“付杰永遠是我的親弟弟。”
親姐弟怎么能談婚論嫁呢。母親后悔不應該和付萍說這些,如果她不說,付萍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過去。付萍的親爸雖說還在,但那個厲害的繼母,鄭好都不讓多管,更不會讓前夫認付萍。可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來了,好在付萍大了,母親相信付萍的本性,不會為此小看自己的。
先不說母親怎么想,單說付萍聽了母親讓她嫁付杰的提議后,見了付杰心里總有點別扭,倒是付杰姐長姐短的,以前怎么樣現在還怎么樣。大年初五那天晚上,付杰從同學家玩回來后,自行車后座上綁著一個裝蘋果的大紙箱子,付萍邊幫著往下解,邊說:“小杰,大正月的,沒見你給人家帶東西去,回來時,倒要人家這么一大箱蘋果,多貴啊!”
“姐,你還沒打開看,里面不是蘋果,是我給你帶回來的書,她妹去年高考用過的,在他床底下擺的,我都給你借回來了,連參考書都有。”
聽弟弟這么說,付萍一把拽住綁箱子的繩子說:“那就不要往開解了,你給人家送回去,我不考。說好的,你考研,怎么能說變就變呢?”
春節過后,正月十四那天,付杰要回學校了。付萍領著一個陌生的小伙子來家里幫付杰扛東西。去火車站的路上,付杰有意走得很慢,付萍以為他走不動,停下來等他,付杰指著走在前面幫自己扛包的人,小聲問付萍:“姐,你不是處對象了吧,他可是個廚子啊。”付萍打斷他的話:“付杰,別這樣說,姐又是什么呢?他是個不錯的廚子,別看他是我們食堂掌勺的二廚,但都說他炒的菜比大廚炒的好吃。”
為了讓母親徹底死心,也為了讓付杰能安心讀研究生,付萍執意要嫁給比自己大六歲的廚子。母親見女兒找了個廚子,雖然心里有點失落,可看著這個小伙子憨厚老實,一米八的個頭,不胖不瘦,人也長得挺好,雖說比付萍大了六歲,但母親知道付萍的心,付萍就是不想等。母親是個明白人,她轉而又勸付萍:談婚論嫁講究個門當戶對,雖說你心氣高,但蒸饅頭的找個炒菜的,也算般配。只有般配了,你日后才不會受他的制。付萍點頭。
母親還是親自己的,母親想讓她嫁付杰,不全是為了母親的養老,更多的是為了自己好,女人誰不想找個比自己高的。可就是打死付萍,她也不能找付杰,不說從姐弟關系一下轉變成夫妻關系,付萍先就擰不過來這個別扭勁,更主要的是,那樣對付杰也太不公平了,倒像是她們母女合起伙來欺負他這個沒親爹親娘的孩子。付杰一個正牌大學的大學生,憑什么要娶一個高中都沒畢業的做飯的她,就因為她把上大學的機會讓給付杰嗎?付萍當初讓付杰去高考,自己頂班,一半是因為母親愿意自己留下,另一半就是自己打心眼里愿意弟弟好。在她心里,自己永遠是付杰的親姐姐。
付萍和二廚的婚禮,定在了那年的八月十九日,專挑了付杰放暑假能回來的月份。婚禮就在付萍他們食堂辦,主持人也就地取材,請了愛熱鬧的食堂管理員,因為兩位新人都是自己食堂的人,管理員就存心要拿這兩個孩子起起哄。面對眾多來賓,管理員學著神父的口氣,問胸前戴著大紅花的新郎:“范廚師先生,你愿意娶我們美麗的饅頭西施付小姐為妻嗎?”
二廚一臉茫然,他下意識地伸出手去捅管理員的胳膊,著急地問:“領導,你沒告過我要問這啊?”管理員不理他,故意對著話筒大聲說:“請新郎范廚師先生當眾回答我的問題。”
說完,就把話筒放在二廚面前,二廚臉紅脖子粗,本來新穿一身藍色的毛料中山裝就夠不自在了,現在更被管理員耍弄得急出一頭汗來,這又不是在教堂,他又不是洋人,讓他當著這么多人的面說“我愿意”三個字,他可說不出口,最后,他對著話筒含糊地表態:“湊合吧。”
聲音雖小,但有話筒擴音,臺下的人還是聽見了,大家先是一愣,后又捧腹大笑。管理員也在笑聲中,換成了嘻嘻哈哈的腔調,轉而又去逗身著大紅套裙的付萍:“美麗的饅頭西施付小姐,你愿意嫁給我們食堂最能干的范廚師、范先生嗎?”
付萍想說,我愿意,本來就是她愿意的嘛。可是,她和身旁的新郎一樣,面對這么多熟悉的親戚、朋友、同事,她也不好意思說“我愿意”。付萍想了想,說:“將就吧。”
付萍的回答再一次把來參加婚禮的人都笑翻了,只有付杰沒笑。想起鄭好,他的眼淚在眼眶里打轉,他覺得他和鄭好,都是有福氣的人,這輩子,他們都攤上了一個好姐姐。雖然付杰不清楚鄭好和付萍到底誰大,但他希望是付萍大,這樣,他的心里好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