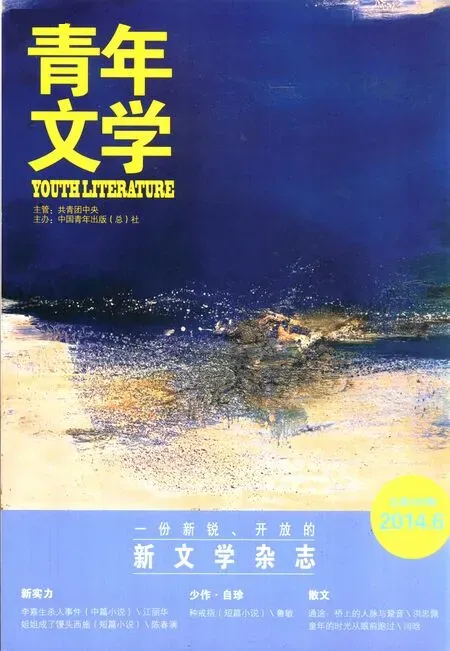黃木葉的詩(組詩)
黃木葉
沉溺
白色的仍屬于白色,
烏鴉也沒有帶走你我中的哪一個。
我開始厭倦,
抽象的詞語在嘴皮子上磨尖,
像親吻一只紅辣椒時,
入秋了。
我夢見自己
嘴里塞滿了鐵屑,發聲器
發不出聲音來。涼風將帶走一萬根手指,
敲打蟬的腹部,
像在黑暗中傳遞火把
與白露。
再讀《一九八四》
山上的玉米,一天綠過一天。
牛的欣喜不可描述,
牛反芻著瑰麗的詞語,和秋雨對視。
我站在鏡子里,
推開空氣,老大哥在看著我。
糧食,也需要一副密封的棺材,
好比酒的釀造史,
掏空成熟的一切,把你填滿,
將你占有,留下酒一般古老的憤怒,
獨酌。
日子
像避開刀刃,文竹獨自托舉著綠
站在夜里。“直到最后,
我們才發現穿著的是件壽衣”,這樣的詩句
曾使你感到害怕。
還有比昨日更溫順的地方嗎?
當鳥屎如子彈般落下,陽光無異于
一場噩夢,幽居的蚯蚓
更懂得收集那暗處涌來的黑,扭動身體
好似在調節太陽的高度。
生存,也是件殘忍的事啊,殘忍得近乎
一雙筷子,分不清左和右,分不清咸和辣。
風扇如此,
躺在西瓜里的夏天亦如此。
只有赤裸成了一種必然,不需要托舉。
保持傾倒的姿勢
月升時,最后一夜停留在了唇上,
這里匯合著所有的喧鬧,鳥鳴穿過絞肉機,
猴子表演著吃火。
讓多余的水繼續制造水聲吧,過多的沉默
只會寵壞我,迫使我
做一位燒水澆花的狠心的詩人。
我愿保持傾倒的姿勢,
追隨一條下沉的河,讓收納箱放進心里
想放的地方,書柜也可以空著。
沒有整塊的云落下來
只有紅色詞語染紅的人和獸,
他們擠進同一個黃昏;
他們飲同一條河里的水,像看著同一朵云;
他們用閃電擦拭著臉,
也用閃電種植了桃花。
誰要是在冬天
咽下一根青草,涼水一定比刀還快。
正在降臨的夜晚
從腳手架開始,一座廢棄的工廠
向后疾駛著。水泥煙囪高過山頂,
河岸行走的人,腳底結了一層薄薄的冰。
車窗外,是正在降臨的夜晚。
把時間交給你,讓你淚流,讓你在停電之后
重新回到密室,渴飲心中的溪水。
連遠處的螞蟻也是五顏六色的,
在詞與物之間,
在火與火焰之間,是錯亂是黑色的羊群;
是鏡子里折回的憂郁的眼神;
是鼓翼而起的湖水;是迎著風的方向,
霧中回旋的鹽粒和大地的低語。
而你總是在冬夜復歸,親愛的馬蒂斯,
像一尾金魚游動在針管內,總有一道光
使你感到了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