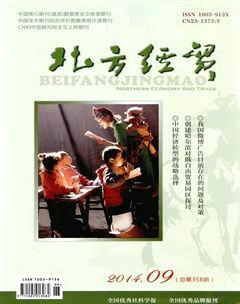仲裁在權利救濟體系中的優勢發揮
姚虹
摘要:權利救濟體系可以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加以區分。多元化的利益沖突和糾紛類型必然要求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仲裁作為一種非訴訟權利救濟方式是介于公力救濟與私力救濟之間的糾紛解決方式。發揮仲裁優勢,協調仲裁在糾紛解決機制中與訴訟的關系,真正使仲裁“深入民心”是仲裁制度未來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仲裁;糾紛解決機制;優勢
中圖分類號:DF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4)09-0063-02
初民社會以私力救濟為常態,公力救濟是伴隨著國家的出現而產生的。文明社會提倡以公力救濟為糾紛解決主要手段,私力救濟為輔助手段的糾紛解決機制。公力救濟與私力救濟共同構筑起現代權利救濟體系。仲裁是介于公力救濟與私力救濟之間的一種“社會救濟”形式,為各國普遍采用。然而其定位的模糊性及仲裁文化缺失成為阻礙仲裁優勢發揮的瓶頸。仲裁制度的完善不能管仲窺豹,只有將仲裁制度納入糾紛解決機制的整體來審視與糾正,才能更大地發揮其優勢。
一、仲裁制度缺陷
(一)仲裁行政化
自1995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施行以來,仲裁制度取得了階段性進步,基本完成了由行政仲裁向民間仲裁的過渡,但是仲裁行政化問題依舊備受理論與實務界詬病。
所謂仲裁行政化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仲裁活動進行管理與干預,使仲裁具有了顯著的行政行為特征。我國《仲裁法》第14條規定:“仲裁委員會獨立于行政機關,與行政機關沒有隸屬關系。”這一立法雖然沒有明確仲裁機構的性質,但堅持仲裁獨立性與自治性的理念卻已表露清晰。當前,關于仲裁機構的性質主要有司法說、行政說與民間說。立法的不明確是造成仲裁定位模糊的直接原因。不過也有學者指出,《仲裁法》關于仲裁機構民間性的表述已十分明確,“有人以仲裁法沒有‘民間性三個字為由,否定仲裁民間化原則。其實,仲裁法沒有規定‘民間性三個字,是立法者認為,這是個常識性問題,是各國通例,而且按照一般人的認識水平,從法律條款不難理解這個問題”[1]我們以為,仲裁法的許多條文需要改,唯獨堅持仲裁的民間性不可動搖。
仲裁行政化的主要表現是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預仲裁工作。《仲裁法》頒布前我們適用的行政仲裁制度,其傳承性導致仲裁制度產生了“路徑依賴”,而這種制度運行上的“慣性”成為改革路程上的障礙。此外,仲裁機構的組成也表現出濃厚的行政化色彩,例如某些地方仲裁委員會辦事機構領導由行政官員兼任,仲裁委員會成員由過大比例的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充任,這種內部結構使得仲裁活動與行政行為具有了千絲萬縷的關聯。包括仲裁制度的推進與普及都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某些行政手段的介入。也就是說,現行行政體制依舊從多個角度多個方面繼續推進著仲裁行政化。
(二)仲裁文化缺失
仲裁文化是仲裁事業發展的基礎與根基。沒有先進的仲裁文化支撐,仲裁制度改革無異于隔靴搔癢,目的實現恐任重道遠。
什么是仲裁文化?什么又可稱為先進的仲裁文化?英國學者泰勒在《文化之定義》中提出:“所謂文化或文明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以及其他人類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各種能力、習性在內的一種復合整體。”仲裁文化作為法律文化的一部分,除具有法律文化的共性之外,還具有其自身的顯著特性,它是以解決商事爭端為根本目的,以仲裁活動為核心背景,集仲裁理念、價值取向、仲裁管理、仲裁相對人意識認同等多個文明要素的集合。先進的仲裁文化則應是平等與公正的守衛者,效率與進步的推進者。我們衡量仲裁文化的先進與否最根本的標準即符合人民利益,有利于推進國家經濟建設。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進程演變的結果體現,它是立體的、綜合的,仲裁文化是長期仲裁歷史積淀于人們意識的文化素質與氛圍。
先進的仲裁文化能夠為仲裁事業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而我們當前由于仲裁舶來品的特質而縮短了仲裁發展所必須的歷史積淀過程,致使很多仲裁文化要素在外力作用下而偏離發展軌道。例如,為改變仲裁案源少的現狀通過某些行政手段拉案源,為實現仲裁糾紛的公正裁決過分夸大調解效用,推廣仲裁理念過程中重形式輕實質等。比較于文化,仲裁文化也許只是文化中十分微小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其構成的復雜程度卻絕不亞于文化。仲裁文化既包括法律意識形態,還包括法律制度形態,是由法律觀念理論、心理、思維模式、行為模式等多方面內容組成。文化的發展不僅需要一定的歷史背景,還需要在發展中逐漸培養出的情感文化,這是一個由外而內的發展過程。筆者以為,仲裁管理文化的進步是仲裁文化其他要素發展的前提。
仲裁是法制精神與人文精神有機結合的過程,平衡利益,回歸理性,真正從文化管理視角去探求仲裁事業的發展路徑才能恰當解決紛爭。仲裁制度與仲裁文化屬于一個范疇的兩種不同形態,[2]制度構建是文化發展的初級階段,文化發展是制度完善的最高形態。
二、仲裁優勢發揮
有學者在仲裁理論探討中提到仲裁競爭力的提升,筆者以為仲裁作為一種非訴訟權利救濟方式與訴訟是并行而非對立的,因此將仲裁優勢發揮作為主題探討更為科學。
(一)仲裁的優勢判斷
比較于訴訟權利救濟,仲裁能夠成為人們的最終選擇一定是緣于其獨到的文化魅力,我們只有準確判斷優勢魅力之所在,才能得以發揮。
縱觀中外仲裁發展歷史,權利自治無不是仲裁發展的原始動因。英國著名學者施米托夫曾說:“商事仲裁的首要原則是當事人意思自治”“仲裁制度最根本的屬性就在于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務,自主選擇,自己參與,充分尊重當事人的地位,發揮當事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當事人的共同協作下解決糾紛,這是多么有吸引力的糾紛解決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規定,當事人可以自主選擇仲裁機構,不受級別和地域管轄的限制,可以自主選擇仲裁庭的組成。還有的國內仲裁機構甚至允許當事人經協商一致,不受仲裁時限和程序的限制。高度的意思自治是仲裁區別于訴訟的最大優勢,是仲裁文化的靈魂與生命力。
效率追求契合商事當事人的價值觀,更符合人們意愿。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效率要求我們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多的效果,這一投入與產出關系正是商事行為的價值追求,與仲裁活動完美結合將對當事人選擇仲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促進。肖揚院長曾指出:“解決民事糾紛的高效率和相對低的成本是當事人選擇仲裁的動因。”[3]當理性的當事人自愿選擇了仲裁作為糾紛解決方式之后,節省了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獲取相對公平的仲裁裁決時,那種自我選擇后的效率實現不只是糾紛解決機制的成功,更是當事人自主參與的滿足。意思自治與效率的圓滿結合是仲裁優勢發揮的最高境界。
獨立公正是仲裁更好服務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屬性。仲裁實質上是解決爭議的一種合同制度,作為一種合同安排,仲裁應當受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支配。[4]其實,當事人在訂立“仲裁契約”之前即已將仲裁行為假設為獨立公正的化身。公正是一切程序制度的共同追求價值目標,訴訟制度是,仲裁制度亦是。公正意味著平等對待爭議的訴訟雙方,不偏袒任何一方,對所有人平等公正的適用法律。法律能否得以純粹適用取決于是否存在對其適用加以干擾的外來因素。因此,獨立性是公正裁判的保障。仲裁的獨立不應僅表現在仲裁機構的獨立上,仲裁庭、仲裁員的獨立在仲裁文化價值體系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果仲裁機構能夠獨立于行政機關,仲裁庭能夠獨立于仲裁機構,仲裁員能夠獨立于仲裁庭、當事人,則真正意義上的仲裁獨立已指日可待。
(二)仲裁優勢發揮的路徑
首先,弘揚仲裁意思自治精神必然要求我們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主線設計仲裁制度。當今國際仲裁法立法趨勢之一即為最大限度追求意思自治。國際仲裁給予當事人廣泛的自由設計爭議解決機制,當事人意思自治體現在仲裁程序的每個階段,這也是國際商事仲裁在國際商事糾紛解決中備受青睞的主要原因。
當前,我國《仲裁法》意思自治原則的貫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以書面協議方式自愿啟動仲裁程序;2.合意約定仲裁事項和仲裁機構;3.自主選擇仲裁員;4.對仲裁方式的審理可以協商確定。以上可稱為相對受限的意思自治原則。在仲裁程序的很多環節,意思自治原則并沒有充分貫徹。對比《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示范法》,我國《仲裁法》在涉外仲裁仲裁地的選擇上沒有賦予當事人充分的自治權,當一方當事人為外資企業的,不能選擇中國大陸以外的仲裁機構。此外,對仲裁員名冊以外人員指定,中國仲裁機構指定的首席仲裁員的更換加以限制都使得意思自治原則大打折扣。意思自治是仲裁的靈魂,應貫穿于仲裁程序的始終,如仲裁代理人和仲裁語言的選擇,仲裁程序的變更等只要不侵害社會公共利益,在既有法律基本框架下,應允許當事人做出自由選擇。只有將意思自治精神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位仲裁員及仲裁當事人的頭腦中,適當放開中國立法上的限制性立場,仲裁制度才會發展更好。
其次,以訴訟缺陷為觀察視角,協調仲裁與司法的關系,籌劃配套糾紛解決機制是發揮仲裁優勢的重要舉措。訴訟在權利救濟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解決利益紛爭,維護社會秩序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訴訟不可避免地存在結構性功能缺陷。歸納起來主要有:1.各種矛盾的不可調和,如法律規則與社會規范之間的矛盾,程序設計專業化與當事人參與常識化之間的矛盾,公平與效益的矛盾等等。復雜的矛盾關系限制了訴訟的功能與效果;2.繁瑣的訴訟程序既增加了糾紛解決的成本,又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為啟動訴訟程序,人們投入人力、物力、耐力,除了獲得或喜悅或失望的裁判結果外,還有對疲憊的訴訟經歷的慨嘆。3.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將爭議雙方當事人完全置于對立立場,增加了和解的難度,也進一步惡化了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某些交易伙伴關系因此而終結。我們應立足于對訴訟缺陷的檢討完善仲裁制度,更好地發揮仲裁優勢。例如,強化仲裁程序中調解工作的重要性,創造誠實、公開的調解環境,強調仲裁員的調解員身份,盡可能地化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提升仲裁公信力。通過簡化仲裁程序,縮短案件審理期限等方式降低仲裁成本構建仲裁效益文化。在同法制文化比較研究過程中,探究仲裁的自身規律,加強仲裁機構與人民法院的交流,實現仲裁與司法的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做好充分準備。
第三,仲裁的獨立公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仲裁主體素質,因此,仲裁主體文化管理在仲裁工作中顯得尤為重要。商事仲裁中流傳著一句名言:仲裁的好壞取決于仲裁員。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如此表達:仲裁的獨立公正取決于仲裁員的獨立公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規定,律師、曾任審判員、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都有可能擔任仲裁員,如何避免律師利用仲裁員身份不恰當保護一方當事人利益,政府官員運用復雜的社會關系網辦人情案恐怕是仲裁制度建設的一大頑疾。筆者以為,除了對仲裁員認真甄選外,細化仲裁回避制度,擴大異地仲裁員比例不失為保障仲裁獨立的良方。公正作為一個價值判斷問題會摻雜有個人主觀認識,每一位仲裁員對公正價值觀的信念是有差別的,我們可以通過仲裁員監督機制建立仲裁員的培訓、評級、除名與懲戒制度,從外部向仲裁行為施壓,實現仲裁公正。
第四,仲裁文化的發展首先依賴仲裁理念的培養,而仲裁理念的建立需要一定方式的傳播、推廣、示范。現有的仲裁宣傳過于表面化,對人們意識形態的影響需要更深層次的表達。例如,利用建立高等院校實踐基地開設仲裁課程,模擬仲裁法庭,舉辦仲裁座談會,注重某些具有典型性的仲裁案件在各類媒體上的宣傳,召開仲裁與法院交流會,從根本上消除仲裁裁決威信低于法院判決的顧慮,讓仲裁文化深入民心。
參考文獻:
[1] 王紅松.鑄造公信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 潘俊星.仲裁文化的特質與發展理念[J].政治與法學,2001(17).
[3] 高 菲.中國法院對仲裁的支持與監督——訪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J].仲裁與法律,2007(3).
[4] 彭云業,沈國琴.論仲裁制度中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擴與限[J].法學評論,2010(4).
[責任編輯:蘭欣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