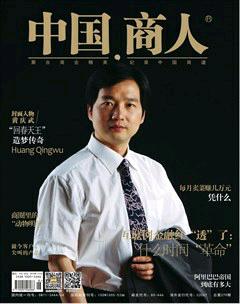誰是你人生的大股東
濟群


如果把心比做舞臺,各種念頭就是其中的參演者,它們在臺上川流不息,交替登場。如果我們投入其中,每個角色登場時都去搖旗吶喊,就會在疲于奔命中耗盡一生。這不僅是對人身的極大浪費,更可怕的是,還會由此積累不良串習,影響未來生命。
欲望就是我們的永動機
欲望之所以會有如此的“能量”,就在于它永遠都處于發展的進程中,如果不從根本上對治它、鏟除它,它就會無休止地驅使我們為之效力。現代人非常重視個人的自由,我們總是在抱怨環境的束縛,抱怨家庭的束縛,事實上,即使外在環境沒有給我們制造任何壓力,我們的心靈也未必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
因為欲望是無所不在的,我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就會被它控制,將自己的主權拱手相讓。欲望又是永無止境的,一個欲望得到了暫時的滿足,新的欲望又會接踵而至,向我們提出更多的要求。當我們有了1000塊的時候,就希望得到1萬塊,然后我們就必須為完成這9000塊的目標努力;當我們有了1萬塊的時候,就會希望得到10萬塊,然后我們又必須為完成這9萬塊的目標努力。常常是我們擁有得越多,反而感覺自己缺少得越多。一個只有1000塊的人,認為自己只缺9000塊;可一個有1萬塊的人,就會認為自己還缺9萬塊。既然世上已存在擁有億萬家產的人,我們希望得到的1萬和10萬似乎并不是過高的要求,希望得到百萬和千萬似乎也不是癡人說夢。且不論我們最后究竟能達到什么樣的目標,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向誰去索取這一切?不論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方式,負擔最終會落到自然的身上,因為大自然才是生產資料的惟一提供者。
人類曾經夢想制造出永動機,其實,欲望就是我們的永動機。具體到每個人,這一生的欲望會隨著色身的消亡而結束。但對于整個人類社會來說,一方面,個人欲望正隨著經濟發展而飛速增長;一方面,人口遞增又制造出了龐大的基數。所以,這臺以欲望作為動力的機器,非但永遠不會停止,還會以更強勁的功率運轉。在現代社會中,習慣以數字來總結一切:人均收入、國民生產總值等等。如果欲望也能以相應的量化指標來進行衡量,我相信,不論是人均欲望還是世界欲望總值,都遠遠超過了以往各個時代。
而和這急劇增長的欲望所對應的又是什么呢?是地球上日益貧乏的資源儲備,是業已失去平衡的生態環境。或許,我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去關心森林的減少,去關心水土的流失,去關心臭氧層的空洞。但即使再麻木的人,也不會看不見河流的污染,不會感覺不到空氣的污染。長此以往,不僅我們所向往的財富會成為無本之木,即使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會受到致命的影響。我們還能喝什么?我們還能呼吸什么?
地球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惟一家園,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我們不能對欲望進行有效的節制,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只能落得自掘墳墓的下場。
名言與真實
我們學習佛法,必須抓住要領,否則很難學出什么名堂。若是從學術層面來認識佛法,只會越學越復雜。若能匯歸到心行上,匯歸到佛法的根本上,我們就會越學越簡單。因為根本不會很多,否則就不成其為根本了。知識是復雜的,但智慧和真理是簡單的。
當然,真理也需要語言文字作為載體,所謂文以載道。但我們要知道,語言文字是最不可靠的。那些異端邪說和虛假廣告,正是利用語言來誤導世人。對于凡夫來說,即使沒有刻意欺騙他人,所使用的語言也往往帶有強烈的傾向性。每個人說話都有自己的角度,難免會有局限性和片面性。我們想做某件事情,可以找到一百條做的道理;不想做的時候,也可以找到一百條不做的道理。知識越多的人,找到的道理就越多,所以知識分子最會講道理。無論是做還是不做,找到的理由都同樣充足。
這說明什么?說明事物的兩面性,所以佛教說事物都是假名安立的。我們聽說某個人如何,某個地方怎樣,只能代表敘述者對此的認識,其中往往夾雜著他的主觀好惡。所以,不能聽別人怎么說,就全盤接受了。我們了解一個人,要聽其言、觀其行;我們了解一個地方,要查找資料并實地考察。當然,先賢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正確的知識,但對事實真相的了解,我們還是需要親自去體驗,這一點非常重要。
佛法也是以語言為載體,但圣人的語言和我們的語言又不同。因為圣人所揭示的是事物本質,作為本質,不論從什么角度去看,都是“法爾如是”。如果從不同角度觀察就會產生變化,就不是本質了。所謂本質,即本來如此,是平等一味、沒有差別的。
但是差別性就不一樣了。比如說這張桌子,如果從知識的層面來闡述,物理學家有物理學家的角度,化學家有化學家的角度,文學家有文學家的角度,哲學家又有哲學家的角度,甚至可以根據各自的專業撰寫一本乃至數本關于桌子的著述。如果從差別性對桌子進行研究,可能終其一生還是無法窮盡,因為每個角度還可以不斷細化。
那么,桌子的本質又如何呢?非常簡單,過去諸佛認為桌子是苦、空、無常、無我,是如夢如幻的,現在諸佛也是這樣認為,未來諸佛還是這樣認為。在真理的層面,不可能有別的認識。所以,佛菩薩的言教,是反映事物本質的圣言量,和世間語言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當然,佛陀說法也不完全是從第一義來說,還有世界悉檀、對治悉檀、為人悉檀,這三種悉檀都有其特定的角度和時節因緣。古人也講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可見古人也發現了語言的局限性,所以,語言只是我們認識真理的橋梁和載體。
緣起的世間很復雜,也就是經典中時常說到的“緣起甚深”。“緣起甚深”包含兩個層面,一是世俗的層面,即生滅的層面;一是空性的層面,即寂滅的層面。作為我們凡夫來說,即使對于生滅層面的緣起,也很難真正的透視它,何況是緣起寂滅的層面?只有以佛法的智慧為指導,我們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不被現象所迷惑。
舞臺和演員
如果把心比做舞臺,各種念頭就是其中的參演者,它們在臺上川流不息,交替登場。如果我們投入其中,每個角色登場時都去搖旗吶喊,就會在疲于奔命中耗盡一生。這不僅是對人身的極大浪費,更可怕的是,還會由此積累不良串習,影響未來生命。正確的態度,是不迎不拒,再喜歡的念頭也不追隨,再討厭的念頭也不拒絕。當心能夠穩定安住時,念頭就會因缺乏呼應而黯然退場。否則,我們往往會被起伏的念頭所左右,繼續注入心靈能量,使之增大廣大。每一次在乎,它的力量就隨之強化。大到一定程度,我們就難以控制局面了。endprint
因為無明,我們會把很多不是我的東西當做是我。人為什么會怕死?就是因為把身體看做是我,自然地,就會害怕“我”隨著這個身體消失。如果知道色身只是生命延續中的一個暫住地,就不會對死亡那么恐懼,那么聞風喪膽了。
生命就像流水,眼前這個色身,只是其中呈現的一朵浪花。浪花雖時起時滅,流水卻在繼續。認識到這個道理,色身的生老病死就不會對我們構成心理傷害,因為那純粹是自己嚇唬自己。如果執著其中有我,才會貪戀不舍,痛苦也就在所難免。
我們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家庭、財富、事業、孩子等等。之所以在意,都是因為前面被冠以“我”的標簽。因為有了這個設定,所以,“我”的家庭就比別人優越,“我”的財富就比別人重要,“我”的事業就比別人出色,“我”的孩子就比別人特殊。于是就會出現攀比,產生競爭。因為這種自我的重要感和優越感,又會帶來自我的主宰欲,總想支配別人,這就使人生處處面臨沖突。
這個舞臺上 你是傀儡嗎
在這個熱鬧非凡的心靈舞臺上,各種角色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我們卻從來搞不清,這些心究竟如何產生,如何活動,如何過渡,因為我們從未管理過自己的心。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樣順其自然不也很好,不也同樣精彩?但我們要知道,就像生活中隨時會制造垃圾一樣,我們的言行也會在內心留下痕跡,產生心靈垃圾。如果不加處理,這些貪嗔癡的垃圾非但不會自行降解,還會繼續滋生新的問題。
所以說,了解心理的形成規律非常重要。因為我們不是活在現實中,而是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們看到的一切,都已經過情緒的投射,經過想法的處理。你覺得某人好,看他什么都順眼;覺得某人不好,看他什么都別扭。這種感覺或許和別人對他們的評價截然相反,為什么?原因就在于,你看到的并非客觀上的那個人,而是你感覺中的那個人。
怎樣才能對心靈進行管理?
我們的心就像一片田地,如果播下荊棘,就會遍布荊棘,給我們帶來痛苦;如果播下花草,就會盛開鮮花,給我們帶來快樂。所以,我們每天想什么、做什么非常重要,因為這就是在給心靈播種。
我們的所思所行會有兩種結果,一是外在結果,即事情的客觀結果。一是內在結果,即起心動念所形成的心理記錄,也就是佛法所說的種子。當這些種子遇到合適環境,還會繼續生長,積聚力量。而在形成一定力量后,又會促使我們去重復它,并在重復過程中日漸壯大。當某種心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主導整個生命。如果這種心理是負面的,就會使我們成為它的犧牲品。就像那些犯罪者,固然是給他人造成了傷害,但他們自己何嘗不是受害者?不同的只是,他們是自身煩惱的犧牲品,是負面心理的犧牲品。此外,有些人是愛情的犧牲品,有些人是名利的犧牲品,有些人是虛榮的犧牲品,有些人是賭博的犧牲品,這種現象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現象?因為他們從未管理內心。最終,在不知不覺中使不良心理強壯起來,結果使自己淪為傀儡。要扭轉這一局面,就必須了解并有效管理內心。對生命來說,沒有比這個重要的。因為心才是和我們關系最密切的,是無從逃避也無法舍棄的。
知識使人復雜 智慧使人單純
經商忙、從政忙、讀書更忙。小學生背著沉重的書包,中學生高考前緊張復習,年輕教師為職稱辛勤奮斗,老教授為帶動學術研究不懈努力。莊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感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何況今天的知識,比兩千年前又增長了百千萬倍。我感覺知識就像太平洋的波濤,人類早就被自己制造出來的知識淹沒了。
任何一個學科,從產生到流傳就出現了許多相關著作,后人對這些原著的研究,又出現了許多成果,每年每月都會在雜志上刊登無數論文。佛教理論自從被學者納入學術研究范圍后,也成了一種純學術。在日本,佛教和文學、物理學一樣,被當作專門學科去研究。
佛教成了佛教學,佛法幾乎就死掉了。把佛學當做學術研究之后,佛學就成了一種專門供人研究的學問。因此,許多研究者反而忘記了佛陀創立佛教的最初意義——佛教是為改善現實人生服務的。許多學者的研究,很少考慮佛教契理契機的問題。為了研究一個問題,把大量時間花在看資料上,整個身心都陷入錯綜復雜的資料堆中,終日案牘勞形,身心疲憊不堪。當然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學佛方式,但那是和做人沒有關系的方式。
真正的學問,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感悟。不是為了應付什么,而是自由、自發的學習。同時,心中不能有任何成見,觀念中不能有任何框框套套。對一個領域的學習,除了掌握一些該學科必要的知識,讀幾本經典性的原著之外,應該有更多的空閑時間,對該學科的重要問題作自由思考。
我覺得治學應該像做人一樣,要簡明。知識使人復雜,智慧使人單純。我們培養出的人才,不能像個圖書館一樣,給人感覺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一開口就不斷冒出各種各樣的知識。而是要有智慧,能過濾吸收,像胃腸一樣,只吸收那些對自己真正有用的東西,把多余的通通排泄掉,絲毫不留在體內,造成生命的負擔。
執著的源頭是我們的內心
心,才是佛法關注的重點,才是修行的入手處和著力點。但不少學佛者卻把念佛誦經作為和佛菩薩交易的籌碼,似乎我念了多少佛,誦了多少經,將來可以把這些功德找阿彌陀佛報銷。更有些人,恨不得立刻就要兌現,就要產生效益。生活中稍稍遇到一點挫折,就抱怨念佛不靈,誦經無用。以這樣的心態來念,效果可想而知。
誦經念佛的關鍵,不在于數量,而在于質量。如果對念誦內容缺乏認識,又無正確發心,這聲佛號就不會念得相應,更無法在內心形成正念。如果正念缺失或不夠強大,一旦妄念現起,我們依然會束手無策,為其所轉。
修行所要解決的,正是心念問題。我們每天都有很多念頭,想著家庭,想著孩子,想著事業,想著人際關系,終日在其中忙來忙去。這些念頭就像高處沖下的瀑布,湍急迅猛,來勢洶洶。在這妄念的瀑流中,我們除了身不由己地隨之漂浮,還有可能把握方向么?
我們每天做些什么,不僅是客觀環境造成的,關鍵還在于我們執著什么,在乎什么,想要得到什么。這種執著的源頭,就是我們的心。有些人會執著于事業,有些人會執著于地位,有些人會執著于兒女,所有這些執著,都是我們長期以來不斷養成的。我們每天想著事業,事業在內心的股份就會不斷增強;我們每天想著兒女,兒女在內心的砝碼就會隨之加重。當這種股份和砝碼占有絕對優勢時,就會成為生命主宰。就像那個掌控最多股份的股東,憑借強大的實力,就能成為最終的決策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