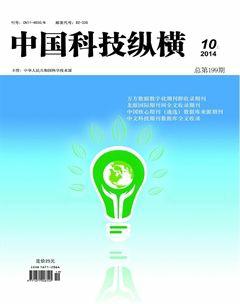牧民定居背景下牧民生計方式的新發展
——以四川紅原縣為例
王春英 于瀟 楊麗雪
(1.西南民族大學,四川成都 610041;2.四川民族學院,四川康定 626001;3.西南民族大學,四川成都 610041)
牧民定居背景下牧民生計方式的新發展
——以四川紅原縣為例
王春英1于瀟2楊麗雪3
(1.西南民族大學,四川成都 610041;2.四川民族學院,四川康定 626001;3.西南民族大學,四川成都 610041)
以四川紅原縣為例,研究在牧民定居背景下牧民生計方式的新發展,探尋當地的經濟發展方向。通過實地調查的手段,調查了紅原地區牧民目前采取的幾種新的生計方式:一部分人開始部分性的或者全部脫離牧業生產,另一部分繼續從事畜牧生產的則在向更加規模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當地牧民在牧民定居過程中采取了積極的態度應對生活方式的變化。文章指出當地脫離牧業生產的新生計方式的發展主要依托還在于旅游業的發展,而旅游業發展尚未達到相當的規模;畜牧業的現代化發展也處于剛剛起步階段。當地的經濟發展應該向多方面拓寬增收渠道的方向努力,一方面大力發展生態畜牧業,促進傳統產業的提升與當地環境的保護;另一方面要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發展其他產業,促進脫離牧業生產人員經濟增收。
牧民定居 生計方式 紅原
紅原縣屬高原游牧帶,是阿壩州唯一的純牧業縣,也是四川省重要的草食畜牧業基地。隨著國家牧民定居工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人們的生計方式與之前的純游牧時代相比,發生了一些新變化,這些變化既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方式,也促使畜牧業向著更加集約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本文擬主要分析這種生計方式的新變化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的新問題,試圖通過牧民對于定居后的城鎮化生計方式所表現出的應對態度探討今后可能的發展方向。
1 關于牧民定居的研究
關于牧民定居的研究,國內已有不少,這些研究中都談到了定居后牧民生計方式的變化。比如阿拉坦寶力格[1]、崔延虎[2]等人對內蒙牧區的研究,都涉及到定居后牧民生計方式的轉變問題。張雯選取位于毛烏素沙地北部邊緣的馬什亥嘎查為研究對象,指出了現代性與沙漠化之間的邏輯聯系[3]。彭定萍則認為如何開拓新的增收渠道是解決牧民適應問題的關鍵[4]。郎維偉等人[5]主要從社會文化角度的變化探討定居的影響,這些因素也是能夠影響到生計方式變化的應該被考慮的因素。袁曉文、石維斌等人關于紅原“帳篷新生活”政策的實施和調查,也為如今的牧民定居工程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研究資料。該政策力圖在定居和游牧間找到一個提高當地生活水平的解決之道[6]。筆者認為無論是對傳統游牧生活的認識,以及對現在牧民定居后的發展探索,都是前人在面臨新的發展狀況下的思考,所有的這些被考慮到的因素都應該作為目前牧民定居工作開展中需要被考慮的方面。而這其中如何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合理有效的發展畜牧業,同時多方面地拓展增收渠道,滿足當地人民的生活需要,無疑是最重要的問題。
2 紅原縣牧民生計方式的變化
目前紅原縣牧農業預計總產值35422萬元,其中畜牧業產值為30300萬元[7],畜牧業占到總產值的85.54%,仍然是該縣的支柱產業。在牧民定居過程中,當地牧民與外界的交往越來越多,其生計方式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牧民對于生計方式的變化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態度。伴隨著當地旅游業與商業貿易的發展,一些牧民部分或者全部地脫離牧業生產,改變了傳統的游牧生產方式;另一部分人則向著更加規模化、專業化的畜牧生產發展。
2.1 脫離的兩種方式
2.1.1 部分性的或變化性的脫離
(1)部分性脫離。本文的部分性脫離,指的是那種自己家里沒有再養牦牛,但是仍然是依托畜牧業生存的那部分人,比如受雇于別的牧民個體或者當地單位的人,通過為別人放牧牦牛而謀生。這部分牧民依靠的仍然是之前擁有的放牧的技能生存,但他只需要放牧的體力付出,而不需要再考慮飼草,產出等問題,所以筆者稱作部分性脫離牧業的人群。 這部分人家,之前自家養殖牦牛數量不太多,考慮到牦牛的放牧都需要轉場,儲備草料,擠奶等等工作,養殖數量少的話,就會提高勞力成本的比例,不太合算,況且隨著牧民對教育的重視,多數年輕人都要進入學校學習。這部分牧民選擇在縣城的附近為別的牧民個體或者單位放牧,每月獲得固定數量的報酬。他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變化,與之前在牧場上的生活不同,他們距離城市更近,咨詢接受更多,已經習慣現在糧食為主的生活。
(2)變化性脫離。本文的變化性脫離,指的是那部分結合了畜牧業和旅游業,服務業因素的生計方式,比如牧家樂。牧家樂的發展基礎,根本還在于游客對游牧生活的興趣和體驗,但是又同時具備了服務業的特點,這就需要經營者不僅需要具有原來的游牧生活技能,而且需要具備一定的商業經營技能,所以筆者稱這部分人為變化性的脫離。
隨著紅原縣旅游的開發,一些靠著公路的人家,開始發展起牧家樂,為游客提供帳篷、酥油茶、吃飯、騎馬等服務。坐在帳篷里面喝一壺酥油茶,要25—100元不等,價格要看游客數量、淡旺季、帳篷大小以及主人的心情而定。還有一些人家將自家原來的黑帳篷仿照傳統樣式布置起來,里面按照老規矩擺放爐灶神龕、農具服飾等等,儼然一個小型的藏家博物館,向希望體驗游牧生活的游客收取門票,一次十元。這應該屬于一種展演性的牧業生活,是適應當地發展變化而產生的。
牧家樂的發展,主要的還是依托于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幾年以前,紅原游客漸漸增多,一些游客便開始向靠近公路放牧的一些牧民去聯系騎馬、酥油茶、糌粑、牛肉的服務。慢慢的一些牧民發現這是可以帶來可觀收入的一個新手段。一些靠近公路的牧民,開始專門的設置休息點,開起了牧家樂,為來到這邊的游客提供體驗游牧生活的服務。酥油茶也從最開始的五塊錢一壺,變成現在的二十五元一壺,酸奶、騎馬也相應的有幾倍漲幅。當地牧家樂的發展有兩個條件:一、臨近公路,有地利之便;二、游客增多,需求帶來市場。這些也為當地牧民脫離牧業生產創造了條件。
還有一些家庭,在夏季利用冬房為游客提供家庭式的住宿,價格在50元/天。如果說這種還不能算徹底的脫離,那么有一部分牧民則選擇了商業經營或者打工,屬于完全性的脫離牧業生產。
2.1.2 完全性脫離
本文指的完全性脫離,指的是那種不需要再用到游牧生活技能的生計手段,比如從事商業、在外務工。或者通過升學參加工作。
從事商業的主要指在縣城開店的一部分人,比如在縣城從事藏裝、藏毯銷售的人。這些人主要銷售青海產的藏毯和藏裝,生意還不錯。作為傳統工藝品的藏毯,兼具實用和收藏的功用,不僅本地人購買作為家庭陳設,很多游客也來購買。外地游客來到此地也愿意買一些富有當地民族特色的物品,而目前紅原縣在旅游商品開發這一塊尚未形成規模,游客的選擇性不多,兼具美觀實用、經久耐用又具有民族手工工藝傳承性的藏毯,就成為一些游客的首選。
一些年齡偏大的牧民,在定居后選擇將牦牛出售,賦閑在家,比如一些原本養殖了兩百頭以上的牦牛的家庭,將牦牛全部出售以后有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完全能夠應付養老所用。而其子女多半已經從事其他工作,家里已經沒有再從事牧業的勞動力。也有些家庭選擇將賣牦牛所得的錢投資其他行業,比如商鋪等等。這些人脫離牧業生產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老一輩年紀大了而家里的年輕一輩又認為牧業生產過于辛苦而不愿意再放牧,家里無人再從事牧業經營。而客觀上,也是因為隨著當地經濟的發展和與外界交往的增多,增加收入的渠道也變得多樣化起來,年輕人相較以前來說有了更多的選擇,也更容易找到其他的工作來代替畜牧業生產。
年輕一代讀書以后出去工作,也是當地人脫離牧業生產的主要方式之一。當地人現在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許多有條件的家庭將子女送到江油、都江堰等地讀中學。這些到內地求學孩子,通常都會更進一步深造,畢業后選擇了其他工作職位,脫離牧業生產。女性在這方面表現得更為主動和渴求。相比男性的放牧而言,牧區女性一天的勞動時間更長、勞動強度更大,所以也客觀上刺激了年輕女性通過讀書擺脫牧業生產的意愿。在產奶季,牧區的女人凌晨四點就要起床擠奶,家里幾百頭牦牛的擠奶工作都要靠女性完成。而擠奶之后還會有打酥油、曬奶渣等等的一系列工作。雖然現在打酥油可以用機械分離,但是擠奶仍是牧區女性的一項繁重工作。而電視網絡等傳媒的普及,也為這些年輕人打開了了解外面世界的窗戶。不少女孩認為,不管是打工還是放牧,挖蟲草,都很辛苦,還是讀書才有前途,不愿意再像母親那樣每天忙于擠奶,很歡迎紅原能夠搞旅游開發,希望見到外面的人來,也希望能出去看看。
2.2 畜牧業的發展更加專業化、規模化
繼續從事畜牧業生產的牧民,規模開始逐漸擴大,200-400頭牦牛的養殖量是普遍情況,這些牧民在自家草場草料不夠的情況下,會去租借那些已經沒有再養牦牛人家的草場,通過租借其他牧民的草場解決飼草問題,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動物營養問題以及牦牛飼料的問題[8]。比如在筆者的調查中發現的,一些牧民開始逐漸的接觸畜牧養殖的一些新理念,比如牦牛的微生物飼料的應用、外地畜種的引進、暖棚的建設等等。為了滿足市場需求,當地的畜群結構在發生變化——產奶產肉率更高的犏牛、雜交牛受到牧民的歡迎;同時當地特產的麥洼牦牛則在進行針對高端市場的品牌打造。為了提高畜牧業的附加效益,當地政府與牧民結合各個鄉鎮的實際情況,積極推進專門從事肉類分割包裝、酸奶加工、草料貯備等的合作社的建立。同時,隨著當地畜群結構的變化,“人、蓄、草”三配套項目和牲畜暖棚建設項目也在積極推進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牧民的畜牧生產已經不是原來的自給自足狀態,而是與市場緊密結合的市場經濟。當地政府與教學科研機構的合作也在大力的推進中,比如西南民族大學在紅原建立的青藏高原生態保護與畜牧業高科技創新實踐研發基地,研究領域涉及到牦牛、藏綿羊等青藏高原特有主要畜種遺傳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高效養殖新技術研究和推廣示范、牧草新品種的引種與篩選、草產品加工等研究和新技術推廣、示范和服務、野生動物保護、生態環境一體化等多個領域,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草地退化、沙化得到修復,牦牛藏綿羊的生長速度和出欄率都有顯著提高,這些成果已經在當地得到推廣應用,牧民的接受程度也在逐漸加大,客觀上促進了牧民向專業化養殖方向發展。
3 結語
當前,牧民生計方式的新發展主要體現在:部分或完全脫離牧業,主要依托當地的旅游業發展。當地雖然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但旅游業的發展尚處于初期,很多基礎設施和配套措施還沒有完全到位,新的生計方式還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比如牧家樂的經營,還不夠規范化、標準化,接待能力也有限。至于家庭式住宿,草原的旅游旺季一般在四五月份開始、到九十月份結束,而這個時期正是牧民舉家在外放牧的時候,很多人家的冬房都是鎖起來的,游客在定居點很少能見到當地的人,即使有人留在冬房里,也往往是家里的老人,與外來游客語言不通、溝通不暢,所以若要發展,還需解決經營接待人員的問題。
隨著當地對教育重視程度的加大,通過讀書等渠道脫離牧業生產的人越來越多,外出打工的人員數量也在增多,但主要從事服務業、建筑業等技術含量偏低的行業。采訪中了解的人員,基本都是在縣城做小生意,或者打零工。進一步提高當地的教育水平,幫助當地人進入更多的工作領域,也是提高當地經濟生活水平的一個努力方向。
畜牧業作為當地的支柱產業,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已不再只是小地區、小范圍、滿足家庭需求的生產。當地人的生活觀念、價值觀已經在悄然發生變化[9],發展專業化、生態化的畜牧業是一個趨勢,如何能夠更好的開展集約化、專業化的畜牧業生產,還需要牧民、政府、社會力量等等多方面的長期合作。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主動的選擇發展生態畜牧業,有利于環境資源系統和生產者、消費者之間的良性循環[10]。如何根據當地的實際條件,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促進當地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是目前需要努力的方向。主要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一、在充分調查當地草場的情況下,建立草原保護制度,利用科學的方法計算出不同季節、不同地區各個草場的合理載畜量,為牧業養殖提供指導意見,超出草地承載量的過度放牧應該被限制;二、采用季節性輪牧的方法,將草地合理劃分成不同的小區,按一定次序采食輪回,既能充分利用轉場淺牧的地方傳統知識,又能避免長距離轉場帶來的牲畜死亡掉膘等問題;三、加強草原生態知識的宣傳教育,促進全民環保觀念的形成,并且掌握具體的保護行為措施;四、促進更大范圍的生態合作,可以將附近農區的農作物秸稈等加工成牦牛飼料,這樣既能解決農區每年存在的秸稈焚燒問題,又能解決牧區冬季補飼的問題。
[1]阿拉坦寶力格.論徘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游牧[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1,38(6):51-58.
[2]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會化問題[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3(4):76-82.
[3]雯.草原沙漠化問題的生態人類學考察——以毛烏蘇沙地北部邊緣的馬什亥嘎查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06.
[4]彭定萍,賀偉光,夏河游牧民定居社區適應性的現狀研究——基于夏河牧區定居新村的實地調查[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58-62.
[5]郎維偉,趙書彬, 藏北牧區定居點向村落變遷初探——以那曲縣達嘎多、宗熱格兩村為例[J],西藏研究,2010,6(12):37-47.
[6]石維斌,鄭茜等.重述游牧神話——“四川藏族牧民定居工程暨帳篷新生活行動”觀察(上、中、下),中國民族,2010,(10).
[7]紅原縣畜牧局,實現現代畜牧業新突破調研報告,2012.
[8]王春英.牧民定居下的現代畜牧業發展現狀調查——以紅原縣為例[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9).
[9]來儀.《從游牧走向定居 從牧場走向市場——四川紅原縣安曲鄉藏族牧民生活方式變革研究》[M]//宋濤等著《傳統裂變與現代超越:西部大開發與西南少數民族生活方式變革問題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263-288.
[10]顏景辰.中國生態畜牧業發展戰略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07.
本文為西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成果,項目編號(12NZYT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