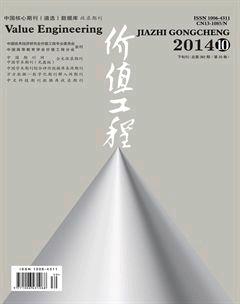揚州評話書場的模式、運營形態及多重關系
肖淑芬XIAO Shu-fen
(揚州大學文學院,揚州 22500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0 引言
揚州評話于2006年進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這也同時昭示它已進入了“被保護者”的行列,所以,對其展開深入的研究已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揚州評話的基本形態是徒口演說故事,只使用醒木和扇子等簡單道具,運用揚州方言進行說表。揚州評話的傳播范圍包括了以揚州、泰州、鎮江為中心的江蘇大部分地區,并傳播至上海等地。
對說書藝術而言,書場是十分重要的。著名評話藝術家王少堂于1956年在上海演出時就因為“臨時書場”的不適,過后說自己說了一場“瞎書”。可見,在評話藝術中,書場并不僅僅是一個經營場所,更是一個說書人與聽書人交流的藝術平臺。這里,主要探討揚州評話書場的模式、經濟運營形態和書場中的各種關系。
1 書場模式
廣義地說,書場即是說書之場所。但說書的場所也是有區別的,歷史上曾出現了露天書場、堂會書場、茶社書場和專業書場,發展到當下又有了社區書場等。
先看露天書場。最原始的說書場所基本上就是在街頭巷尾。明末清初的張岱在《陶庵夢憶》卷四中就曾描繪過揚州當年“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的情景。但這種露天書場每逢天氣惡劣便不能運作。再看堂會書場。所謂“堂會”,就是主人家里的房子。嘉慶時人林蘇門在《邗江三百吟》中說,按揚州習俗,無論大小人家,凡遇喜慶事,必請評話藝人來家里說書。應該說,說書藝術從露天到登堂入室是跨越了一大步。再看茶社書場。茶社書場即是在茶館里設書場,聽眾邊喝茶便聽書。揚州的茶社歷來就頗多。《邗江竹枝詞》中就有“邗江遍處是茶坊”之詠。而且,李斗在《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記載,揚州評話藝術的祖師柳敬亭就經常活動于茶社中了。還有專業書場。專業書場人們又稱之為“清書場”。清書場與茶社書場的區別在于,清書場常年均有藝人演出,并設有固定的書臺;茶社書場則并非天天說書,書臺也不必如專業書場那般正式。發展到今天,揚州書場基本上是專業書場的模式,但又分為不同的情況。條件最好的是大型劇場型的,它可以做任何藝術表演的場所,自然評話也可以在這里演出。次之則是在圖書館、辦公樓里開設的書場,這樣的書場隨時可以開設,也隨時可以撤銷。再次之則是社區書場,因為聽眾越來越老齡化,所以,一些社區在活動室里設了書場。這類書場比較簡陋,可以根據聽眾數量的變化而隨時調整。
2 運營形態
揚州評話經濟上的運營形態,經歷了最初的現場收費、后來的門票制以及當下的義務說講。
露天書場資費少得可憐,堂會書場因家境而異,但資費頗豐。要考證歷史上最具書場代表性的書場經濟形態,“茶社書場”比較典型。茶社可以分為葷茶社、素茶社和書茶社三種。葷茶社即賣茶水,又賣點心菜肴。素茶社又叫“清茶社”,一般只賣茶水。書茶社就是書場的第三種形態——茶社書場。書茶社通常上午賣茶,下午說書。
早年的書場不是收門票,而采用中途收錢的方式。書說到一半便中場休息,這即為收錢時刻,錢放在一個大碗里。休息結束了,這個收錢的大碗就放在藝人旁邊,結束后,說書藝人與茶社分賬。
解放后,書場改用了收門票的經營方式。隨著歷史的發展,門票的價格也發生了變化,從0.2 元到后來的2 元錢一張不等。近幾年來揚州評話已經進入了義務演出的新時期,也就是說取消了門票。
由此可見,揚州評話十分繁榮的時候,它的經營模式是以經濟收入為基本前提的。而隨著揚州評話向“遺產”靠攏,它已經失去了經濟方面的優勢,但當下的人們已經從歷史的高度看到了加強對它的保護的重要性,所以,義務性的傳播已是揚州評話書場的常態。
總之,書場的變化,折射了揚州評話由微至盛、由盛至衰的發展歷程。
3 多種關系
在書場中有多種關系存在,其中,書場經營者與說書人的關系、說書人與聽書人的關系是在揚州評話的發展中相互制約的鏈條關系。
首先來看書場經營者與說書人的關系。說書人每欲講新書,書場老板事先要在各街巷張貼海報,以招攬聽眾。既然為說書人做了宣傳,為說書人提供了場地,有的還提供食宿,那么,與說書人共享書資便是必然的了。有四六分、三七分、二八分,也有按單、雙日分的,這主要看說書人的名望。
這種關系中有雇傭的因素,但又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雇主和雇工的關系。一般意義上的關系,雇工只是打工而已,雇主只剝削他的勞動力;而書場老板與說書人還有另一層利益鏈:說書人自身的威望、能力和資源能給書場帶來更多的收入、更大的利益,所以,與一般的雇工相比,書場老板對說書藝人會更加關照、友好。
在書場中,說書人與聽書人的關系也是揚州評話發展鏈條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說書人的功力如果不夠,聽書人是不買賬的。揚州評話書場中有一個“捧大碗”的習俗。某年,有一位說書先生說的是武將帶兵打仗,其中說到了“馬”,但收場時有一位聽客居然端起了裝錢的大碗并口中大喊:“請先生還我馬頭來”,這是因為說書者沒有交代武將沖鋒時收起寶劍換成長槍的細節,那么,寶劍豈不會把馬頭砍掉嗎?于是,“捧大碗”就成了聽眾制約說書人的手段,是給說書人顏色看。正因為如此,揚州評話藝人對自己說的書是不敢怠慢的。
總之,書場在揚州評話的發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的存在模式、運營形態和其間的各種關系,都與揚州評話藝術的發展息息相關。所以,在傳承揚州評話藝術的過程中,加強書場的建設是十分必要的。
[1][清]李斗著.王軍注.揚州畫舫錄[M].中華書局,2007.
[2]汪景壽,王決,曾惠杰.中國評書藝術論[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3]趙昌智.文化揚州[M].廣陵書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