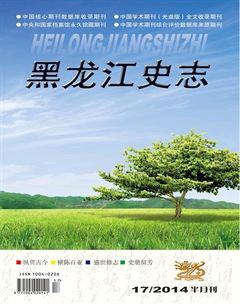淺議地方志編纂與檔案工作的關系
李剛
編修地方志是中國幾千年來優良的文化傳統,自古以來產生的數以千計的地方志書在范圍、體例、方法、內容上雖各不相同,各具特色,但卻有共同的一點,即在資料的選用上,無一例外地利用了大量檔案資料。檔案是歷史的原始記錄,檔案資料是最具權威性的資料。歷代的史官編史修志主要靠的是檔案資料。地方志是綜合記述一地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歷史全面情況的資料性著述,是一個地域的百科全書。地方志書所涉及豐富的內容、詳實的資料、突出的地方特點和時代特色,其資料來源主要是檔案資料。而今續修新方志,其所用資料是指各級各類志書、年鑒及相關地情文獻在編纂和管理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和使用價值的文字、圖表、照片、聲像等各種載體的材料,同樣必須依靠各級檔案部門的全力支持和配合,這些資料是城市“百科全書”的基礎元素,是記錄一個城市發展脈絡的重要符號。因此,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地方志與檔案之間的相互關系,對于推動編修史志和檔案管理工作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檔案史料是編修方志的基礎
方志與檔案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它最早的起源是從古代史官的記述發展而來的,是古代史官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周禮》一書記載,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據有關的注疏來看,所謂“方”是指“四方”;所謂“志”,是記的意思。記述四方之事,就是方志。
歷史上編纂的地方志書,主要是為了“資治”和保存地方文獻。志書的取材比較謹慎,注重史事的考證。而地方志書所依據的資料,多為檔案、私人著述、金石(《李清照》電影中李清照與丈夫趙明誠提到的,終生對金石情有獨鐘。)文物以及社會調查等資料,并較多地錄用了地方官府的檔案和其他原始材料。志書的內容全面詳細,具有一定資料性和可靠性,盡量把志書修成“一方之全史”和“信史”。檔案是人們社會實踐活動的原始記錄,是修志最有價值和最可靠的重要資料。所以歷史上的一些志書,在“凡例”(關于本書體例的說明)中往往規定“以官文書為據”。黃炎培在編修《川沙縣志》時,在例言中曾講:“全書資料,大部分錄自檔案”。
建國后編纂的社會主義新方志,更離不開檔案,方志與檔案的關系更加密切。因為要編纂一部內容翔實、真實可靠的新方志,大都較完好地保存在各級各類檔案館中。所以沒有這些檔案資料作為歷史的依據,編志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有人將二者的關系概括為:檔案是方志的源泉和基礎,方志是檔案的縮影和結晶,二者互為補充,相輔相成。所以,寫好一部質量上乘的志書,如果沒有足夠量的基礎資料,可以說不是很容易的事。就像建設樓房一樣,沒有足夠的沙、石、水泥、鋼筋等基礎材料,要想把大樓蓋得很高、很堅固,是不可想象的。
二、編志工作有力地促進了檔案工作
首先,編志能促進檔案基礎工作的全面提高,編志工作利用檔案范圍廣、數量大、時間長,是對檔案工作的一次大檢查,能發現不少薄弱環節和缺點,大大促進和改善檔案的基礎工作。可促進檔案的收集工作,充實檔案內容,豐富館藏;可促進檔案的整理和鑒定工作,對修志利用工作中發現的部分卷宗區分不合理、分類歸卷不妥當、檔案保存價值劃分不準確等缺點可及時進行調整;可促進檔案的編目和檔案的編研工作,通過“兩編”使檔案管理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其次,編志可以使檔案資料得到全面系統的利用。檔案是志書的“食糧”和基礎,編修方志離不開檔案,一部志書,內容豐富,包括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它的編修完成,是對檔案的一次全面、綜合的利用。再次,修志可以補檔案之不足。方志內容廣泛、豐富。它詳細地記載和反映了社會實踐的各個方面。加上方志主要是以檔案資料為基礎編纂的,其內容基本是可靠的,所以志書是各有關檔案館收集和保管的主要資料。它可以補檔案之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檔案發揮了作用。從志書的編纂體例看,歷史志書的“掌故”(歷史上的人物事跡、制度沿革等)、“文徽”部分,近似現在的檔案資料匯編,其目的是為了保存史料和證實史實的。現在志書的“附錄”部分,繼承了歷史志書的體例(規則),主要是選錄檔案文獻,以保存重要的檔案史料,流傳后世。迄今我國保存下來的相當數量的地方檔案史料,就是以志書的形式流傳下來的。
從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檔案學與方志學的研究對象——檔案與方志、檔案工作與編志工作之間的關系歷來就非常密切。因此,兩學科之間應互相學習,共同發展。方志學的創始人章學誠(清朝的歷史評論家)從檔案史料與修志的密切關系考慮,注重平日檔案材料的收集和保存以解決修志中遇到的材料困難,提出在州、縣六科之外增設志科的主張。盡管受當時的歷史條件的限制未能實現,但其遠見卓識很值得檔案學研究和學習。又如方志學在突出地方特色、資料收集、整理和考證等方面的理論、原則和方法,可資檔案學學習,而檔案學在檔案整理、價值鑒定、檔案檢索、編研及提供利用等方面的理論、原則和方法,也可供方志學借鑒,兩者相互滲透,取長補短,以求共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