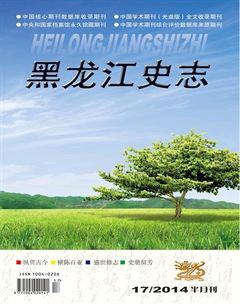別廷芳與宛西地方自治
[摘 要]20世紀30年代的近代中國,軍閥混戰、外族入侵。宛西地區靠軍事起家的別廷芳為了達到“自救”的目的,在其轄區推行“自衛”、“自治”、“自富”的地方自治,成果斐然。但隨著別氏的逝世,轟動一時的宛西自治也隨之夭折。
[關鍵詞]別廷芳;自衛;自治;自富
近代以還,抗戰軍興。中原大地土匪蜂起、禍害桑梓;軍閥割據,無意剿匪;捐稅沉重,民不聊生;經濟脆弱,無以自存。“民元至民十年間前后,桿匪不下百數十起,燒殺奸擄到處皆然,山寨被破者十之八九,人民流離,十室九空。”[1]當如此之世,宛西三縣卻相對如一方凈土,成為吸納安置外來避難人員的“世外桃源,自治天堂”[2],新唐大捷更是讓宛西聲名鵲起,暇邇共聞。論及這一切,不能不提到一個人,那就是別廷芳。
一、別廷芳的崛起與地方自治的肇始
別廷芳出生于1883年,逝世于1940年。[3]他有生的58年期間,正是五千年中華文明古國處于政治腐敗、列強入侵、軍閥混戰、國無寧日的階段,也是人民民主革命高漲、激烈變化的階段。地處河南省西南部的西峽縣,位于豫、陜、鄂三省交匯處,政府管控難及。別廷芳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以13支步槍起家,先后剿滅周邊匪首山寨,最終東達桐泌,西至商洛,南抵均光,北連嵩盧[4]。
1927年別廷芳于西峽口馬王廟組成民團司令部,利用軍閥混戰、“官治”無望之機,推行地方自治。關于宛西地方自治,彭錫田曾經有很精辟的縮小了的“三民主義”,被認為是宛西地方自治的理論基礎。[5]彭錫田認為宛西地區所患者,不是異族的侵略,而是土匪、匪式軍隊、貪官污吏三種壓迫。對這三種壓迫希望政府來解救,是不可能的。非“自衛”不可,把“自衛”辦好,才能“自救”。所以,“自衛主義”就是宛西的“民族主義”;在現今的中國,自治這種事,萬無官民合作之理,要想進行自治,就得推倒官治,豪劣才沒有護符,進行自治才沒有障礙。所以說“自治主義”就是縮小了的“民權主義”;同樣,農業不自己去改良,沒有人替我們改良;水利不自己去興,沒有人替我們去興;森林不自己去造,沒有人替我們去造。[6]生產有辦法,分配有方法,才能“自富”,就是宛西的“民生主義”。所以說“自富主義”就是縮小了的“民生主義”。
二、宛西自治的具體舉措
別廷芳根據彭錫田的“三自主義”,結合宛西的實際,明確認定:治安是一切先決的問題,治理地方,推行自治,必須先由自衛入手。他的辦法有五:(一)組建民團。堅持地方民團“人不離槍,槍不離鄉,寓常備兵于工,予備兵于農,人人皆兵,保衛地方,不受官家節制”的原則。組建正規民團,培訓帶兵干部。再依靠這些干部,在全縣建團。(二)編查保甲。十戶為一甲,設甲長;十甲為一保,設保長;數保或十保為一聯保,設聯保主任。保、甲互相監督,發生事故一律連坐。(三)推行“五證”。“出門證”、“通行證”、“遷移證”、“乞丐證”、“小販營業證”。編查保甲,是嚴密內部組織,對內發生作用;而推行“五證”,是糾察來往行人,對外發生效用,相輔相成。(四)修道路,架電線。據統計,在別氏統治期間,公路和主要的牛車路共有57條,行程長達一千多公里。縣境電線線路達991公里,裝機200余部。
自治主要是調整地畝,清理田賦,整理契稅,在不觸及所有制的情況下,實行平均負擔,建立牢固的地方財政體系。(一)調查地畝,清理田賦。通令全縣丈量地畝,以稞石制代替明清以來的銀兩制。以此減輕一般民眾負擔,從而增加縣財政收入。(二)整理契稅。設立契稅管理局,規定契約格式、稅款。由區發給蓋有縣府紅印的正規文約作為憑證。(三)控制金融,印發紙幣。通過大量印制紙幣,投放市場,以掌握地方經濟力量。(四)建立息訟組織。通令各區鄉成立“調解委員會”(又名息訟委員會),以達到村村無訟的目的。(五)治法與治人。別氏認為“有治法還需有治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治人之條件,實重于治法。”其地方自治所以小有成效,是與他嚴格選拔、培養地方干部有很大關系。
自富的辦法有八:(一)治窮先治愚,興辦學校,開發民智。至1940年別氏逝世止,全縣中小學達300所,在校學生3萬余名。(二)實行五禁。禁鴉片、禁賭博、禁紙煙、禁洋貨、禁洋靛。五禁的大力推行,不僅節制了財源外流,還促進了地方工農業發展。(三)發展生產,興辦實業。其開辦的實業,涉及兵工、紡織、水電、印染、農械等領域,年創產值數千萬元。其中,1936年創辦的西峽口蓮花寺崗水力發電廠,是河南省第一家水力發電廠。(四)植樹造林,保持水土。別氏親請留日學生農林專家陳鳳梧、陳鳳桐兄弟指導農業生產。各區鄉聯保均設專職的護林員、質檢員。經常巡視該管地段,嚴禁砍伐損傷。(五)治河改道,擴大耕地。治河是理順河道,以暢其流。先在關鍵處修石壩,迫使洪水改道歸漕。壩外載三、四重“雁翅柳林”以護堤壩。改地是在壩堤,雁翅柳圍護的河灘上,壘成一塊塊方方正正的田,然后開渠筑堰,引山洪灌田。(六)改良農業,提高產量。創辦示范農場,引進浙江“雄町”、“浙大三號”兩個優良品種,還引進絨長潔白的“十字棉”,高壯有力的南陽黃牛與水牛等。(七)辦信用社,設借貸所。成立信用合作社、農民借貸所,籌集資金幫助農民購買農具、肥料、種子。(八)辦醫院,出醫書。先后籌辦民團醫院、內鄉中醫學校。同時還主持編輯了兩本醫書《醫方遺存》和《青囊秘訣》。[7]
三、宛西自治成效淺析
別廷芳推行地方自治歷時十年。雖然與他所定的目標“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村村無訟”相距甚遠。但在那個戰亂不息、苦難重重的時期,宛西一帶治安穩定,生產發展,教育普及。較之國民黨統治的河南其他縣,水、旱、蝗、湯(擾民害民的湯恩伯軍隊[8])災害頻繁,人民流離失所,真不啻天壤之別。
別氏實施地方自治的成就,加上他后來統領的宛西、宛東十數萬民團武裝的力量,使他受到國民黨政府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的側目而視。1937年春,河南省府組織各界20人的參觀團到廣西參觀地方自治。李宗仁在接見參觀團時,大力頌贊宛西自治,說:“廣西是從宛西學來的,你們何必舍近而求遠?[9]1938年9月,蔣介石委任別廷芳為河南省第六區(南陽)抗敵自衛軍少將司令,頒發陸海空軍一級勛章。[10]1939年5月,日本侵華部隊調集其主力第13、16兩師團和騎兵團,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防守陣地。15日,別廷芳調集所屬民團配合第二集團軍進行全線總反攻,連克新野、唐河,史稱“新唐大捷”。1959年,閻錫山在其為韓亮《宛西御倭鴻憶錄》一書所作的序言中說:“如別、彭這樣的人,沒有當國家的權,真是何等的不幸!”[11]
別廷芳的地方自治也引起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關注。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曾對豫西南地委書記郭以青說:“別廷芳這個人很聰明,他抗日,他不會輕易上蔣介石的當……為防止局勢惡化,建議南陽的同志做好別廷芳的統戰工作。”1938年5月,周恩來對河南統戰委員會主任彭雪楓說:“宛西各縣有數十萬英勇強悍的民眾武裝,這是我們建立根據地,進行游擊戰爭的先決條件。河南省委要迅速向豫西發展。”
但是,由于宛西自治派從根本上代表的是地主階級的利益,維護的是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因此,在別廷芳去世后,宛西“三自主義”也日漸被廢棄。1941年,宛西自治四縣之一的鄧縣在實施土地呈報時,田管處副處長賀耀堂及其雇員,向業主敲詐勒索,貪污分肥。宛西地區貪污腐敗之風有增無減、百姓又回到水深火熱的窮困生活中,自治自此失敗。
雖則宛西自治固多可議之處,然而民國的國家機器尚不足以保障農村民眾基本的社會秩序,即便是有自治、保甲等地方行政的變革,而其結果,無外乎是地方精英侵奪國家權力,宰割農村社會。梁漱溟在1929年即已指出,以當時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情況,勉強實行所謂地方自治,不特增加農民負擔,抑且必將助長“土豪劣紳”的威勢。[12]是以別氏以一己之術,難有回天之力;自治能解一時之困,卻難救一世之貧。
參考文獻:
[1]別廷芳,《地方自治大綱》[Z],南陽市檔案局,編號18
[2]萬新芳,《宛西自治“三自主義”“理論群體”初探》[J],《史學月刊》,2002(10)
[3][5][9][10]陳照運、孫海震、黃天錫編著,《別廷芳地方自治紀實》[Z],西峽縣人民政府內部資料,1999
[4]趙有章,《抗戰時期河南淪陷區學校播遷宛西的原因及作用》[J],《南都月刊》,1996(1)
[6]牛崚歧,《民眾讀本》[Z],內鄉縣建設委員會,1936
[7]別丙坤,《有關祖父別廷芳的回憶》[M],《河南文史資料》1990(1)
[8]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11]楊儀山,《河南省自治史略》[M],河南省自治協會,1937
[12]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M],臺北學術出版社影印本
作者簡介:張冉(1986-),男,河南西峽,四川師范大學四川省高校干部(師資)培訓中心,助教,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