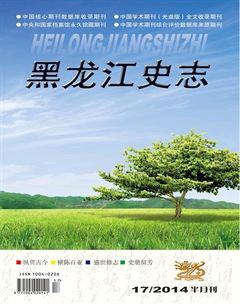論《詩經》中的野合之詩
[摘 要]《詩經》中有許多表現男女情愛的詩篇,其中不乏直接表現性愛的作品,更有許多為儒家所不能接受的野合之詩。脫離《詩經》產生的時代,認為其悖于倫理實則是對《詩經》的曲解。因為在原始宗教背景下,性愛是神圣的,也是一種神秘的力量,充滿生命力的原始性愛是在私有制產生之后才逐漸被賦予了額外的道德意義。
[關鍵詞]《詩經》;野合;原始宗教
一、《詩經》中的野合之詩
《詩經》作為儒家經典之一,在很多朝代都是統治者實行“詩教”的政治教材,其秉承了“溫柔敦厚”的詩風,得到了“思無邪”的高度評價。而實際上,作為《詩經》的精華,有大量吟詠男女之情的篇章,《詩經》的開篇之作《關雎》便展現了一個青年男子鐘情于“窈窕淑女”卻又“求之不得”的彷徨的內心,其表面上尚能彰顯“樂而不淫”的特點。但《詩經》中也從不缺乏大膽之作,如《鄭風·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于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于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此詩描寫的是春季來臨時,在河岸上舉行村社慶典的情形。青年男女在河岸上相互求愛,競相追逐,然后進行性交。[1](P26)他們嬉戲游玩,互贈芍藥以結情愛,“芍藥”一詞也成為后世色情文學中女性生殖器的代稱。《鄭風·野有蔓草》也同樣講述了男女二人在野外歡會時的情景: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歐陽修在《詩本義》中評價曰:“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于田野間。”[2](P126)《詩經》中涉及到“野合”之事的不在少數。又如,《召南·野有死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詩中的青年男女在野外一見鐘情,歡愛之事便順理成章,女子還嬌滴滴的嗔怪:“慢一點,不要動我的圍裙,不要惹得狗兒汪汪叫。”一副自由和諧的野合之圖躍然紙上。此外,《鄘風·桑中》中也有詩句云: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這里講的同樣是男女野外的桑林之會。
這些詩歌在歷代的解讀和注解中都被認為是成為發乎情止乎禮的贊歌,顯然是正統思想對其的改造。因為藝術是對現實的再現,風詩中對禮義廉恥的強調,明顯是后世的附會,詩歌的原貌比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原始的多。聞一多在《詩經的性欲觀》、《說魚》等作品中,已解讀了其中充斥著的性因素,揭示了國風中男女情愛詩篇的原始風貌,讓我們真實的感受到了原始文學的赤裸。上述表現野合的詩歌,作為《詩經》情欲文學的一部分,其實只是對原始生活的一個真實的反映與再現。
二、原始宗教背景
產生《詩經》的原始社會是我們解讀它的重要依據,其原始宗教背景更是我們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原始初民在恐懼與敬畏中渴望解釋自己所處的世界,大自然的變化莫測讓他們畏懼并崇拜。他們首先注意到了自然萬物的繁衍與自身種族的生育之間的相似性,性崇拜由此產生并成為原始宗教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
先民們無法解釋他們在性交中體會到的高度快感,從而將這種絕無僅有的快樂視為一種魔力,認為這是神靈對他們的恩賜,因而性行為是神圣的。在當時巫風盛行的社會風氣下,人們相信人與神之間是可以相互溝通的,溝通的途徑便是性交,獲得性快感的時候便是與神相通的時候,所以原始宗教文化與性文化是相通的。對神的敬畏后來逐漸具體化發展成為祖先崇拜,先民們認為人的靈魂是不死的,死去的祖先會化為神靈保佑他的子孫后代。為祈求祖先的保佑,人們要舉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動。《墨子·明鬼篇》曰:“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這里所說的祖、社稷、桑林、云夢便是各國祭祀祖先的地方。祭祀活動有相應的儀式,理安·艾斯勒認為,史前重要的宗教典禮上很可能有色情儀式。理由有三:其一,性與春季萬物再生在舊石器時代的宗教形象中非常突出,而宗教符號和神話通過宗教儀式來表達;其二,學者們稱為圣婚的色情儀式是稍后新時期時代和青銅時代宗教藝術的主題,甚至在更晚的神秘傳統中還有殘余;其三,歐洲許多著名的民間節日中也有這種傳統的遺跡。[3](P66)祭祀活動中有性交儀式,這在楚國的祭祀中最為明顯。楚國信巫鬼,重淫祀,較之北方諸國的祖先崇拜,“其信仰和祭祀的是一種較為原始的,有關自然山川、天空星群、生存萬物的人格化的自然神,超出了社會親族死老病死,祖祖輩輩的魂靈祖先的崇族性概念”[4],其對象更加廣泛。泛神論的原始思維方式以及淫祀的儀式,將人與神擺在了較為平等的地位上,從而使人與神的溝通成為可能。溝通人與鬼神關系的媒介為“巫”,其職責便為降神通靈,手段是“以性娛神”,即充分展示自己的性別魅力以迎接神靈的到來。與神靈的溝通必須陰陽相對,即“以陰巫下陽神,以陽巫接陰鬼”(朱熹語)。所以“性和性的感召力是降神巫術的前提條件”[4]。由此可知《離騷》、《九歌》等楚辭作品中所浸潤著的人神相戀色彩,實際上是楚地巫風文化中性祭祀的反映,是原始宗教的產物,而這也是《詩經》產生的背景。
性交因為與原始宗教相通而具有神圣性,而隨著性交和生殖的因果關系認識的加深,人們逐漸發現性交能夠創造生命。農業社會中的先民便很自然的將人類的生子與植物的結果聯系到一起,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的交感巫術理論進一步為我們做出了解釋:
我們未開化的祖先把植物的能力擬人化為男性、女性,并且按照順勢的或模擬的巫術原則,企圖通過以五朔之王和王后以及降靈節新娘新郎等等人身表現的樹木精靈的婚嫁來促使樹木花草的生長……如果沒有人的兩性的真正結合,樹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長繁殖的……世界其他地區還有未開化的種族仍然有意識地采用兩性交媾的手段來確保大地豐收。[5](P129)
弗雷澤的巫術交感理論說明了原始宗教信仰中,兩性的交媾對植物生長的作用。在原始思維中,人們無法區分自我與自然,他們認為人與自然是一致的,放縱自己的情欲有利于動植物的繁殖。所以,在春天播種或植物生長的時候,在田地中性交能夠促進植物生長。同樣從“天人感應”的原始思維出發得到的另一個結論是:性交可以治雨。因為男女性交即為陰陽交合,象征著天地交合,天地交合的表現為下雨。所以原始社會中的祈雨儀式也往往伴隨著性交活動。
在原始社會中,性交是快樂,是生命,是溝通神靈,達成愿望的手段,具有著神秘的力量,所以它是神圣的,先民們沐浴在它的光輝中。
三、文化闡釋
春秋戰國時期,廣大的北方中原地區,理性主義已經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原始宗教在濃厚的理性因素之中慢慢溶解,被逐漸限定在祖先崇拜的一系列要求嚴格的禮節規范中,實體的性祭祀行為也逐漸消失,性行為的宗教意義消失了,成為了一個遙遠的民族記憶符號,宋玉《高唐賦》中的高唐神女便是遠古原始宗教的產物。但是催生原始宗教的原始思維卻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為我們打開了一個解讀《詩經》的窗口。
在古代農業社會中,農作物生長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社會和人們的生活的穩定與否。因而在春天來臨之前都會舉行相應的慶祝活動祭祀土地,以祈求豐收。舉行慶祝活動的地方叫做“社”,《禮記·郊特牲》:“冬至祭天曰郊,夏至祭地曰社。”人們會在社中舉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動,上古時期的原始宗教認為性交能夠促進植物的生長,所以社地的祭祀總是與性愛聯系在一起。集會之社地,便是男女自由發生性行為之處。《左傳》中所載的魯莊公如齊觀社,觀的其實是男女性交,正因為如此才會遭到曹劌的反對,認為是失禮之事。又舉行祭祀的社地多種植樹木,社中之木多為桑,所以“桑林”、“桑中”、“桑社”等地便是人們野合之處,這些地方后來與情愛密切相關,成為青年男女的約會之地。
其實,祭春之時青年男女可以自由結合,這是遠古遺留下來的習俗。更早的時候,這種野合甚至是平民的主要婚姻形式:
當春天來臨,農家都從冬季住所遷至田野,村社組織春節慶祝。屆時少男少女乃一起跳舞、輪唱、踏歌。所有這些歌幾乎千篇一律都與生殖崇拜有關,并常常帶有不加掩飾的色情性質。每個青年男子都挑選姑娘,向她們求愛,并與她們交媾。以此作結的男歡女愛持續于整個夏季和秋季,并且在這些家庭搬回冬季住地之前,被人們(也許是村中長者)以某種手段使之合法化。合法的標準恐怕是看姑娘是否懷孕。[1](P26)
至《詩經》產生的時代,自由結合或許已經不再是平民成婚的主要手段,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時期仍可“短時期內重新恢復舊時的自由的性交關系”[6](P45)。
《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即在春天的這個時候,人們對于性行為是不加以限制的,統治者甚至明文要求人民必須這樣做。統治者之所以這樣規定,是為了繁衍人口,壯大國家力量。而從“天人感應”的原始思維角度來講,春天在桑林中性交是與春天在田地里播種一樣自然合理的。所以,桑林歡會是一種廣為人們接受且由來已久的習俗,桑林由此成為情愛之地,《詩經》中除了直接表現野合的詩篇與桑林相關之外,還有許多作品涉及情愛與桑林。如《小雅·隰桑》在桑園中表達相思之情,《小雅·白華》、《魏風·十畝之間》中也都含蓄的涉及到了桑園與情愛。又傳說商朝的大臣伊尹誕生于空桑,《史記·孔子世家》也記載孔子生于空桑之地。即他們都是當時桑社之中自由結合的產物。此外,據《呂氏春秋》、《尚書》等的記載,天下大旱,湯曾“禱于桑林之社”,可見桑林原是個神圣的地方。所以在當時而言,桑林野合是正常合理的,它是一種婚姻形式,也是一種生育手段,其本身不帶有后世所看待并賦予的道德因素。
性的不自由是伴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的,私有制產生了階級壓迫,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6](P61)。
古代遺留下來的兩性間的關系,愈是隨著經濟生活條件的發展,從而隨著古代共產制的解體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樸素的原始的性質,就愈使婦女感到屈辱和難堪;婦女也就愈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貞操、暫時的或長久地只能同一個男子結婚的權利作為解決辦法。[6](P48)
私有制的產生完成了婚姻制度由雜婚制向個體婚制的過渡。而與私有制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產生了有利于其發展鞏固的上層建筑。原始性愛的自由被新建立起來的婚姻道德所取代,久而久之,自然狀態下神圣的歡愛成為了淫亂和放蕩的代表,表現原始性愛的野合之詩也成為了后人所不齒的淫奔之詩。
綜上所述,《詩經》中表現野合的詩歌,真實的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現實,而要理解這些現實,體會詩歌的本意必須從當時原始宗教、原始思維的歷史背景出發。性愛是神圣的,又是自然的,先民們所表現的性愛并不是倫理綱常所強調的性愛,它們要更加神圣,更能表現歡喜和感激,更加充滿愛與快樂。
參考文獻:
[1]高羅佩.中國古代房內考[M].李零,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向熹.詩經譯注[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3]理安艾斯勒.神圣的歡愛[M].黃覺、黃棣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4]梅瓊林.《離騷》與巫風性文化[J],社會科學,1994,(05).
[5]弗雷澤.金枝[M].徐育新等,譯.北京: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M]//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簡介:徐勝男(1989-),女,山東濰坊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唐文學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