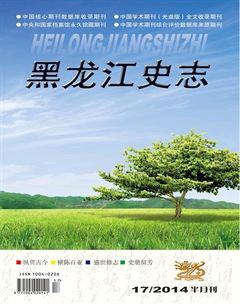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通訊站研究
[摘 要]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通訊站是人民郵政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本文在搜集大量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對邊區通訊站的組織機構、郵路設置、業務狀況以及通訊站工作的改進情況做了詳細的考察,也對邊區通訊站和中華郵政在抗戰中的各個時期的關系進行了動態的梳理。邊區通訊站保障了戰時邊區通信的暢通,也為后來的郵政事業的發展積累了經驗。
[關鍵詞]抗日戰爭;陜甘寧邊區;通訊站
陜甘寧邊區通訊站建立前,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已經有了發達的郵政系統。1935年1月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西北郵政管理局。1936年7月,西北郵政管理局改稱中華蘇維埃西北郵政總局。1937年3月,陜甘寧特區成立后,中華蘇維埃西北郵政總局改為陜甘寧特區郵政管理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設立了陜甘寧邊區郵政管理局。當時,中華郵政(國民政府的郵政系統)陜西郵政管理局在邊區共設有11處郵局,延安設膚施郵局。因而,邊區內有邊區郵政和中華郵政兩套機構。
根據國共達成的協議,邊區不建立銀行和郵政系統,也不發行郵票。中華郵政陜西郵政管理局一再催促膚施郵局要求取消邊區郵政系統,還派視察員何載陽到延安交涉。1938年3月22日,邊區郵政局停止營業。這樣,中華郵政獨攬邊區郵政業務。“由于一般的邊區公文交給中華傳遞,有人便故意把文件發錯,如把寄給陜西省志丹縣的信給發到了西安,把定邊縣政府的信寄到甘肅;還有些機關收到的信件只剩下空信皮,內容已被竊走。”[1]雖然邊區黨政重要文件由邊區黨委傳送,但邊區的工作還是收到很大的影響。1938年5月,邊區政府決定重新建立邊區郵政系統,但考慮到統一戰線的因素,沒有使用“郵政”二字,而改為陜甘寧邊區政府通訊站。
一、陜甘寧邊區通訊站的組織結構和郵路設置
1938年5月30日,陜甘寧邊區通訊站正式成立。通訊站“收遞邊區范圍內,或附近邊區八路軍駐扎地各黨政軍民一切信函、文件、書報、刊物等事宜而設立之。”[2]1938年8月10日,邊區政府民政廳頒布了《陜甘寧邊區通訊站暫行章程》,共7章,61條。內容涉及通訊站的設置目的、組織系統、通訊站與邊區各級政府及其他交通機關的關系、郵寄函件規則、通訊紀律等。
陜甘寧邊區通訊站由邊區政府民政廳管轄,共由總站、分站、縣站和聯絡站四級組成。總站設在延安,設站長一人。“總站最初設收發科和總務科,后增設計核科。1941年,又擴大為郵務科、人事科、會計科和秘書室、視察室。1942年取消兩室。1943年簡政后,總站只設收發科和總務科。”[3]站長依次為井憲章、張玉珍、劉篤義和劉義維。在總站領導下設若干分站,各縣設縣站,在必要的區鄉、市鎮要道設立聯絡站。“邊區各地方政府,應負責監督各地通訊站之工作,并負責解決各地通訊站之困難。”[4]邊區通訊站四級組織機構及人員配置,有利于郵寄分段轉運和快速準確送達,同時也確保機構人員不至過多,節約工作經費。
邊區通訊站成立初期,設立了5個分站(延安、關中、三邊、綏德慶環),14個縣站(店房攤、甘泉、富縣、店頭、甘谷驛、延長、延川、神府、安定、靖邊、鹽池、志丹、華池、慶陽),各設站長一人;聯絡站七處(安塞、固林、蟠龍、清澗、新寧、赤水、淳耀),各聯絡站的代辦員和通訊員都是由不脫離生產的人員組成,不設專人,是代辦性質,通訊站只解決通訊工人食宿問題。“1940年,總站搬到延安后,還有分站4處,縣站最多發展到24處,聯絡站發展到16處。”[5]
邊區通訊站郵路是以延安為中心,北至神府,南達淳耀,西通慶陽,后來和晉西北也通了郵。建站初期,“形成了以延安為中心的4條干線:延安——綏德,延安——安定,延安——關中,延安——慶陽;支線14條:綏德——吳堡、曲子——馬渠、延安——安定、慶陽——華池、綏德——神府、合水——新寧、真武洞——靖邊、慶陽——鎮原、安定——鹽池、關中——淳耀、靖邊——橫山、延安——西川口、慶陽——環縣、甘谷驛——臨鎮。”[6]干線是逐日班,支線為間日班。1942年,又開辦了晝夜兼程快班。1943年,延安綏德線又改為逐日雙人班。到通訊站后期,干線郵路發展到8條,郵路總長5080公里,形成了以延安為中心,至各專署、縣府的郵政通訊網。這個通訊網基本上把邊區的政治中心延安與各縣、主要口岸連接起來,保障了戰時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重要方針政策快速送達邊區各個地方,同時也有利于邊區各地的信息快速送達中樞延安。
二、陜甘寧邊區通訊站與中華郵政的關系
1938年邊區通訊站建立后,邊區人民并沒有中斷和邊區外的郵務聯系。《陜甘寧邊區通訊站暫行章程》中明確規定了通訊站與中華郵政的關系。邊區寄往國統區的郵件由中華郵政代辦,凡寄往外埠的信件,寄件人按中華郵政章程貼足郵票,由通訊站負責代送到附近郵局;外地寄往邊區的信件通訊站代為傳遞。邊區通訊站不代售中華郵政的郵票,郵票是由寄件人自備的。這樣既方便了邊區政府各機關和人民群眾與國統區的通訊,也保證了邊區郵政系統的獨立自主。
雖然邊區政府采取措施保障邊區和國統區的郵政聯系,但國民黨對邊區實行政治、經濟、軍事封鎖,使邊區和國統區的郵政工作遇到極大的困難,同時中華郵政和軍郵也受到很大的影響。1940年5月9日,周恩來接見了負責陜、甘、寧、晉等省軍郵事務的第三軍郵總視察段總視察林卓午。周恩來提出希望溝通國共兩區的郵政往來,使民間自由通信。周恩來親筆為林卓午題詞“傳郵萬里,國脈所系”。1941年12月,林卓午再次赴延安和中共商談正常通郵的事宜。雙方經過協商,就通郵中途軍政對郵政的檢查,設立軍郵聯絡電臺,邊區中華郵政在業務中法幣和邊區邊幣的比率和兌換辦法等問題達成協議。該協議于1942年1月14日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的名義簽發,即《關于郵務問題通令》。1942年3月20日,邊區政府轉發了此通令,認為“該通令內容頗適于邊區,且對于邊區境內郵政與金融兌換都有幫助,故決予以采納施行,現特明令公布,務希各級政府各軍警機關與人民團體切實遵守為要。”[7]通郵協義公布后,陜甘寧邊區和國統區的通郵狀況有了很大發展。以延安郵局為例,1942年1月“外來郵件包裹頗多,以信件言:掛號信比去年同月多十余倍;平信、包裹亦多至十倍。匯兌數額月達四五萬元,向外匯者亦較前增多。”[8]
1942月1月,國民黨軍郵延安辦事處成立,又企圖取消邊區通訊站。1943年,陜西郵政管理局派視察員何載陽兩次到延安,以便利軍民通信,節省開支,符合統一戰線,維護國家法統等理由,提出中華郵政與通訊站合并的談判。邊區政府針鋒相對,提出五項合并條件,主要是:承認通訊站一切員工為中華郵政合格人員,并由通訊站負責其調動;通訊站員工與中華郵政員工待遇相同;通訊站負責邊區境內的通信為內地局,中華郵政郵局負責對邊區外通信為外地局,不得管內地局的事務;包裹物品統一稅收,每月向邊區稅局結賬。中華郵政拒絕以上條件,但采取種種手段以擠垮通訊站。通訊站采取措施壓縮中華郵政的業務。例如凡邊區內的一切郵件,由通訊站收寄;國統區寄往邊區的郵件一律交由通訊站轉送。1944年,在延安由通訊站設立三個代辦所,專門替中華郵政轉邊區各機關寄往外地的郵件,使中華郵政同邊區各機關斷絕了直接往來,通訊站業務日益上升,同時也加強了邊區的保密工作。
三、陜甘寧邊區通訊站簡政和工作的不斷改進
通訊站建立后,業務量不斷增加。1941年后,國民黨加緊對邊區封鎖,日寇也頻繁對邊區掃蕩,邊區遇到了嚴重困難。通訊站在黨的領導和部署下,進行三次簡政,開展生產自給運動。
1941年,通訊站第一次簡政。當時通訊站部分領導強調“正規化”,想把通訊站辦成和中華郵政一樣的機構,成立郵政管理局,設立各個等級的郵局和代辦所,設置軍郵局,并且郵件收取資費,也開辦包裹、匯兌業務,通訊員由文化程度較高人員擔任等改革意見。由于這些意見和邊區的實際情況不相符,總站機構和工作人員反而擴大。這次簡政后,通訊站的工作有一些改進,但機構龐大,工作效率并沒有顯著提高。
1942年8月,通訊站進行第二次簡政。為了改進通訊站的工作,邊區民政廳廳務會議專門進行討論。劉維義站長提出六點改進辦法:“一、改善組織領導及與各地政府當局的關系;二、提高工作人員質量;三、增加通訊工人,延綏、延慶、延關加開雙班,并增設支線若干條;四、提高工作人員及通訊工人之待遇,實行薪津制;五、統一邊區通訊管理工作;六、建立本市通訊聯絡。”[9]同年9月,民政廳又邀請延安通訊交通機關舉行聯席會議,并確定9月22日成立“邊區通訊工作研究委員會”,“以劉篤義、霍克(邊區通訊總站)……張良(邊區新華書店)等七名同志為委員,并以劉篤義為召集人,專事邊區通訊工作改革問題,以便制成方案,提交政府。”[10]第二次簡政后,總站機構只剩3個科,各縣站改為不設專人的代辦所,開辦延安至慶陽的日夜快班,整頓延安至關中馬欄郵路等。
邊區通訊站于1943年4月進行第三次精簡整頓。這次簡政針對實際情況,提出改革方案,批評主觀主義、自由主義、鬧獨立性和不切實際的“正規化”等錯誤思想。改革方針著重是精簡上層,加強基層,實現領導一元化。
通訊站經過三次簡政和改進工作后,不僅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且還降低了費用,節約了一筆巨款。在簡政之前,通訊站收發信件書報經常發生錯誤和積壓的現象。簡政以后“不僅積壓與錯發等毛病基本清除,而且投遞書信由(1943年)1月至4月平均每天16661件,驟增到9月至11月平均每天30078件,投遞速度也大增,延綏只需五天,延慶線只需八天,而且取消了夜班制,運輸費也取消了。”[11]錯發郵件數量也大量減少,據統計“過去每月總要錯發數十件,今年(1944年)1月至10月總共錯發十余件;去年(1943年)7月一個月總誤工二百二十七天,今年(1944年)十個月誤工六百九十三天,平均每月不到七十天。從去年四月到今年,總計運輸、燈油、印刷等項節約即折合小米一百一十余石。”[12]
四、陜甘寧邊區通訊站業務量
邊區通訊站建立后,業務發展很快。郵件種類主要有平信、文件、書報、掛號、快信等。匯兌、包裹、物品不在收寄的業務范圍內,所有的郵件都不收費。“通訊站初成立時,信件、報刊不多,只跑白班。郵件少的路線,用包袱捆好背上就可以了。郵件多的線路,或有零星包裹時,就用扁擔挑。”[13]據統計,從1938年5月通訊站建立到1939年3月全站每月收遞及轉口信件的總數為1139件,1939年3月則增加到33459件,增加了295%。郵件數量的增加,極大地降低了投遞成本,1938年平均每個信件成本為1角,1939年3月時降到了4分3厘。根據1939年12月31日邊區民政廳制的《1939年收發就地信件統計表》可知:1939年共收發平信193000件,掛號信19817件,書包1837件,掛號書535件,掛號文件490件。1941年郵件劇增,1月至8月“共寄平信183469封,文件90207件,書6105件,掛號信13777件,掛號文件4353件,掛號書482件;轉口平信277040封,文件99275件,書11743件,掛號信20308封,掛號文件1594件,掛號書712件。除轉口信件外,平均每月寄遞37466件,每天寄遞1248件。”[14]“1941年度全邊區各站收遞郵件計:掛號書籍864件,掛號文件6041件,掛號信25235件,平件126614件,平寄書籍6490件,平信372418件。共計郵件538635件,轉口郵件尚不在內。”[15]
1938到1941年“三年中共送出平信557703件,文件178820卷,書報10925包。掛號信件46297封,文件4950卷,書報1275包,合計共約800000件,共用經費71000元,平均不足9分錢一件。”[16]邊區通訊站業務中占第一位的是平信,政府文件占第二位。
郵件數量的不斷增加表明通訊站工作走上成熟的工作軌道,其工作得到了邊區機關和人民群眾的認可。通訊站在工作中不斷總結經驗,形成了一套通信收發制度,使用寄單、掛單、排單、書單、投遞等,郵件數量也不斷增加,郵遞的速度和質量不斷提高。
從1938年5月邊區通訊站正式成立到1946年3月通訊站改為邊區郵政管理局的七年多的時間里,通訊站的郵政網絡極大地便利了邊區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息傳遞,有利于抗戰時黨的政策向基層傳播,也方便了群眾的生產和生活。1942年8月7日《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加強通訊交通》的社論,指出通訊站的工作“對邊區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幫助,它是革命事業中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在戰時更有其重要性。”邊區通訊站的建立和發展離不開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領導人對郵政通訊事業的重視和支持。邊區廣大的郵政人員在“沒有馬,沒有車,憑著兩條腿,兩只手和肩,擔負起邊區通訊工作”[17],當時除了總站一輛自行車,曲子二輛自行車外,郵政人員均為步行,每個通訊員每天要走七十到九十里路。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郵政通訊人員保持著踏實的工作作風,圓滿完成各項通訊任務。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通訊站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郵政通訊事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促進了人民郵政事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鄭游.中國的郵政和郵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14.
[2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三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816.
[3]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編.中國解放區郵票史·西北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0.
[4]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三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819.
[5]陜西省志郵電志編委會.陜西省志·郵電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436.
[6]黃正林.陜甘寧邊區社會經濟(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51.
[7]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陜甘寧政府文件選編(第五輯)[M].檔案出版社,1988:337.
[8]袁武振.論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郵政事業的發展及其經驗[J].西安郵電學院學報,1998,3(4):66.
[9]改進通訊站工作民政廳務會議商討具體辦法[N].解放日報,1942-8-19.
[10]加強通訊交通有關機關進行研究[N].解放日報,1942-9-16.
[11]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三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832.
[12]邊區通訊總站召開分站站長聯席會[N].解放日報,1944-12-9.
[13]郵電部郵電史編輯室.難忘的戰斗歲月革命戰爭時期郵電回憶錄[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8:145.
[14]莫艾.邊區通訊站[N].解放日報,1942-2-1.
[15]邊區通訊站去年工作成績[N].解放日報,1942-3-1.
[16]邊區通訊站三年來寄信八十萬件[N].解放日報,1941-10-14.
[17]莫艾.邊區通訊站[N].解放日報,1942-2-1.
作者簡介:司勝杰(1990.4-),男,漢,河南商丘人,碩士研究生,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研究方向:陜甘寧邊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