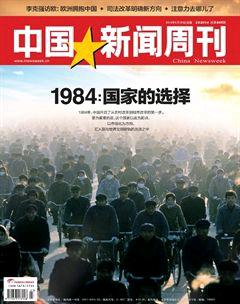中歐關系“升級版”路線圖
徐方清
就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后至今的一年多里,李克強共有五次對外出訪,其中三次都到了歐洲。
此次李克強對英國和希臘的訪問后,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完成了對歐盟“三駕馬車”英、法、德的訪問。3個月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了歐洲四國荷蘭、法國、德國和比利時,并成為首位訪問歐盟總部的中國國家元首。而去年,李克強在其就任總理后的首次外訪中到訪瑞士和德國,后又出訪羅馬尼亞,并出席在羅馬尼亞舉行的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法國《歐洲時報》評論稱,3個月前習近平主席訪問的是歐洲陸地國家,此次李克強總理到訪的是歐洲的兩個海洋大國,而且希臘還恰恰是2014年上半年的歐盟輪值主席國。今年的兩次歐洲行各有側重,又相互補充、高度統一,“在中國領導人的平衡外交戰略下,歐洲、歐盟的力量正越來越得到北京的倚重”。
如果將已經擁有“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中俄關系視作是獨立于中歐關系之外的第三方,那么在中歐 “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進入第十個年頭前后,中歐關系出現明顯升溫的勢頭。

釋放中歐經貿合作潛力
“歐洲在今年中國外交議程中排在優先的位置”。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今年全國“兩會”回答一家法國媒體采訪時表示,中歐關系的關鍵詞是“合作”,作為當今世界兩大力量、兩大文明和兩大市場,我們之間的合作理應是全方位和戰略性的。尤其是在中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啟動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當中,歐洲是我們極具潛力和空間的戰略合作伙伴。
去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十六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上,中國新一屆領導人與歐洲領導人首次會面。峰會前后,掀起一股歐洲領導人訪華潮,荷蘭首相馬克·呂特、英國首相卡梅倫、法國總理埃羅先后到訪中國。
中國原駐烏克蘭大使、上海合作組織前副秘書長高玉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關系的發展補上了以往中歐關系中的一塊短板,是中歐關系的重要補充和新動力,而且,“這不會對中歐關系產生不利影響,中國支持歐洲一體化的方向不會變”。
雙方共同制定并發表《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并提出加強經貿合作的目標,力爭到2020年貿易額達到一萬億美元,幾乎是在現有的基礎上翻一番。李克強總理將這份《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稱之為“上天下海入地”的全面合作,從航天航空到反盜版,從城市化到能源,其涵蓋面之廣“前所未有”。這份規劃也被認為是未來十年中歐深化互信合作、打造中歐關系“升級版”描繪出 “路線圖”。
歐盟27國領導人在2010年6月的歐盟夏季峰會上正式通過的“歐洲2020戰略”,成為歐盟未來十年的發展藍圖,確定了歐盟未來發展的3個重點,即實現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智能增長”,以發展綠色經濟、強化競爭力為內容的“可持續增長”,以及以擴大就業和促進社會融合為基礎的“包容性增長”。
相比較2000年出臺的歐盟發展戰略 “里斯本戰略”中多達數百個量化目標,“歐洲2020戰略”目標更加明確,也更具可操作性。這份戰略規劃還具體列出了未來發展的5大核心目標,分別涉及促進就業、增加研發投入、完成減排指標、增加青少年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以及削減歐盟貧困人口等。
日本《外交學者》雜志分析認為,隨著中國外交變得更加積極,中國的發展成為歐洲的一個巨大機遇,更多歐洲政治家們已經意識到這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今年3月,在出席于荷蘭海牙舉行的全球核安全峰會前后,習近平和奧巴馬各自對歐洲進行了訪問。有媒體進行了比較分析,稱美國和歐洲雖同屬西方文明的聯盟,但奧巴馬無法為歐洲提供其急需的“營養”,例如經濟市場和就業崗位,因此,歐洲更想要中國當它的“新好友”。
歐洲央行前不久出臺了貨幣新政,力圖消除歐元區通縮風險。對于正努力走出債務危機困局的歐洲經濟來說,“拼經濟”成為歐盟第一要務。對中國而言,正處轉型期的經濟下行風險亦不容忽視,結構改革任重道遠。去年,中歐貿易額達5591億美元,歐盟連續10年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作為全球最具活力的經貿關系之一,中歐經貿往來正從互補走向互融互通。此外,未來雙方投資和自貿協定的達成,將進一步釋放中歐經貿合作潛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王義桅還認為,2013年中國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宏大構想,其終端正是歐洲。
歐洲不只把中國人當商人
2012年,上任法國防長僅僅15天的勒德里昂就來到了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這個由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國防部攜手組織的年度對話始于2002年,每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得名“香格里拉對話”,正式的名稱是“亞洲安全大會”。
勒德里昂是歐盟國家中較早對香格里拉對話顯示出熱情的人,他在2012年的發言中提醒歐盟,不應該再對亞洲持“善意忽視”的態度,也告誡亞洲最好別再把歐盟僅僅視為次要的伙伴。
2013年,歐盟“三駕馬車”英、法、德三國防長悉數到新加坡參會,歐盟也派出了以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凱瑟琳·阿什頓和軍事委員會主席洛希爾斯為代表的規格極高的代表團。
很長時間以來,歐盟對亞洲的注視,僅僅停留在經貿領域。但隨著亞太地區日漸成為世界政治和經濟重心,以及美國“重返亞洲”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歐盟意識到需要積極介入亞太事務,以防止“被邊緣化”。有媒體分析稱,歐盟也已經開始布局自己的“重返亞洲”戰略,以避免出現既被美國邊緣化,也被亞洲邊緣化的情況。
本月初,又一次來到香格里拉對話會場的歐盟軍事委員會主席洛希爾斯,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私下進行了一場雙邊會談。
對于歐盟的“東移”,前北約秘書長、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索拉納認為,其與美國“重返亞洲”的不同之處是,歐盟不是太平洋勢力,沒有身為超級大國的負擔,“而恰恰是歐盟在亞洲的潛在優勢,因為這提供了美國這樣的重量級選手無法具備的外交靈活性”。他還認為,在一些重要的全球問題上,歐盟和中國或許會發現它們是天然伙伴。
歐盟“東移”的變化也在去年11月中歐共同發布的《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得以體現。規劃將和平與安全作為中歐合作的首要領域,之后才是經貿與人文合作等領域。
在中國前駐英國大使馬振崗看來,中國和歐洲關系發展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基礎,就是雙方都不嫉妒相互的發展,都把相互發展視為一種機遇;此外,中歐之間沒有地緣政治的沖突,不會擔心中國的發展挑戰其地位。“這和美國不太一樣,美國一方面希望中國的發展能為其增加機會,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的發展會挑戰其地位。”
美國著名亞太問題專家、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會長包道格則認為,中歐關系的基礎并未發生明顯改變,對歐洲具有吸引力的,依然是中國在不斷增強的投資和經濟實力。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也承認,歐洲對中國的興趣確實在逐年增加。
不過,從歐盟的角度看,仍有若干因素干擾中歐關系的發展。除了因為經貿合作的加深所導致的此起彼伏的貿易摩擦外,歐盟加緊與美進行政策協調,推動“跨大西洋貿易投資伙伴關系”(TTIP)談判,而中歐自貿區談判進展緩慢;日本通過領導人訪問、建立“2+2”磋商機制等手段促使歐洲國家在中日問題上選邊站隊。
但隨著歐洲對中國的興趣和重視程度的加深,雙方在處理分歧和問題上也更有智慧。去年,中歐在光伏爭端上的雙贏和解案例,就是通過“妥協文化”來化解分歧的一個案例。而在本月初于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七國峰會(G7)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主張在會議公告中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行動予以點名批評,但其努力宣告失敗,會議公告只是在全文行將結束之際用一段話表述了對東海、南海問題的關切。
“如果歐洲還僅僅把中國人當作商人,那就沒有比這更加陳舊落伍、拆自己臺的態度了。”英國國王政策研究所主席尼克·巴特勒認為,歐洲需要摒棄自己的偏見,邀請中國人成為座上賓。
法國《歐洲時報》評論稱,如今的中歐關系除了在貿易額數據這些“硬指標”上相向而行,還有一層“軟實力”,是歐洲對華視角的變換以及信任與理解的加強。而對于中國而言,不僅要與歐洲單個國家發展良好關系,還要與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歐盟組織尋找共同語言,不僅要與歐洲人做好各個領域的生意,還要在此基礎上創新歐亞大陸合作模式,令彼此成為更親密的朋友,最終成為經濟上乃至政治上名副其實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