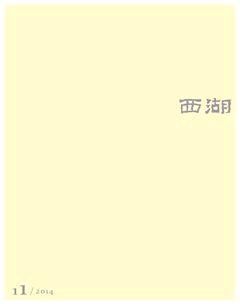“若我燃燒,任我灰燼”
白連春+姜廣平
關(guān)于白連春:
白連春,四川瀘州人。1985年開(kāi)始發(fā)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北京文學(xué)》雜志編輯,詩(shī)人。作品曾獲《詩(shī)刊》和《中國(guó)作家》優(yōu)秀作品獎(jiǎng)。 白連春是個(gè)吃過(guò)苦的作家,從小被父母遺棄,上學(xué)后又被老師逼得投江。以后參軍回來(lái),到北京的魯迅文學(xué)院打工,受到汪曾祺關(guān)照。1997年,《星星》詩(shī)刊組織全國(guó)讀者投票選出最好的詩(shī)歌,白連春得了第一名。他的小說(shuō)《拯救父親》發(fā)表后,先后被《小說(shuō)月報(bào)》、《新華文摘》、《小說(shuō)選刊》、《中華文學(xué)選刊》轉(zhuǎn)載。
導(dǎo)語(yǔ):
白連春筆下出現(xiàn)最多的是農(nóng)民。他寫《逆光勞作》,寫《拯救父親》,都是寫農(nóng)民的日常生活,寫他們的憂傷和夢(mèng)想。他寫露宿街頭的農(nóng)民,寫當(dāng)建筑工人的農(nóng)民,寫賣菜的婦女,寫撿垃圾的老人與乞討的孩子,他還寫農(nóng)村的風(fēng)物和景致。有評(píng)論者說(shuō),他是那種和泥土、和在泥土上生長(zhǎng)的事物有著切近關(guān)系的詩(shī)人。白連春自己說(shuō),我寫的東西既不傳統(tǒng),也不現(xiàn)代,也沒(méi)有什么技巧。那是直接來(lái)源于內(nèi)心深處的一種傾訴。
白連春表示,自己不在乎別人如何稱呼他,只在乎寫什么,怎么寫。他始終將自己定位為“一個(gè)生活在社會(huì)最底層的打工者”,“當(dāng)寫作的時(shí)候,我不是一個(gè)作家,也不是一個(gè)詩(shī)人,我只是一個(gè)普通人”。
在白連春看來(lái),文學(xué)和宗教一樣,好的文字是教人“善”的,有愛(ài)在里面。一篇文章里有沒(méi)有愛(ài),有多少愛(ài),有怎樣的愛(ài),可以看出一個(gè)作家的水平。愛(ài)就如同鹽,已經(jīng)放在菜里了,看不見(jiàn)更摸不著,必須親口嘗才知道。愛(ài)放在文字里,會(huì)不知不覺(jué)改變文字的味道。他說(shuō),他的一切文字里面都是有愛(ài)的。“我是一個(gè)小人物,一個(gè)名字注定要被遺忘,一個(gè)身體死后注定要腐爛的人。活著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愛(ài)著,忍受著,寫著,為了報(bào)答當(dāng)初父母生下我,為了對(duì)得起將來(lái)的死亡。”
一
姜廣平(以下簡(jiǎn)稱姜):我們還是從詩(shī)歌說(shuō)起吧!雖然,在詩(shī)歌面前,我還真沒(méi)有多少發(fā)言權(quán)。所幸,我與食指等詩(shī)人都有過(guò)接觸,也與國(guó)內(nèi)很多詩(shī)人是朋友。做評(píng)論時(shí),有時(shí)手癢,也曾寫過(guò)一兩篇詩(shī)歌評(píng)論。這樣,我就覺(jué)得,我們應(yīng)該還能構(gòu)成對(duì)話關(guān)系。
白連春(以下簡(jiǎn)稱白):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被稱為詩(shī)人了,不管自己承認(rèn)與否。很多時(shí)候我不知道我是生來(lái)就是詩(shī)人呢,還是后來(lái)通過(guò)努力寫詩(shī)才成為詩(shī)人的?為什么我會(huì)這樣?因?yàn)楹芏鄷r(shí)候,即使在生活中,我的血總是很熱,我的心總跳得很快,我的情感總是控制不住。比如,我看見(jiàn)一個(gè)老農(nóng)在侍候莊稼,我肯定會(huì)跑到他的身邊,陪他一會(huì)兒,和他說(shuō)說(shuō)話,稱贊他的莊稼好,當(dāng)我不得不轉(zhuǎn)身離開(kāi),我肯定會(huì)突然淚流滿面,我肯定想這個(gè)侍候莊稼的老農(nóng)是我的父親多好,我肯定愛(ài)他,我肯定盼望從此永遠(yuǎn)守著他。再比如,我看見(jiàn)一只孤單的螞蟻,我總是要彎下腰,我甚至要坐下來(lái),說(shuō),我累了要休息一會(huì)兒,實(shí)際上,這,只是我想多看看這只螞蟻的一個(gè)借口。再比如,我看見(jiàn)一棵樹(shù),大地之上的一棵樹(shù),無(wú)論什么樹(shù),小樹(shù),大樹(shù),有葉子無(wú)葉子,有果實(shí)無(wú)果實(shí),開(kāi)沒(méi)開(kāi)花,我都會(huì)不由自主地伸出手貼近身體,摸摸,抱抱,聞聞,親親,靠靠,我多么情愿留下來(lái)和這棵樹(shù)在一起,我多么企求自己是另一棵樹(shù)。再比如,我看見(jiàn)一棵草,我就想立刻躺在這棵草的下面。我不是做作,我天性如此。所以,我忍不住想詩(shī)人是天生的。
姜:你說(shuō)的這種情形,其實(shí)古時(shí)候的孟子也曾說(shuō)到過(gu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還有,恩足以及禽獸……大詩(shī)人與大作家,看來(lái)都是懷有憐憫之心的。
白:我為我被生成詩(shī)人高興,哪怕我永遠(yuǎn)無(wú)名,哪怕沒(méi)有一個(gè)人懂我,哪怕我還活著就已經(jīng)被這個(gè)繁華的權(quán)力和金錢的世界徹底拋棄了。
我從沒(méi)有想過(guò)要當(dāng)別的。
姜:《一顆漢字的淚水——白連春詩(shī)歌自選集》被人稱為是一部苦難的詩(shī)集,一部愛(ài)的詩(shī)集,一部在巨大的不幸面前永不投降的詩(shī)集。
白:這部詩(shī)集總的說(shuō)來(lái)就兩個(gè)意象,一漢字,二淚水,我把二者加在一起成為一顆漢字的淚水。在我之前,據(jù)我所知:從來(lái)沒(méi)有詩(shī)人和作家這樣為漢字和淚水寫過(guò)任何作品。這部詩(shī)集要表達(dá)的遠(yuǎn)不止我個(gè)人的生活,根本就是整個(gè)人類的濃縮,至少是中國(guó)人吧,所以要有不屈不撓的愛(ài)的品質(zhì),其次是對(duì)一切黑暗苦難不公平不正義和不幸的抗議。當(dāng)然,作為一部詩(shī)集,里面的每一首,單獨(dú)來(lái)說(shuō),實(shí)際上是既沒(méi)有思想也沒(méi)有藝術(shù)的,她只是我心靈深處的最微妙的情感。我為自己能夠?yàn)闈h字寫一部詩(shī)集自豪。這自豪是發(fā)自我的內(nèi)心的。這就是詩(shī)人的好處。每個(gè)詩(shī)人都有自己秘密的幸福。在寫作這部詩(shī)集的時(shí)候,我發(fā)現(xiàn)自己真的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幸福我生在中國(guó)。我幸福我用漢字寫作。我更幸福我一邊在臉上流滿淚水一邊站在電腦前敲打鍵盤,而屏幕上顯示出來(lái)的,正是,全是,我想要的漢字。
再次感謝我的祖先為我創(chuàng)造了漢字。這些漢字,這所有漢字,我一個(gè)人的漢字。
我為漢字死,更為漢字生,一生一生又一生。
姜:這是一種可敬的母語(yǔ)情懷。這讓人感動(dòng)。你自己如何評(píng)價(jià)這部詩(shī)集呢?
白:我如何評(píng)價(jià)這部詩(shī)集?我不知道她好還是不好,她好和不好我不管,反正里面的每一首詩(shī)每一枚漢字都是我的心。
無(wú)論別人認(rèn)為她好與不好,她都是我的心,她只是我白連春一個(gè)人的心。
姜:讀這本書(shū)時(shí),我最大的感覺(jué)是,你是一個(gè)真的人,是一個(gè)認(rèn)真的人。這年頭,像你這樣執(zhí)著而認(rèn)真的人,確實(shí)真的成了“稀有品種”了。
白:你太表?yè)P(yáng)我了。我只是在寫作的時(shí)候認(rèn)真。在生活中,我是一個(gè)極其馬虎的人,馬虎到甚至近于愚蠢。我常常想:為什么我白連春等于白癡?為什么我個(gè)人的生活中總是出現(xiàn)這樣那樣如此多的令我不能解決的麻煩?究竟是生活太麻煩還是我自己太麻煩?
我唯一能做的是:在寫作的時(shí)候,尤其在寫詩(shī)的時(shí)候,盡可能不說(shuō)謊。
我不逃避現(xiàn)實(shí),我永遠(yuǎn)站在人民一邊。
我不靠謊言生活,我要大聲說(shuō)出祖國(guó)和人民正在經(jīng)歷什么。
因?yàn)椋@不是別人的祖國(guó),不是別人的人民,這祖國(guó),這人民,全部,統(tǒng)統(tǒng),都是我的,我白連春一個(gè)人的。
我至死都要愛(ài)他們,都要把他們緊緊抱在懷里。我白天愛(ài)他們,抱著他們,黑夜,我睡著了,仍舊不放開(kāi)他們。我做夢(mèng)也要夢(mèng)見(jiàn)他們。他們是我在人間唯一真正擁有的,唯一使我能夠被稱為詩(shī)人的。
我死了,化成泥土,也要任憑他們踩踏。
姜:另一方面,我又發(fā)現(xiàn),你是一個(gè)被放逐的人。而放逐你的,恰恰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我這樣的說(shuō)法對(duì)不對(duì)。當(dāng)然,我們發(fā)現(xiàn),我們所處的這個(gè)現(xiàn)實(shí)世界,也有著很多可詬病與詛咒的地方。我們能夠安慰自己的,可能正如狄更斯所言:這是一個(gè)最好的世界,這也是一個(gè)最糟的世界。
白:放逐,且是自己放逐自己。我第一次聽(tīng)見(jiàn)有人這樣說(shuō)我。也許是吧。因?yàn)槲椅磪⒓尤魏稳ψ樱参传@過(guò)真正的獎(jiǎng),就是說(shuō),實(shí)際上,我并未被大多數(shù)人承認(rèn),更未被世界承認(rèn)。
很好。為什么說(shuō)很好?因?yàn)檎胬韽膩?lái)不在大多數(shù)人手里,因?yàn)槭澜鐝膩?lái)不等于人民,更不等于祖國(guó)。照我看:這個(gè)世界因?yàn)樵愀猓院谩F鋵?shí),我們目前所處的世界并非我們想象的那么糟糕,至少,在我的祖國(guó),人民還生活在和平之中。在和平中,平淡地活著,這最簡(jiǎn)單的要求,現(xiàn)在已經(jīng)最難實(shí)現(xiàn)了。我看見(jiàn)除了我的祖國(guó),世界上到處都在打仗。
為和平干杯。
為我們都還活著干杯。
為人民干杯,至少為中國(guó)人民干杯。
姜:這是不是你刻意建立的自身與世界的關(guān)系呢?或者說(shuō),你發(fā)現(xiàn)了你與世界,應(yīng)該是以這樣的關(guān)系方式相互依存著。委實(shí),我也覺(jué)得,一個(gè)真正的作家,其實(sh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建立好自己與這個(gè)世界的關(guān)系。而這關(guān)系,究竟是何種關(guān)系,又因具體的作家而相異了。
白:刻意建立自身與世界的關(guān)系?這個(gè)問(wèn)題太深?yuàn)W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從來(lái)沒(méi)有刻意建立過(guò)與世界的關(guān)系。我只是,我從來(lái)都是,我一直以來(lái)就是,站在泥土一邊,站在莊稼一邊,站在于泥土上侍候莊稼的人一邊,我無(wú)法選擇。這是根本不容我選擇的。因?yàn)椋瑥拈_(kāi)始到結(jié)束,我都是泥土的一捧,我都是莊稼的一片葉子,我都是那在泥土上侍候莊稼的人額上汗珠中的一顆。如果你恰巧看見(jiàn)我閃爍,告訴你吧,并不是我的光芒,那侍候莊稼的人是宇宙的太陽(yáng)。我沒(méi)有光芒,我也是需要被照亮的人。
我是泥土的一捧,誰(shuí)不尊敬泥土,我反對(duì)誰(shuí)。這容不得我自己。
我是莊稼的一片葉子,誰(shuí)損毀莊稼,我反對(duì)誰(shuí)。這同樣容不得我自己。
我是那在泥土上侍候莊稼的人額上汗珠中的一顆,誰(shuí)不把那在泥土上侍候莊稼的人當(dāng)人,我誓死反對(duì)誰(shuí)。這,更加,容不得我自己。
當(dāng)然,誰(shuí)反過(guò)來(lái),我就擁抱誰(shuí),雖然我的擁抱微不足道。真的我的擁抱微不足道嗎?
姜:有人謂,“白連春是這個(gè)世界唯一一個(gè)活著的、用生命寫詩(shī)的詩(shī)人。他的詩(shī)歌無(wú)限向下,深入大地,找到骨頭。詩(shī)歌意象層層遞進(jìn),像一臺(tái)顯微鏡看見(jiàn)單體細(xì)胞,看見(jiàn)染色體。詩(shī)歌的想象空間無(wú)限大,大到生命和宇宙。他與海子的方向正好相反:海子詩(shī)歌無(wú)限向上,深入太空,找到上帝。因此可以說(shuō)白連春與海子殊途同歸,這也注定了這個(gè)‘只想抱緊自己骨頭回家的瀘州人會(huì)與海子一樣,成為這個(gè)世界最重要的詩(shī)人。”這話又讓我想到一點(diǎn),看來(lái),作家與世界的關(guān)系,有時(shí)候是表現(xiàn)為作家對(duì)這個(gè)世界投入的程度或深入的深度,當(dāng)然,也可以說(shuō),是一個(gè)作家熱愛(ài)這個(gè)世界的程度。
白:這一段談話似乎是前一段的深入。在此,我必須指出:我個(gè)人,我自己,從未把白連春和海子比。海子已經(jīng)是故人已經(jīng)是經(jīng)典。我只能向海子致敬。我永遠(yuǎn)向海子致敬。說(shuō)到大地,說(shuō)到骨頭,是的,我承認(rèn),我曾在不止一首詩(shī)中寫過(guò),我寫我在被無(wú)情挖掘開(kāi)的大地之下尋找我祖先的骨頭,我要把我祖先的骨頭,全部,重新埋在我的胸膛里,重新埋在我的詩(shī)里。在此,我還必須指出:一個(gè)不尊重祖先的民族是沒(méi)有希望的民族。一個(gè)不尊重土地的民族同樣沒(méi)有希望。一個(gè)不尊重人民的民族更加沒(méi)有希望。
我的另一部詩(shī)集《在一棵草的根下》中,這類詩(shī)作更多,這種土地情結(jié)更重,這些對(duì)祖先的情懷更加無(wú)法釋放。毫不夸張地說(shuō),我收入這部詩(shī)集里的詩(shī),字字血淚。然而,一個(gè)真詩(shī)人的聲音再血淚,也是十分渺小的。因?yàn)樵?shī)壇,因?yàn)槲膲瑥膩?lái)都是功利的,從來(lái)都是可以被某些人拿來(lái)隨便亂用的。某些人吐口痰,他們說(shuō)是好詩(shī);某些人撒泡尿,他們說(shuō)是好詩(shī);某些人拉坨屎,他們更加說(shuō)是好詩(shī)。他們給這些好詩(shī)各式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獎(jiǎng)。真詩(shī)都被這些所謂“好詩(shī)”淹沒(méi)了,就像大地上有生命力的草,從來(lái)都被裝滿垃圾的巨大的歷史車輪,碾壓著,呼嘯而過(guò),一樣。然而,野火燒不盡的是草,垃圾車輪壓不死的同樣是草。
當(dāng)我們完全消滅了土地,消滅了莊稼,消滅了草,消滅了祖先,消滅了真詩(shī),我們所有人都將無(wú)家可歸。到那時(shí),我們縱然還剩下骨頭,我們縱然還可以抱緊自己的骨頭,但是,已經(jīng)沒(méi)有家讓我們回了。
大地之上,全是鋼筋水泥玻璃和塑料,我們的血肉之軀,無(wú)處可逃。
人啊,你該往何處去?
姜:這里,我們又勢(shì)必發(fā)現(xiàn)一個(gè)文學(xué)與世界的關(guān)系。在你看來(lái),文學(xué)與世界究竟存在著一種什么樣的關(guān)系呢?
白:文學(xué)與世界沒(méi)有關(guān)系,因?yàn)樗形膶W(xué)都是世界,因?yàn)槿渴澜缍际俏膶W(xué)。文學(xué)就是反映世界的。文學(xué)即世界本身。世界是白的,文學(xué)就是白的;世界是黑的,文學(xué)就是黑的;世界是和平的,文學(xué)就是和平的;世界是幸福的,文學(xué)就是幸福的。世界等于文學(xué),文學(xué)等于世界。至少,我白連春的文學(xué)等于我白連春的世界,全部都等于。別人的如何,我不了解,不發(fā)表意見(jiàn)。
姜:看來(lái),在你這里,文學(xué)與世界完全是一回事。
白:這樣說(shuō),是不是我把文學(xué)和世界混凝成一體了?就像曾經(jīng)有人形容我:分不清詩(shī)歌和生活的界線。詩(shī)歌和生活有界線嗎?文學(xué)和世界有界線嗎?
文學(xué)和世界從來(lái)都不是對(duì)立的。如果有人把文學(xué)和世界對(duì)立起來(lái),硬要厘清文學(xué)和世界究竟什么關(guān)系。我以為:這是一個(gè)錯(cuò)的命題。
文學(xué)和世界是這樣的關(guān)系,哪里有世界哪里就有文學(xué),就像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反抗。世界即文學(xué),所以叫世界文學(xué)。打幾個(gè)人們見(jiàn)慣的比喻:世界是鏡子,文學(xué)是影像;世界是籠子,文學(xué)是豹子;世界是水,文學(xué)是月;世界是花,文學(xué)是香;世界是道路,文學(xué)是腳印;世界是燈,文學(xué)是光……懶得再比喻了。很多時(shí)候作家的寫作跟不上世界的發(fā)展和變化,小說(shuō)遠(yuǎn)不如生活殘酷、陰險(xiǎn)和繁復(fù)。
實(shí)際情況是:文學(xué)的表達(dá)力比生活低,低得多。許多生活中真實(shí)發(fā)生過(guò)的事件,作家卻無(wú)力把這些事件照實(shí)寫出來(lái)。另外,許多真實(shí)歷史成為禁區(qū)。為什么成為禁區(qū)?
有關(guān)部門不準(zhǔn)作家寫。
作家誰(shuí)寫誰(shuí)倒霉。
流放作家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
二
姜:現(xiàn)在,我們具體地說(shuō)說(shuō)你的小說(shuō)吧。先說(shuō)《拯救父親》。讀過(guò)這篇小說(shuō)的人,一定看出了這部小說(shuō)極強(qiáng)的紀(jì)實(shí)性。或者直白地說(shuō),這篇小說(shuō),真實(shí)地再現(xiàn)了父親的生活,再現(xiàn)了農(nóng)民的生活,再現(xiàn)了父親的兒子們那種激情、無(wú)奈、憤懣……你在寫作的時(shí)候,如前所說(shuō),是想寫出作品中涉及的人們對(duì)生活對(duì)世界的那種關(guān)系吧?
白:《拯救父親》這篇小說(shuō),先有真實(shí)的故事,至少,小說(shuō)里面父親的故事在生活中千真萬(wàn)確是發(fā)生過(guò)的。整個(gè)大地之上的農(nóng)民,他們,不是我們的父親就是我們的母親。每天,發(fā)生在他們身上的不幸,數(shù)不清。其中許多都無(wú)法進(jìn)入作家的視角,或者說(shuō),作家都視而不見(jiàn)。我不是一個(gè)有使命感的作家,我不是一個(gè)自以為偉大的作家,在我寫作的時(shí)候,我唯一做的,只是,盡可能地還原生活的真實(shí)。
姜:關(guān)于還原之說(shuō),我一直是非常認(rèn)同的。有一段時(shí)間,也就是我在開(kāi)始進(jìn)入文學(xué)寫作的時(shí)候,我就認(rèn)為,在我們的文學(xué)寫作中,還原應(yīng)該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的。就是到現(xiàn)在,我仍然覺(jué)得,文學(xué)的主要工作與方式還是還原。作家的使命之一,就是將世界的本真還原給我們的讀者。
白:如果我能還原生活真實(shí)的千分之一,我就很滿意了。我寫作的時(shí)間已經(jīng)不短了,至少三十年了吧,這樣的滿意還很少。我很羞愧,面對(duì)大地,面對(duì)農(nóng)民,面對(duì)我們的父親母親,我常常無(wú)地自容。我不配做他們的孩子。我不配被稱為詩(shī)人和作家。在他們面前,我只不過(guò)是一個(gè)無(wú)所事事的人,罷了。
姜:說(shuō)到關(guān)系,就肯定想到角色,在讀你的作品時(shí),我突然想到一點(diǎn),我們每一個(gè)人都在這個(gè)世界上扮演著一種角色,同時(shí),這個(gè)世界,也似乎要求我們?nèi)グ缪菀环N角色。這里的關(guān)系,似乎又有點(diǎn)復(fù)雜了。就以我說(shuō)吧,有時(shí)候,我似乎也沒(méi)有找到我在這個(gè)世界的位置,也無(wú)從知道自己必須要成為一個(gè)什么角色。
白:世界,生活和我。我懂得:沒(méi)有我,世界照樣進(jìn)步,生活的滾滾洪流照樣一日繼續(xù)一日。我來(lái)到世界是偶然的嗎?不。我來(lái)到世界是必然的嗎?也不。我只是想:作為人一生,有限得很,我能留下點(diǎn)什么?垃圾。垃圾。是只有垃圾,還是除了垃圾之外,還有點(diǎn)別的,比如讓某人愉快的東西?讓某人想起來(lái)會(huì)心一笑的東西?
如果在這個(gè)世界上,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必須成為一個(gè)角色的話,我想成為一個(gè)朋友:一個(gè)失眠者的朋友,一個(gè)失戀者的朋友,一個(gè)失敗者的朋友,一個(gè)孤獨(dú)者的朋友,一個(gè)窮困者的朋友,一個(gè)被侮辱者的朋友,一個(gè)農(nóng)民的朋友,一個(gè)工人的朋友……我特別想成為一個(gè)孩子的朋友。
可惜今生,我都找不到這種機(jī)會(huì)了,我是指成為一個(gè)孩子——我自己孩子的——朋友。
姜:你自己孩子的朋友,這又回到《拯救父親》的主旨上了。父子關(guān)系,其實(shí)也是文學(xué)關(guān)系中的重要內(nèi)容。這是任何一個(gè)偉大的作家都繞不過(guò)去的一種關(guān)系。所以,從《拯救父親》說(shuō)開(kāi)去的話,我們發(fā)現(xiàn),文學(xué)有時(shí)候在這個(g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可能真的微乎其微。
白:世界太過(guò)于強(qiáng)大,生活太過(guò)于強(qiáng)盛,文學(xué)就顯得異常蒼白。這里的世界和生活實(shí)際上都是被操縱的。說(shuō)到底,古人說(shuō)得好,苛政猛于虎。當(dāng)苛政猛于虎,文學(xué)的作用,僅僅是,知音賞。如果連知音都不賞,那,文學(xué)就沒(méi)有存在的價(jià)值和必要了。作家的寫作只是為政治服務(wù)的話,我寧可不做作家,我任何書(shū)都不讀。我寫作的時(shí)候從來(lái)不管政治。什么領(lǐng)導(dǎo),什么偉人,什么世界和政黨,全被我忘記了。我心里只有人,莊稼和土地。
姜:說(shuō)到此,我們就都會(huì)想起一首古人的詩(shī):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
白:文學(xué)的力量被這位古人形容得多么準(zhǔn)確。
姜:關(guān)于《拯救父親》,我一直有一個(gè)問(wèn)題想請(qǐng)教你,這里的周連國(guó),詩(shī)人谷禾,你將這個(gè)真實(shí)的人物身上所發(fā)生的事情搬到了作品中,這一方面需要一個(gè)作家的勇氣,另一方面,你是尊重了生活的真實(shí)呢還是尊重了文學(xué)的真實(shí)?你又是如何處理這兩方面的關(guān)系的呢?
白:這事你一說(shuō)就復(fù)雜了,其實(shí),很簡(jiǎn)單,周連國(guó)即詩(shī)人谷禾,給我講他父親的故事。聽(tīng)后,我說(shuō),連國(guó),我要把這事寫成小說(shuō),你不反對(duì)吧?不反對(duì)。周連國(guó)回答。于是,我說(shuō),好,那,我就在小說(shuō)里用你和你父親的真名。有意思的是:周連國(guó)叫周連國(guó),我叫白連春,我們兩個(gè)人的名字中間那個(gè)字都是連字,拋開(kāi)姓,他叫連國(guó),我叫連春,我們不想成為兄弟都不可能。
姜:這倒是一種暗合與巧合了。看來(lái)這個(gè)世界,還真的跟人開(kāi)著很大的玩笑。劉震云說(shuō)過(guò),為什么我的眼里飽含淚水,是因?yàn)檫@個(gè)玩笑開(kāi)得太大了。
白:開(kāi)個(gè)玩笑,連國(guó)加連春等于中國(guó)的春天。這個(gè)玩笑是不是太大了?是不是太自以為是了?不管,反正,我喜歡“加”字。朋友們都知道我喜歡“加”字。《我和你加在一起》,我早年寫的一首詩(shī),其實(shí)不是我詩(shī)歌中最好的,被中央電視臺(tái)的主持人在中央電視臺(tái)新年新詩(shī)會(huì)上朗誦過(guò)。
我喜歡我祖先為我創(chuàng)造的每一個(gè)字。
所有漢字。
姜:看來(lái),漢字與人的命運(yùn)是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什么樣的字,與什么樣的人,是有緣分的。
白:話說(shuō)回來(lái),一篇小說(shuō)或一首詩(shī),對(duì)于一個(gè)作家或一個(gè)詩(shī)人,都是有緣分的,不是任何作家和詩(shī)人可以處理得來(lái)的。好小說(shuō),好詩(shī),根本就是在那里放著的,一直在等待作家和詩(shī)人動(dòng)筆,不是某個(gè)作家和某個(gè)詩(shī)人寫作出來(lái)的。你在對(duì)的時(shí)間寫出了一篇對(duì)的小說(shuō),你成功了。你在對(duì)的時(shí)間寫出了一篇錯(cuò)的小說(shuō),你失敗了。你在錯(cuò)的時(shí)間寫出了一篇對(duì)的小說(shuō),你照樣要失敗。為什么?緣分沒(méi)到。
當(dāng)然,在緣分來(lái)到前,一個(gè)作家和詩(shī)人,要做足準(zhǔn)備工作。
姜:《母親萬(wàn)歲》這篇小說(shuō),充滿了詩(shī)性。但這里的詩(shī)性,卻非常沉重,非常凄涼。在這一部小說(shuō)里,你寫到失去土地的母親,寫到一只母雞,寫到長(zhǎng)江邊兒子的那座城市,寫到了兒子、兒媳、孫子與母親的關(guān)系,最后寫母親從樓頂上墜樓而死。這無(wú)疑是一個(gè)悲情故事,是寫“丟失”或“遺忘”的主題的。這篇小說(shuō)的寫作動(dòng)機(jī),你能為我們談一談嗎?
白:是的,每首詩(shī),每篇小說(shuō),其作者都是有動(dòng)機(jī)的。究竟什么原因促動(dòng)我寫這樣一篇關(guān)于母親的小說(shuō)?明明是一個(gè)母親自殺的故事,偏偏要取名叫《母親萬(wàn)歲》,不是自欺欺人嗎?在這篇小說(shuō)里,我只是寫這個(gè)故事發(fā)生在長(zhǎng)江邊上的一座城市。故事里的母親、兒子、兒媳、孫子等人物都是沒(méi)有名字的。為什么不給小說(shuō)里的人物取個(gè)名字?因?yàn)檫@是一個(gè)極其普通普遍的故事,里面的人物不需要名字都可以完成。就是說(shuō),到了今天,我們嫌棄母親,我們遺棄母親,逼迫母親最后不得不自殺,已經(jīng)是很司空見(jiàn)慣的事了。新聞里這樣的真實(shí)案件很多。在此,我要決絕地說(shuō),那些連自己的母親都不愛(ài)的人,不配“人”這個(gè)漢字,豬狗都不如,禽獸都不如。
很多人都不要自己的母親了,使年老的母親不得不自殺,說(shuō)明一個(gè)世界集體道德淪喪。這,本身就是凄涼的沉重的。再不改善,人類離毀滅就不遠(yuǎn)了。
愛(ài),讓我們先從愛(ài)自己年老的多病的貧窮的母親開(kāi)始吧。
不要再讓哺育了我們的母親自殺了。
救救我們的母親吧。
救救我們的父親吧。
還有,救救我們的孩子吧。
救救“人”這個(gè)漢字吧。
姜:看來(lái),《母親萬(wàn)歲》首先是一個(gè)關(guān)于拯救的故事。說(shuō)到失去土地,我曾經(jīng)想過(guò),這是一種關(guān)系的缺失,農(nóng)民與土地的關(guān)系。現(xiàn)在,農(nóng)民沒(méi)有了土地,就勢(shì)必成為一種漂浮的狀態(tài)。這里的疼痛,坦率說(shuō),當(dāng)代作家們一直在努力書(shū)寫著,但將土地移到樓頂?shù)倪@一令人心疼的努力,應(yīng)該說(shuō)是第一次出現(xiàn)。趙本夫的《無(wú)土?xí)r代》曾經(jīng)別出心裁地寫過(guò)讓城市的街心花園都長(zhǎng)上了麥子。應(yīng)該說(shuō),趙本夫,白連春,都是在土地上摸爬滾打過(guò)的,才能有這樣的神來(lái)之筆。
白:趙本夫的情況我不了解,至于我,決不是什么神來(lái)之筆。把泥巴搬運(yùn)到樓頂,我看到很多人做過(guò),我本人也親自做過(guò)。這叫什么?這叫先有生活后有文學(xué)。這叫文學(xué)來(lái)自于生活。土地都被開(kāi)發(fā)商開(kāi)發(fā)了,農(nóng)民都住進(jìn)了樓房。小區(qū)的地面寧可長(zhǎng)滿雜草也不準(zhǔn)種菜,今天農(nóng)民種上,明天就被物業(yè)拔了。更別說(shuō)到城市的街心花園種麥子了。要真到城市街心花園種麥子,早被城管和警察抓幾百上千回了。命都丟了,還種什么麥子?所以說(shuō),趙本夫的是神來(lái)之筆,我的不是。我記得,在我之后,作家羅偉章也曾寫過(guò)在樓頂上種莊稼的故事。如果一個(gè)世界,農(nóng)民真的只能在樓頂上種莊稼,我們?cè)O(shè)想一下:這個(gè)世界還能存在多久?縱然這個(gè)世界的經(jīng)濟(jì)如何發(fā)達(dá),樓房修得如何遼闊和雄偉。
姜:正是在閱讀你的作品的過(guò)程中,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令人遺憾的現(xiàn)象,我們的評(píng)論家同行,可能過(guò)多地關(guān)注了你的詩(shī),而對(duì)你的小說(shuō)作品沒(méi)有給予更多的關(guān)注。
白:你這樣一說(shuō),仿佛評(píng)論家真的過(guò)多關(guān)注了我的詩(shī)歌似的。其實(shí),對(duì)于我的詩(shī)歌的評(píng)論不過(guò)寥若晨星的幾篇,我自己收集到的不超過(guò)五篇。而對(duì)于我的小說(shuō)的評(píng)論,怎么說(shuō)呢,也是少之又少。還好,我在寫作之前就有自知,我不是為評(píng)論家寫作的。我為誰(shuí)寫作?說(shuō)我為人民寫作,太大了,也太故意拔高自己了,不怕你笑話,從來(lái),我都是為我自己寫作的。一首詩(shī),不寫我難受;一篇小說(shuō),不寫我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寫了。我的心要我寫。我的靈魂要我寫。寫好之后,我才想到給最好的朋友看,希圖得到這最好朋友的表?yè)P(yáng),即所謂知音賞。然后,才投稿,如果發(fā)表了,就算了,如果沒(méi)有發(fā)表,也就算了。
姜:說(shuō)到底,寫小說(shuō)也好,寫詩(shī)歌也好,其實(shí)都是自己的事。首先是為自己寫的,為自己的良心寫的。
白:我的詩(shī)歌寫成了,我的小說(shuō)寫成了,我已經(jīng)釋放完了,我已經(jīng)在寫作的過(guò)程中得到想要的快樂(lè)了。
如果發(fā)表了,那,是給我意外的驚喜,如果還得到了稿費(fèi),更是意外的驚喜,喜上加喜。至于獲獎(jiǎng),乖乖,我從來(lái)沒(méi)有夢(mèng)想過(guò)。獎(jiǎng),和我無(wú)關(guān)。
我還活著,我還愛(ài)著,我還寫著,這,就是上帝給我的最大的獎(jiǎng)。
姜:我們繼續(xù)說(shuō)拯救土地的話題。像《泥土火焰》這樣的作品寫到了掠奪,起于掠奪土地,終于掠奪生命。惟歌生民病。主題是非常重大的。
白:掠奪。在我的小說(shuō)里可是沒(méi)有這個(gè)詞的。這篇小說(shuō)和我別的小說(shuō)類似,也是寫土地被無(wú)情地占據(jù),農(nóng)民先是喪失土地最后喪失生存機(jī)會(huì)的故事。如果你仔細(xì)讀過(guò)我的全部詩(shī)歌和小說(shuō),將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是我一貫的主題。地球這顆星球是由土地構(gòu)成的。歷史上的戰(zhàn)爭(zhēng)也幾乎由土地引起。沒(méi)有土地,人怎么活命?這是一個(gè)用腳趾頭都可以想的問(wèn)題,偏偏我們的世界不往這方面考慮。莊稼,土地,農(nóng)民,是人類永恒的主題。莊稼的痛就是土地的痛,土地的痛就是農(nóng)民的痛,而農(nóng)民的痛實(shí)際上是整個(gè)人類的痛。世界如此龐大,怎么就沒(méi)有一顆明白腦袋?要我一個(gè)小小的詩(shī)人操心。在這個(gè)關(guān)系到民族存亡的時(shí)刻,連詩(shī)人都不站在莊稼一邊,都不站在土地一邊,都不站在農(nóng)民一邊。這一邊,眼看著,就要被歲月那架無(wú)情的機(jī)器給消滅了。當(dāng)“這一邊”真的被消滅,地球就毀了,人類不再存在,我更加不再存在。這樣一個(gè)主題大嗎?說(shuō)大,關(guān)聯(lián)著整個(gè)地球;說(shuō)小,只因?yàn)槲蚁牖钪?/p>
姜:這篇小說(shuō)是一篇典型的苦難敘事的作品。看來(lái),與其他篇什一樣,你也顯示了你與其他作家的巨大不同。別人是將文學(xué)投入到人生,你則是將人生完全地投入到文學(xué)。我不太知道這篇小說(shuō)在社會(huì)上的反響。你不妨為我們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
白:《泥土火焰》是我個(gè)人生命中最珍貴的文字之一,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全部真實(shí)。人物和故事都生長(zhǎng)發(fā)生在我的出生地,同《母親萬(wàn)歲》一樣,都在長(zhǎng)江邊上。一些人物早已去世,一些人物現(xiàn)在還活著。長(zhǎng)江是我的詩(shī)歌和小說(shuō)永遠(yuǎn)無(wú)法躲避的主題。這篇小說(shuō),我用盡了我所有的文學(xué)和人生知識(shí),發(fā)表起來(lái)很困難,更不要說(shuō)在社會(huì)上有反響了。在四川就開(kāi)始寫,到了北京后又接著寫。寫好后放了很久,投了多家雜志都無(wú)法發(fā)表。一個(gè)機(jī)會(huì)終于來(lái)了,我的一個(gè)朋友,和我一樣漂在北京的易水,去了《青年文學(xué)》做編輯,需要稿子。他找到我,我就給了易水這篇到處都無(wú)法發(fā)表的小說(shuō)。易水要去了我的小說(shuō),沒(méi)多久就離開(kāi)了《青年文學(xué)》。那段時(shí)間,我還擔(dān)心這篇小說(shuō)最終發(fā)表不出來(lái),后來(lái),還是發(fā)表了,2001年第10期,責(zé)任編輯署的是易水和柳宗宣的名。發(fā)表時(shí),編輯把題目改成了《火焰》。發(fā)表后,沒(méi)有引起任何人的關(guān)注。出書(shū)時(shí),我又恢復(fù)成為《泥土火焰》。為了這篇小說(shuō),我哭過(guò)無(wú)數(shù)回,淚水差不多都可以流成另外一條長(zhǎng)江了。寫的時(shí)候哭,修改的時(shí)候哭,修改一次哭一次,再修改一次又哭一次,修改好了讀,還哭,過(guò)了很久,每次翻來(lái)讀,照樣哭。噢,必須指出:我哭不是矯情,更不是控訴。我哭是由于我的心太軟了。我哭是由于生活太硬了。我太軟的心沒(méi)有辦法不被太硬的生活碰傷。
說(shuō)實(shí)話,這篇小說(shuō)能夠發(fā)表,真的要感謝易水。不知道易水現(xiàn)在何處,做著什么工作,日子過(guò)得是否如意?易水是個(gè)好朋友,我很想念。易水先前搞文學(xué),后來(lái)不搞了。
柳宗宣的詩(shī)和散文一直很棒,他的生活很穩(wěn)定,可以說(shuō)豐富。我不擔(dān)憂柳宗宣。
姜:你這里有文本的創(chuàng)新,你先寫了下部。這里的文本創(chuàng)新,應(yīng)該不是倒敘那么簡(jiǎn)單地把下部先呈示給讀者吧?因?yàn)椋谖覀冏x者,其實(shí)并不管你哪一個(gè)部分先開(kāi)始。而且,從小說(shuō)敘事角度講,從哪里開(kāi)始敘事,都是可以的。你這樣安排的意圖是什么呢?
白:小說(shuō)取名《泥土火焰》,既然泥土與火焰,她們本身都是從下部開(kāi)始的,所以小說(shuō)也從下部開(kāi)始。下部白色,最后又以下部結(jié)束,還為白色。中部依次為紅色、黃色或紫色。然后上部,黑色和灰色;正中間頂部無(wú)色。開(kāi)始的下部有兩個(gè)小故事,一河灘地,二石頭開(kāi)花。中部依次有四個(gè)小故事,一耳垂,二牛,三蠶房里的燈,四桃花。然后上部一個(gè)小故事,長(zhǎng)滿苔蘚的石頭。正中間的頂部還是一個(gè)小故事,星星是稻的種子。再接下來(lái)是上部,三個(gè)小故事,一小土耗子,二吃土的手,三推土機(jī)。再接下來(lái)的中部,還是三個(gè)小故事,一我們貧窮,但是純潔;二問(wèn)題;三病。最后下部一個(gè)小故事,槍斃。整篇小說(shuō)結(jié)束。這時(shí),又恰是整篇小說(shuō)的開(kāi)始,因?yàn)槟嗤梁突鹧娑际菑南虏块_(kāi)始的,而我作為作者,客觀存在的寫作,也是從下部開(kāi)始的。所以,這篇小說(shuō)其實(shí)是一個(gè)循環(huán),一個(gè)泥土形狀和火焰形狀的圓。
姜:小說(shuō)其實(shí)是圓形結(jié)構(gòu)。但是,進(jìn)而言之,在談到小說(shuō)的結(jié)構(gòu)時(shí),我曾經(jīng)就作家朱輝的小長(zhǎng)篇《白駒》作過(guò)探討,我認(rèn)為,小說(shuō)的結(jié)構(gòu)應(yīng)該是圓形的結(jié)構(gòu)。我的“文學(xué)有機(jī)本體論”認(rèn)為,小說(shuō)結(jié)構(gòu)就是圓形的。它從哪里開(kāi)始,都是完全可以的。
白:整篇小說(shuō)的講述由兩個(gè)“我”展開(kāi),一個(gè)“我”就是我自己——詩(shī)人白連春,另一個(gè)“我”是老農(nóng)民楊五老漢,中間再穿插第三人稱的講述。整篇小說(shuō)的基本故事是兩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一、幾十年前的那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抗日戰(zhàn)爭(zhēng)也好解放戰(zhàn)爭(zhēng)也罷;二、幾十年后的土地戰(zhàn)爭(zhēng)。何謂土地戰(zhàn)爭(zhēng)?就是開(kāi)發(fā)商瘋狂占領(lǐng)土地,把土地原本的主人農(nóng)民變得無(wú)家可歸的戰(zhàn)爭(zhēng)。兩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同樣殘酷,同樣鮮血淋漓。小說(shuō)正中間的頂部為無(wú)色,有“我”與兩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的參與者、受害者楊五老漢,楊五老漢對(duì)詩(shī)人白連春的講述,此地此刻,有我有你,老農(nóng)民直接面對(duì)詩(shī)人說(shuō),是傾訴,不是控訴。
姜:為什么說(shuō)是傾訴不是控訴?
白:因?yàn)楣适吕镉袩o(wú)限的愛(ài)。這個(gè)小故事的主人公楊五老漢甚至對(duì)詩(shī)人白連春說(shuō)“生命的規(guī)律不是生老病死,而是愛(ài)”。他還說(shuō):“生命就是生命,它不受任何非生命的東西的駕馭。誰(shuí)也無(wú)權(quán)支配和改變生命。誰(shuí)能命令一棵松樹(shù)立刻死掉?誰(shuí)能把一棵白菜變成一塊石頭,或者一只綠翅膀的鳥(niǎo)?誰(shuí)硬要這么做,誰(shuí)就將制造一場(chǎng)災(zāi)難。我們經(jīng)歷的災(zāi)難已經(jīng)不少了。每天,我們的地球都在低語(yǔ)和傾訴。我們的地球再也經(jīng)不起折騰了。作為一個(gè)農(nóng)民,我的責(zé)任就是保護(hù)好我的土地(它是我們的地球的一部分),我要讓我的土地長(zhǎng)滿莊稼。”
姜:這里的無(wú)限的愛(ài),我們可以理解為大愛(ài)了。這才是大愛(ài)。
白:這篇小說(shuō)里有一則小故事,名為《星星是稻的種子》,內(nèi)文包含了我早年的一首完整的詩(shī)作《稻》。我覺(jué)得,這首詩(shī)是整篇小說(shuō)的核心,在此,請(qǐng)?jiān)试S我將此詩(shī)移植到這里。因?yàn)榈就瑯涌梢宰鳛檫@篇對(duì)話的核心,稻不僅是這篇對(duì)話的核心,而且還是整個(gè)地球和整個(gè)人類的核心。我這樣說(shuō),沒(méi)有人會(huì)反對(duì)吧?至少天天吃稻的人不該反對(duì)。
稻
稻是一粒很小的東西
拿在手里很輕
放到牙上才能嚼碎
泥土的黃內(nèi)緊緊包裹著
心靈的白
稻的殼是父親的汗和母親的淚
照耀了我一生
稻的核是兒子的夢(mèng)和女兒的歌
燃燒了我一生
稻是一粒很小的東西
一座又苦又咸的海,濃縮
在一片葉子上
為了稻的熟
我一次次俯下身
成了卑賤且貧困的一群
爬在地上
愛(ài)了一生
姜:這篇小說(shuō)繼續(xù)了你小說(shuō)寫作中的詩(shī)性風(fēng)格。我們現(xiàn)在索性將一個(gè)問(wèn)題提到前面來(lái)談吧:在小說(shuō)里,洋溢的詩(shī)性,會(huì)不會(huì)虐殺掉小說(shuō)之美呢?當(dāng)然,我的這一問(wèn),確實(shí)顯得非常幼稚。我們讀過(guò)普希金的詩(shī)體小說(shuō),讀過(guò)歌德的書(shū),應(yīng)該說(shuō),詩(shī)性之美與小說(shuō)之美,是并行不悖的。但我為什么要問(wèn)及這一點(diǎn),你肯定也非常明白,現(xiàn)在,還有誰(shuí)能有這樣的耐心,去品味詩(shī)中的情趣與美感呢?這個(gè)快節(jié)奏的年代,有誰(shuí)還能夠沉下心來(lái)領(lǐng)受這樣的詩(shī)美呢?
白:這個(gè)問(wèn)題實(shí)際上涉及到我為誰(shuí)寫作。我說(shuō)過(guò),我不為任何別人寫作,我從來(lái)都是為我自己寫作。寫作是我心靈的需要,是自我滿足。是不是我太自私了?無(wú)論我寫詩(shī)還是寫小說(shuō),當(dāng)我開(kāi)始寫,我就忘了整個(gè)世界,全心全意只有一個(gè)目的,就是,只是,把這首詩(shī)和這篇小說(shuō)寫到我認(rèn)為的最好。我不管詩(shī)性之美還是小說(shuō)之美,這些,我都不懂。我所有的文字全部來(lái)自我的心靈,來(lái)自我的情感自然流動(dòng)。當(dāng)我開(kāi)始寫,我只有心靈,我只是一個(gè)情感動(dòng)物。所以,我才不管什么快節(jié)奏的年代呢,讓快節(jié)奏的年代在我的寫作中見(jiàn)鬼去吧。我就是要慢下來(lái),我就是要一個(gè)人阻擋年代快速前進(jìn)的車輪,至少在我的詩(shī)中和小說(shuō)中。我相信,凡是愿意讀我文字的讀者都是有心靈和情感的。
姜:為什么會(huì)這樣肯定?
白:為什么我這樣肯定?因?yàn)槲业男撵`就是你的心靈就是他的心靈,就是整個(gè)人類的心靈。同樣,我的情感也是。
當(dāng)然,話說(shuō)回來(lái),小說(shuō)過(guò)多地沉浸在詩(shī)中,不是成功之舉。我的小說(shuō)也不是都這樣。我的小說(shuō)也有純粹講故事的。我有一篇小說(shuō)《天堂》,由于故事太直接太尖銳,太缺乏詩(shī)意,人人都能夠一讀就可以隨意按自己的理由歪曲,發(fā)表后,就被自以為是“革命”的革命者舉報(bào),遭禁了。其實(shí),那只不過(guò)是一篇關(guān)注農(nóng)民生存的小說(shuō)。說(shuō)到底,一篇小說(shuō)能反動(dòng)到哪里呢?能反動(dòng)到何等地步呢?
姜:是啊,一篇小說(shuō)之輕,與一個(gè)世界之重,其實(shí)是不對(duì)等的。
白:一個(gè)世界真的有必要禁止一篇小說(shuō)嗎?禁止了一篇小說(shuō),農(nóng)民的生存問(wèn)題就得到解決了嗎?如果世界真的解決了農(nóng)民的問(wèn)題,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打死我我也不寫作了。誰(shuí)有權(quán)規(guī)定別人是反動(dòng)的?誰(shuí)肯定自己就是革命的?到了今天,“革命”這個(gè)詞和“反動(dòng)”這個(gè)詞,都需要我們重新認(rèn)識(shí)。多年以后,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反動(dòng)也好,革命也罷,可能都不過(guò)是垃圾,都會(huì)被時(shí)間無(wú)情地淘汰。誰(shuí)革命?誰(shuí)反動(dòng)?站在造反者一邊就革命?站在農(nóng)民一邊就反動(dòng)?那么,我情愿一生反動(dòng)。
扯遠(yuǎn)了。看,詩(shī)人就這毛病。控制不住自己的血,總是像大海和群山一樣,沸騰。所以歷朝的運(yùn)動(dòng),都是詩(shī)人先遭殃。
即使懂得自己會(huì)先遭殃,我仍舊愿意做詩(shī)人。
你拿我怎么辦呢?
大不了,你打死我,你打死我吧?你真要打死我嗎?
姜:說(shuō)笑了,哪能呢。你是我們的好詩(shī)人、好小說(shuō)家。與之相關(guān)的問(wèn)題是,你現(xiàn)在還寫詩(shī)吧?你在寫詩(shī)時(shí),與在寫小說(shuō)時(shí)的感覺(jué)是怎么樣的呢?詩(shī)歌,我覺(jué)得追求的是一種意境之美,一種語(yǔ)言的凝練之美;而小說(shuō),我一向認(rèn)為是一種如水的品質(zhì),它要能夠讓讀者沉浸其中,從而悟出小說(shuō)的真諦。
白:我當(dāng)然寫詩(shī)了。作為天生的詩(shī)人,我沒(méi)有辦法不一直寫詩(shī)到死。我只是寫詩(shī)累了,作為休息才寫小說(shuō)的。寫詩(shī)是我的正餐,寫小說(shuō)是我的茶點(diǎn)。
在我看來(lái),寫詩(shī)和寫小說(shuō)區(qū)別不是很大,因?yàn)槎际莵?lái)自我的心靈需要,還因?yàn)閷懺?shī)和寫小說(shuō)時(shí),我都是站著的。很早以前,我就站著寫了。硬要說(shuō)詩(shī)和小說(shuō)的不同,我認(rèn)為詩(shī)是百米沖刺,小說(shuō)是萬(wàn)米競(jìng)走;詩(shī)是做愛(ài),小說(shuō)是談情;詩(shī)是大海,小說(shuō)是天空;詩(shī)是糧食,小說(shuō)是蔬菜;詩(shī)是陽(yáng)光,小說(shuō)是空氣……還有,我認(rèn)為真正好的小說(shuō)除了故事外都應(yīng)當(dāng)有一顆詩(shī)的內(nèi)核。沒(méi)有詩(shī)核的小說(shuō)如同一張廢紙。
姜:這樣區(qū)別與認(rèn)識(shí)詩(shī)跟小說(shuō),確實(shí)非常到位,也非常準(zhǔn)確。當(dāng)然,更非常形象。
白:我甚至相信:當(dāng)初,我的祖先創(chuàng)造漢字時(shí),每一枚漢字都是按照寫詩(shī)的標(biāo)準(zhǔn)創(chuàng)造的。就是說(shuō),我相信每一枚漢字里都有詩(shī),因?yàn)椋恳幻稘h字都有屬于自己的心靈,不容玷污,不許損毀。誰(shuí)玷污了漢字,誰(shuí)損毀了漢字,最后,那被玷污的被損毀的,只能是他自己。
姜:看來(lái),我們定位你首先是做小說(shuō)的,確實(shí)是錯(cuò)了。
白:其實(shí),很多時(shí)候,我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寫詩(shī)還是在寫小說(shuō)。
其實(shí),很多時(shí)候,我都不清楚自己是誰(shuí):詩(shī)人白連春?農(nóng)民白連春?流浪者白連春?被禁者白連春?
姜:也許,每一個(gè)真正的作家,都會(huì)有這樣的恍惚。
白:若我燃燒,任我灰燼。
若我死了,等我腐爛。
若我侍候莊稼,給我一地球土地讓我流汗,給我十億人民讓我養(yǎng)育。
若我飛,埋下你的臉,看我如何把露珠吻上你的睫毛……
三
姜:我們的對(duì)話中都能有這詩(shī)意的存在。真好。《天有多長(zhǎng)地有多久》不一樣了,徹底拋開(kāi)了詩(shī)味,寫了一個(gè)天長(zhǎng)地久的愛(ài)情故事。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這里的賬可能算錯(cuò)了。小說(shuō)的結(jié)尾,顧小月成了一個(gè)七十多歲的女人,然而,改革開(kāi)放三十年,作為小姐的顧小月,或者作為二奶的顧小月,她的青春時(shí)代應(yīng)該往前推五十年吧?這里的賬,是不是你故意賣出的破綻呢?
白:小說(shuō)的結(jié)局不是在今天,而是在不知道哪一天的明天,因?yàn)樾≌f(shuō)的結(jié)局太完美了。這樣完美的結(jié)局,在今天絕對(duì)是不被允許存在的。所以在這篇小說(shuō)里,實(shí)際上是沒(méi)有時(shí)間的賬的,雖然表面上是按照時(shí)間順序?qū)懙模嬲钊肫渲凶x到最后,你會(huì)發(fā)現(xiàn):在這篇小說(shuō)里,時(shí)間是消散了的,像湖面美麗的水紋終究被風(fēng)帶走了。故事結(jié)束,小說(shuō)并未結(jié)束,心靈之旅在合攏書(shū)之后才開(kāi)始。這篇小說(shuō)表面上沒(méi)有詩(shī),實(shí)實(shí)在在還是一首詩(shī)。
姜:為什么說(shuō)它還是詩(shī)?
白:因?yàn)檫@樣的愛(ài)情故事,在當(dāng)前的人間不被允許存在,根本,只是一個(gè)理想,一個(gè)夢(mèng)想,所以才叫《天有多長(zhǎng)地有多久》。
天有多長(zhǎng)地有多久?是一個(gè)沒(méi)有答案的問(wèn)題。誰(shuí)能回答?除了上帝。
這篇小說(shuō)的意思,或者說(shuō),這首詩(shī)的意思,是:愛(ài)無(wú)限。
姜: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一個(gè)大作家的內(nèi)心是那樣的浩浩茫茫與莽莽蒼蒼。上一次是在與畢飛宇對(duì)話時(shí)感受到的這一點(diǎn)。這次與你對(duì)話,我再次感受到了這一點(diǎn)。這篇作品,看來(lái)你是非常偏愛(ài)的,你用它的題目做了書(shū)名。在我看來(lái),這篇作品主要以時(shí)間為小標(biāo)題來(lái)標(biāo)示一種似水流年與天長(zhǎng)地久。從這一點(diǎn)上看,這應(yīng)該是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篇幅,你卻處理成了中篇。在此,我就想問(wèn)一點(diǎn):你在寫作長(zhǎng)篇《在黑暗中擁抱》、《上帝不在家》時(shí),有沒(méi)有考慮過(guò)將《天有多長(zhǎng)地有多久》寫成長(zhǎng)篇呢?這一問(wèn)也可以這樣說(shuō):在寫作這篇小說(shuō)時(shí),你有沒(méi)有考慮過(guò)把它處理成長(zhǎng)篇?
白:我本詩(shī)人,寫長(zhǎng)篇小說(shuō)實(shí)在太累了,單是語(yǔ)言我就承受不起。何況一部真正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如果沒(méi)有經(jīng)得起時(shí)光磨練的故事細(xì)節(jié)和人生知識(shí),早晚被淹沒(méi)算是好的,成為垃圾也有可能。《天有多長(zhǎng)地有多久》單一個(gè)愛(ài)情故事,處理成長(zhǎng)篇太薄弱了,還得添加次要人物和許多背景環(huán)境的枝枝葉葉,比如像《霍亂時(shí)期的愛(ài)情》、《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赫索格》、《呼嘯山莊》。這樣,這篇小說(shuō)勢(shì)必繁雜。這是我不情愿的。我樂(lè)意這篇小說(shuō)就是,只是,干干凈凈的愛(ài)情故事。
姜:原來(lái)這里深藏著一個(gè)詩(shī)人,呵,一個(gè)小說(shuō)家的“謀略”。
白:我寫作,不管詩(shī),還是小說(shuō),更不管短篇中篇或是長(zhǎng)篇,都不刻意按照技術(shù)層面去寫,而是只求符合我心靈的需要。技術(shù)上來(lái)講,這篇小說(shuō)的材料可以寫成長(zhǎng)篇。我這一生寫過(guò)兩部長(zhǎng)篇,夠了。也許因?yàn)閼校苍S因?yàn)殚L(zhǎng)篇更難發(fā)表,也許因?yàn)橥瓿砷L(zhǎng)篇會(huì)讓我更多的夜晚睡不著,也許更因?yàn)殚L(zhǎng)篇擁有更多的生活和更多的歷史,反正,我不準(zhǔn)備再寫長(zhǎng)篇。我從不認(rèn)為寫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作家優(yōu)越,雖然他們比別的作家更容易獲獎(jiǎng)更容易成為世界作家。
姜:這也是一個(gè)作家的生存狀態(tài)。在你這里,我們感動(dòng)的是,你確實(shí)在為我們這個(gè)世界提供一個(gè)作家的可能性。
白:很多時(shí)候,面對(duì)長(zhǎng)篇小說(shuō),縱然是閱讀,我都會(huì)恐慌。全世界每年不知道要生產(chǎn)出多少部長(zhǎng)篇,其中幾部是真正可以讓人靜下來(lái)讀的小說(shuō)呢?我們的時(shí)代不需要作家,作家太多了;需要讀者,讀者太少了。很多時(shí)候我都懷疑:作家比讀者多。還有多少人真正在讀書(shū)呢?很多作家,自從成為作家后就不再讀書(shū)了。
現(xiàn)在,我寧愿花更多時(shí)間去讀小小說(shuō)。很多小小說(shuō),其心靈的容量足以裝下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休士的小小說(shuō)《感謝您,太太!》,博爾赫斯的小小說(shuō)《死人的對(duì)話》,屠格涅夫的小小說(shuō)《白菜湯》和托爾斯泰的小小說(shuō)《太貴了》都令我震驚,說(shuō)實(shí)話,許多長(zhǎng)篇小說(shuō)還起不到這個(gè)作用。這些小小說(shuō)是珍珠,是金子,而許多長(zhǎng)篇小說(shuō),只是垃圾,是廢墟。
今后,我要向大師們學(xué)習(xí)寫作小小說(shuō)。
姜:我發(fā)現(xiàn)了一點(diǎn),你在寫作中,一直將自己放在一個(gè)非常卑微的角度上。這種姿態(tài),是一種敬畏的姿態(tài)。當(dāng)然,也就有了悲天憫人的心態(tài)。坦率說(shuō),縱觀目前中國(guó)文壇,有著敬畏之心與悲天憫人之情的作家委實(shí)太少了。真正的作家應(yīng)該是懷有敬畏之心與悲天憫人的柔軟的。
白:是的,這個(gè)世界太堅(jiān)硬;作家都不柔軟,就再?zèng)]有人柔軟了。我不知道我把自己放在了非常卑微的角度上。這不是我刻意要放的。這是不知不覺(jué)的,也許,這恰巧就是心靈的姿態(tài)?這種姿態(tài)對(duì)于我是難以抗拒的。為什么這種姿態(tài)我難以抗拒?因?yàn)槲沂且粋€(gè)沒(méi)有野心的人,我從來(lái)沒(méi)有想過(guò)要成為什么,要獲得什么,我只想通過(guò)我的筆說(shuō)出某些被精致隱藏起來(lái)的真相,同時(shí),我也不想說(shuō)教,我不是道德家,我僅僅是選擇了一個(gè)立場(chǎng),即前面說(shuō)過(guò)的:站在泥土一邊,站在莊稼一邊,站在農(nóng)民一邊,還有,加上站在漢字一邊,具體說(shuō),站在父親一邊,站在母親一邊,站在孩子一邊,站在蕓蕓眾生一邊。總之,我是時(shí)刻準(zhǔn)備著站在這一龐大的默默無(wú)聞的人和物一邊的。
我雖然站在他們一邊,并不代表他們,我沒(méi)有資格代表別人,我唯一可以代表的就是我自己。其實(shí),不是我選擇了站在他們一邊,真正的原因是: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中的一分子。我不得不站在他們一邊。我不站在他們一邊就是對(duì)他們無(wú)情的背叛。還有一個(gè)我不好意思說(shuō)出口的原因是:我只有站在他們一邊,這樣,我受到的傷害損毀侮辱才會(huì)減少,甚至減少到零。他們是善良的一群。他們是從不傷害人損毀人侮辱人的一群。他們不僅不傷害我不損毀我不侮辱我,他們還會(huì)保護(hù)我。他們是我的保護(hù)者。他們是我的樂(lè)園。他們是我的心靈。
我沒(méi)有辦法告訴你:他們是如何深入我的肉體,深入我的骨髓,最終成為我的心靈的。
現(xiàn)在我要問(wèn)你:在今天,一個(gè)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如何活下去?一個(gè)還有土地可以種植的農(nóng)民又如何活下去?一個(gè)農(nóng)民老了如何活下去?一個(gè)父親如何活下去?一個(gè)母親如何活下去?一個(gè)孩子如何活下去?特別是那些,那許多,那無(wú)數(shù)留守父親母親和兒童們,他們究竟該如何活下去?
誰(shuí)真正懂得他們?誰(shuí)照亮他們黑暗中悲壯的掙扎?誰(shuí)和他們一起哭泣?
現(xiàn)在,某些世界的作為,某些開(kāi)發(fā)商的作為,是禽獸也不曾干過(guò)的。
我說(shuō)出這些,不是憑思想,不是憑藝術(shù),是憑感情。我是一個(gè)沒(méi)有思想頭腦和藝術(shù)細(xì)胞的人。
我堅(jiān)信:感情遠(yuǎn)比一切思想和一切藝術(shù)干凈、徹底和純粹。
這,就是我更多時(shí)候在寫詩(shī)的原因。詩(shī)是完全釋放感情,而小說(shuō)則要控制感情。
姜:說(shuō)到你的小說(shuō),《背叛》是繞不過(guò)去的。關(guān)于這篇廣為人知的小說(shuō),我們先談一些外圍的東西吧。首先,你是否想以背叛小說(shuō)文本的方式來(lái)一次小說(shuō)的寫作行為上的背叛?
白:老兄誤會(huì)了。我可沒(méi)有想過(guò)自己要背叛什么小說(shuō)文本。《背叛》這篇小說(shuō)實(shí)際上十分傳統(tǒng),從頭到尾都是書(shū)信體,只不過(guò),這是人類最后一個(gè)人,這個(gè)人在小說(shuō)中就叫連春,你可以當(dāng)他是我,也可以不,反正我用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他已經(jīng)死了三十年或者三百年了,然而他從來(lái)沒(méi)有離開(kāi)過(guò)人間一天,上帝不允許他離開(kāi)。那時(shí)候的地球什么都沒(méi)有了,只剩下沙子,到處都是沙子,除了沙子還是沙子。人類最后一個(gè)人連春,每天除了掃沙子,就是給上帝寫信,上帝回人類最后一個(gè)人的信。故事就這么簡(jiǎn)單。
問(wèn)題自己就出現(xiàn)了,為什么人類就只剩下最后一個(gè)人了?什么原因造成的?這人類最后一個(gè)人,他經(jīng)歷了什么?他如何生活?他又如何給上帝寫信?上帝,高高在上的上帝,又如何回復(fù)他的這些,這許多的信?這信的內(nèi)容都寫了些什么?
這些信,這些漢字,最終說(shuō)明的是背叛的后果。這后果是人類最后一個(gè)人也死去三十年或者三百年了。
姜:看來(lái),這里真的深藏著一種宇宙觀了。
白:誰(shuí)背叛了誰(shuí)?在這篇小說(shuō)里,當(dāng)然是人背叛了神,從一開(kāi)始就是。所以,人的結(jié)局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所作所為,人的每一次作為,實(shí)際上,都是對(duì)神的背叛。人背叛神,同時(shí),更是背叛人自己。
因?yàn)槿耸巧裨斓摹R驗(yàn)樯袷菫槿撕玫摹R驗(yàn)槿颂焐怯性旆淳竦摹?/p>
造反有理,不是嗎?造反革命,不對(duì)嗎?
姜:這篇小說(shuō)雖然很是引起了一次討論與爭(zhēng)鳴,但似乎現(xiàn)在已經(jīng)塵埃落定了。多希望有更多的人認(rèn)識(shí)到這篇小說(shuō)多維而深刻的主題,關(guān)心一下這《背叛》中所提到的我們丟失的初心。
白:十分感謝《飛天》雜志發(fā)表這篇小說(shuō),并且組織了評(píng)論家的很多討論和爭(zhēng)鳴。在我這一生中再?zèng)]有哪一家雜志對(duì)我這樣好了。
至于你說(shuō)的多維而深刻的主題,丟失的初心,我反倒有些緊張了。因?yàn)檫@些在我寫作的開(kāi)始,我都是沒(méi)有考慮的。我只是憑著一股激情要反對(duì)世界把人民變成某架機(jī)器上的零碎部件,反對(duì)一切違背自然的行為。我是天生的詩(shī)人,對(duì)生活所知甚少,只知道:人是神造的,自然是神為人造的,若違背了,將有可怕的后果;這后果不是一場(chǎng)或幾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不是死多少人,不是多少人無(wú)家可歸,而是直接導(dǎo)致人類最終毀滅。我們都知道:人類總有一天要?dú)纾瑫?huì)毀滅。我只是將這時(shí)間放到這篇小說(shuō)里了。所以,我給這篇小說(shuō)設(shè)置的人物是人類最后一個(gè)人。
人類最后一個(gè)人,他的孤獨(dú),他的寂寞,他的悲傷,他的絕望,是可想而知的。他把這些全都傾訴給了上帝。他的一生太復(fù)雜了,太被動(dòng)了,有太多話可以傾訴,應(yīng)當(dāng)傾訴。上帝始終耐心地聽(tīng)著。上帝真好。上帝一直沒(méi)有遺棄這最后一個(gè)人,一直管他叫親愛(ài)的孩子,而且,上帝給他的回信永遠(yuǎn)在清晨。清晨,一天中最美好的時(shí)光。
人類最后一個(gè)人,他的一生該多么漫長(zhǎng),漫長(zhǎng)到無(wú)邊無(wú)際的地步。當(dāng)他給上帝寫信,在他心里,他眼里,他筆下:真理和謊言,文學(xué)和生活,歷史和現(xiàn)實(shí),革命和反革命,道德和偽道德,落后和先進(jìn),貧窮和富裕,都已經(jīng)很難區(qū)分了,也可以說(shuō)無(wú)意義了。為什么很難區(qū)分?為什么無(wú)意義?因?yàn)闀r(shí)間太長(zhǎng)了,把這一切混淆了,迷離了,彌散了。
只有好壞,只有善惡,只有忠奸,只有黑白,只有戰(zhàn)爭(zhēng)和平,沒(méi)有對(duì)錯(cuò)。從來(lái),人類就不靠對(duì)錯(cuò)生活。地球是圓的,去羅馬的路有很多條,到達(dá)北京的辦法也數(shù)不清。八國(guó)聯(lián)軍到達(dá)北京的辦法和日本鬼子到達(dá)北京的辦法就不同。我這一生已經(jīng)多次去過(guò)北京了,每一次和上一次到達(dá)的辦法都有區(qū)別,無(wú)所謂對(duì)錯(cuò),只要到達(dá)了就行。
如果硬要說(shuō)錯(cuò),不聽(tīng)上帝的話,就是錯(cuò)。
關(guān)鍵是有個(gè)別人,這樣的人不少,總自以為自己是上帝。人類的毀滅就是這些自以為是上帝的人帶來(lái)的。
沒(méi)有人可以自以為是上帝。上帝是自然。上帝是宇宙。上帝是靈魂。上帝從來(lái)不是某一個(gè)人,哪怕這個(gè)人再偉大。人自以為是上帝,就是對(duì)人自己同時(shí)也是對(duì)神最大的背叛。
復(fù)雜嗎?不。簡(jiǎn)單嗎?不。
我在這篇小說(shuō)的開(kāi)篇引用的瑞典詩(shī)人特朗斯特羅姆的詩(shī)《論歷史》,似乎可以很形象地說(shuō)明一些問(wèn)題:
仿佛有人在遠(yuǎn)處掀動(dòng)被單,
這就是歷史:我們的現(xiàn)在。
我們下沉,我們靜聽(tīng)。
姜:除了主題多維而深刻之外,小說(shuō)本身那種想象力異彩紛呈,確實(shí)令人佩服。你在小說(shuō)中的想象力,可能與你的詩(shī)歌寫作有關(guān)。我于是發(fā)現(xiàn),《背叛》這一篇小說(shuō),同樣洋溢著一種詩(shī)性。雖然這種詩(shī)性帶著一種激越,一種傷感、絕望。真想問(wèn)一下,你是在一種什么樣的靈感刺激下寫成這篇作品的?
白:所謂靈感,即我前面說(shuō)到的緣分。一篇小說(shuō)或一首詩(shī),她本身就是存在著的,在時(shí)間和空間的某處,一直在等待著作家或詩(shī)人把她呈現(xiàn)出來(lái)。實(shí)際上,是這篇小說(shuō),不,不止這篇小說(shuō),我所有的文學(xué)作品都是:是她們找到我的,不是我把她們寫出來(lái)的。她們本身在那里,恰巧被我遇見(jiàn)了。
當(dāng)然,我一生在我的祖國(guó)之內(nèi)四處流浪,也一直在尋找我小說(shuō)里的人物。同樣,我小說(shuō)里的人物也在尋找我。我們遇上,一篇小說(shuō),就誕生了。
我的小說(shuō)總是先有人物,然后這個(gè)人物告訴我他的故事。
他說(shuō),我寫,小說(shuō)就成了。
不需要靈感。靈感是什么?我不懂。靈感被一些人說(shuō)得十分微妙。我一直認(rèn)為靈感是那些老師拿來(lái)蒙學(xué)生的,是騙人的。
小說(shuō)和詩(shī)歌一樣,和別的文學(xué)作品一樣,需要的是生活,是作家在世界上不停地奔走,尋找他的人物。出于同樣的原因,這些小說(shuō)里的人物,也在世界上不停地奔走,尋找可以把他們寫出來(lái)的作家。
靈感就是你在這樣奔走的時(shí)候,停下來(lái),看一看身邊的人,愛(ài)一愛(ài)身邊的人,或許,這個(gè)人恰巧就是你的人物呢,是不是?
隨便說(shuō)一下,想象力是天生的,就像詩(shī)人是天生的,一樣。
好詩(shī)和好小說(shuō),也是天生的。
那些小說(shuō)技巧,那些詩(shī)歌技巧,當(dāng)你在寫作的時(shí)候,一定要徹底拋在一邊,不然,你就是另外一架機(jī)器。冷冰冰的機(jī)器。我們的世界機(jī)器已經(jīng)太多了。
寫作需要的是血,熱血,越熱的血越好,越熱的血越感人,熱到睡不著,熱到沸騰。寫作不需要冷冰冰的機(jī)器。
我反對(duì)機(jī)器。
姜:《背叛》這個(gè)中篇,應(yīng)該屬于中國(guó)當(dāng)代中篇的里程碑之作。我這絕不是恭維。然而,在我們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生態(tài),已經(jīng)頗為不堪了,真正的好作品無(wú)法讓更多的讀者讀到,而一些善于“運(yùn)動(dòng)”的作家們,卻可以將一篇篇平庸的作品送到讀者面前。
白:謝謝老兄表?yè)P(yáng),從來(lái)沒(méi)有誰(shuí)說(shuō)過(guò)我是里程碑。不知老兄和別的作家對(duì)話時(shí),是不是也這樣說(shuō)?我大約瀏覽了一下老兄在我之前對(duì)過(guò)話的作家,至少一百位了。我看見(jiàn)在我的前面有許多已經(jīng)是真正的大師了。我真應(yīng)該在和你對(duì)話前,把那些對(duì)話都復(fù)制下來(lái)好好讀一讀,免得自己開(kāi)黃腔。
開(kāi)黃腔,老兄懂嗎?四川話。說(shuō)起四川話,我寫作時(shí)很少運(yùn)用。許多時(shí)候我是刻意不用的。忘了早年看過(guò)哪位前輩作家說(shuō)的,少用家鄉(xiāng)土話,多用普通話寫作,我以為他說(shuō)得有道理,因?yàn)樽骷也皇峭茝V家鄉(xiāng)土話的,作家沒(méi)有這個(gè)使命,說(shuō)到底,其實(shí)作家沒(méi)有任何使命。作家寫作是作家自己的事,誰(shuí)給的作家使命呢?作家沒(méi)有這個(gè)權(quán)力。當(dāng)然,可以換一種說(shuō)法,把使命說(shuō)成是義務(wù)。然而無(wú)論哪種說(shuō)法,縱然是義務(wù),我以為作家也沒(méi)有。
作家寫作,如果是小說(shuō),我想應(yīng)當(dāng)提供的只是人性,而詩(shī)歌則是激情。如果一篇小說(shuō),在故事里或故事背后沒(méi)有人性,這小說(shuō)無(wú)論運(yùn)動(dòng)得多好,都是平庸的,同樣,如果一首詩(shī),里面不含激情,也無(wú)論運(yùn)動(dòng)得多好,照樣平庸。
一個(gè)人有一個(gè)人的人性,一個(gè)世界有一個(gè)世界的人性。每個(gè)人的人性不同,每個(gè)世界的人性也不同。或許,一個(gè)人在不同階段,他的人性也是不同的。或許,一個(gè)世界在不同時(shí)期,它所容包的人性也是變化的。什么帶來(lái)的這不同?什么引起的這變化?如何不同?怎樣變化?作家要寫出這不同,要寫出這變化,照實(shí)寫呢,還是批判著寫,還是表?yè)P(yáng)著寫?這,反映了作家的立場(chǎng)。作家的寫作應(yīng)當(dāng)揭示出不同變化的真相,而不是維護(hù)不同變化的謊言。然而什么為真相什么是謊言?需要作家自己辨察和判斷。在這辨察和判斷中,讀者可以讀出作家的心。因?yàn)檫@里面包含著善惡好壞黑白是非曲直。這善惡好壞黑白是非曲直是不容半點(diǎn)混淆的。
有時(shí)候?yàn)榱藢懗鋈诵裕骷冶仨殑?dòng)用方方面面的知識(shí),宗教的,政治的,天文的,戰(zhàn)爭(zhēng)的,歷史的,現(xiàn)代的,城市的,鄉(xiāng)村的,等等。
我熱愛(ài)的美國(guó)詩(shī)人費(fèi)羅斯特曾說(shuō)過(guò):“作者不流淚,讀者不流淚。作者不驚奇,讀者不驚奇。”同時(shí),他還說(shuō):“不管多么悲傷,不許憂傷,哀而不傷。”這就涉及到作家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在小說(shuō)里不能感情泛濫,在詩(shī)里也不能。
一篇作品完成了,高明的作家應(yīng)當(dāng)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為平庸之作。
比平庸之作更可怕的是垃圾之作。我們今天的文壇被這些東西充滿了。為什么平庸之作和垃圾之作很多?因?yàn)檫@是一個(gè)權(quán)力和金錢的時(shí)代。
作家,歌頌權(quán)力者最終會(huì)得到權(quán)力,鉆營(yíng)金錢者最終也會(huì)得到金錢,而這些和真正的寫作無(wú)關(guān)。
世界很大,遼闊無(wú)邊,應(yīng)當(dāng)允許部分作家這樣。只是,我,不這樣。權(quán)力我喜歡嗎?喜歡。金錢我喜歡嗎?喜歡。喜歡歸喜歡,我不刻意追求,更不扭曲自己去得到。
姜:《背叛》的先鋒性是非常強(qiáng)烈的。我繼而讀到的《作為故鄉(xiāng)的北京》,在風(fēng)格上似乎與其有著很多接近。
白:《背叛》的故事發(fā)生在人類末日,全世界只剩下最后一個(gè)人,而且這個(gè)人已經(jīng)死了三十年或者三百年了。《背叛》寫的是未來(lái),而通篇都是回憶。《作為故鄉(xiāng)的北京》寫的是過(guò)去,而故事發(fā)生在今天。今天的人如何回到過(guò)去?不是回憶,是行動(dòng)。在這篇小說(shuō)里,人物是要回到1969年去。為什么要回到1969年?因?yàn)椋?969年的北京是我們的故鄉(xiāng)。1969年發(fā)生了什么?后來(lái)的許多年又發(fā)生了什么?我們能回去嗎?我們回去做什么?這不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跟風(fēng)的穿越故事。這篇小說(shuō)我寫得很早,早到那時(shí)穿越還不流行。真正的好小說(shuō)發(fā)表是十分困難的。等到我的這篇小說(shuō)發(fā)表的時(shí)候,穿越已經(jīng)登陸中國(guó)了。
為什么我寫了這樣一篇關(guān)于北京的小說(shuō)?因?yàn)樵缒晡覠嵫獩_動(dòng),去了革命圣地延安,這次延安之旅,我碰到幾位從北京來(lái)到延安的知青。他們一直留在延安,再也無(wú)法回到北京了。他們的生活當(dāng)然是很困苦的。他們理直氣壯地成了我這篇小說(shuō)里的人物。然而,我的故事沒(méi)有直接寫他們,是寫他們都死了,他們的孩子,如何回到北京。他們回北京的愿望實(shí)現(xiàn)不了,要他們的孩子替他們實(shí)現(xiàn)。
每一個(gè)離開(kāi)故鄉(xiāng)的人,他的一生都在想如何回到故鄉(xiāng)。然而,故鄉(xiāng)遠(yuǎn)不是他離開(kāi)時(shí)的故鄉(xiāng)了。就是說(shuō),無(wú)論他多么努力,他都是回不去的。作為作家我是清楚的,但是作為小說(shuō)里的人物他是不清楚的,所以,他執(zhí)迷不悟地要回到故鄉(xiāng)。于是故事就出來(lái)了,小說(shuō)就誕生了,作家和人物都無(wú)法逃避。
一系列問(wèn)題于是也無(wú)法逃避:我們?yōu)槭裁匆x開(kāi)故鄉(xiāng)?誰(shuí)要我們離開(kāi)故鄉(xiāng)的?我們離開(kāi)后誰(shuí)把我們的故鄉(xiāng)怎么了?換個(gè)更流行的說(shuō)法:誰(shuí)動(dòng)了我們的故鄉(xiāng)?他怎么動(dòng)的?他把我們的故鄉(xiāng)動(dòng)成什么樣子了?這動(dòng)了我們故鄉(xiāng)的人為什么要?jiǎng)游覀兊墓枢l(xiāng)?憑什么他可以動(dòng)我們的故鄉(xiāng)?
有些人的故鄉(xiāng)千年未變,有些人的故鄉(xiāng)短短幾年就面目全非了。
可笑的是,面目全非不叫面目全非,叫面目一新。什么是新?什么是舊?也許在你看來(lái)是新,在他看來(lái)恰巧是舊,也不是不可能。
你說(shuō)到風(fēng)格,我倒不以為《背叛》和《作為故鄉(xiāng)的北京》有多接近,你說(shuō)她們接近,是指她們不像《拯救父親》和《母親萬(wàn)歲》那樣寫實(shí)吧?其實(shí),這兩篇小說(shuō),我仍舊是寫實(shí)的。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寫實(shí)的,包括我最近剛完成的《我死后那些事兒》。
姜:《作為故鄉(xiāng)的北京》似乎與《二十一世紀(jì)的第一天》有相互嵌入的關(guān)系。或者說(shuō),《作為故鄉(xiāng)的北京》也寫到了苦難。這篇小說(shuō),誠(chéng)如你所言,它挑戰(zhàn)著所有讀者的想象力,挑戰(zhàn)著所有讀者內(nèi)心深處最為黑暗的地方。這可能是到目前為止,很多評(píng)論家對(duì)這篇小說(shuō)諱莫如深的地方。坦率說(shuō),像我,也只是用心在感覺(jué)這部作品中的黑暗、殘酷、無(wú)奈與痛苦的。
白:你提到了《二十一世紀(jì)的第一天》,僅是點(diǎn)到即止。這篇小說(shuō)和我別的小說(shuō)一樣,也是先有人物的。這篇小說(shuō)里的人物是我的一個(gè)老師,叫王杰軍。這老師的形象和名字,我照樣搬進(jìn)了小說(shuō),即小說(shuō)里的祖父。小說(shuō)里,那孫子實(shí)際上就是我,他的名字我都懶得改,就叫春兒。這篇小說(shuō),我可以肯定地說(shuō),是我們中國(guó)最早寫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的。2001年10月就發(fā)表在了《中國(guó)作家》上,還不早嗎?那時(shí)“留守”這個(gè)詞還未被創(chuàng)造出來(lái)。一個(gè)留守老人和一個(gè)留守兒童他們一天的故事,這一天是二十一世紀(jì)的第一天;講這一天,農(nóng)民進(jìn)城賣菜的遭遇。這一天,看看他們,那些高高在上的城市管理者們都對(duì)農(nóng)民做了什么?他們做的,前面已經(jīng)說(shuō)過(guò),是禽獸都不曾干過(guò)的。這些所謂的城市管理者們,他們禽獸不如。當(dāng)然,現(xiàn)在的狀況已經(jīng)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這一點(diǎn)必須肯定。農(nóng)民進(jìn)城不再受到像以前那么多的歧視了。現(xiàn)在,我們把暫住證換成居住證了。說(shuō)到底,即使今天,農(nóng)民和城市居民還是不一樣。這就是不公平。
至于老兄你說(shuō),評(píng)論家不評(píng)論我的小說(shuō)《作為故鄉(xiāng)的北京》,我倒不以為然。為什么?因?yàn)槲覐膩?lái)不是一個(gè)被評(píng)論家關(guān)注的作家。
經(jīng)你這樣一說(shuō),我現(xiàn)在才發(fā)現(xiàn),這篇小說(shuō)是有那么一點(diǎn)黑暗、殘酷、無(wú)奈與痛苦,然而在我寫作的時(shí)候,我并未感受到這些。
在我寫作的時(shí)候,我唯一做的,就是把這個(gè)故事原原本本地講出來(lái)。這個(gè)故事不普通,它是發(fā)生在離開(kāi)北京的知青的孩子們身上的。
在孩子們身上,什么故事不能發(fā)生?
姜:《作為故鄉(xiāng)的北京》有著極強(qiáng)的時(shí)空感與虔誠(chéng)的宗教感,還有一種極為黑暗的罪惡感。這篇作品里出現(xiàn)的北京、外國(guó)人、信使、火車、1969等,似乎都有著極其厚重的內(nèi)涵,說(shuō)它們是一系列符號(hào),可能還真不很恰當(dāng)。
白:在我的作品里,所有漢字都不代表符號(hào)。沒(méi)有一個(gè)漢字我是當(dāng)符號(hào)來(lái)寫的。符號(hào)是死的東西,而所有漢字都是活生生的生命體,和人一樣,漢字的生命——甚至,肯定——比寫作的作家的生命還長(zhǎng)久。
也許別人讀我的小說(shuō)時(shí),會(huì)把某些特定的文字當(dāng)符號(hào),這,是我沒(méi)有辦法的事。這些被當(dāng)成符號(hào)的漢字,也可以說(shuō),她們都是有一些象征意義的。
至于兄說(shuō)到這篇小說(shuō)有黑暗的罪惡感,我不知道,也許,有黑暗的罪惡感的人,會(huì)讀出黑暗的罪惡感來(lái)吧?啊,我不是說(shuō)老兄有黑暗的罪惡感。老兄的意思我懂,你是說(shuō)我的小說(shuō)揭示了一種黑暗的罪惡感。有黑暗的罪惡的不是讀者,而是產(chǎn)生這篇小說(shuō)的時(shí)代。
說(shuō)到時(shí)代,并不是所有時(shí)代我都不喜歡的。還是有我喜歡的時(shí)代。我喜歡沒(méi)有汽車的時(shí)代。我喜歡坐火車可以開(kāi)窗的時(shí)代。那些時(shí)代,人們坐火車能夠呼吸到田野里的新鮮空氣,現(xiàn)在坐火車只能聞到臭烘烘的味道,進(jìn)入車廂很久我的頭都痛。我完全相信我們目前的世界再?zèng)]有比火車更臭的東西了。火車?yán)锏某粑墩f(shuō)到底是人散發(fā)的,臭的還是人。可是為什么當(dāng)我在原野上,在大地上,行走,碰到任何一個(gè)人,無(wú)論男女老少,都是聞不到臭味的呢?是什么把人變臭了呢?真的是現(xiàn)在的火車嗎?誰(shuí)能告訴我?
在沒(méi)有汽車的時(shí)代,人們靠馬和毛驢出門遠(yuǎn)行。真好。阿凡提騎毛驢。俠客們都騎馬。當(dāng)然強(qiáng)盜們也騎馬。在俠和盜中間是俠盜,我覺(jué)得當(dāng)一個(gè)俠盜很好。中國(guó)是否有俠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個(gè)外國(guó)的俠盜叫羅賓漢。還有許多海盜實(shí)際上也是俠盜。
我堅(jiān)信早年的李白是騎馬的,早年的杜甫則可能騎毛驢。為什么?因?yàn)槎鸥](méi)有李白有錢,李白拿來(lái)喝酒的錢都比杜甫拿來(lái)吃飯的錢多,而且杜甫遠(yuǎn)不如李白瀟灑。那個(gè)時(shí)代給杜甫的苦難太多了。杜甫一定不喜歡他所在的那個(gè)時(shí)代。
我聽(tīng)說(shuō),就是現(xiàn)在,一個(gè)叫芬蘭的國(guó)家,應(yīng)該不是很小的國(guó)家吧,整個(gè)國(guó)家只有四輛公車。我還看見(jiàn)過(guò)紐約市市長(zhǎng),就是現(xiàn)在的,天天騎自行車上下班的照片。紐約市,比我家鄉(xiāng)的市不知大多少倍。也許紐約市市長(zhǎng)上班就是坐在辦公室看報(bào)紙吧?不然,他怎么有那么多的精力騎自行車?
乖乖,扯得太遠(yuǎn)了。打住。
姜:新作《泥巴泥巴》里的“他”與“她”,可能倒是有著符號(hào)學(xué)的意味。而泥巴作為一種意象,似乎又讓人感覺(jué)到,你又開(kāi)始回到詩(shī)性的追求上了。這是一篇雖然仍然充滿了痛苦,但是卻非常明亮的小說(shuō)。
白:我最近的作品《泥巴泥巴》發(fā)表在《黃河文學(xué)》上。整篇小說(shuō)什么都沒(méi)有寫,除了一個(gè)人對(duì)泥巴的愛(ài)。一篇單寫愛(ài)的小說(shuō),而且是一個(gè)人對(duì)泥巴的,肯定故事性不強(qiáng),讀者很少。現(xiàn)在,除了我小說(shuō)里的人物和作為作者的我,誰(shuí)還關(guān)心泥巴?
然而,沒(méi)有泥巴,我們的世界建筑在哪里?這篇小說(shuō)的主題仍舊是反映土地問(wèn)題和農(nóng)民問(wèn)題的。這個(gè)問(wèn)題只要我寫作就無(wú)法逃避。
我堅(jiān)信:就像詩(shī)歌離開(kāi)情感就不存在,小說(shuō)離開(kāi)人物就不存在,道德離開(kāi)真話就不存在,高尚離開(kāi)善良就不存在;世界離開(kāi)了土地,照樣也不會(huì)存在。
對(duì)于這個(gè)問(wèn)題的追根究底,任何時(shí)候,無(wú)論什么條件下,我都是不會(huì)妥協(xié)的,更不會(huì)投降。前面說(shuō)了,我要一生,永生,站在泥土一邊,站在莊稼一邊,站在農(nóng)民一邊。
你說(shuō)這篇小說(shuō)明亮,也許吧,在我寫作的時(shí)候,我只想寫得干凈一些,干凈一些,再干凈一些。因?yàn)橐粋€(gè)人對(duì)泥巴的愛(ài),必須,自始至終,都像泥巴本身一樣,干凈。
全世界的物質(zhì)中,我以為泥巴最干凈。一個(gè)人在人間辛苦勤勞一生,死了,能夠埋進(jìn)泥巴里是最幸福的事,是對(duì)這個(gè)人一生最大的獎(jiǎng)勵(lì)。這,實(shí)際上,本來(lái)應(yīng)當(dāng)是最低的要求,現(xiàn)在,對(duì)于普通人來(lái)說(shuō),都無(wú)法實(shí)現(xiàn)了。
因?yàn)椋厍蛏希喟驮絹?lái)越少,就快沒(méi)有了。
不少人在活著時(shí),就把墳地買好了,花幾十萬(wàn)甚至上百萬(wàn)上千萬(wàn)。這,是普通百姓無(wú)法辦到的。
四
姜:最后部分,我們花點(diǎn)時(shí)間談?wù)勛骷野走B春。有人說(shuō)過(guò),除了文學(xué),白連春一無(wú)所有。
白:朋友曾說(shuō)我一無(wú)所有,其實(shí)不過(guò)是形容,夸大了,我并非一無(wú)所有。一我有單位,我的單位是四川省瀘州市江陽(yáng)區(qū)文化館,領(lǐng)導(dǎo)對(duì)我很好,按月給我發(fā)著工資。工資不多不少,然而足夠衣食無(wú)憂。同時(shí),我還在給《北京文學(xué)》打工,《北京文學(xué)》這家我早年在北京打工過(guò)的雜志,我離開(kāi)了,回四川了,仍舊沒(méi)有開(kāi)除我。除了領(lǐng)導(dǎo)對(duì)我的關(guān)心和照顧,我說(shuō)不出別的理由。絕對(duì)不是因?yàn)槲矣胁牛任矣胁诺娜藬?shù)不清。絕對(duì)不是因?yàn)槲矣嘘P(guān)系,比我關(guān)系深厚的人同樣數(shù)不清。這樣,我才可以靜下來(lái)寫作,寫詩(shī)歌寫小說(shuō),還有別的,比如逢年過(guò)節(jié),市里區(qū)里演出,我寫點(diǎn)串詞。串詞都是簡(jiǎn)單的,歌頌的,一聽(tīng)就懂的。二我有住的地方,雖然在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家鄉(xiāng),我失去了土地和房子,但我仍舊有住處,我住著我二弟大女兒的房子,她的房子我出的裝修錢,算是租金。我沒(méi)有住在山洞里,我沒(méi)有浪跡天涯。我的出生地土地被占,房子被拆,所有人,包括警察,鄉(xiāng)政府職員,教師,遠(yuǎn)嫁外省的女人,假結(jié)婚者,想盡辦法把戶口弄到了當(dāng)?shù)氐男涡紊娜耍嫉玫搅朔颠€房,只有我一個(gè)詩(shī)人未得到。我曾威脅有關(guān)人員,到我五十歲還不賠我房就再次跳長(zhǎng)江(我十五歲那年跳過(guò)一次),眼看我就五十歲了,我不真的跳,只是說(shuō)說(shuō)罷了。幸福生活我還沒(méi)過(guò)夠哩。三我有親人,我祖父祖母去世了,我父親去世了,我外婆去世了,我母親還活著,我還有幾個(gè)兄弟,關(guān)系不好不壞不痛不癢,真有事情來(lái)了誰(shuí)也幫不上我的忙,還得自己扛著。我一直獨(dú)自生活。四我有很多朋友,其中不少朋友稱得上知音了,比如廣州的黃榮,四川的張宗政和鐘正林。五最重要,我有夢(mèng)想,這夢(mèng)想是我對(duì)幸福的渴望,我堅(jiān)信自己總會(huì)幸福的,我堅(jiān)信自己一直是幸福的。
姜:我在前面也說(shuō),別人是將文學(xué)投入人生,你是將人生投入文學(xué)。文學(xué)是你的全部。在這樣的年代,作出這樣的選擇,不唯需要勇氣,需要虔誠(chéng),需要決心,還需要一種我說(shuō)不出來(lái)的品質(zhì)。是一種什么品質(zhì),這是要你給我們說(shuō)說(shuō)的。
白:你說(shuō)我將人生投入文學(xué)比較準(zhǔn)確,因?yàn)榻^對(duì)是由于文學(xué),我現(xiàn)在仍舊一個(gè)人,無(wú)妻無(wú)子,今后很長(zhǎng)時(shí)間還會(huì)一個(gè)人,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學(xué)上。
我有什么品質(zhì)?很難說(shuō)。我不知道我具體有什么品質(zhì),也許就是不放棄,不妥協(xié),不投降吧?雖然物價(jià)飛漲,雖然別人都成雙成對(duì)妻子孩子一大家子,雖然街上汽車很多沒(méi)有一輛是我的,雖然我寫作幾十年仍舊名氣很小,甚至漸漸被遺忘了。
話說(shuō)回來(lái),這些,這一切,我擁有的和我沒(méi)有的,我不曾付出一丁點(diǎn)兒代價(jià)。
舉手之勞,甚至舉手之勞也不勞,差不多可以算是不勞而獲吧。想想自己竟然不勞而獲了如此多的珍寶,還不滿足,從我身上,就看出了人心之不足。我就感到自己很可恥,很無(wú)恥,很羞愧,很無(wú)地自容。
而且,我還有臉活著,每天都大口大口地呼吸我祖國(guó)的空氣,每天早中晚都吃三頓我祖國(guó)農(nóng)民奉獻(xiàn)的糧食和蔬菜,很多比我小得多的人早死了。
像我這樣一個(gè)人,能有什么好品質(zhì)呢?
姜:你對(duì)自己的作品如何評(píng)價(jià)?
白:不說(shuō)世界,單在今天的中國(guó),最少有一百位作家的作品比我好很多。這些作家在我之前,你已經(jīng)和他們對(duì)話過(guò)了。
姜:我們都知道,你是一個(gè)病人。你覺(jué)得你身上的病痛,對(duì)你的寫作起了一種什么影響?對(duì)了,說(shuō)到這里,我想問(wèn),真正影響你走向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之路的作家與作品是哪些?卡夫卡,或者,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我覺(jué)得,你應(yīng)該是中國(guó)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很多作品的風(fēng)格也非常接近。不知我這樣的判斷是不是到位而又合你的感覺(jué)?
白:全世界所有人都是病人,每個(gè)人都有這樣那樣的病,我沒(méi)有什么特別的。忘了什么時(shí)候,我在電視和報(bào)紙上先后看到:一個(gè)五歲女孩得了肝癌晚期,沒(méi)治了,只能等死。醫(yī)生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問(wèn)女孩母親孩子平常愛(ài)吃什么?母親回答醫(yī)生,孩子愛(ài)吃三種食品:一方便面,二火腿腸,三可樂(lè)。就是這三種中國(guó)人民愛(ài)吃的食品使一個(gè)年僅五歲的女孩得了肝癌晚期。可樂(lè)嗎?不可樂(lè)。我們的世界為什么不想想:究竟哪里出了問(wèn)題?為什么到了今天人人都是病人?人有多少種病,我懶得舉例,我沒(méi)有這個(gè)義務(wù),我不是研究病的專家,沒(méi)有發(fā)言權(quán)。可是,我實(shí)在忍不住要問(wèn):那些專家,那無(wú)數(shù)的專家都干什么去了?拿著昂貴津貼的專家們,為什么不為了人民把好食品的關(guān),要讓人民吃了得數(shù)不清的病?不說(shuō)了,再說(shuō)我要?dú)庵约毫恕N覟槭裁茨脛e人的錯(cuò)誤氣自己?
影響過(guò)我的作家數(shù)不清。中國(guó)的白居易、杜甫、李白、蘇東坡、李清照、蒲松齡、汪曾祺,外國(guó)的弗羅斯特、惠特曼、聶魯達(dá)、里爾克、葉賽寧、龐德、艾略特、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福克納、海明威、西蒙、薩特、杜拉斯、格里耶、莫泊桑、都德、契訶夫、納博科夫、高爾基……太多了,數(shù)不過(guò)來(lái)。但是,我想告訴你的是影響我最多最深的三個(gè)人,兩個(gè)老外一個(gè)祖先,一是法國(guó)畫家米勒,二是智利女詩(shī)人米斯特拉爾,三是沙張白,清朝詩(shī)人。
你稱我是中國(guó)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把我抬得太高了,會(huì)摔傷我的。俄羅斯作家偉大的很多,陀斯妥耶夫斯基我并無(wú)特別偏愛(ài),記得讀過(guò)他四本書(shū)《罪與罰》、《白癡》、《地下室手記》、《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相反,俄羅斯的蒲寧,我更喜歡。蒲寧把俄羅斯的鄉(xiāng)村寫得太絕了。也許我是從鄉(xiāng)村出來(lái)的吧。蒲寧的小說(shuō)和詩(shī),我能找到的都找來(lái)讀了。俄羅斯作家美國(guó)作家法國(guó)作家德國(guó)作家意大利作家甚至朝鮮作家,更多更重要的拉丁美洲作家,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無(wú)法磨滅的烙印,其中很多人已經(jīng)流淌進(jìn)了我的血液中。
姜:最近在文學(xué)上有什么動(dòng)作?
白:沒(méi)有特別安排,我是個(gè)隨意的人,遇到好題材就寫,遇不到就不寫。說(shuō)到好題材,先打個(gè)廣告,我最近決定寫一篇對(duì)于我同樣十分重要的小說(shuō),題目叫《請(qǐng)告訴我我的父親究竟是誰(shuí)?》,內(nèi)容是一個(gè)七十歲的老太太尋找父親的故事。她要在死前知道她的父親是誰(shuí)。從她記事起,她就在尋找她的父親。她找了一生,求了數(shù)不清的人,都沒(méi)有人告訴她。她的父親是個(gè)謎。因此,她自己也是個(gè)謎。她想破解這個(gè)謎,在她死前。
一個(gè)人活了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shuí),是不是很悲哀?這事就發(fā)生在我的身邊。
誰(shuí)能告訴她她的父親是誰(shu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