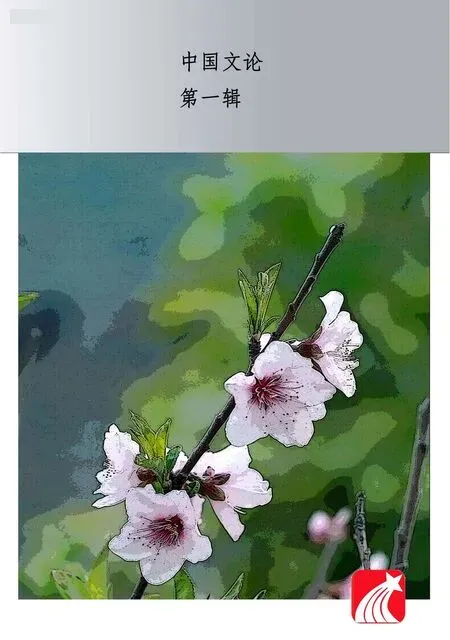《劉子》研究三十年
陳志平
《劉子》研究三十年
陳志平
筆者是在2011年武漢大學舉行的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百年龍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加入本學會的,在那次會議上,我和臺灣的游志誠、山東的朱文民分在了一個討論小組,游志成和朱文民提交的論文均和《劉子》有關,然其他入會代表均表示對此問題毫無研究,所以也無從討論。對此,我感到十分的詫異,一方面,改革開放后《劉子》作者問題研究已經推進了一大步,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該書和劉勰有關聯,這需要《文心雕龍》學者的積極回應;另一方面,《文心雕龍》研究的一些重要參考書如《文心雕龍學分類索引》在論文部分“劉勰生平和著作”和“專著”部分均附錄有關《劉子》的研究成果;作為《文心雕龍》研究的參考書之一,《劉子》也是研究《文心雕龍》時應該翻閱的,怎么能說毫無研究呢?會上游志誠妙語連珠,展示了學貫《文心雕龍》、《劉子》的深厚功力,引來入會代表的陣陣掌聲,也讓我見識了臺灣學者的學術態度。相較而言,有的大陸學者的學術視野則略顯狹隘。我覺得,無論是否承認《劉子》為劉勰創作,既然有歷史記載,有學者舉證,作為權威的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的會員就應該有所了解和回應,這總比做學術上的“鴕鳥”要好。
當時很多代表以不熟悉、不了解回避了對《劉子》的討論,說明《劉子》這部書對于學界還是很生僻的,其研究成果也不太為人注意,所以筆者想對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劉子》研究略作介紹(偶爾兼涉臺灣),一方面是應此次大會主題之景,另一方面也是想引起大家對此書的注意。
據《劉子集校合編》附錄三《劉子研究論著索引》,自1984年至2011年,共發表與《劉子》有關的論文86篇,其中21篇是關于作者問題的討論;碩士、博士論文5篇;出版專著10部,其中7部是文獻整理。可見,在目前的《劉子》研究中,作者考證和文本整理占的比重很大;而在思想研究方面,則存在明顯的不足。
一、《劉子》作者研究論爭激烈
《劉子》最早見錄于《隋書·經籍志》,無撰者姓名。于是《劉子》的作者是誰,就成為《劉子》研究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也是爭論最多、分歧最大的問題。從唐代至現在,共有九種說法:一、西漢末年劉歆作,二、東晉時人作,三、梁劉孝標作,四、劉勰作,五、劉晝作,六、袁孝政作,七、貞觀以后人作,八、金人劉處玄作,九、明人偽撰說。唐張鷟《朝野僉載》和“最早”為《劉子》作注的“唐代”袁孝政認為是北齊劉晝著,兩《唐書》著錄為梁劉勰撰。此后,“劉晝撰”和“劉勰撰”兩說成為最主要的看法,在后代爭論不休。20世紀三四十年代,余嘉錫、楊明照等人認為該書是北齊劉晝作,此觀點一度為人們所接受。改革開放后,林其錟、陳鳳金和朱文民力主梁劉勰撰,程天祜、傅亞庶、陳應鸞則認為劉晝作,另外還有人提出劉遵撰,甚至有人提出“別有一劉姓”作者。諸人對《劉子》作者問題均發表了很好的意見,雖然至今看法還沒有統一,卻有力地推進了這一問題的研究。
1937年,楊明照在《文學年報》第三期上發表了《劉子理惑》,力排《劉子》為劉歆、劉孝標、劉勰、袁孝政作,認為是北齊劉晝作,證據有二:(1)《北齊書·劉晝傳》載“晝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后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楊認為“以晝自言數十卷書計之,《劉子》必在其中,于數始足(《高才不遇傳》四卷、《帝道》若干卷、《金箱璧言》若干卷、《六合賦》若干卷,再益以《劉子》十卷,差足云數十卷書)”。(2)傳稱晝“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今以《劉子》全書驗之,其緝綴辭藻與言甚古拙,皆極為顯著。
20世紀80年代,林其錟、陳鳳金出版了《劉子集校》、《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兩書,均題劉勰撰,并撰文《論〈劉子〉作者問題》、《劉子作者考辨》詳細論證《劉子》的作者為劉勰。
首先,林其錟、陳鳳金認為四庫館臣的反對意見不足塙證《劉子》不出于劉勰之手。(1)針對前人提出《劉勰傳》除《文心雕龍》,不見更載別書,林其錟、陳鳳金認為“既然史載有‘文集行于世’,又有這么多未被本傳列舉現已證實是劉勰著作的書文例證,怎么不可以認為《劉子》五十五篇亦屬其‘文集’的一部分呢?”(2)關于“北音”問題,林其錟、陳鳳金認為兩部書談問題的前提是不同的,《文心》談的是“樂”的起源,《劉子》談的是“淫樂”的起源,所以采取了不同來源的說法。(3)關于勰長于佛理,《劉子》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問題,林其錟、陳鳳金認為應該聯系南朝的社會思潮、學術風氣以及劉勰生平和思想變化來加以考察。南朝門閥等級制度森嚴和晉代以降,儒釋道彼此對立,又互相滲透的時代特點給劉勰的思想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在其著作中留下了痕跡。從《文心》看,劉勰只是反對道教,不反對道家,并且有玄佛并用的色彩。
其次,林其錟、陳鳳金認為劉晝是不可能寫出《劉子》的。(1)今能直接見到的唐人著錄,一致認為《劉子》的作者是劉勰。尤其是敦煌遺書《隨身寶》中有“流子,劉協注”和《一切經音義》有劉勰著書四卷,名《劉子》的記載。(2)《劉子》的思想內容同劉晝的身世、思想不一致。劉晝是典型經生,沒有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社會實踐經驗,且文風古拙,而《劉子》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廣泛領域,語言淺顯輕蒨,兩者對不上號。劉晝性格孤高、不阿權貴,怎么能夠設想會在《劉子》一書寫出公然論證并鼓吹投靠權貴、攀附達官以成其事的篇章?劉晝詆佛,《劉子》找不到任何詆佛的思想言論;相反,后世佛徒釋道反把《劉子》引為同調。(3)更主要的是,十歲左右的劉晝無法寫成《劉子》。《劉子》最早見錄于《隋書·經籍志》,在《時務論》條下注云“梁有《劉子》十卷,亡”。《隋書·經籍志》參考了梁阮孝緒的《七錄》,凡注“梁有今亡”,皆阮氏舊有。則《劉子》亦為《七錄》所著錄,《七錄》序末署“有梁普通四年撰”,書當成于梁普通四年(523),此時劉晝年方十歲或十一歲,是無法寫出像《劉子》這樣的書的。
其三,《劉子》和《文心雕龍》,“從它們的思想方法、材料選用以及‘分類鑄詞’等方面看,則雷同之處隨處可見”。如《劉子·審名》篇有“東郭吹竽,而不知音”;《文心雕龍·聲律》篇也有“若長風之過籟,東郭之吹竽耳”。兩書并用“東郭吹竽”,而一般書籍均作“南郭吹竽”。
林其錟、陳鳳金是迄今論證《劉子》作者為劉勰最詳盡,主張最堅決的兩位,其后杜黎均、張光年等都表示贊同,近年朱文民撰文《把〈劉子〉的著作權還給劉勰——〈劉子〉作者考辨補證》等,依然是呼應林其錟、陳鳳金的觀點。《劉子》作者是劉勰,雖然沒有為學界一致認同,卻打破了當時“一統”的局面,使學界不得不重視這種觀點。
在林其錟、陳鳳金的文章發表后,楊明照也發表了《再論劉子的作者》,在舊文《劉子理惑》的基礎上,進一步堅持《劉子》作者是劉晝,對林其錟、陳鳳金的觀點進行了商榷。
楊明照認為:(1)《隋志》梁有某書若干卷或梁有某書亡注語,并不是都指《七錄》,因為《隋志》所據的底本是《大業正御書目錄》,而不是《七錄》,同時梁代書目不止《七錄》一種。“因而對《劉子》的考辨只局限在《七錄》一書上,似乎不夠全面。”(2)阮孝緒《七錄序》中的“梁普通四年”,是《七錄》開始撰寫的時間,而不是《七錄》完成的時間。(3)梁代著錄《劉子》的目錄書,絕不是只有《七錄》。(4)《隨身寶》“流子劉協注”一則,“注”與“著”涵義既殊、音讀亦異,不能等同,同時《隨身寶》雜亂無章、錯誤很多。對其不能估計過高,只好存疑俟考。(5)《劉子》屬于子部,不會是屬集部的劉勰《文集》的一部分。(6)《劉子》與《文心雕龍》各有特色,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從思想傾向看,《劉子》以道家為主,《文心雕龍》以儒家為主。從語言結構看,《劉子》的文筆整飭、平板,排句多,好緝綴成文;《文心雕龍》的文筆流暢、生動、儷句多,善自鑄偉詞。另外,兩者字句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劉子》習用“由此觀之”、“以此觀之”、“以此而言”、“以夫”等,《文心雕龍》全書從未使用,而《文心雕龍》習用的“原夫”、“觀夫”、“若乃”、“若夫”、“至于”、“蓋”(句首)、“耳”(句末),《劉子》也不曾使用。所以“《劉子》絕非出自劉勰之手,劉晝才是《劉子》的作者”。而周振甫也發表《劉子與文心雕龍思想差異》,對劉勰撰《劉子》提出懷疑。
楊明照和林其錟、陳鳳金對于《劉子》作者的有關材料作了詳細的收集整理和考辨工作,為我們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們將作者集中到劉勰、劉晝上和將證據集中在《七錄》與《隋書·經籍志》關系的討論上,也成為以后討論《劉子》作者的兩個關鍵問題。
80年代,程天祜也是主張《劉子》作者為劉晝很堅決的一位,他認為“《劉子》和《文心雕龍》非出一人”。從體系上看,《文心雕龍》體系嚴密,條科分明,《劉子》根本沒有構造理論體系的自覺要求;從思想傾向看,《劉子》主張儒道互補而傾向于道,《文心雕龍》崇儒輕道,強調“經子異流”;《劉子》認為諸子的宗旨相同,《文心雕龍》認為諸子中有純、駁之別。從袁孝政序、張鷟《朝野僉載》等文獻記載和《劉子·惜時》篇透漏的信息分析,“劉晝說難以否定”。傅亞庶在不少地方承襲了程天祜的觀點。
2008年,陳應鸞發表《劉子作者補正》,認為“《劉子》之用典、用詞顯見北朝之特色”、“《劉子》中存在著許多錯誤,與史傳所載劉晝的心性特征十分吻合”,所以“《劉子》的作者應該是劉晝”。值得注意的,這篇文章是2000年代以來唯一一篇正面主張《劉子》作者為劉晝的文章,但文中諸多例證不久就遭到周紹恒的反駁。
2012年,林其錟《劉子集校合編》由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劉子集校合編》的另一重要學術價值就是對《劉子》作者問題的重新考辨。在《劉子集校合編·前言》中除書名、篇名、卷帙、版本、研究概況等系統梳理之外,花了很大的篇幅集中于作者的考辨,對研究中十余個爭議點考察,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據新的證據,林其錟更加堅定地認為《劉子》作者為劉勰,而非劉晝。
在《前言》中,林其錟提出的所謂唐人袁孝政注序,完全是后人偽托,袁孝政根本不是唐人。研究者提出了五點新的證據:(一)注者傳記無憑,來歷不明;(二)迄至南宋初年,全無《袁注》記錄;(三)南宋初袁注出現之時即為目錄學家質疑;(四)袁注異體字與隋寫本不成比例;(五)袁注注書體裁和唐人注書體裁不相屬。
袁孝政序言在《劉子》研究史上的影響是重大的。所有關于《劉子》“劉晝撰”的說法均以它為起點。歷來學者對其身份知之甚少,卻少有提出懷疑者,如王叔岷曾推測:“袁氏《新》、《舊唐書》無傳,其為何時人,未可塙斷。……袁《注》本諱至高宗,或即高宗時人邪?”楊明照《劉子理惑》云:“孝政注之前,諸書征引已眾(《新》、《舊唐書》俱無孝政注,他書亦無論及者,故其生卒不可考。然非初唐人則可臆測也。敦煌兩寫本均無注,尤為確證)。”兩人均無法判定袁孝政具體時代,但依然篤信袁孝政為唐人。現林其錟將袁孝政注序斷為南宋人偽托唐人而作,此無異釜底抽薪,徹底打掉了支持“劉晝撰”說的證據。此觀點更有待于《文心雕龍》研究者的積極回應。
也有學者認為劉勰、劉晝都不是《劉子》作者,如張嚴認為“《劉子》五十五篇,因不著撰人姓名,后人又勿之深考,以致張冠李戴,有此名實不符之嫌”。曹道衡《關于〈劉子〉的作者問題》認為“《劉子》可能是另一位劉姓學者所作,歸諸劉勰和劉晝都出于后人臆測,未必可從”。更有甚者,以為《劉子》的作者是梁代的劉遵。這些論文猜測的成分多了一些。
在此,筆者想說幾句題外的話:
《劉子》作者為劉晝是被“假定”和考證出來的。《劉子》作者至南宋才有學者明確定為劉晝。南宋初年人吳曾讀到了有袁孝政注的《劉子》,其《能改齋漫錄》是最早提到袁孝政注的著作。稍后,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明確記載該書“近出”,“終不知晝為何代人”。博學如陳振孫,此時都不知道劉晝是誰,足見學界對《劉子》和劉晝的陌生。隨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黃震《黃氏日抄》中均有關于《劉子》的記載和討論。而至王應麟(1223—1296)《玉海》時才明確知道《北齊書》和《北史》中有劉晝傳,足見南宋人對劉晝的了解是逐步清晰的,所謂“《劉子》劉晝撰”的觀點是在袁孝政注日益流行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而明清以來所謂的“劉勰撰”說和“劉晝撰”說之爭,實發端于南宋出現的袁孝政注序,唯將陳振孫等尚存疑問的“劉晝”徑直題曰“北齊劉晝”,曲解腰斬南宋人本意。如《四庫總目提要》宣稱:“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目,題晝之名,而附著其抵牾如右”,一方面認為《劉子》作者存在爭議,另一方面卻仍然信從《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題《劉子》為劉晝。殊不知,晁氏、陳氏對《劉子》的作者也是存疑的,而題作劉晝者,是目錄學家照實著錄書籍的一種方式,而著錄者自己的意見往往附于提要之中。四庫館臣置晁氏、陳氏二家之懷疑于不顧,徑直截取其言之前半截從之,故題《劉子》作者為北齊劉晝。今人置四庫館臣之懷疑于不顧,徑直截取其言之后半截從之,真的以《劉子》作者為北齊劉晝。正所謂“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為是。傳彌廣,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劉子·審名》篇)。真相反而遮蔽不出。下面這段文字取自《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讀后,四庫館臣之意見當一目了然,以《四庫總目提要》而定《劉子》作者為劉晝者可以休矣!
是書或題劉歆,或題劉勰,或題劉孝標,惟袁孝政序定為劉晝。然其書晚出,至《唐志》始著錄,九流一篇,全襲《隋書經籍志》之文,疑即孝政所偽作,而自為之注也。然雜采古籍,融貫成篇,雖風格稍卑,而辭采秀倩,即出孝政之手,亦唐代古書也。
可見,所謂《四庫全書》題作“劉晝”,是一種“假定”。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楊明照、余嘉錫考證《劉子》作者為劉晝。楊明照的觀點前已經介紹,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劉子》認為張鷟《朝野僉載》中已經記載此書為劉晝所作,對比劉晝生平和《劉子》思想,多相符合。對于袁孝政《劉子》注序中提到“天下陵遲,播遷江表”與劉晝傳記中未曾提到他流落江南的矛盾,余嘉錫解釋為劉晝視江南為衣冠文物存焉,而“齊自高洋之后,皆昏暴之君,行同禽獸,晝既不遇于時,自憾生于夷狄之邦,不及睹衣冠文物之盛,而揖讓于其間”,“孝政推知其意,故曰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也。特孝政文理不通,不免詞不達意耳”。余氏隨意替古人改文章以合己意,其證據的勉強不用多說。
學界輕易接受四庫館臣的“假定”和楊明照、余嘉錫并不完美的“考證”,反而對《劉子》作者為劉勰的觀點不聞不問,既不重視古人兩《唐書》的記載,也不注意今人不斷提出的新證據,讓人頗感意外。
二、《劉子》文本整理成績斐然
早在唐代的時候,袁孝政就對《劉子》進行了注釋,該注現仍保存在《道藏》本《劉子》中,宋代奚克讓有《劉子音釋》三卷和《音義》三卷,今不見存。清孫星衍、黃丕烈、盧文弨、孫詒讓、陳昌濟、民國孫楷第等均曾對《劉子》進行過校勘,其中黃丕烈尤為用力。清末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在敦煌遺書中發現《劉子》殘卷多種,羅振玉、傅增湘、王重民均曾參與整理,校勘成果頗豐。
當代《劉子》整理、注釋本有多種。楊明照《劉子校注》,題劉晝撰,巴蜀書社1988年版;林其錟、陳鳳金《劉子集校》,題劉勰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臺灣王叔岷《劉子集證》,刊于1961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四,大陸中華書局2007年9月重版。1998年中華書局出版傅亞庶《劉子校釋》,后附“歷代《劉子》序跋”等資料。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又出版了江建俊《新編劉子新論》,并附有資料五種。2008年,林琳出版《劉子譯注》。2012年,林其錟出版《劉子集校合編》,是《劉子》文獻整理的最新成果。
有感于唐袁孝政《劉子》注的疏漏紕繆,1938年,楊明照在《文學年報》第四期上發表了《劉子校注》,除對《劉子》諸版本文字異同作出校勘外,更對《劉子》作了全面注釋。“詞求所祖,事探其原;諸本之異同,類書之援引,皆迻錄如不及。”此書1988年由巴蜀書社重版,書前附錄了《劉子理惑》、《再論劉子的作者》兩文。王叔岷認為楊明照的《劉子校注》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楊氏長于陳言故實之考證。然考證陳言故實,當留意直接來源,或間接來源。同一成言故實,見于數書,其最相合者為直接來源。某書雖晚出,而為直接來源,當以晚出之書為主,早出之書為輔。楊氏往往忽之。”因此,王叔岷“發揚幽光,從吾所好,因綴輯諸家之說,修正補苴,寫成《集證》十卷”。這就是《劉子集證》。該書備舊說、審取舍、多創見,使《劉子》注釋益臻完善。1998年傅亞庶出版《劉子校釋》,該書博采眾家之精華,參以己見。在版本方面,搜羅不同版本29種,在校勘方面,全面吸收了清孫星衍、陳昌濟、孫詒讓,近代傅增湘、羅振玉和今人孫楷第、王重民、楊明照、王叔岷、林其錟、陳鳳金等人的成果;在注釋方面,采納了唐袁孝政注,明程榮、孫鑛、鐘惺等評注和楊明照、王叔岷的注釋成果。同時援引類書、子書,拾遺補缺,加以自己的論斷,既全面反映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體現了作者自己的觀點。該書還附有《劉子》主要版本序跋14種,校注諸家序跋5種,全書集眾說為一,資料翔實,是一部集成式的著作。而2001年,92歲高齡的楊明照先生準備以涵芬樓影印道藏本為底本,詳細校注《劉子》五十五篇,預計字數在四十余萬字。惜2003年,先生歸于道山,其后陳應鸞繼續整理,于2008年出版了《增訂劉子校注》。全書60萬字,改以《道藏》本為底本,參校42種版本,且注解也增加不少。
林其錟、陳鳳金是當代對《劉子》版本用力最勤的學者。他們不僅著有《論〈劉子〉作者問題》、《〈劉子〉作者考辨》等論文,力主《劉子》為“劉勰撰”。同時,他們出版了《劉子集校》和《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兩書。《劉子集校》廣收《劉子》版本和名家校勘,書中列有抄本、刻本和前人校勘記共45種,囊括了現存的所有善本。校勘底本為乾隆重刊《漢魏叢書》本,諸家異文逐條附于篇后。“如此廣泛的校勘工作,不僅使原著中的許多疑點得以冰釋,還可使讀者從中看到一批珍貴版本的面貌。”孫楷第給林其錟、陳鳳金寫信贊道:“此書校勘時所據本之多,用力之勤,度越前人,為《劉子新論》的校勘學立下了一個十分鞏固的基礎,是以辛苦換來的極有價值的著作。”今人清理《劉子》版本,是必須參考他們的研究成果的。
2012年,林其錟又出版《劉子集校合編》,是作者30年研究《劉子》的心血之作,該《劉子集校合編》分上、下篇和附篇。書首有序、前言、目錄,書末有后記。上篇:《敦煌西域〈劉子〉九殘卷集校》,內容包括敦煌遺書伯三五六二卷、伯二五四六卷、伯三七○四卷、伯三六三六卷、斯六○二九卷、斯一二○四二卷、何穆忞舊藏唐卷子、劉幼云舊藏唐卷子、新疆塔里木盆地麻札塔格遺址出土M.T.○六二五卷等原本影印、文字標校。篇前有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原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手書《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序》;篇后六個附錄:(一)敦煌遺書《劉子》著錄資料;(二)敦煌西域遺書《劉子》殘卷校跋敘錄;(三)敦煌西域遺書《劉子》殘卷、宋本、寶歷本常見異體字;(四)敦煌西域遺書《劉子》殘卷存篇示意圖;(五)、(六)敦煌西域遺書《劉子》九殘卷、宋本、寶歷本異文對照表(一)、(二)。下篇:《日本寶歷本〈劉子〉集校》,內容包括日本寶歷新雕《劉子》原本影印、文字標校。篇前有《集校所用版本及主要書目提要》,附《〈劉子〉主要版本卷帙分合一覽表》。附篇:(一)歷代《劉子》序跋;(二)《劉子》作者考辨;(三)《劉子》研究論著索引;(四)承教錄:題錄、書簡。《劉子集校合編》乃校編者費三十年之功積漸而成的力作,不僅囊括了《劉子》今存所有善本,包括多種敦煌西域殘卷、宋刻、明、清鈔本、刻本等四十多種,而且對版本真偽、作者誰屬都作了深入考證。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曾有“搜羅廣博,考校詳審,所取得的成果大大超過前人”之評。因此本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文獻價值。1985年,林其錟先生出版了《劉子集校》;1988年,又出版《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劉子集校合編》正是在前期扎實豐富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又不斷收集新資料,同時對《劉子》作者等有關問題進行深入思考而形成的集大成式整理著作。
敦煌殘卷《劉子》是校勘文本的寶貴資料,自發現以來,羅振玉、王重民均參與了整理;而林其錟、陳鳳金集錄敦煌遺書中的《劉子》資料和前人校勘成果,匯為《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一書,題劉勰著,上海書店1988年出版。敦煌殘卷多不易得,此書影印敦煌殘卷《劉子》六種,同時著錄相關資料五種,省減了研究者的勞碌之苦,頗有益于學林。對敦煌本《劉子》進行過研究的還有許建平,他發表了《敦煌本〈劉子〉殘卷舉善》、《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證》、《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證補》等論文,校勘了敦煌本《劉子》的文字,同時對殘卷的時代考證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如對于伯2546,王重民認為此卷“于唐諱‘世’之字為‘代’,‘治’之字為‘理’,則寫于開、天之世也。字小行密,然頗清秀”,許建平則認為“中宗至憲宗時才出祧不諱,則此卷當非開天寫本。愚以為作于高宗、武后時期,即公元650—705年”。
200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琳的《劉子譯注》,這是目前唯一的一本《劉子》譯著。在《劉子》文本普及方面,還需要學界的努力。
可以說,今人對《劉子》的研究,文本校釋是取得成就最多,也是最大的一個領域。
三、《劉子》研究的思想“缺席”
相對于《劉子》文獻整理的“熱鬧”,思想在《劉子》研究中“缺席”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只零碎出現了一些研究劉子美學、文藝、教育、人才思想的論文,如《試論劉晝的美學思想》、《〈劉子新論〉的正名邏輯思想》、《劉晝文藝觀初探》、《〈劉子〉人才思想初探》,這些數量有限的論文均只涉及《劉子》思想某一方面,沒有深入研究《劉子》的思想體系,更沒有對其思想史地位進行定位。
林其錟的《劉子思想初探》認為:“此書不失為今天研究南北朝時期的哲學、政治、經濟、文化等思想的寶貴史料,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該書中,體現了作者:(1)因時而變的社會歷史觀和與時競馳的人生觀;(2)從農本出發的富民經濟思想;(3)從民本出發的清明政治思想;(4)知人、均任的人才管理思想;(5)“文質并重”、“各像勛德應時之變”的文藝思想。此是一篇比較全面概括《劉子》思想的論文。傅亞庶《劉子的思想及史料價值》則認為:“《劉子》全帙內容豐富,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以儒學為綱,吸收各家所長,其言修身治國之要,可總括為治身、治人、治農、治軍四個方面。”
林其錟的《“適才”“均任”是用人之道的主要內容》主要是談《劉子》的人才思想,作者認為:“《劉子》作者立足于魏晉南北朝森嚴的門閥制度的現實,繼承和發展了先秦諸子的用人思想的許多精華,大膽地提出了沖破憑靠‘華裔世胄’唯親是薦的門閥制度,要求‘因事施用,因便效才’和‘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它反映了廣大處于受壓抑,被摧殘的寒門知識分子的愿望和要求,在歷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皮朝綱、詹杭倫的《試論劉晝的美學思想》是一篇討論《劉子》美學思想的論文,作者認為“劉晝在書中雜取九流,融匯儒道,表述了自己的美學思想。他對美的本質、美丑的具體性和相對性、美感的普遍性和差異性、審美標準及其賞評態度、文質關系等美學問題,都在前人基礎上形成了一些自己獨到的見解”。文章從“行象為美,美于順也”,“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丑無定形,愛憎無正分”,“情實、理真”幾方面進行了分析。
張辰、曹俊英《劉晝文藝觀初探》從文情與文用,文質與文德,文道論,劉子與劉勰、鐘嶸之比較,劉子文藝觀的思想基礎五方面就劉晝的文藝思想作了探討,“概括地說,劉晝的文藝觀是以儒、道思想為核心,以‘中和’、‘適用’為美學思想基礎,以維護封建統治為最終目的的一個整體系統”。
李軍的《劉晝的教育思想》則從生平和著作、教育價值論、道德修養論、論學習心理及相應教學原則等方面討論了《劉子》的教育思想。作者認為:“實際上,劉晝的《劉子》是通過討論教育問題來討論治國之要的。我們可以把它稱作‘教育政治學’。他廣泛吸收儒、道、法、農、縱橫、兵、雜等各家的傳統理論作為思想資料,根據時代的發展變化,結合自己的人生境遇和社會現實,提出了以儒家的倫理道德問題為核心的、體大慮周的、理想的教育理論,不時體現出辯證的、科學的思想火花,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價值。”
燕國材在《中國心理學史》中辟有專節討論《劉子新論》的心理思想,他認為:“其中《清神》、《防欲》、《去情》、《崇學》、《專學》、《知人》、《心隱》、《和性》、《殊好》、《觀量》諸篇,包含有頗為豐富的心理思想。”作者分“形”、“心”、“神”,“情”、“欲”、“性”,注意問題和學習問題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這些論文或概述了《劉子》的思想,或深入論述某一方面的內容,但都尚未觸及《劉子》作為雜家著作的思想體系和哲學概念、范疇等。
王叔岷說“惜其作者不明,討治者不多”,道出了思想研究“缺席”的部分原因。知人論世是中國古典文學、歷史和哲學思想研究的重要基石之一。一部著作的寫作時代能為研究者提供一個參照的坐標,有效地對研究對象的價值和意義定位,而作者的生平是發現寫作動機和追尋思想淵源的重要資料。但《劉子》成了“反面典型”,有關它的評論材料為它提供了一個上至漢代,下至唐代可能出現的漫長時間段和劉歆、劉孝標、劉勰、劉晝、袁孝政等數個可能的作者,其時間長達近四百年。在這么長的時間里,朝代幾經替換,南北合而又分,分而又合;思想學術也是風云變幻,經歷了數次變化,如章太炎認為“漢晉間,學術則五變”。如果將《劉子》模糊定位在如此長的時間段里會大大降低它的思想學術價值。盡管當代研究者們通過敦煌殘卷伯3562和《北堂書鈔》的引用以及該書中引用的典故涉及曹操和劉備,從而將討論的時間范圍縮小到了魏晉至隋之間,又依據對歷代目錄和史傳、筆記等記載材料的分析,將作者“嫌疑”重點放在了劉勰和劉晝身上,但支持雙方的材料勢均力敵,仍很難判斷誰才是真正的作者。且二人的思想和生平經歷均同《劉子》有不相容之處。在這種既不知道寫作時代又無法確定作者的情況下進行思想研究,很是有些冒險。
當然,從研究策略上講,大可不必等作者問題完全弄清楚之后再進行思想研究。揭橥哲學著作的思想體系,揭示并闡釋它的重要哲學命題,為它在哲學、思想史上定位都是研究者可以從事的工作。馮友蘭說“哲學家必有其自己之‘見’,以樹立其自己之系統”。但面對《劉子》,這樣的期待又會落空。《劉子》篇幅不長,涉及的內容卻很多,頗顯龐雜;而且分為五十五篇,最多的一篇字數為1 000多字,最少的為300多字,全書平均每篇不到六百字,給人一種簡潔淺顯,缺乏思想深意之感。更讓人沮喪的是《劉子》的寫作方法難脫“抄襲”的嫌疑。《劉子》有很多觀點和近四分之一的段落、語句襲自《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有的是稍稍改寫化用,有的則是原原本本襲用。《黃氏日鈔》卷五十五稱:“《劉子》之文類俳,而又避唐時國諱,以‘世’為‘代’,往往雜取九流百家之說,引類援事,隨篇為證,皆會粹而成之,不能自有所發明,不足預諸子立言之列。”“會粹而成之”,是批評《劉子》一書創造性太少,無法自成一家之說,人們想要在書中尋找新意的想法很難實現。正所謂“《清神》、《防欲》、《去情》三篇,道家之說也。《崇學》、《專學》二篇,荀卿、王符以降所同之說也。《貴農》一篇,王符、仲長統以降所同之說也。《法術》則慎、申之說,《審名》、《鄙名》則尹文之說,《知人》、《薦賢》又王符以下之說也。《因顯》、《托附》、《通塞》、《遇不遇》、《命相》、《妄瑕》、《適才》、《均任》、《傷讒》,則王充、王符、葛洪之所同衍也。《誡盈》、《明謙》、《大質》、《兵術》、《閱武》、《禍福》,則《呂覽》、《淮南》之所同衍也。略舉其近已如此,若一義片言莫不本于周、秦,則不可勝數也。”
作者的不確定,內容的淺顯,使思想界對《劉子》不太重視,一般思想史、哲學史著作根本不提及它。
盡管《劉子》思想研究有種種困難,依然有學者在做這方面的嘗試,如陳志平的《劉子研究》,曾勾勒過《劉子》的五十五篇的思想結構圖,并對《劉子》學派歸屬和思想體系進行了分析。作者借用了思想史“問天”與“問心”理論的傳承轉變,以為《劉子》正處在兩種理論的交接點上,體現了思想史轉型時期的典型特點。而林其錟《魏晉玄學與劉勰思
想——兼論〈文心雕龍〉與〈劉子〉的體用觀》,則認為:“劉勰不僅是個杰出的文論家,而且也是個杰出的思想家。劉勰生活的時代正是社會大變動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時代,以哲學為骨干的學術思潮也正從析同為異諸子分流到合異為同諸家互融的玄學主導時期。”玄學對劉勰影響頗深,這在《文心雕龍》和《劉子》中有著共同的反映。該文為從哲學的角度為《文心雕龍》和《劉子》尋找共同的思想基礎,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論文。近年,涂光社也在《諸子學刊》上發表了有關《劉子》思想研究的論文。這些,都透漏出一種新的信息,《劉子》思想研究正在突破簡單的人才、心理、教育等社會學“斷章取義”式的研究,而回歸了它作為諸子著作的本質。諸子學著作,應該有其自己的研究方法,一批學者正以《劉子》為研究對象,在探索諸子學著作的研究方法,這也許是《劉子》研究的又一新領域。
陳志平,湖北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