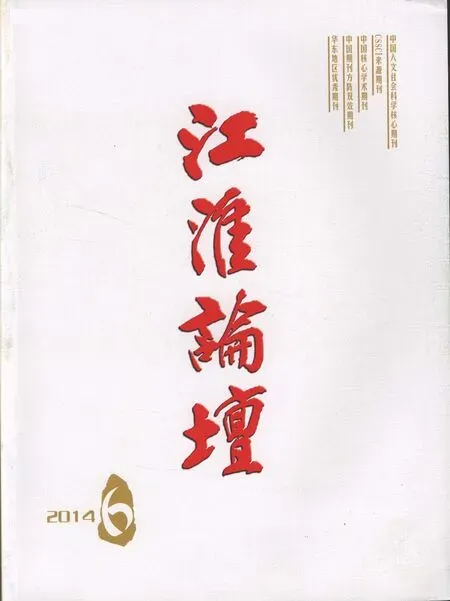20世紀20年代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玄學派挑戰的回應*
朱慶躍何云峰(.上海師范大學哲學學院,上海 0034;.上海師范大學知識與價值科學研究所,上海 0034)
20世紀20年代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玄學派挑戰的回應
朱慶躍何云峰
(1.上海師范大學哲學學院,上海 200234;2.上海師范大學知識與價值科學研究所,上海 200234)
在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論戰中,除了對科學派進行批判外,玄學派對在中國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也進行了質疑,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知識理性、價值理性、實踐理性功能。為此,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積極的回應,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真理性、價值真理性、實踐真理性。具體體現為:初步闡述了科學與哲學的辯證關系,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真理性;深刻論述了自由人生觀或自由意志的不“自由”,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真理性;較為正確地分析了通過變革實行社會主義救國論的現實依據,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真理性。這些回應,既鞏固了之前批判東方文化派所取得的成果,即進一步回答了為什么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更重要地在于為之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如何正確地推進指明了方向。
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玄學派;挑戰;回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20世紀20年代初,圍繞科學與哲學、科學與人生觀間的關系等內容在中國的學術界發生了一場論戰,即“科玄”論戰。這場論戰聯系到當時中國具體的歷史情境來看,其背后折射的是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以及如何解決方面的爭論。正如李澤厚所指出的“當社會和政治危機伴隨著原有文化根基失落時,便迫切需要意識形態。……科玄論戰的真實內涵并不真正在對科學的認識、評價或科學方法的講求探討,而主要仍在爭辯建立何種意識形態的觀念或信仰”。正基于此,論戰后期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參加進來,與科學派結成統一戰線對玄學派的文化保守主義所構成的挑戰進行了回應,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以及論證由此指導的社會主義救國論的現實正當性。可以說,對玄學派挑戰的回應是“五四”前后對文化保守主義批判的繼續和深入,因為相對于之前的東方文化派,玄學派以一定的理性、思辨色彩呈現在人們面前,它所隱蓋的文化保守主義危害性更大。
一、初步闡述了科學與哲學的辯證關系,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真理性
如果說之前以杜亞泉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在馬克思主義知識真理性的認識上,用“偏狹式”的理解來詆毀其科學性,則玄學派的相關質疑和否定,往往披著迷惑性的“學理”外衣。他們的論證思路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認為“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應該呈現出客觀的、邏輯的、分析的、因果關系的、相同現象的等特征,盡管這些在物質科學里面能夠獲得體現,而在精神科學里面卻不能獲得“確證”,從而得出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也就“大打折扣”這樣的結論。在這個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張君勱,他認為自然界現象之特征,則在其互同,即由公例支配;而人類之特征,則在其各異,即人類是有意志的、是有自由的,這就造成了其無公例可求,也難以稱之為“科學”。“吾所欲問者,則精神科學中有何種公例,牢固不撥如物理學之公例者乎?有何種公例可以推算未來之變化,……無他,精神科學無牢固不撥之原則,且決不能已成之例算推未來也。”同樣,瞿菊農也指出:“科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的各方面,科學家研究自然,必須假定自然是死的,否則無從下手。但因此便為人類設了一敵,卻不道根本上原是調和的”。二是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犯了科學方法“萬能論”的錯誤,把自然科學或物質科學里面的研究方法不顧條件地擴大到人文社會科學里面,沒有認識到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本身亦是有條件限制的。如在《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一文中,張君勱強調“科學以分科研究為下手方法,故其答案經常限于本范圍以內,然人類所發之問,往往涉及數種學科,故科學之所回答者非即吾人之所需,惟有令人常以‘此另一事’四字了之”。而在《科學之評價》中,他更具體地指出自然科學的目的在于求一定的因果關系,是將這些關系化為分量的,這種因果也是官覺之所及的,對于各問題是“不能為徹底回答”。上述兩種論證,玄學派最終的目的就是由否定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性”,進而也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理性功能。“與穆氏孔氏同時,而其致力方面與兩氏異者,社會黨領袖之馬克思是也。馬氏著書,與兩氏同不脫十九世紀中葉之彩色,即謂社會進化有一定公例,而為科學方法所能適用是也。……然自今日觀之,以歐洲而言,資本主義之成熟,英遠在俄上,顧勞農革命,何以不起于英而起于俄乎?以俄與德較,則德資本主義之成熟又在俄上,何以德之革命成績,反居俄后乎?”可見,如果說在科學主義或科學方法“萬能論”的影響下,科學派認為“哲學”包括“玄學”是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只有“科學”才能做到;那么玄學派則采取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認為物質方面“科學”是有益的,而精神層面只能通過“玄學”來解決,通過質疑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從而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理性功能。
針對玄學派的上述論調,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至少從三個方面給予了反擊:一是將哲學視為一種把握人與世界總體關系的世界觀學說,強調哲學與具體科學是一般與個別、共性與個性的關系。如李大釗認為“哲學是于科學所不能之外,去考察宇宙一切現象的根本原理”。瞿秋白指出哲學就是“綜合各種科學的種種公律”的學問,具體來說表現為對于宇宙或自然的解釋、對于社會關系的詮注。這個層面的闡釋在于揭示了玄學派所提倡的“玄學”與哲學是有本質區別的,它一味注重“形而上”的特征本身也說明其是非科學性的,哲學而不是這種“玄學”才是“科學的科學”。二是強調人類社會雖與自然界不同,共同之處卻在于它與自然界一樣也存在著能被發現和揭示的客觀規律。如陳獨秀認為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都是客觀的、有規律的,只是社會現象更加復雜。在《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中,瞿秋白強調“社會里與自然界同樣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處,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內部隱藏的公律所支配。科學的職任便在于發見這些公律”。而對于這些“公律”到底有哪些,瞿秋白認為最主要的就是 “社會有定論”,即社會現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為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人若能探悉這些因果律,則其意志行為更切于實際,而能得多量的自由,然后能開始實行自己合理的理想”;社會現象的“最后原因在于經濟”,“精確些說,是生產力”。這個方面的論述在于回擊了玄學派所稱人類社會無“公律”和對其研究無科學性方法的謬論。三是在上述兩個論證層面的基礎上,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惟有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哲學”的論斷。對于馬克思哲學的“科學性”,瞿秋白將它歸結為堅持了“合于客觀的事實的”,而不是所謂的“必須與人的實際需要發生關系”或強調有利于人的利益性。陳獨秀認為在于它堅持了徹底的物質一元論,而不是二元論或精神一元論。“唯物史觀的哲學者也并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只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礎之本身。”陳獨秀的這種觀點也獲得了鄧中夏的認同:“唯物史觀,他們亦根據科學,亦運用科學方法,……只是他們相信物質變動則人類思想都要跟著變動,這是他們比上一派尤為有識尤為徹底的所在”。
二、深刻論述了自由人生觀或自由意志的不“自由”,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真理性
對于科學為何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的論證,玄學派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借用柏格森、倭伊鏗等西方生命哲學作為理論依據,對“人生觀”作了意志主義或意向主義的解釋。如張君勱指出人生觀之特點在于“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一性的”;梁啟超盡管作了折中主義的解釋,認為“人生”就是人類從心界、物界兩方面調和結合而成的生活,人生觀就是懸一種理想來完成這種生活,但對于張君勱的“尊直覺尊自由意志”是完全贊成的,只是不贊同他將其應用的范圍過于寬泛化而已;張東蓀認為人生觀就是最神秘的生命精神、感情意志,是“偉大的智慧”;瞿菊農則強調“人格是絕對的有自由的”;等等。那么以此為基礎,玄學派就得出了這種以自由意志為本質的“人生觀”理所當然就非“科學”所能解決的結論。如張君勱就提出人生觀問題的解決惟有“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而“決非科學所能為力”,因為人生觀的自由變動性是“科學”的“三公例”(即同一、矛盾、折中)和“兩方法”(即歸納、演繹法)所不能論證和推定的。如果說科學派希望以科學方法的信仰作為一種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而放棄了哲學作為世界觀、人生觀理論的職能,那么玄學派則走入到另一極端,即放棄科學對世界觀、人生觀解決中的某些價值功能,而把人生觀問題的解決視為一種哲學的自我理解即“玄學化”的幻想。相應地,在玄學派的眼光中作為知識理性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已經缺乏“科學性”而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同樣作為哲學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就人生觀問題所提出的價值理性原則也是不具有指導意義和必然的正確性,因為人生觀問題本身及其解決就是自由意志的體現和反映。“亞丹斯密,個人主義者也;馬克斯,社會主義者也;叔本華、哈德門,悲觀主義者也;柏剌圖、黑智爾,樂觀主義者也。彼此各執一詞,而決無絕對之是與非。”
針對玄學派所提出的“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以及強調人生觀是個人自由意志的體現和反映這些謬論,科學派的反擊表面上非常“迅猛”、“華麗”而實質卻“無力”。因為這些反擊更多地采取簡單枚舉法來佐證科學能夠解決人生觀,即“表現在什么”的問題,而沒有從深層次探討背后的根源,即“為什么”的問題。在吸取科學派的相關教訓基礎上,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重點從兩個方面對玄學派進行了反擊:一是論證了“玄學”為何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二是探討“科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為何能夠解決人生觀問題。前者方面,除闡述“玄學”的非科學性之外,更多地圍繞玄學派所主張的人生觀本身的錯誤來展開,即強調他們那種自由人生觀或自由意志實質上是不存在的。如陳獨秀運用唯物史觀為指導,指出人生觀不是個人主觀的直覺的自由意志的產物,無論是何種形式的人生觀“都是生活狀況不同的各時代各民族之社會的暗示所鑄而成”,只有這種客觀的物質原因才能“變動社會”和可以“支配人生觀”。而瞿秋白的論證最顯著特色就是將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結合起來,避免了機械物質性。他從意識與存在的關系、自由與必然的關系、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展開了深刻的論述,以批判玄學派自由人生觀或自由意志的虛假“自由性”。如在意識與存在的關系上,主張行動者固然是有意識的人,各自都有一定的目的,而這并不能否認歷史進程中的“共史同因果律”即歷史現象的最后原因卻是“造成這些種種動機的現實力量”;在自由與必然的關系上,強調“人的意志愈根據于事實,則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據于事實,則愈不自由”;在理想與現實的關系上,指出“真正的理想就是明天的現實。現在的現實是過去的果,亦就是將來的因。現實是流變不居的;既有流變,便有公律,依此現實流變不居的里面公律而后能預見將來的現實;這種將來的現實對于現在便是理想”;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提出了“歷史工具說”:“個性孕育在社會里,他受當代社會心理的暗示,他亦受當時社會里階級斗爭的影響”,“個性的先覺僅僅應此斗爭的需要而生,是社會的或階級的歷史工具而已。他是歷史發展的一因素,他亦是歷史發展的一結果”。如果說上述對玄學派自由人生觀或自由意志的非“自由性”的探討,間接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真理性;那么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就馬克思主義為何能夠建立乃至實現科學人生觀的相關論證,則從直接層面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真理性。這種論證集中體現在馬克思主義科學地解釋了人生觀的變遷。如瞿秋白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釋人生觀,而且足以變更人生觀”,因為它強調了每一時代的人生觀是由特定時代的科學知識所組成,而新科學知識來自于“經濟基礎里的技術進步及階級斗爭里的社會經驗”。馬克思主義明確了樹立科學人生觀的思想指導和基本準則。如陳獨秀從世界觀、社會歷史觀與人生觀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他認為世界觀決定了社會歷史觀,而社會歷史觀決定了人生觀,人生觀是世界觀和社會歷史觀在人生問題上的具體化。為此,樹立科學的人生觀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特別是社會歷史觀為指導。“‘唯物的歷史觀’是我們的根本思想,名為歷史觀,其實不限于歷史,并應用于人生觀及社會觀。”馬克思主義規定了科學人生觀的內容,即人生的根本意義和價值在于服務于群眾、服務于社會。早在1918年所發表的《人生真義》中,陳獨秀就認為科學的人生觀就是 “努力造成幸福,……并且留在社會上,后來的個人也能夠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在《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中,瞿秋白就指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有定論”和“歷史工具說”,就必須要樹立“利己”與“利他”相統一、在“利他”中實現“利己”的人生觀,而對于無產階級來說就是要樹立解放全人類方能解放自己的人生理想。“個性的動機僅僅是群眾動機的先鋒,階級動機的響導”,“‘非解放人類直達社會主義不能解放自己’,實在亦是利他。個性之于階級,亦與階級之于人類的關系相同”。一定程度上說,這些內容也為如何評價和衡量科學人生觀是否正確實踐提供了一個價值標準。
三、較為正確地分析了通過變革實行社會主義救國論的現實依據,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真理性
就當時中國實際問題產生的原因上,玄學派指出這是因科學主義的盛行或將信仰 “科學”視為人生觀而引發的。如張君勱認為國人相率而崇拜科學,紛紛辦廠,結果“人生如機械然,精神上之安慰所在,則不可得而知也”,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重蹈歐洲人的“覆轍”。張東蓀強調近年來一切現象都是由階級之間的利害沖突上發生出來的,而利害沖突背后有一個極重大的沖突即“天性觀的沖突”,具體來看就是“支配階級”的所謂“荀子的人性觀”與“被受配階級”的所謂“孟子的人性觀”之間的沖突而引發的。瞿菊農則把現代的悲哀、人生的煩悶歸咎為西方文藝復興的兩種精神即“個人主義和機械主義的文明”。在這種唯心主義文化觀的邏輯論證思路下,玄學派提出了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方案自然就是大力倡導玄學“人生觀”。如張君勱指出我國立國之策“在靜不在動,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質之逸樂”,為此就必須實施包括 “發揚人類自由意志之大義”在內的玄學教育。盡管張東蓀所主張的人生觀內涵豐富多樣、包羅萬象,諸如“自然”、“創造”、“樂天”、“化欲”、“無我”等,但他還是將“主智”列為第一條。瞿菊農則主張開展所謂的意志教育即相信“意志自由”,從而“使人人了解人生的意義與價值,領會了解超人格的活動,實現個人與宇宙的調和”。而這種玄學的“人生觀”實質到底是什么?如果說張東蓀、瞿菊農還比較含蓄、隱密的,那么張君勱毫不避諱地強調就是恢復宋明理學。“若夫國事鼎沸綱紀凌夷之日,則治亂之理,應將管子之言顛倒之,曰:‘知禮節而后衣食足,知榮辱而后倉廩實’。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學者,其微意在此。”可見,這其實與之前的東方文化派所鼓吹的“儒家文化救國論”并無本質的各異,這也是將玄學派視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根本原因所在;它很明顯是與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力主通過社會變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救國論”相對抗的,并且也消解了唯意志論自身之初反封建“宿命論”的積極性色彩,而蛻化成一味維護封建綱紀禮教的工具。因為它說明了“綱常名教已失去了現實性的內容,變成不合理的東西”,而只能“憑主觀意志加以維護了”。
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論證玄學派的 “玄學”是非科學的“哲學”、強調人生觀具有非“自由性”,實質就是對玄學派的“儒家文化救國論”的立論基礎進行根本的瓦解。同樣他們也并不是一味地“破”,而是在“破”的過程中也進行了“立”,即不僅僅把馬克思主義視為科學真理、價值真理,更在于將馬克思主義理解成一種實踐真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徹底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方案以及所依賴的路徑進行了較為正確的分析。具體體現在:其一、對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方案上,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社會主義救國論”,因為它“密切聯系著現實生活”。而這種現實生活就是當時中國的“國情”特別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現實情境,瞿秋白將它概括為宗法社會、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陳獨秀歸納其為國民經濟“還停頓在家庭手工業上面”、政治“仍然是封建軍閥”、社會思想“仍是宗法社會”;蕭楚女認為目前中國處于“國際帝國主義與國內的武人封建政治之下”。另外,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社會主義”方案實現的積極意義也進行了論述。特別是針對玄學派所倡導的“自由”,瞿秋白強調這種社會主義的實行真正有助于“人類才能有意識的制造自己的歷史,人類的意志方才漸漸的能實現”。其二、在“社會主義救國論”的實現路徑上,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在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務必采取徹底性的變革即“革命”。如瞿秋白就認為徹底改造現存制度“非用革命方法不可”,因“階級所處的地位不同,這‘應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中國的第三階級,要應付軍閥的壓迫,所以是革命的”。相對于瞿秋白從現實因素進行考量,鄧中夏則從唯物史觀的根本特征方面尋找革命的合法性,他強調唯物史觀區別于其他哲學的顯著性標志之一就是“態度——是進取的,革命的”。但在采取這一“革命”的主觀能動性方式時,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們也指出這并不是對唯物史觀相關規律的否定,而同樣是要堅持社會發展規律的指導,兩者是辯證統一的。
上述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玄學派挑戰的回應,因他們自身理論水平還尚處于提高階段,相應地在“回應”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諸如陳獨秀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還有機械主義的傾向,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根本區別等;即使這一期間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較為深刻的瞿秋白在“回應”中強調了“必然性”而卻對“偶然性”并未給予準確的論述,自由與必然的關系在現實中具有復雜性但也并不如他所指的呈現絕對“正比例”關系等。另外,現代化過程中所涉及的科學與人生觀的關系問題,也不可能因這一次論戰特別是對玄學派的批判而徹底獲得求解。畢竟“瑕不掩瑜”,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閾來看,對玄學挑戰的“回應”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歷史價值:一是鞏固了之前對杜亞泉等東方文化派批判的成果,在強化“中國為什么需要馬克思主義”這一認識中,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受眾面。“在人生觀問題的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者比較正確地闡明了社會歷史中的心物關系、群己關系,顯示了唯物史觀較之其他哲學學派的優越性,因而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二是直接或間接地為如何正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明了方向。如在思想認識層面,要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中必須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核心特質,決定了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理論基礎地位,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不僅僅是唯物史觀的中國化,也包括唯物辯證法的中國化;在價值主體層面,要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必須重視實踐主體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內化”問題,因為他們是影響和決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的根本性力量;在現實實際層面,要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正確認識國情,這是首要的前提問題。而20世紀30—40年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推進無不是上述脈絡的演繹和展示。如瞿秋白、李達、艾思奇等人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化實踐,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因為“只有體系化,才能一方面最有力地駁倒其他競爭對手,另一方面最有效地傳播于廣大民眾”;延安時期,毛澤東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道德主體”的培育問題;以及科玄論戰之后爆發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更多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參與進來,體現了對國情認識的高度重視等。雖然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還沒有完整地把握“成熟的社會主義”之全部內核,但在后來的中國革命實踐中,中國文化與中國式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他們的認識和思考具有合理性。
[1]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58.
[2]鐘離蒙,楊鳳麟,主編.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匯編(第一集第六冊)——科學與玄學論戰 (上)[M].遼寧大學,1981.
[3]張君勱,丁文江.科學與人生觀[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4]李大釗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87—597.
[6]陳獨秀文章選編(中)[M].北京:三聯書店,1984:351.
[7]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8]李毅.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現代新儒學[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9]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王南湜.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程及其規律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44.
[11]何云峰,胡建.馬克思論“成熟的社會主義”[C]//何云峰,主編.理論經緯·2012.合肥:黃山書社,2013:10.
[12]袁峰.中國文化與中國式民主[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
(責任編輯 黃勝江)
B26
A
1001-862X(2014)06-0045-005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www.jhlt.net.cn
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近現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想論戰研究”(2014M551430)
朱慶躍(1977—),安徽含山人,淮北師范大學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博士后研究人員、知識與價值科學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何云峰(1962—),重慶開縣人,上海師范大學知識與價值科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管理、教育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