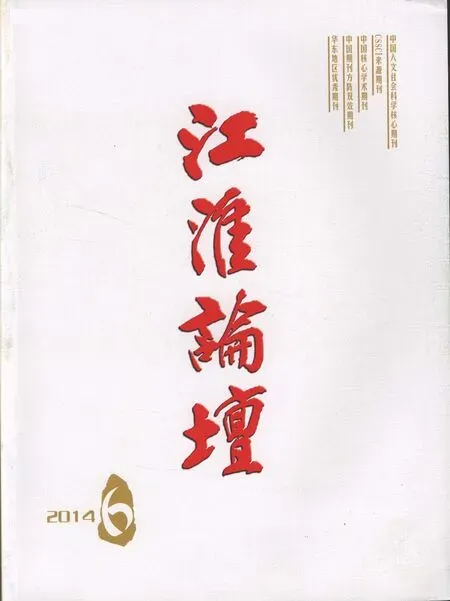經濟、環境、社會發展與人:從可持續發展觀到包容性綠色增長
張曉穎(中國農業大學,北京 100083)
經濟、環境、社會發展與人:從可持續發展觀到包容性綠色增長
張曉穎
(中國農業大學,北京 100083)
1992年,巴西里約,世界各國元首承諾給地球一個更好的未來;2012年,巴西里約,共識越來越少,信任越來越少。曾經的可持續發展路向何方?逐漸流行的“綠色”、“低碳”理念是可持續發展的升級還是替代?本文將圍繞“可持續發展”、“綠色增長”、“低碳增長”等幾個概念展開,理清這些概念的發展軌跡及本質區別,找到每種概念產生的背景、特點及主要倡導機構,并分析其缺陷。同時,結合我國的發展現狀,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戰略,即包容性可持續發展道路。
可持續發展;綠色;低碳;包容性
引言
大量發展中國家的證據顯示有限的環境承載能力已經無法支撐“先增長再治理”的發展模式(Bauer et al,2012)。同時,隨著人類活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不斷加劇,氣候變化等因素加劇環境退化,突發性氣象災害不斷增加,國際社會對于發展綠色經濟的呼聲不斷增加,我國領導人也多次指出中國要發展“綠色經濟”、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創新“低碳經濟”,實現“綠色增長”。本文將圍繞“可持續發展”、“綠色”、“低碳”等概念展開,理清這些概念的產生背景、發展軌跡及內在區別,找到每種概念的實踐特點及主要倡導機構,并分析其局限性。
一、經濟、環境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發展經濟學家很早就開始研究經濟增長與資源、人口或社會發展的關系,例如著名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資源詛咒”理論等。但是關于經濟增長、環境治理與社會發展的綜合研究則始于20世紀60年代。1962年美國科學家蕾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不但首次論述了農藥污染(主要是DDT)對自然環境的危害,還對長久以來占據主流的“征服自然”理念進行了抨擊,對之后不同領域的科學家深入研究該領域有重要啟示作用。1972年,第一次國際環保大會——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也稱《斯德哥爾摩宣言》)提出保護環境關系到各國人民的福利和經濟發展,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各國政府應盡的責任,發展中國家的多數問題是發展遲緩引起的。因此應先致力于發展,同時也要顧及到保護和改善環境。在工業發達國家,環境問題一直是伴隨著工業和技術發展產生的,同時人口自然增長也不斷引發環境問題。《宣言》的發布標志著國際社會開始正視環境問題,并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環境問題的根源。倡導各國采取行動,共同保護環境。
(一)現代“可持續發展”觀的產生及發展
“可持續”一詞最早見于歐洲啟蒙運動時期(1713年)德國皇家礦業辦公室發表的一份針對木材資源短缺的報告中(Grober,2007)。后來“可持續”一詞被大量援引在國際組織或政府有關自然資源管理及利用的文獻中。“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概念被明確提出是在1980年由國際自然資源保護聯合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等聯合出版的《世界自然保護戰略: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生存資源保護》中。這份報告指出:“(可)持續發展依賴于對地球的關心,除非地球上的土壤和生產力得到保護,否則人類的未來是危險的。”(馮華,2004)1981年美國農業學家萊斯特·R·布朗在其著作《建設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中首次對可持續發展觀進行了系統論述,主要依賴于控制人口數量、保護資源基礎和開發可再生資源等三大途徑,并對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作了多側面的描述,社會發展的理念進入可持續發展框架,至此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始具雛形(馮華,2004)。
1983年聯合國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1987年在該委員會的報告 《我們共同的未來》(又稱布倫蘭特報告)中首次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現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產生,同時這個定義也成為被多次引用的經典定義。這里的“可持續發展”強調了兩個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貧困人民的基本需要,應將此放在特別優先的地位來考慮;“限制”的概念,技術狀況和社會組織對環境滿足眼前和將來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我們共同的未來)。這份報告提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即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環境保護。
隨后中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進了完善和修正,但都圍繞 “當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論述展開。最近的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定義來自UNDP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中關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闡述:“人類可持續發展是指在采取合理措施盡量避免嚴重影響后代自由的前提下,努力擴大當代人們的實質性自由。”(UNDP,2011)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把 “可持續發展”理解為一種在保護環境的同時滿足當代人及后代人發展的資源利用方式,這種發展方式的關鍵是“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并由此引發了關于“弱”與“強”兩種可持續發展研究范式的討論。
所謂“弱”可持續發展觀,實際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延伸,這種觀點認為對子孫后代十分重要的人造資本和社會資本 (或許包括其他形式的資本)總和,而不是自然資本本身。簡言之,按照“弱可持續性”的觀點,這一代人是否利用完資源并不重要,只要造出了足夠的機器、道路、機場進行補償就行,或者是直接進行經濟補償(諾伊邁耶,2005)。他們關注的焦點是資本總存量而不是自然資源的枯竭(UNDP,2011),世界銀行的大部分觀點都基于這一立場。相反地,“強可持續性”假定自然資本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力很強,人造資本和自然資本不能完全相互替代 (劉鴻民等,2010)。同時,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介于“弱”與“強”可持續性的中庸觀點,例如埃里克·諾伊邁耶(Eric Neumayer)認為,兩種范式都不能證明是虛假的,因此度量可持續發展時要謹慎。
(二)對可持續發展的批判認識
不同領域的學者對“可持續發展”質疑。以羅伯特·索洛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首先對“可持續發展”提出了疑問,索洛將極大極小規則應用于分析代際問題時發現可持續發展可能將社會鎖定在永遠的貧困之中,其論點可概述為,極大極小規則意味著最差一代的效用必須極大 (諾伊邁耶,2005)。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起初那一代的條件,如果按照可持續發展原則,上一代在消耗他們那一份資源時作出犧牲,都會影響后一代的福利,尤其是對于初始階段就很窮的社會。類似的還有一種由貝爾曼克和海伊斯提出的 “可持續發展要求選擇更差的效用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可持續發展實際上是要求社會選擇一種低效用不變的道路,而不是不斷上升的,可能有短暫下降的道路,赫曼(2000)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原因主要有二:效用不能計量;即便效用能計量,我們也不能將它流傳下來。因為效用是一種經驗,不是一種物品。孫耀武(2007)認為可持續發展缺乏可操作性,就“滿足當代人……后代人……”這一定義而言,它既沒有體現可持續發展究竟是什么,也沒有說明應該怎么做,是突出發展還是保護環境,或是兩者的協調,即便是協調,協調的實際可操作性也是突出問題。并且,資源是有限且稀缺的,在對資源作代際分配的時候,應該按照什么年限劃分,即便運用經濟學原理對分配的年限有了科學的論證,在此年限之外的發展還能可持續嗎?
此外,人類學家也從實踐的角度對“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批判。很多人類學家在實地調研后發現,所謂的“可持續發展”項目并不能像設計之初時那樣滿足大眾的利益,而是極大地滿足了其他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渴望,包括國際援助提供者、非政府組織以及國家等。西方科學家試圖代表地球說話,要求實現可持續發展,他們的重點并不是環境本身而是在執行可持續發展項目時推廣西方的技術。同時,那些環境保護或資源管理項目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由于發展中國家政府能力有限,這些項目事實上非但沒有真的起到保護環境的作用,反而對土著居民的原有生活造成了負面影響(Smyth,2011)。
(三)可持續發展的實踐
盡管到目前為止,學界對可持續發展觀的爭論仍在繼續,但國際社會已經開始了可持續發展的實踐。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的《21世紀議程》標志著“可持續發展”從認識到實踐已實現過渡。我國于1994年頒布《中國21世紀議程》,履行了在里約大會上的承諾,并于同年成立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負責具體實施工作。由于該議程并不具備法律效力,此后,我國陸續頒布了 《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30多部環境資源法律,以保證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聯合國是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倡導者和協調者。從1992年的聯合國環發大會到201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里約峰會,雖然參會各方分歧不斷,但是聯合國仍在積極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需求。世界銀行是國際組織中另一個推廣可持續發展的活躍分子。世界銀行也認為,可持續發展是實現減貧的根本途徑,包容性綠色增長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
1971年首個環保NGO綠色和平組織在加拿大建立,此后環保NGO逐漸成為一支活躍力量在政府與民眾間展開斡旋。與政府相比,NGO的優勢在社區,他們往往更愿意深入基層開展活動,但與發達國家成熟的NGO管理體系相比,中國的環保NGO在組織管理、項目執行、立法、籌資等方面都處于發展初期,NGO各自為營,無法形成合力。從生存狀況來看,民間草根NGO較政府設立的NGO更為艱難,且容易被政府排斥。因此創新NGO管理機制,將NGO吸納為政府的補充力量是目前環保類NGO發展的挑戰和機遇。
二、從“可持續”到“綠色”
“可持續發展”理念在上世紀末尤其是199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之后廣為流傳,但進入新千年后,“綠色經濟”、“綠色發展”、“低碳經濟”等概念逐漸活躍于各類政府文件、倡議及行動方案中,這使得“可持續發展”更加模糊,“綠色增長”或“綠色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還是“可持續發展”的延續?
(一)綠色增長不是可持續發展
“綠色增長”并不是“可持續發展”的新說法,而是從另一個方面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種更加靈活、可操作的方法,以實現一種穩定的、可測量的經濟環境發展過程(OECD,2012)。“綠色增長”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2005年韓國首爾(時稱漢城)舉行的第五屆亞洲及太平洋環境與發展部長會議上通過的《漢城綠色增長倡議》中(UNDESA,2012)。這份倡議指出,綠色增長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及聯合國千年目標中(尤其是目標1、7)的關鍵戰略。
“綠色增長”這一理念產生的時間并不長,不同的機構、學者也對其定義各異。UNESCAP認為綠色增長是一種強調環境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過程以促進低碳社會包容發展。OECD認為綠色增長是“在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同時也要保證自然資源能夠持續提供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和環境服務”(OECD,2012),而世界銀行的報告則更加清晰地點出了綠色增長是在增長的過程中保證資源利用有效、清潔且有彈性,但沒有必要放緩增長(Hallegatte等,2011)。 中國學者對綠色增長的定義更加寬泛。彭紅斌(2002)認為,綠色經濟增長方式是一種健康的、科學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的,能夠實現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綠色增長并不排除集約增長方式,而是一種“可持續的集約型”。王有捐認為綠色增長指的是保持環境友好的經濟增長,它的核心是節能減排,并且與綠色GDP概念的提出緊密聯系(王有捐等,2011)。以上這些定義的表述雖各不相同,但都強調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兼顧增長質量,并主要依靠科技和政策創新。
金融危機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但國際社會對重振經濟的要求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簡單,綠色增長逐漸成為各國的發展主線。韓國于2009年首先制定了國家綠色增長戰略——“國家綠色增長戰略”及“綠色增長五年戰略”,并在國際社會大力推行綠色經濟。同年,由該國作為主席在巴黎召開OECD環境政策委員會部長會議,來自30個成員國及包括中國在內的10個非成員國代表(占世界經濟的80%)決定聯手發展綠色經濟,并由OECD牽頭研究如何將經濟、科技、環境、金融等發展要素融為一體的綠色增長戰略,從此以后OECD成為國際社會中倡導綠色增長的主要力量之一。2011年OECD的《邁向綠色增長(Towards Green Growth)》出版,這份報告為如何實現國家經濟增長并抗擊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提供了政策框架、指標及監管體系,是第一本關于國家綠色增長戰略的工具書。
(二)發展綠色經濟成為后金融危機時期各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改革戰略
“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是金融危機以后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常用的術語之一。“綠色經濟”最早見于1989年英國一份由皮爾斯等主流經濟學家起草的《綠色經濟藍皮書》(UNDESA,2012)中。但在這份報告中除了標題中包含“綠色經濟”外,并沒有對發展綠色經濟作進一步的說明,1991、1994年在《綠色經濟藍皮書2:綠色世界經濟》和《綠色經濟藍皮書3:測量可持續發展》中作者又將一些世界問題,例如氣候變化、雨林過度開采、發展中國家資源流失等問題包含其中,這三份報告對進一步完善綠色經濟理念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如同“綠色增長”一樣,目前國內外并沒有一種統一的“綠色經濟”定義,UNEP在里約+20峰會之前發布的綠色增長旗艦報告中指出綠色經濟能夠在提高人類福祉和社會公平性的同時極大地減少環境風險及生態稀缺。簡言之,綠色經濟是低碳、有效地利用資源,同時具有社會包容性。這是目前常引用的“綠色經濟”定義。在國內,“綠色經濟”的定義也形式各異,例如趙斌(2006)認為綠色經濟是以人為本的經濟,始終強調經濟發展的生態化,同時是效率最大化的經濟,努力追求高層次的社會進步。綠色經濟不但包含了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科學理論,又擴展了創新和效率最大化的內容。從實踐來看,要從綠色消費、綠色技術與綠色生產、實施綠色GDP、構建區域綠色經濟等方面構建。楊美容(2009)認為綠色經濟是指人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通過正確處理人與自然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高效地、文明地實現對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使生態環境持續改善和生活質量持續提高的一種生產方式或經濟發展形態。概括而言,在綠色經濟中,公共及私營領域投資的增加是發展經濟和就業的動力,這些投資主要用來減少碳排放和污染,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防止生物多樣性和生態服務減少等(UNEP,2012)。
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在這種背景下發展綠色經濟成為各國制定經濟改革戰略時使用的高頻詞匯。例如,在韓國,綠色經濟戰略主要是依照上文提到的 “國家綠色增長戰略”及“綠色增長五年戰略”展開;在墨西哥,為發展綠色經濟,政府增加了共同交通的支出及環境污染治理;肯尼亞為發展綠色經濟,政府通過采用社區資源管理的方式增加食物及就業;而中國政府主要是通過發展清潔能源和戰略新興能源發展綠色經濟。也是在金融危機之后,聯合國系統包括UNEP、UNCAD(聯合國貿發組織)、UNDESA(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UNCSD(聯合國持續發展委員會)等成為綠色經濟的主要倡導者和行動者,其中尤以UNEP積極。
(三)強調“人”的“包容性綠色增長”理念
“綠色增長”與“綠色經濟”看來相似,都強調環境與經濟的交叉協調關系,但也有差別。綠色增長傾向于一種 “自下而上”的在產品生產、制造、服務等環節采用綠色技術和服務的方法,而綠色經濟則強調一種“自上而下”的,要求創新經濟政策,改革經濟體制以適應環境要求。也有機構、學者認為“綠色增長”、“綠色經濟”理念存在缺陷。如上文所述,世行(2012)認為經濟快速增長對于滿足世界貧困人口的迫切發展需求是必要的,但如果增長不具備社會包容性,不是綠色的,從長期看就沒有可持續性。而當前全世界的增長模式不僅不具備可持續性,更嚴重的問題是浪費和低效。如果各國現在就采取行動,其成本要大大低于污染型增長或在增長模式不可逆時治理污染的成本,這種污染型增長不僅成本高,而且會導致社會變革中斷。“綠色增長”、“綠色經濟”概念的提出是必要的,它強調了要有效利用資源、減少污染、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但卻忽略了政治、行為慣性并缺乏金融工具支持等影響,另外如果這種“綠色增長”或者“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它就應該具體提出一個能夠以地方發展為目標的短期目標,而不是現在這樣寬泛、模糊。最后,綠色增長需要有更好的指標來監測評估經濟表現,現行的GDP等國民經濟指標只衡量短期經濟增長,而綜合財富指標則可以幫助我們確定經濟增長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因此世行倡導 “包容性綠色增長 (Inclusive GreenGrowth)”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包容性綠色增長”不是一種新的模式,而是強調了要在發展過程中協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減貧與避免不可逆的、昂貴的環境破壞之間的矛盾,強調了對“人”在環境、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對窮人和脆弱群體的包容,可以理解為具有包容性的綠色增長。它具體強調五點:高效的綠色經濟增長對實現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政治壁壘、固化的行為范式、缺少融資手段是綠色增長的主要障礙;綠色增長必須著力制定未來5~10年的政策,以逆轉破壞性的政策帶來的治理成本高、公共衛生代價大等問題;包容性除了社會包容外,也包括學科包容,需要利用多種途徑松綁制度約束,創新融資機制;窮國和富國都應根據自身特點制定包容性綠色增長,要打破過去對貧困國家發展經濟只能選擇依靠能源、污染環境、先開發再治理的錯誤認識。
(四)邊界模糊但包羅萬象的“綠色發展”理念
類似的,一種 “綠色發展 (Green Development)”的概念也在悄然興起,尤其是在許多中文報告中,常用“綠色發展”強調與“綠色經濟增長”的區別。“綠色發展”最早是空間規劃和開發時使用的術語,它重點關注建筑環境、社區和土地利用。而目前的“綠色發展”概念事實上比“綠色增長”、“綠色經濟”等概念更加籠統,邊界更加模糊,它包含了綠色增長、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的所有概念,是一個強調了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的綜合概念,是一種對“綠色”發展觀的綜合性描述,同時也是對舊有“黑色”發展觀的反思。簡言之是綠色經濟發展的簡稱(李揚,2012)。
(五)“綠色”理念的實踐
相較于“可持續發展”概念,綠色概念新添了和諧、公平、包容等內容,并且更加清晰地闡明了經濟、環境與社會三要素的具體內容,其中綠色經濟要素包括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科技及創新、私營領域投資等,綠色社會要素包括稅收、分配、公共投資、提供基礎服務的能力、基礎設施建設、醫療、教育、住房等,綠色環境要素包括保護自然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節能減排、提高能效、應對氣候變化等。更加具體而言,綠色經濟工具包括增加服務業就業、綠色信貸、發展戰略性新興能源等,綠色社會工具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防災減災項目、住房醫療教育改革、婦女兒童保護等,綠色環境工具包括生態補償、生態功能區劃分、資源稅、碳交易、使用清潔能源等。
一些機構和學者已經開始嘗試為綠色增長建立指標體系并進行測量。2009—2011年,綠色增長的倡導者OECD制訂了綠色增長測量框架用以測量國家層面的綠色增長進步情況并進行國際比較。O EC D成員國捷克、韓國、荷蘭已經利用這一框架并結合自身國情評估了本國的綠色增長情況。這一測量框架包括環境及資源生產力、自然資源基礎、生活的環境質量、經濟機會及政策回應4個指標組,每個指標組包含3~5個主題,共16個,每個主題包括1~2個具體指標,共30個,指標的選擇根據國情而定,例如韓國在測算時選擇了22個指標。
在經合組織的支持下,拉丁美洲開發銀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經濟系統(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System)及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墨西哥、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危地馬拉和巴拉圭也運用OECD的綠色增長指標來確定國家發展的關鍵領域,改善政策工具設計、選擇及實施。另外,除OECD外,其他機構也在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對綠色增長設計指標進行測量,例如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CSIRO)首席科學家Heinz Schandl從生態經濟學的角度選擇了經濟、社會、生態、治理方面設計了綠色增長指標體系。
綠色經濟領導者UNEP自2008年開始在20多個國家開展了大量的綠色經濟行動,并于2011年發布了《綠色經濟報告》。在這份報告中UNEP提出了一個評價綠色經濟進步的框架,并利用該框架的指標及度量體系為政府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了一些選擇政策建議,包括部門綠色轉型、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生產率等,并且建議政府可以根據國情選擇指標對本國的綠色經濟進步情況進行分析,該指標框架包括5個指標組,22個指標。
許多發展中國家雖然沒有明確制定國家層面的綠色指標體系,但已將“綠色增長”作為國家發展的核心戰略,例如,中國十二五(2011—2015年)規劃提出“綠色發展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印度在十二五(2012—2017年)規劃中強調了“快速、可持續和更加包容的增長”,這是印度首次在國家五年規劃中突出可持續增長這一重點,表明了國家戰略重點的轉移(Bauer等,2012)。
三、氣候變化背景下產生的“低碳發展”和“低碳經濟”
隨著氣候變化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不斷增加,“低碳”一詞逐漸活躍于各類政府文件中。“低碳發展(Low Carbon Development)”最早見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UN,2012),因為低碳發展戰略主要是以減排為主要手段,所以目前的“低排放發展戰略(Low-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LEDS)”、“低碳發展”或者“低碳經濟(Low Carbon Economy)”等提法其本質都一樣,而且也沒有明顯的界限和統一定義,核心都是圍繞減少碳排放和增加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展開。國際上使用 “低排放發展戰略(LEDS)”較多,而國內則以“低碳發展”或“低碳經濟”更為常見。OECD的“低排放發展戰略”是目前較多引用的概念,它是“一種前瞻性的以低排放或氣候適應增長(Climate-resilient Growth)為重點的國家經濟發展計劃或戰略”(OECD,2010)。徐瑞娥(2009)更加全面地總結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2009年經濟大國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論壇領導人會議以后,包括澳大利亞、巴西、中國等17國領導人承諾制定低碳增長戰略,隨后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亞、印度等國陸續頒布低碳增長戰略,而中國早在2007年就率先制訂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成為第一個頒布國家低碳減貧戰略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從實踐的角度來看,我國目前的低碳發展戰略僅限于城市,低碳城市建設存在規劃不合理、基礎薄弱、居民低碳意識不強以及關鍵著力點缺乏等問題(中國環境網,2012)。許多多邊組織也在積極參與低碳發展政策及工具的開發與創新,例如碳交易、碳融資等。目前沒有機構或學者提出低碳發展指標體系。
四、結 論
“可持續發展”到“包容性綠色增長”概念的變化本質上體現了人類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發展的認識變化,即從最早期單純的保護環境,到強調經濟、環境和社會協調發展,到目前的強調“公平”、“以人為本”的包容性綠色增長觀。“可持續發展”、“綠色增長 (或經濟)”、“低碳增長 (或經濟)”雖然都涉及了經濟、社會、環境三大要素,都強調了經濟增長、環境保護與社會和諧發展,增長的“質”勝于“量”,但是這些概念仍有明顯的區別。簡言之,“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宏觀發展目標,是人類追求的社會發展狀態。“綠色增長 (或經濟)”是實現該目標的重要途徑。減少溫室氣體,增加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是實現 “綠色增長(或經濟)”的重要環節,而“低碳增長(經濟)”恰是這一環節的主要組成部分。
目前,很多多邊組織,如世界銀行、聯合國系統 (主要是UNEP)、OECD等都針對不同主題開展了大量活動。世界銀行以減貧為宗旨,世行認為“可持續發展”與減貧密不可分,因此強調通過與政策制定者、公民社會及私營領域攜手解決氣候變化并推行“包容性綠色增長”。經歷了金融危機以后,國際社會開始反思過去的增長模式,OECD順勢倡導“綠色增長”,旨在通過技術及政策創新為經濟增長提供長期的增長動力,例如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與投資。類似的,UNEP開始倡導“綠色經濟”,雖然與OECD的工作有很多交叉,但“綠色經濟”更加強調綠色的經濟,是對過去“黑色經濟”的修正。
綠色經濟(增長)強調的是增長的手段和方式,其核心是技術創新。OECD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國家在綠色技術方面具有優勢,因此在全球范圍內推廣綠色增長。發展中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減貧,他們擔心由綠色增長概念引發 “綠色投資”、“綠色援助”、“綠色貿易”等壁壘,擠壓發展空間,因此更加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所以更加積極地支持“包容性綠色增長”,即給“綠色增長”加一個“包容性”定語,這就強調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機會公平,富人與窮人機會公平,避免陷入發展的“綠色陷阱”。
[1]Bauer S,Ellis K,Harris D,et al.Unlocking Business Dynamism to Promote Green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Growth:Learning from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R].ODI,2012.
[2]GroberU.DeepRoots-AConceptualHistoryof‘SustainableDevelopment’[R]. 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enterBerlin,2007.
[3]ISSD.SustainableDevelopmentTimeline[R].InternatioanlIsntitute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2012.
[4]OECD.InclusiveGreenGrowth:FortheFutureWe Want[R].2012.
[5]SmythL.AnthropologicalCritiquesofSustainable Development[R].2011.
[6]TheWB.InclusiveGreenGrowth:ThePathwayto SustainableDevelopment[Z].TheWorldBank,2012.
[7]UNDESA.AguidebooktotheGreenEconomy[R]. 2012.
[8]UNDP.SustainabilityandEquity:ABetterFuture forAll[R].2011.
[9]UNEP.GreenEconomyPathwaysto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PovertyEradication[R].2011.
[10]馮華.怎樣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可持續發展思想和實現機制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4.
[11]胡鞍鋼.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綠色發展[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0,(2):5-10.
[12]劉鴻明,鄧久根.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的兩種范式述評[J].經濟縱橫,2010,(4):122-125.
[13]諾伊邁耶英.強與弱,兩種對立的可持續性范式[M].王寅通,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14]彭紅斌.綠色型經濟增長方式: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J].理論前沿,2002,(8):29-30.
[15]薛維忠.低碳經濟、生態經濟、循環經濟和綠色經濟的關系分析 [J].科技創新與生產力,2011,(2):50-52.
[16]鄭良海,侯英.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2,(3):141-145.
[17]孫耀武.促進綠色增長的財政政策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07.
[18]王有捐,林衛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綠色增長[J].經濟研究參考,2011,(1):3-12.
[19]徐瑞娥.當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政策的研究綜述[J].經濟研究參考,2009,(66):34-40.
[20]楊運星.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與低碳經濟之辨析[J].前沿,2011,(8):94-97.
[21]中國環境網.《中國低碳城市發展戰略研究》發布[EB/OL].http://www.cenews.com.cn/.
(責任編輯 吳曉妹)
F062.2
A
1001-862X(2014)06-0094-007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www.jhlt.net.cn
張曉穎(1982—),女,山西太原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扶貧與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