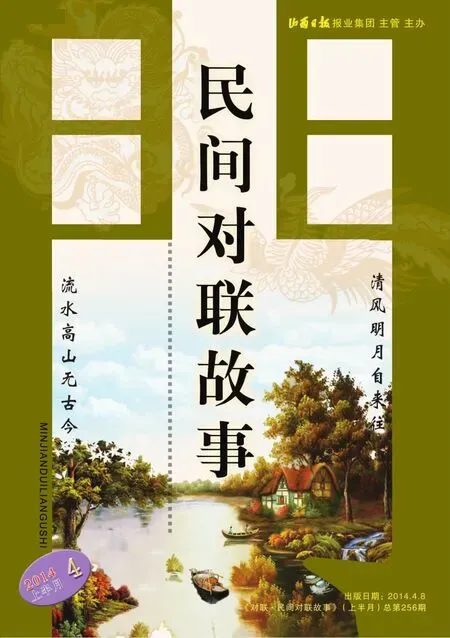對聯創作為何要『貼著地面飛行』
——對聯的現實語境暨嚴海燕現象寫作研討會發言紀要
(本刊記者傅海青整理)
編者按:去年五月,本刊刊登了西安財經學院文學院副教授嚴海燕先生《我為什么要在楹聯界提出“現象寫作”的概念》一文,在聯界引起強烈反響。
今年3月8日,西安財經學院舉辦“對聯的現實語境暨嚴海燕現象寫作”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對聯理論研究者、作者、學者等30余人,聚集于長安古城,從不同角度暢談自己的觀點。本刊擇其精要刊出,以饗讀者。
中華對聯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劉太品:
現象寫作是一種信仰的引領
嚴海燕先生關于“現象寫作”的主張,是站在嚴肅文學的角度,對當代對聯創作進行的一種思考和實踐,應該說,起碼對聯界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但是,自從觀點提出,就引發不少爭議,也出現不少誤解。其中一種觀點,是認為現象寫作只是描寫社會的黑暗面。實際上,“現象寫作”只是倡導面對客觀現實的細節來寫作,并不特指光明面還是陰暗面。就如歌中所唱:“為什么蛙鳴蟬聲都成了記憶?”這種以敏銳的感知,捕捉因社會轉型而發生的失衡,因社會巨變而產生的失調,是直接指向世界的本身,指向我們的心靈深處。這種微妙和犀利,無法簡單地用光明或者黑暗來概括。
對聯文體,是由文學性、實用性和諧巧性這“三位一體”的方式構成。要追求實用,自然難以回避那些廉價的頌揚文字;要增強趣味性、追求諧巧,也難免會伴生內容空洞的文字游戲。這種既是優勢,同時又容易滑向低俗的文體構成特點,加上在市場環境下,文學極易成為權勢和金錢附庸的現實,使得我們很難純粹從文學性上去把握對聯的創作方向,形成既具有文學性,又貼近社會、貼近現實、貼近心靈的寫作方式。
那么,在時代環境和對聯文體特性的雙重制約下,我們為什么還要力挺嚴海燕關于“現象寫作”的創作理念呢?換句話說,“現象寫作”有什么現實的積極意義呢?
在這里,我想用“信仰與心靈”的關系來做個類比: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信仰”似乎最不“實用”,因為它帶不來任何“實惠”。但是,信仰對于我們的心靈卻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對聯是由文學性、實用性和諧巧性構成一樣,我們的心靈,其實是由神性、人性、獸性這三部分組成。對聯無法排除實用性和諧巧性而拔高為純粹的文學性,我們的心靈也無法超越獸性和人性而完全上升到神性。所以,我們就需要信仰,因為只有信仰才是引導我們向上的力量,使我們永遠趨向于神性。在對聯創作方面,我們同樣需要這種向上的引領,而嚴海燕先生“現象寫作”的主張,事實上就起到了這樣一種引領的作用。
對聯理論界二十多年來,一直糾結于平平仄仄的低層次爭論,亟需創作手法和主題內容方面的創新。我愿意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圍內,支持嚴先生的探索,讓更多的作者理解這一觀點,實踐這一理念,以提升當代對聯創作的境界和水平。
張志春教授(陜西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陜西師大教授)點評:
劉太品先生從創作手法和主題內容層面,對于聯界的創作弊端和理論誤區,進行了具有穿透力的剖析,并對嚴海燕的聯語主張予以肯定并支持。但是,聯語構成是否能概括為文學性、實用性和諧巧性三要素,且這三要素能否與人的神性、人性和獸性相對應,提倡純文學性是否就是對聯語的拔高?還值得我們進一步斟酌與討論。
西安市楹聯學會名譽會長解維漢:
“現象寫作”是文人擔當精神和憂患意識的自覺浸染
一、“現象寫作”的擔當意識
嚴海燕倡導的“現象寫作”,初衷是從轉型期的生活現象出發,寫出屬于我們自己的發現、思索和感慨。它無關乎個人利益的變現,也不受人際因素掣肘,著力跟蹤和記錄轉型時期普通人的生存、各種文化的處境以及詩意化變遷。
這種“現象寫作”的提出和初步實施,無疑反映了嚴海燕置身文學前沿陣地的高度敏感,對轉型期對聯寫作的高度關注和深沉思考,尤其對社會和民生的全面聚焦,具有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責無旁貸的擔當意識。我對嚴海燕的憂患意識和求索精神由衷叫好。
易生先生將嚴海燕的“現象寫作”歸納為三點:一是自主性寫作;二是現實性寫作;三是本色性寫作。我認為闡述得很精確也很全面。
縱觀中國古代詩歌史,其實這種“現象寫作”早已有之。杜甫的“三吏三別”和《北征》《兵車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羌村三首》等,都詳盡而真實地通過親歷所見所聞,記錄了安史之亂帶給人民群眾的深重災難,因而被稱為“詩史”。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等詩歌,也深刻反映了當時社會沉重的賦稅、宮室的盤剝、豪強的欺壓對底層百姓的凌辱和掠奪。“一束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成為千古名句。詩人借助“田舍翁”的一聲“長嘆”,尖銳地反映了剝削與被剝削的深刻社會矛盾和強烈對比的貧富差距。鐘云舫在崇麗閣長聯中呼喚的“且向危樓俯首,看、看、看,哪一塊云是我的天。”集中傾吐了那個時代的民生疾苦,家愁國難,抨擊時政積弊,口誅筆伐污吏貪官,其犀利的筆鋒,最后指向整個反動統治集團和維系其統治的思想體系和根本制度,閃爍著鮮明的民主性、戰斗性光輝。繼承前輩詩人聯家深邃的洞穿力和犀利的戰斗精神,是后輩學人的責任。目前,我們雖然身處改革開放的盛世,但同時也面對著諸多的時代積弊和社會矛盾,而回避矛盾的風花雪月之作太多、直面現實矛盾的作品太少,可能是嚴海燕振臂高呼的特定背景。
二、征聯寫作的功過研判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和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對聯文化也迎來“盛世興文”的鼎盛時期。與社會對文化的需求相適應,當代征聯活動也此伏彼起、聲勢浩大、空前活躍。許多聯人,已幾乎將應征創作視為個人創作活動的全部。而因征聯活動有時間、題材、體裁限制,又有獎金、獎品激勵,帶有明顯的功利特征,嚴海燕將這種非自主性寫作形態,稱之為“遵命文學”和“材料作文”。
其實,在我國古代,也有應制詩和臺閣體,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等,都寫過應制詩,畢竟詩人不是在真空中生活,或朝堂奉命,或同僚唱和,都是促使他們寫作應制詩的現實緣由。況且,應制創作也并非不能出精品,《阿房宮賦》、《滕王閣序》等,實際上都是應制而作,其中也不乏阿諛之詞,但也彪炳千秋,流芳百世。
所以,應制創作與現象寫作,在文學的本質上并不矛盾。文學脫離現實,一味風花雪月或憤世嫉俗,反而會顯得空洞無物。當代征聯寫作的繁榮,是因為有著廣泛的現實需求。征聯單位有用聯需求,聯人有著以對聯藝術造福當代、服務社會的使命,因而,提倡“現象寫作”不可否定和貶低征聯寫作,實際上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征聯寫作。需要警戒和避免的,是受功利所驅動,一味投其所好,刻意夸張,美譽迭加,極盡稱頌,為征聯主體評功擺好的膚淺應征作品。而在一些名勝景點和紀念重大歷史事件、歷史名人的征聯活動中,對于那些既具思想性,藝術性又較高,并充滿愛國情懷、中華美德的作品,則應充分褒揚。
三、憂患意識的自覺浸染
讀一些“現象寫作”例句,感到文學性不是很強,有的還存在標語口號化傾向。一直以來,我都堅持一個觀點:對聯不是萬金油。任何一種文學體裁都自有其長處,也有其短板,揚長避短應是題中應有之義。相對來說,山川勝跡聯、祠堂寺廟聯、緬懷哀挽聯、格言聯、行業聯以及春聯等類別可以更好地發揮對聯的長項,蘊育豐厚的內涵,彰顯華美的文采。而一些抨擊聲討性聯作,相對就遜色一些,記得多少年前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楹聯報上刊登整版的聲討對聯,雖然義憤填膺,刀鋒筆劍,但藝術性就欠缺許多。
由此我想,“現象寫作”也不必刻意自成一類,有意去捕捉方方面面、點點滴滴的社會表象進行寫作。只有胸懷憂患意識,將大愛與責任滲透在一切對聯創作之中,并變為一種常態化的自覺行為,才會保持恒久的藝術生命力。《毛詩·大序》中說:“詩者,志之所至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歌是由人內心的感發所產生的。一千多年前,陷于亂世,沒有人給杜甫出題目,下任務,杜甫完全是一種自覺意識,寫出不朽“詩史”。今天,我們仍然崇敬這種自覺的憂患意識。
張志春點評:
植物的茂盛,在于高低稀稠不同群落的匯聚與競爭;人文事業的繁榮,在于多元化觀念的對談與撞擊。解維漢先生的發言,既肯定了提倡“現象寫作”的優點,又從創作實際指出它的局限。這說明一種創作主張的提出,它期待的呵護與滋養,不是簡單地捧殺與棒殺,而是疑義相與析——既要從學理上梳理以溯源分流,也需要與創作實際對接來檢驗與證偽。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增益與完善,凝結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觀點。
著名聯家徐熙彥:
詩學精神之“興觀群怨”在對聯現實語境中的缺失
文學性不只是對文學意趣的孤芳自賞,而應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關照。所以當下的楹聯界,缺失的不僅是文學性,更缺失詩學精神。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是這樣,作為“詩中之詩”的楹聯也應當是這樣。反思“興觀群怨”的詩學精神在楹聯界的體現,我們很容易產生和嚴海燕教授共同的憂慮。我想,嚴海燕教授提出的在對聯現實語境中的文學性表現,就是“興觀群怨”的詩學精神在對聯創作中的體現。分開來看,“興”和“群”相對體現得比較好,這兩類對聯的數量都很大,且不乏精品。“觀”則體現得不夠充分,只有對自然的“觀”,而缺失“對”社會的“觀”,這里的“觀”不僅有心靈的觀察,還有筆墨的關照。“怨”則很少得到體現, 類似“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這樣諷刺現實,傳達民聲的聯語,更是嚴重缺失。很多在全國征聯活動中頻頻問鼎折桂的好手很少有這一類作品,我自己也一樣。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我自覺不自覺地減少了參加全國征聯比賽的次數,改而關注身邊的事,關注家鄉的變化和民生的熱點話題,嘗試用對聯的形式反映民生民情。這是對嚴海燕教授“現象寫作”的一種回應,也是對自己對聯視野的拓展。借此機會,拋磚引玉,請大家多提意見,也希望更多的楹聯作者,參與到“現象寫作”的實踐中來。
張志春點評:
作為一個國內有影響的青年聯作家,徐熙彥將“現象寫作”的內核提煉為“詩學精神”予以肯定,并將其與孔子主張的“興觀群怨”審美功能揉合起來。這當然是從純文學的層面來展示的。而且,他還以創作上的實踐表示對這一主張的呼應和支持。這是難得的。我覺得,如果要舉出評判創作與理論的一個簡單標準,那就是看你的創作能否擊中讀者心靈柔軟之處,就是看你的理論能否為作家所折服,并心甘情愿接受你理論的指導。徐熙彥實實在在的話語,讓我們對“現象寫作”的主張及其指導下的實踐有了更多的期待。
原《長安聯苑》主編李文西:
高層次對聯,應以人文關懷為己任
就目前情況而言,各種征聯熱鬧非凡,但對聯文體的品格與作家的風格則不顯。對聯文體的品格,其個性特征就是親近社會,親近百姓。作家的風格就是要把自己寫進去,要從身邊發生的事情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東西。我從生活現象與對聯使命的角度,談兩點對“現象寫作”的認識。
其一、風格多樣化
二十年前,嚴海燕曾提出關于對聯創作風格多樣化的理由:“對于個人來說,他當然有權利長期乃至終身吟風弄月或者歌舞升平,但是對于一個有著諷刺幽默文學傳統的文明古國,在社會問題迭起叢生的時候,依然讓一種文體呈現出清一色的明亮,而少有‘我為人民鼓與呼’的作者,這無論如何都是叫人費解的。”
然而“風格多樣化”這句話,說起來不易,做起來更難。對聯不僅講究文字凝練,而且與舊體詩詞比起來,還多了實用性、游戲性。春聯、婚聯,按照民俗習慣是不可說敗興話的。勞累了一天的聯友,晚上上網玩聯時也大都喜歡風花雪月。至于征聯參賽就更不用說了,人家出錢“買”聯,你不投其所好而是多發忤逆之言,會有好果子吃嗎?
但這樣一來,那些不一定美麗但卻一定真實的生活以及人們對它的真實感受,要想在當代對聯格局里找到自己的棲身之所,就不大不容易了。二十年后,嚴海燕特意為這些不受待見的對聯開辟了一個園地——“現象寫作”專欄。無論你鶯歌燕舞或者感嘆憂愁,只要你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貼著地面飛行”,皆有希望入列其中。
其二、寫什么
“現象寫作”,一寫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及個人際遇,二寫現實生活中事物的變遷。前一個是平民視角,后一個是文人視角。她不逃避現實,而是與時俱進,真正踐行古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的文學主張。她只顧平實寫來,不單純倚重“長久的藝術生命力”,也不刻意追求“華麗、喜慶、浩大、詩意”的美學效果。
嚴海燕說,他曾看到一副《題找工作》的對聯:“瞰四海千帆競過,俯九原萬馬齊喑,應憐北戰南征,偶曾夢話說三顧;相逢皆蹄虎之驢,所學盡屠龍之術,堪笑寒來暑往,無可奈何又一年”,并頗為欣賞,只是感到同類對聯似不多見。
事實正是這樣。當下更多的對聯作者“熱衷于對預設主題的集體表現”,“而放松了對身邊變化的境況的個人關照”(嚴海燕語)。君不見國人正為米面油以及“菜籃子”是否安全而提心吊膽,而有些人卻“不失時機”地引進“蘇丹紅”、“瘦肉精”等“高科技”;君不見風沙已大規模入侵長城內外,工業排廢使中國無污染河流所剩無幾,而某些官員卻繼續祭起“土地財政”的法寶不放;君不見上海290種原生植物或已消失,而不無爭議的轉基因大豆、玉米正涌向東北和廣西;君不見中國貧富分化嚴重,原本屬于革命時代的“土豪”一詞重新進入流行詞語之列,而社會底層人物卻經常遭遇“被幸福”、“被平均”……對此,不少對聯作者似乎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仍整天穿梭于各類征聯之間,你有奇思妙構,我有華詞麗句,贊美不擔風險,附和只有好處,爭奇斗艷,樂此不疲。難怪有人借來兩句“格言”來進行調侃:“情,是用來維系社會的;才,是用來粉飾社會的”。
“文學是人學”,凡認同高層次對聯屬于文學的對聯作者,都應以人文關懷為己任。建議優秀的對聯作者,在進行其他品種的對聯創作之余,不妨將自己的才華與當下的現實結合起來,嘗試著寫出別樣的對聯來。也許,這是嚴海燕提出“現象寫作”的初衷之一吧?
張志春點評:
李文西先生極其精警地強調聯語的民本立場,強調聯家的獨立精神。或許我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會感到這一強調如同主旋律一般不斷顯現,但它是一種讓有扭曲傾向的文化藝術活動走向正道的努力,仍然讓我們浮想聯翩,仍然透地氣,仍然為現實所期待,這就值得我們反思,值得我們琢磨。
長安詩鐘社名譽社長李文平:
“現象寫作”是反映社會現實的需要
“現象寫作”,我個人的理解就是把自己所觀察所剖析的社會萬象、社會亂象、社會怪象,以文人的良心,文人的憂樂情懷,文人的傲骨和秉性,把它構思成文學作品。旨在撥亂反正,除惡揚善,傳遞正能量。
“現象寫作”,在先賢們的小說、詩、賦、詞、曲、楹聯中已有不少傳世佳作,就是在最年輕的格律文體——詩鐘作品中也屢有發現。如,鼎革封建教育,推進教育現代化的先驅者、著名教育家嚴修(1860—1929),曾以《樂·新(七唱)》為題拈鐘一首:“魚躍正因添水樂;牛棲安識發硎新”。此鐘上下句雖然都是白描,“躍”與“棲”動靜形成對比,而“樂”含喜,“新”卻藏悲。上句從“海闊憑魚躍”名句化來。對魚而言,自然是水越多越好,句意看是在添水,更是在為魚添“樂”,當然是喜事了。下句的“新”字里卻深藏著悲恨,因為著硎磨刀,以發新刃,牛就要挨宰了,悲恨憤然而生。字里行間暗示著某些社會現象,給讀者留下了廣袤的聯想空間,發人深思,耐人尋味。又如,現代詞學家、書法家、詩鐘大師張伯駒(1897—1982),有《庸醫·占卜(分詠)》詩鐘一首:“新鬼煩冤舊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庸醫自古有之,于今為甚更為惡,假以偽科學坑人、害人、殺人。上句自杜甫《兵車行》中“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詩句集來。下句詠占卜,集自李商隱《馬嵬坡》之一“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詩句。句意揭示他生難以預測,而今生先已休矣,直指占卜的虛無和迷信;同時,也是對在街頭墻角那些搞占卜、弄神鬼、坑人、騙人、斂財者自身的一個辛辣諷刺。
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水平突飛猛進,物欲在急劇地膨脹,人們的傳統觀念遭到挑戰,文明道德的底線屢被沖破。所以,而今的社會現象則更為復雜紛繁,嚴重影響著社會最底層民眾的生活、生態和生存。我非常認同嚴海燕先生所說的:“我們深感自己有責任,同時也有權利放棄一切先入為主的東西,親自跟蹤和記錄轉型時期普通人的生存、各種文化的處境以及詩意的變遷。”也正如嚴海燕先生所提出的“現象寫作”是“一種訴諸概念的提醒,一種‘貼著地面飛行’的寫作方式。”當然,也是當代文人的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
時代在發展,語境在變化,文化藝術(包括詩、賦、詞、曲、聯、詩鐘等等)也應當隨著時代脈搏的跳動,敲著時代的鼓點闊步前進。嚴海燕先生關于“現象寫作”的提出,為我們在新時代新的語境中,如何提高創作水平,如何反映揭示社會現狀,貼近社會現實,開辟了一個探索和創作的方向。
張志春點評:
感謝李文平先生對“現象寫作”定義式的表達,以及對詩鐘的介紹。那些看似文字游戲的詩鐘文體,實則是把作家觀察且剖析的社會萬象寫成特殊樣式的文藝作品。這確乎是貼地面飛行的詩意創造,是穿透人生的生命體驗。而這里的舉例則是從更深的時間長度中為“現象寫作”搜集來了令人心服口服的創作依據。
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安市作協副主席楊樂生:
中國缺乏影響世界的作家群,是因為不敢面對現實
現實主義文學在中國曲曲折折,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也正因此,中國不容易出現影響世界的作家群,因為我們不敢面對現實。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說,嚴海燕“現象寫作”的提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界來講新意不多,因為我們現當代文學界一直在強調現實主義文學,也就是說它沒有超出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大框架,但對于對聯界來講“現象寫作”極富意義。
對聯界應該走進現實,走向現代,對聯作品要有內容,對聯作者要有創新。
就我個人看到的日常對聯而言,模式化比較嚴重,陳詞濫調較多,動不動“耕讀傳家”、“國泰民安”。你大字不識幾個,也敢寫“耕讀傳家”!
具體到征聯,你當然可以征,問題是如何征。要防止偽文化,警惕脆弱的虛榮心。應該體現個性,發掘我們內心深處的東西。對聯屬于大雅,我不同意稱它為民間文藝的東西。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好對聯都是大文人創作的。
張志春點評:
人常說西北大學是陜西的北大,樂生教授那種個性張揚的風采很有魏晉風度。他的話語沒有拘束,海闊天空,坦率直爽,他有時甚至為了忠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惜一任話語走向極端。但我們從他“‘現象寫作’的提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界來講新意不多”,“但對于聯界來講‘現象寫作’極富意義”的判斷中,可以感受到清醒而視野宏闊的表達,感受到自在隨意地宣泄中有著學術的嚴謹,有著悠遠的意味。
西安財經學院教授、著名小說家馬玉琛:
征聯未必征不到好作品
我認為,征聯未必征不到好作品。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就帶有“命題作文”的性質。關鍵問題在作者身上,作者要有生活體驗和生命體驗。有了足夠的營養,就有一定的高度。從清代紀曉嵐的對聯可知,對聯講擔當,也講情趣,不能總是講擔當。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的語境不同,要根據現代漢語的特點,發掘它的現場感。
張志春點評:
馬玉琛教授語淺意深,給我們啟迪良多。他從創作層面道出了當代聯家一個普遍的困惑,即生活在白話語境之中,卻要創造的一個源于古漢語語音、詞匯和句式的文體。這就是一種疏離。近現代以來國家種種內憂外患,文學藝術多講擔當而忽略情趣,又是一種疏離。現代人如何進入聯語寫作現場?如何像古人那樣將學養融滲入生命體驗之中?如何將眼前所遇、耳邊所聞、心中所想、身所經歷化為聯作?這大概是當代聯界所有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要面對的問題。
長安詩鐘社社長王小鳳女士:
“現象寫作”對詩鐘創作也非常必要
今天大家討論嚴海燕老師提出的“現象寫作”這一話題,其實不光是對聯界,對我們長安詩鐘社來說,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在我們詩鐘社的創作活動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即提倡多寫風花雪月,少碰敏感問題,怕惹政治麻煩。仔細想想,為什么古人的那些名篇能夠歷千年而魅力不減,而我們現在創作出來的一些東西有時遭人嘲笑,應該說,這與我們的創作一定程度脫離現實生活有關。
張志春點評:
感謝王小鳳女士的介紹,讓我知道了長安還有一個詩鐘社,而且展開活動有十年之久了。她談到自己創作時的膽怯和嚴海燕談理論創新時的猶豫,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過去年代極左意識迫害文化藝術創造所帶來的陰影。而這種陰影雖然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逐漸邊緣化,但卻未能完全消失,這也是聯語創作需要面對的語境之一。其實我們都知道,聯語是千古事業,若無膽識,怎么能千古呢?
著名聯家王天性:
我們要在接地氣的情況下把對聯寫好
對聯作為國粹藝術,與我們民族的文化習慣密不可分。因為對聯具有實用性、裝飾性特點,說好話于是也成為創作的慣例。婚聯如斯,壽聯如斯,春聯、賀聯等莫不如斯!一個人去世了,不管他生前人品、功過,挽聯也都表現出少有的寬容。雖然不同流俗者歷代大有人在,其經典作品至今仍在流傳,但我們依舊面對著這樣一個事實:有一種文體不顧真相而偏好評功擺好!這種狀況讓人尷尬,卻很難脫俗。
楹聯想要最終成為一種文學文體進入文學史,寫作非實用性對聯,不受傳統對聯愛說好聽話的影響,全方位地描寫看到、聽到、想到的一切,淡化粉飾,強化寫實,并力爭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許是真正成為文學的必由之路。
作聯要用真事,說真話,少寫假話、空話、套話、大話!盡可能寫得短一點。通俗不是流俗,文雅也不是讓人看不懂。鐘馗就是鐘馗,西施就是西施。西施很美,鐘馗頂多是另一種美,事實擺出來優劣自現,不要亂貼標簽。評價人和事也要慎重、中肯,切莫讓功利心主宰了判斷,說其壞便是一無是處,要說好時連耳朵都給涂上雪花膏。
以社會現象、生活現象入聯,無疑拓寬了對聯的取材空間。“現象寫作”關注現實一點不假,但也不是放棄浪漫主義,因為真正的浪漫主義是在間接地反映著現實。
其他文體能描寫社會變遷,抒寫人生的喜怒哀樂,對聯當然也能!只要我們把筆觸伸向廣闊的社會生活,文藝創作的素材就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社會生活千形萬象,反映到文藝作品中來自然應是豐富多彩。謳歌光明和批判丑惡,都能產生高質量的文藝作品。這就像有兩堆土,先裝在兩只筐中是兩堆土,后裝進兩只桶內,還是兩堆土,只有將土放到窯里,放進南方的景德鎮窯或者北方的耀州窯,才能燒出好瓷器來。杜鵑開在高山上,玫瑰還帶著刺兒,由于花好備受人們喜愛;水田里的雜草和旱天里的雜草固不相同,但因干擾作物生長而同樣令人厭惡!贊頌美是在肯定美,抨擊丑也是在肯定美!我們就是要在接地氣的情況下把對聯寫好。
張志春點評:
眾所周知,王天性先生是國內有影響的聯家。他的創作有質有量有激情有張力。于是我們從他的感悟中聽出了來自創作實踐的豐沛底氣,感受到一種隨心所欲不逾距的自由境界。他是以創作者的共鳴來呼應“現象寫作”這一理論主張的。聯語創作在突破粉飾現狀的文化之膜,而要直面現實,他從創作體驗中,道出聯語和其它文體一樣能應于社會轉型,能表達繁雜的外在與內在世界。這是當代聯家的一種文體自覺與自信。
西安財經學院文學院教師田子爽博士:
“現象寫作”不僅開辟了一個認識欣賞對聯的新穎角度,也提供了一個寫作對聯的方法途徑
當今社會多元化、多語境的文化氛圍中,對聯日漸流于形式,不僅被社會主流意識所漠視,更是被擔負著文化傳承重任的青年一代所忽視。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年輕人的責任和義務。在對聯如此尷尬之境地,嚴海燕老師提出的“對聯的現實語境”、“現象寫作”,認為對聯應貼近現實生活,對生活進行心靈觀察與筆墨關照,從而更加豐富對聯的功能。這樣的理念讓我們重新審視對聯這個易被忽略的文體,不僅開辟了一個認識欣賞對聯的新穎角度,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寫作對聯的方法途徑,對我們年輕人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張志春點評:
這位80后學者對對聯文體有著特別的感悟。她意識到傳統聯語因與生活深切地關聯而成為富有特色的文化符號,而今天聯語為主流意識和年輕一代所忽視,癥結恰恰在于這一文體空殼化、形式化。而提倡現象寫作說就是為其恢復生命活力的方法與途徑。時下多以年齡長幼來評估論說的深與淺,在這里我們聽到了年輕人厚重的聲音。難得。
西安財經學院文學院教師張穎博士:
創作理論要成為創作實踐的“領跑者”
嚴海燕老師是九十年代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碩士,但多年來,他似乎遠離現當代文學而一直在從事古典詩詞和傳統對聯的寫作和研究。今天,從他提倡的楹聯“現象寫作”理論中,我似乎又看到了現代文學所具有的的現實性品格和當下關懷的潛流和回響。
當下的文學藝術研究中,文學理論和批評實踐處在一種尷尬的跟隨創作、解釋創作的陪跑狀態。今天會議上諸多楹聯創作者對嚴海燕“現象寫作”這一理論的呼應和認可,說明創作理論對創作實踐有著敏銳的發現和及時的引導,它不只是創作的陪跑者,還是“領跑者”,理論和批評正是在與創作實踐的互相砥礪中煥發出新的活力。希望有更多的理論研究和批評爭鳴者共同參與,不斷豐富“現象寫作”的理論內涵。
張志春點評:
作為80后學者,張穎博士對現象寫作主張的評估放在了當代文學藝術總體格局內,放在了理論創造與創作實踐的互動關系之中。這是一種寬闊的眼界,一種有所思的表達。
西安楹聯學會副會長支勝利:
文學要客觀反映社會,而不能選擇性失明
嚴海燕老師的“現象寫作”是在2012年《長安聯苑》先行推出,后在《對聯》雜志等媒體正式發表的。我們的社會正處于轉型期,成績顯著,問題很多,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但我們的對聯作品特別是征聯作品,很多卻是鶯歌燕舞,應景特征明顯。文學要反映社會,就應全面、客觀,而不能搞選擇性失明。要在創作上“百花齊放”,就應允許理論上百家爭鳴。針對聯界的浮夸和跟風現象,嚴海燕老師保持著自己的清醒,以羸弱的身軀承擔起一個沉重的話題。“現象寫作”拒絕刻意迎合他人,拒絕虛假浪漫主義,同時也不矯情,不專門寫社會陰暗面,是一個比較全面的主張。
張志春點評:
支勝利先生告訴我們,“現象寫作”主張最初萌生于《長安聯苑》這樣一個地方性的內部刊物,然后走向全國。這也啟示我們,任何一種文化的創造與創新,最初都需要一種呵護與扶持的土壤。哪怕它不太起眼,但很重要。倘想起唐代的詩人都是成群出現而卓然成家的,詩才獲得肯定的平臺是官場考場情場等博大的空間,我們就會心事浩茫連廣宇。有一群可以切磋琢磨的朋友,有一個可以發聲刊文的平臺,就是聯語作品與理論滋長的重要語境。雖說這是一種看似格局不大的語境,其實往往是很重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意義會不斷放大而顯豁起來。
張志春教授總結:
本次研討,極為充分地體現了三個關鍵詞:現實語境、文學性和現象寫作。
先說現實語境。諸位從生活疏離、文體疏離或觀念疏離等層面展開,作了多角度闡述。而嚴海燕談理論創新時的露怯,王小鳳詩鐘社創作時的敏感,都是怕扣帽子怕惹政治麻煩,仍有浩劫時代的陰影。這當然也是讓我們俯仰古今感喟萬端的現實語境。
第二個問題,文學性。過去人們不承認,不敢提,以為聯語不過是生活中的小點綴而已。梁啟超曾集聯一冊也只說是“痛苦中的小玩藝”。我自己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古今作家名聯選》后記中強調其文學性,呼吁聯語寫入文學史。其實當時我也不明白聯語具有雙重的文學性,或者叫做聯語文學的兩個維度。一種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這一點今天都認可。它以文本為精準標準,講究抒情性、意象性、意趣性和表達精美的音樂性,追求使人沉浸其中的意境。但聯語還有一種性質,是民間文學性。民間文學大于文學,它更像多媒體一樣立體狀態的多向度展示,不是傳統文學那樣單向度。它在絕對意義上可以說不是文學。因為在學科上,它在二級學科上屬于民俗學,一級學科屬于社會學。如果說傳統文學意義上的聯語講究精英立場的意境,那么,民間文學意義的聯語則講究民間立場,講究儀式,而且更神圣。因為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沒有哪種文體,像聯語一樣深入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歲時年節、婚喪嫁娶的人生禮儀,喬遷、自家書房,公眾校舍廟宇,亭臺樓閣山水,無處不聯,無時不聯。有人據此以為聯語作為一種文體先天性的不足,似乎太實用了。其實不然。它講究儀式就自然有一種尊嚴與自由,而不是依附式的工具。我們知道,在生活情境中,書寫什么字體,紙張什么顏色,張貼什么地方,什么時間,都有特別的意味,特別的講究。即使有的聯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天南海北地反復呈現,如祝壽的“福如東海常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春聯的“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商家的“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等,那也是歲歲年年聯相似,年年歲歲意不同,從純文學上看或許會有審美疲勞,但從儀式層面來看,仍有神圣須得敬畏的一面。你敢設想大年時節給人家門口貼非紅色的聯語紙張么,或者居喪之家門聯貼出非白色的聯紙!純文學沒有這個講究,而民間文學卻絲毫不能馬虎。所以談文學性至少應該從這兩個維度談起。
第三點是現象寫作。這是嚴海燕提出極有意義的聯語寫作主張。它的起根發苗或許兆源于現象學“不要想,只是看”的響亮口號,但我看他主要是有感于多年來國內聯語創作積弊的登高一呼。它敏銳地暗示出聯語創作與當下語境某種意味的脫節與疏離。它要求聯語表達眼中所見、耳邊所聽到的生活本真情境,而不是路徑依賴般借助陳辭濫調地建構出一層厚厚的文化膜,甚至那明顯可看出有瞞和騙的東西。倘若從創作與理論的互動關系來看,這一聯學主張的新穎度和力度便陡然可見。在國內更多的文學或藝術理論被動地跟隨在創作腳后,或為解釋,或為圓場,或為包裝,或墮落為偽創造的吹鼓手的時候,嚴海燕這一主張的提出,得到了理論界的呼應,引發了思考與爭論,也引發了國內不少聯家的創作,如徐熙彥、王天性等人的創作呼應,都是難能可貴的。
在我看來,嚴海燕“現象寫作”的主張是從純文學意義上提出的。他當然是為了提升聯語創作的整體境界而考慮的,但卻未意識到聯語另一重要品質。“現象寫作”其實是一種深刻的偏頗。倡導者既然拒絕本質主義,既然是從往昔美好的意向(大雁、烏鴉、螢火蟲等)和語匯入手而反觀當下,則不妨從西方現象學的角度對其“現象寫作”理念予以完善。在民間文學層面,儀式方面是有禁忌的,更有表達理想的趨向。如春節不說破茬話,平常說話低調的人,春聯上也會將自己的理想合盤捧出。事實上從來也沒有一個觀點能夠涵蓋一種文體的全部,只要它能引起聯界的關注,引發理論界的反思,創作界或多或少的呼應,那就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所以我要說這種理論主張即便偏頗,那也是深刻的偏頗。比起那些沒有棱角、沒有任何作用卻永遠正確的話語,它更重要,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