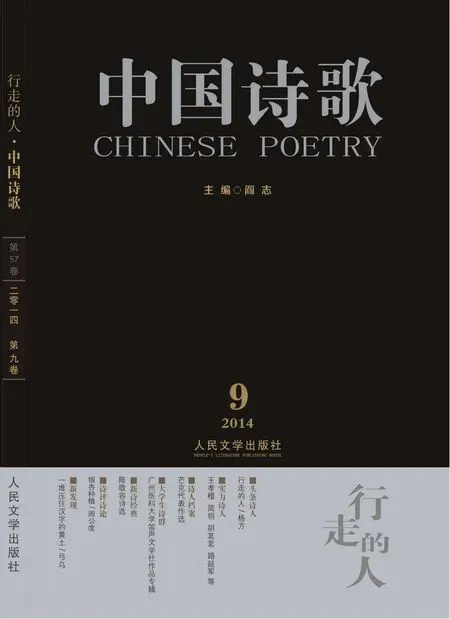行走的人(組詩)
2014-11-14 23:39:45楊方
中國詩歌
2014年9期
楊方
行走的人(組詩)
楊方
這些年,我看到了詩人楊方的不斷進步。從她的第一本詩集《像白云一樣生活》,到第二本詩集《駱駝羔一樣的眼睛》,她的詩從簡單走向豐富,從稚嫩走向成熟。她詩中源自生命深處的憂傷沒有消失,她詩中對少年時代生活的那片土地刻骨銘心的愛沒有消失。生命的痛感,發自心底的真摯的呼喚,對文化的敬畏和對大自然的愛,以及對他者的理解與同情,這些構成了楊方詩歌作品的基本品質和感人至深的力量。
在楊方的許多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吸收和對其他藝術門類及西方現代詩歌的借鑒與融會。正是這些,讓她的詩歌有了詩歌藝術情感的深度,語言的根底和文化的價值。也正是因為這些,我們看到,她的詩歌近些年在不斷地變化與上升。
——林莽
尋鹿記
我見過那只鹿,十幾年前
被一根粗繩子拴著,在河洲上吃草
誰能相信,那么大的河洲
只有一只鹿在那里吃草
只有一只鹿頂著森林一樣交錯的鹿角
低下頭吃草
有一次,我看見它以繩子為半徑,一圈圈奔跑迎著風向嗅著遠山的氣息,呦呦地鳴叫
別離那頭鹿太近,那是危險的事情
養鹿人這樣對我發出警告
他用鋼鋸鋸下鹿角
鹿茸切成片泡酒,鹿血摻著白酒喝下
而受傷的鹿,被破布包扎
養鹿人不懂,那龐大的鹿角
是繁星和一座森林組成的,回家的路
在長出新角之前,那只鹿是多么憂傷和憤怒后來它掙脫繩索,狂奔而去……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