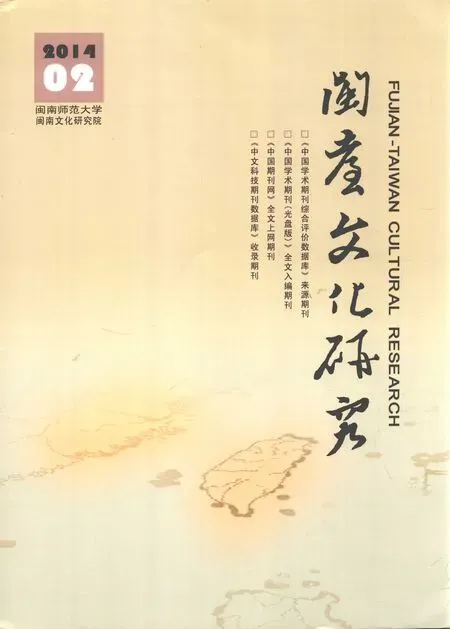澳甲制的源流及演變
李堅(jiān)
(韓山師范學(xué)院潮學(xué)研究院,廣東潮州521041)
澳甲制的源流及演變
李堅(jiān)
(韓山師范學(xué)院潮學(xué)研究院,廣東潮州521041)
澳長(zhǎng)制為南宋時(shí)期國(guó)家治理中國(guó)南部海域的一項(xiàng)重要舉措。清時(shí)期澳長(zhǎng)制與基層里甲制度進(jìn)一步結(jié)合,將船戶編甲與船只編甲緊密結(jié)合,并逐步職能化,進(jìn)一步形成澳甲制;同時(shí),將施行范圍從沿海海域延伸至內(nèi)河航道,設(shè)立了內(nèi)河澳甲,協(xié)助管理內(nèi)河船只。
澳甲;澳長(zhǎng);船政
澳甲制為歷史時(shí)期施行于中國(guó)南部沿海地區(qū)的一項(xiàng)涉及海防及船政的管理制度,產(chǎn)生于南宋時(shí)期南部海域抗擊海盜的過程中。在歷史時(shí)期,澳甲制成為地方州(府)縣官員治理沿海島嶼、維持海道秩序的重要舉措。管見所及,學(xué)界尚未有關(guān)于澳甲制度的專門研究。有鑒于此,本文對(duì)澳甲制度的源流及演變進(jìn)行梳理,重點(diǎn)考述南宋及清代兩個(gè)重要時(shí)期。
一、從保伍法到澳長(zhǎng)制:南宋及元明時(shí)期南方沿海的海域治理
(一)南宋時(shí)期澳長(zhǎng)制的產(chǎn)生及發(fā)展
從現(xiàn)有史料看,澳長(zhǎng)制最早施行于南宋初期的福建沿海地區(qū),由乾道年間(1167~1168)出任福建兵馬鈐轄的鄭興裔提出。南宋初期中國(guó)南部的福建及廣東沿海,海盜為患,而這些地區(qū)自北宋以來海防力量一直都較為薄弱。南宋政權(quán)建立以后,在李綱的建議下,南部沿海區(qū)域的海防建設(shè)逐步展開。除了創(chuàng)建水軍寨、增設(shè)水軍、改進(jìn)戰(zhàn)船等基礎(chǔ)設(shè)施外,民間武裝力量也出現(xiàn)在地方官員構(gòu)建的海防藍(lán)圖中。
福建沿海海盜活躍,正如鄭興裔指出:“海之大不知幾千萬里,不逞之徒乘風(fēng)猝至,覘其無備,壞民居、奪民食,海濱郡縣屢被焚劫。朝廷征兵以剿之,而調(diào)遣于內(nèi)地,豈能朝發(fā)夕至。兵甫四集而海上之寇又飛云掣電,牽率以遁。若欲從而追擊之,則巨浪之中不能坐立,安能與之格斗哉。及夫守備解嚴(yán),而肆劫者如故,我來則彼去,我去則彼來,軍士疲于奔命。”水軍駐扎地遠(yuǎn)離瀕海地區(qū),缺乏深海作戰(zhàn)的經(jīng)驗(yàn),無法及時(shí)應(yīng)對(duì)突發(fā)的海盜事件。即便與海盜發(fā)生遭遇戰(zhàn),也無必勝的把握,“巨浪之中不能坐立”。為此,鄭興裔認(rèn)為,“為今之計(jì),莫若令沿海之民自為捍守,瀕海州縣各有嶼、澳。澳置一長(zhǎng),擇地方之習(xí)知武藝者而任之,仍令結(jié)為保伍,旦夕訓(xùn)練。以追則迅,以戰(zhàn)則克。如其無事則盡力于農(nóng),不仰食于縣官。一旦寇至,澳長(zhǎng)徑率其眾御之,不使登劫。彼皆有父母、妻子、兄弟、室家之系,驅(qū)之必力。更責(zé)其兩鄰互相策應(yīng),如有能殺賊者,州縣第其勞以賞之,容隱坐視者罰無赦。”
鄭興裔認(rèn)為,澳長(zhǎng)與地方正規(guī)軍兵相比有其自身獨(dú)特的優(yōu)勢(shì),如澳長(zhǎng)多為地方土豪,熟識(shí)地方形勢(shì),“不仰食于縣官”,能夠更及時(shí)的對(duì)海盜施以打擊等等。因此,令瀕海地區(qū)的民眾結(jié)為保伍,同時(shí)推選武藝高強(qiáng)者任澳長(zhǎng),賦予其率眾抗擊海盜的職責(zé)。鄭興裔提出的澳長(zhǎng)制實(shí)質(zhì)上也是民兵政策。
類似的民兵政策在福建地區(qū)有其根源。北宋元豐元年(1078),大臣蹇周輔奏請(qǐng)令福建民戶結(jié)成保甲,按戶抽取槍杖手,于農(nóng)隙時(shí)校閱,有捕盜職責(zé),維持基層治安,成效顯著。南宋初南方各地紛紛成立忠義巡社,抗擊草寇、兵匪等。福建有保伍法,為忠義巡社之一:“福建保伍者,鄉(xiāng)村自相團(tuán)結(jié),而立豪戶為首領(lǐng),所以備盜也。閩中人素勇悍,在熙寧間有槍杖手五千余人,建炎初嘗用之,紹興后廢。建炎元年八月,又用張誠(chéng)伯言,置諸路忠義巡社,其制甚備。紹興初,言者以為擾民,遂罷,惟福建獨(dú)存。”從槍杖手到保伍法,反映出民兵政策的延續(xù)性及發(fā)展。
澳長(zhǎng)制與保伍法一樣,均是令鄉(xiāng)村民戶“結(jié)為保伍”、“自為捍守”,自我武裝,以達(dá)到維持地方秩序的目的,只不過澳長(zhǎng)制主要施行于瀕海泊船區(qū)域及島嶼。
從保伍法到澳長(zhǎng)制的實(shí)施,并非個(gè)案。在廣南東路地區(qū),情形與福建大體相似。嘉祐六年(1061),廣、惠、梅、潮、循五州率先按戶抽取槍杖手,后進(jìn)一步結(jié)為保甲。這一制度在兩宋之際得到培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團(tuán)體,地方民兵首領(lǐng)往往在抗擊盜賊、維持地方穩(wěn)定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以聚落的首領(lǐng)、統(tǒng)率等地方土豪,通過自我武裝、相互協(xié)作,成為南宋以降廣南東路地區(qū)維護(hù)地方治安的重要且經(jīng)常性的方式。
南宋初,為抗擊海盜,不少?gòu)V東官員嘗試在沿海地區(qū)推廣民兵政策。紹興五年(1135),廣東帥臣連南夫奏請(qǐng),按地域令沿海居民結(jié)社,其法“五百人結(jié)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為社首,其次為副社首,備坐圣旨,給帖差捕。蓋濱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平時(shí)無力往擒爾。今既聽其會(huì)合,如擒獲近上首領(lǐng),許保奏優(yōu)與補(bǔ)官,其誰不樂為用。”社首由地方上的“材勇物力人”擔(dān)任,由官府賦予追捕海盜的職能,許諾論功行賞,將這些基層力量納入到官方的海防體系之中。
不難發(fā)現(xiàn),“社首”、“澳長(zhǎng)”均源于北宋時(shí)團(tuán)結(jié)民兵的理念,雖然在施行的具體情節(jié)上有所區(qū)別,但在實(shí)際中這些“澳長(zhǎng)”、“社首”往往能夠協(xié)助官府應(yīng)對(duì)來自海上武裝力量的威脅。南宋初期,在鄭興裔、連南夫等官員的大力推動(dòng)下,民間武裝愈發(fā)普遍地參與抗擊海盜的行動(dòng)中。據(jù)隆興元年(1163)地方官員調(diào)查,當(dāng)時(shí)海盜遍布閩粵沿海,“竊見二廣及泉、福州多有海賊嘯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資給,日月既久,遂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門、潮州沙尾、惠州潨落、廣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是停賊之所。官兵未至,村民為賊耳目者往之前期告報(bào),遂至出沒不常,無從擒捕。乞行下沿海州縣嚴(yán)行禁止,以五家互相為保,不得停隱賊人及與賊船交易,一家有犯,五家均受其罪,所貴海道肅清,免官司追捕之勞。”
要切斷沿海村民與海盜之間的往來,必須借助保甲的連坐。因此,利用澳長(zhǎng)對(duì)沿海漁民的行為進(jìn)行監(jiān)督,成為地方官員的選擇。淳熙九年(1182),為有效處理廣州大奚山的私鹽走私問題,官員建議利用地方的澳長(zhǎng)參與剿捕,同時(shí)監(jiān)視地方民戶的行動(dòng)。十一月,“詔廣東經(jīng)略司曉諭:大奚山民戶,各依元降指揮,只許用八尺面船采捕為生,不得增置大船。仍遞相結(jié)甲,不得停著他處逃亡人。如有逃亡人,令澳長(zhǎng)民戶收捉,申解經(jīng)略司,重與支賞。”次年五月“大奚山私鹽大盛,令廣東帥臣遵依節(jié)次已降指揮,常切督責(zé)彈壓官并澳長(zhǎng)等嚴(yán)行禁約,毋得依前停著逃亡等人販賣私鹽。如有違犯,除犯人依條施行外,仰本司將彈壓官并澳長(zhǎng)、船主具申尚書省,取旨施行,仍出榜曉諭。”
福建大員真德秀、包恢亦相繼在閩粵沿海大力剿捕海盜,針對(duì)海盜問題提出的海防舉措,包括澳長(zhǎng)等在內(nèi)的民間武裝力量,成為官府剿捕海盜的重要力量。嘉定年間(1208~1224),真德秀在圍捕閩粵沿海南澳島海域的海盜行動(dòng)中,潮州“柘林部長(zhǎng)林四”參與了剿捕南澳島海盜的軍事行動(dòng),“據(jù)(潮州)水軍寨及小江巡檢司申,賊船復(fù)在大坭海劫掠漳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拋泊,出沒行劫。因依當(dāng)具申本路經(jīng)略安撫使司及移文漳州,乞發(fā)兵船前來,會(huì)合沿海駐扎官軍船只并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據(jù)小江巡檢狀繳到:東界新埭柘林部長(zhǎng)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早驀被賊船一十余只乘載五六百人,持槍仗上岸劫掠,復(fù)使船到柘林澳,擄去鹽綱船二只。目今見在深澳拋泊出沒行劫。”
文中的“深澳”指的是閩粵邊界的南澳島,深澳、柘林澳及上文所提到的沙尾,是這一海域海上貿(mào)易的必經(jīng)之處,也是海盜出沒的地方。柘林澳是潮州轄內(nèi)的瀕海小島,也是潮州的鹽產(chǎn)區(qū)之一,“柘林部長(zhǎng)林四”應(yīng)該就是柘林澳民間武裝領(lǐng)袖。在發(fā)生了劫掠事件后,林四第一時(shí)間將情況反映給了駐扎在該區(qū)域的小江巡檢司。在處理上述海盜問題時(shí),這些民間武裝力量的機(jī)動(dòng)性及適應(yīng)性,正是國(guó)家正規(guī)軍隊(duì)所不具備的。在潮州海域,類似于柘林的澳嶼不在少數(shù),見于文獻(xiàn)的如“深澳”、“南洋”、“沙尾”、“萊蕪”、“吳田”等等。
確切而言,南宋所推行的澳長(zhǎng)制,是官方進(jìn)行沿海海域治理的一種策略,是吸納民間武裝力量以構(gòu)筑其統(tǒng)治體系的策略,而不能簡(jiǎn)單歸諸為制度。正因如此,澳長(zhǎng)制的推行有其不確定性及不穩(wěn)定性,它的施行與官方的正規(guī)軍力量的布防情況、澳長(zhǎng)的生存策略、歷史局勢(shì)等等因素密切相關(guān),且因時(shí)因地而異。這當(dāng)中,既有國(guó)家宏觀政策的調(diào)控,也受地方社會(huì)傳統(tǒng)因素的制約。
(二)元明時(shí)期概貌
澳長(zhǎng)制在元代及明初的推行情況,管見所及,未見相關(guān)的資料,或斷裂,或延續(xù),不敢妄下結(jié)論。不過,類似“澳長(zhǎng)”的沿海島嶼、聚落首領(lǐng)的普遍存在,應(yīng)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官方在對(duì)待此類民間武裝力量的策略上將有助于我們對(duì)此問題的探索。
元初朝廷組建了一支強(qiáng)大的海上力量,與以陸戰(zhàn)見長(zhǎng)的蒙古軍隊(duì)互補(bǔ)。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支水軍以歸降的宋朝水軍及投誠(chéng)的沿海民間武裝力量為主,因此南方的海上武裝勢(shì)力事實(shí)上長(zhǎng)期處于羈縻統(tǒng)治之下,有著較為自由的活動(dòng)空間。如陳懿勢(shì)力盤踞潮州達(dá)數(shù)十年之久,蒲壽庚家族則長(zhǎng)期控制泉州海外貿(mào)易,海盜出身的朱清、張瑄等皆活躍于地方。元代水軍的組建模式,實(shí)際上承繼了宋代以來的“民兵”政策,在施行海域治理的策略上,與“澳長(zhǎng)制”并無太大區(qū)別,陳懿、蒲壽庚等其實(shí)就是“澳長(zhǎng)”的另外一種呈現(xiàn)。
明朝建立以后,在沿海地區(qū)相繼建立衛(wèi)所,構(gòu)筑了較完整的海防體系。與此同時(shí),施行“海禁”政策,嚴(yán)厲禁止海上貿(mào)易。原本掌控海上航運(yùn)力量的“澳長(zhǎng)”勢(shì)力受到鉗制,結(jié)果廣東、福建沿海相繼出現(xiàn)了吳平、林道乾等著名海盜。明代嘉靖年間,潮州最大的海盜勢(shì)力之一許朝光,占據(jù)潮州沿海島嶼,自立為“澳長(zhǎng)”,對(duì)過往商貿(mào)船只強(qiáng)制收費(fèi),乃至聚眾抗擊官軍。
明中后期,沿海的倭寇活動(dòng)愈演愈烈,各地在應(yīng)對(duì)倭寇的策略上不盡相同。嘉靖二十四年(1545)郭春震出任潮州知府,期間通過對(duì)閩粵沿海海盜的調(diào)查,他指出:
近年真倭少至,多閩粵人與浙省之溫、紹亡命,竄入海島。遂肆猖獗,致為濱海患。……其弊有三:一曰“窩藏”,沿海勢(shì)要之家,坐地分贓,為賊逋逃之藪,事發(fā)輒多方蔽護(hù),以計(jì)脫免;一曰“接濟(jì)”,黠民窺賊所向,載魚米貿(mào)易,以邀重利,贍彼日用,且作奸細(xì);一曰“通番”,閩粵之人,駕雙桅船、挾私貨,百十為群,往來東西洋,幸售諸番,獲奇貨,固得意而歸,不幸折本,遂肆為劫掠。此三弊者,閩粵大略相同。
正因?yàn)楹1I成分的復(fù)雜及其交際網(wǎng)絡(luò)的綿密,因應(yīng)的對(duì)策也不可過于單一。在提出問題之后,郭春震建議聯(lián)合閩粵兩省的軍事力量,試圖通過優(yōu)勢(shì)兵力殲滅海盜。這種主要仰賴于官方威懾力量的代表性舉措還包括在潮州增設(shè)沿海巡檢寨、增設(shè)沿海水寨、屯兵南澳島等等。
在福建,曾經(jīng)長(zhǎng)期施行于閩粵沿海的澳長(zhǎng)制重新得到地方官員的認(rèn)可。以民間力量的面貌出現(xiàn)的澳長(zhǎng)制,具備在基層監(jiān)控船戶行為及船只行動(dòng)方面的優(yōu)勢(shì),這無疑有助于解決郭春震所指出的“窩藏”、“接濟(jì)”的問題,因此成為地方官府在衛(wèi)所等正規(guī)軍以外的維持海道秩序的另外一種策略。
嘉靖十五年(1536),福建巡按御史白賁提請(qǐng)數(shù)條防備倭寇的建議,其中之一即對(duì)沿海及海島的漁民進(jìn)行姓名登記,并推選澳長(zhǎng)。“海澳舟居之民所有見丁皆令報(bào)官,折立澳長(zhǎng)一人,小甲二人,籍記澳民姓名。一船被劫,澳長(zhǎng)小甲即率眾追之。仍禁制澳民不得下海通番。”白賁建議賦予澳長(zhǎng)維持基層治安以及監(jiān)控漁民行為的職能。此建議后為都御史朱紈所采納,“以海滄、月港等澳耆民充捕盜補(bǔ)之備倭”。
萬歷四十年(1612),福建巡撫丁繼嗣亦指出:“欲絕勾引,必清海販,欲清海販,必先自勢(shì)豪之家,有犯必處之重典。”強(qiáng)調(diào)基層保甲制度的重要性,連坐之法必須堅(jiān)決執(zhí)行。“沿海縣分,挨次編為保甲,凡船埠船匠籍名在官,如有異船異貨拿獲,一家有罪,十家連坐。”這當(dāng)中,責(zé)任落于澳甲。
天啟年間(1621~1628),曹履泰任泉州同安知縣,為應(yīng)對(duì)鄭芝龍集團(tuán)來自海上的威脅,他大量招募沿海的漁民壯丁,進(jìn)行編甲,對(duì)各個(gè)聚落的澳甲、澳長(zhǎng),有詳細(xì)的要求:
一、糧餉。遇有警報(bào),本縣飛檄到澳。澳長(zhǎng)即時(shí)點(diǎn)集出水。以是日為始,每人日給銀三分。如五日以內(nèi)獲有賊船首級(jí)者,除功賞另行外,口糧每人日加二分,錢糧俱本鄉(xiāng)自處給發(fā)。
一、器械。有自備者,有官給者,及火藥等項(xiàng),澳長(zhǎng)各先料理。毋至臨時(shí)方請(qǐng),致誤事機(jī)。
一、功次。凡兇賊執(zhí)械拒敵者,俱聽澳民登時(shí)斬首,赴縣報(bào)功。寨游將領(lǐng)敢邀搶及買求者,稟明申究。如真正被擄,不持兵仗逃水自匿,或偃伏船艙者,不許妄殺。此又是各人自存心地,毋造冥業(yè),何俟余言。
一、鹵獲。凡牽獲賊船,惟神飛、百子諸大火器,報(bào)官存用。其余刀槍及一切所有之物,俱聽有功員役,自行分取,以為剿賊之資。
一、船只。凡以擊賊致有損壞者,即官為估計(jì)給價(jià)賠修;所獲賊船,各存該澳;一面整理給澳長(zhǎng)收管,以便急需。
一、應(yīng)援。凡澳口鄰近,倘有賊船分舟宗突入者,左右澳長(zhǎng),俱須督率澳兵,前后邀擊,毋得坐視。
由此可見,明嘉靖之后福建沿海推行的澳長(zhǎng)制,基本沿襲了宋代該區(qū)域的澳長(zhǎng)制,白賁及曹履泰等官員對(duì)瀕海地區(qū)及島嶼澳長(zhǎng)的倚重,反映了地方官員對(duì)于地方傳統(tǒng)的依循。
二、從澳長(zhǎng)制到澳甲制:清代前期的完善
清軍入關(guān)后,尤其康熙后期,海面局勢(shì)穩(wěn)定,航運(yùn)業(yè)隨之興起。清代所施行的澳甲制功能亦有新變化:一方面借鑒了澳長(zhǎng)在基層的船只編甲及登記管理方面的經(jīng)驗(yàn),進(jìn)一步將其規(guī)范化、職能化;另一方面消除了宋元明時(shí)期澳長(zhǎng)作為軍事武裝力量的威脅。具體而言,清代對(duì)船只、船戶管理的條例較之宋元明時(shí)期更為完備,依托于地方保甲制度所產(chǎn)生的澳甲,為新時(shí)期船政管理的重要輔助。“澳甲”一名的由來,更為突出的正是基層的保甲制度。
康熙四十六年(1707),福建沿海地區(qū)的出洋船只進(jìn)行編甲,所有出洋船只,包括商船及漁船,十船編為一甲,同時(shí)施行甲內(nèi)連坐:
四十六年,議準(zhǔn)福建漁船桅聽其用雙用單,各省漁船止許單桅。欲出洋者將十船編為一甲,取具一船為匪余船并坐,連環(huán)保結(jié),若船主在籍而船出洋生事者,罪坐船主。……。又議準(zhǔn)福建商船值漁期欲出海取魚者,赴地方官呈明換領(lǐng)漁照,取具澳甲、里族各長(zhǎng)并鄰右保結(jié),同船連環(huán)互結(jié),準(zhǔn)其入海取魚。俟魚期過后將漁照繳銷仍換給商照,該地方官將換給船照緣由匯報(bào)上司存案,如過期不歸,即行察究,永不許出海取魚。
乾隆初期,廣東“凡大、中、小三項(xiàng)出海商、漁船只,各州縣必須照陸上保甲制度編排,十船為一甲,互相保結(jié)。一船犯案,它船必須舉報(bào)。若一甲中無人舉首,即予連坐。十甲為一澳,設(shè)澳長(zhǎng)一名,如船在一百五十分號(hào)上,則設(shè)澳長(zhǎng)兩名分管。其商船按雙桅、單桅分甲合對(duì)。澳長(zhǎng)由各州縣選殷實(shí)并無過犯重役之人取結(jié)承充。五年一換。如在任內(nèi)怠玩滋事,隨時(shí)裁革,另舉他人。澳甲設(shè)立后,其它水練埠保名色,一律革除。各州縣每年將澳長(zhǎng)姓名、年籍、所管船只、甲數(shù)、號(hào)數(shù)造冊(cè)繳查。”
通過這種以船只為單位進(jìn)行編甲的方式,實(shí)際上將澳甲(長(zhǎng))與船只緊密的聯(lián)系在一起。而清代以前的編甲,則通常是以地域聚落為單位進(jìn)行的,選取的澳長(zhǎng)更多的是帶有地方強(qiáng)人角色的私人武裝力量首領(lǐng)。事實(shí)上,編甲以及連坐,正是地方保甲制度的要義,這兩個(gè)內(nèi)容推行于沿海地區(qū)的澳長(zhǎng)制施行范圍,用于對(duì)船只、船戶的管理,標(biāo)志著清代澳甲制的形成,也反映了清代船只管理制度的完善。
清代的船只管理,實(shí)際上是采用船只及船戶的交叉管理方式,通過海關(guān)、州縣衙門等水運(yùn)管理機(jī)構(gòu)的協(xié)作,從而實(shí)現(xiàn)對(duì)船只的形制、航程等信息的登記,以及航道秩序的維持。依照規(guī)定,所有船只均須在官府處登記,同時(shí)獲取“牌票”,有了“牌票”便具備官府承認(rèn)的營(yíng)運(yùn)資格。牌票事實(shí)上可以理解為州縣給予船戶及其船只的備案憑證,船戶在申請(qǐng)牌票的這一過程中,同時(shí)也被納入到官府的監(jiān)管之下,船戶必須履行相應(yīng)的職責(zé)。依照條文,渡口船只大小、航程、載人額數(shù),渡夫的姓名、往來的渡口等等信息必須登記在案。“每船置大白粉牌一面,將渡夫姓名、往來埠埗、船身梁頭丈尺、水程里數(shù)、載人、收錢各數(shù)目,及歸何處捕巡、河泊所等官管理,逐一開載”。
另外,船戶還必須由“身家殷實(shí)”之人承充,或由地方紳士對(duì)其進(jìn)行擔(dān)保,其鄰接戶族亦互為擔(dān)保。政府透過一系列的舉措,以達(dá)到對(duì)境內(nèi)河道及出海船只的監(jiān)管,這其中,基層的澳甲無疑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施行出海船只的管理制度當(dāng)中,澳甲制事實(shí)上是基層保甲制向近海海域的延伸,推選出來的澳甲,成為基層管理的施行點(diǎn)。澳甲(長(zhǎng))由州縣遴選可靠之人充任,履行官府的使命,對(duì)甲內(nèi)船只、船戶的行為納入官府的規(guī)定之內(nèi)。此外,澳甲(長(zhǎng))必須為甲內(nèi)的商船、漁船進(jìn)行擔(dān)保,包括漁戶制造出洋的捕魚船只之前的責(zé)任擔(dān)保及畫押。澳甲(長(zhǎng))對(duì)出海船只管理方面的職能,主要以下幾個(gè)方面:
1、對(duì)出洋漁船的擔(dān)保
(康熙)四十二年覆準(zhǔn)出洋漁船止許用單桅,梁頭不得過一丈,舵水人等不得過二十名,取魚不得越出本省境界。未造船時(shí),先行具呈州縣,該州縣詢供確實(shí),取具澳甲、戶族、里長(zhǎng)、鄰右當(dāng)堂畫押保結(jié),方許成造。造完報(bào)縣驗(yàn)明印烙字號(hào)、姓名,然后給照。其照內(nèi)仍將船戶舵水年貌、籍貫開列以便汛口地方官弁察驗(yàn)。
2、對(duì)出洋商船的擔(dān)保
覆準(zhǔn)商賈船許用雙桅,其梁頭不得過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過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頭者不得過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梁頭者不得過十六名,一丈二三尺梁頭者不得過十四名。于未造船時(shí)亦具呈該州縣取供嚴(yán)察,確系殷實(shí)良民親身出洋船戶取具澳甲、里族各長(zhǎng)并鄰右當(dāng)堂畫押保結(jié),然后準(zhǔn)其成造,造完該州縣親驗(yàn)烙號(hào)刊名,然后給照。
3、對(duì)船戶行為的擔(dān)保
沿海等省商、漁船只取具澳甲族鄰保結(jié),報(bào)官準(zhǔn)造,完日由官驗(yàn)明給照。商船將船主、舵工、水手年貌、籍貫并填照內(nèi),出洋時(shí)取具,各船互結(jié)至汛口照驗(yàn)放行。漁船止填船主年貌、籍貫,至泛口查明舵工、水手名數(shù),官為填注。倘有租船出洋為匪,將船主、澳甲分別治罪。
閩省不法棍徒,如有充作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偷渡之人,包攬過臺(tái),索取銀兩,用小船載出澳口復(fù)上大船者,為首發(fā)近邊充軍,為從及澳甲、地保、船戶、舵工人等知而不舉者,俱杖一百徒三年,均不準(zhǔn)折贖。
4、對(duì)近海地區(qū)船只的稽查
內(nèi)洋采捕小艇責(zé)令澳甲稽查,至內(nèi)河一切船只于船尾設(shè)立粉牌,責(zé)令埠頭查察。其漁船網(wǎng)戶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歸就近保甲管束。
三、清代中后期內(nèi)河澳甲的出現(xiàn)及其演變
清代澳甲的職能并非僅僅體現(xiàn)在沿海海域的管理方面。隨著18世紀(jì)航運(yùn)業(yè)的興起,航行于內(nèi)河航道的船只數(shù)量更為龐大。為此,內(nèi)河澳甲的出現(xiàn),有助于內(nèi)河航運(yùn)管理。
乾隆三十一年(1766),廣東率先將船只編甲推行至境內(nèi)的內(nèi)河航道區(qū)域:“粵東商漁大小船只,每州縣不下一二千,易致匪徒竄跡,竊劫為害。現(xiàn)通飭各府州縣,將境內(nèi)所有商船漁艇按數(shù)編排。十船設(shè)一甲長(zhǎng),十甲設(shè)一澳長(zhǎng)。無論船身大小,令于篷桅頭艕書刊某州縣某號(hào)某甲某人某船字樣。除商船載明船主、柁水、貿(mào)易何地、往返何時(shí)。凡屬漁船,必使出捕定有方向,收港定有限期。配鹽食米,定有章程。俾內(nèi)河外海,無不明書標(biāo)識(shí)之船;漁戶水手,無不按籍可稽之人。倘有歹船混入,一目了然,哨巡不難即捕。”
依照規(guī)定,內(nèi)河的澳甲負(fù)責(zé)船只的登記造冊(cè)等具體事項(xiàng),這樣做自然有助于官府維持河道的秩序,客觀上也促進(jìn)了內(nèi)河船只管理的完善。
河道澳甲另外一個(gè)職能,是替地方官府?dāng)埣{、承充各種使用船只的差使,如大小官員迎來送往等。雇傭船只的價(jià)碼,有明確的規(guī)定。粵東韓江沿岸出土的航運(yùn)碑刻,記載了有關(guān)于內(nèi)河澳甲的相關(guān)內(nèi)容:“為此示諭各州縣船戶及船頭、澳甲、差役人等知悉,嗣后凡遇文武衙門過往官員,出有印封雇用船只,務(wù)照現(xiàn)在加給船價(jià)章程。按照水手多寡:凡逆水,如用水手四名,每站給錢六百七十五文;水手三名,每站給錢五百零六文;水手二名者,每站給錢三百三十七文。下水概行八折算給。”
在廣東內(nèi)河航運(yùn)較為發(fā)達(dá)的廣州及佛山,有類似澳甲的船行組織,其規(guī)章可供參考。據(jù)載,廣東地區(qū)于乾隆十五年(1750)頒行了“船行規(guī)條”:“詳各屬境內(nèi),照省城、佛山之例,查召身家殷實(shí)、堪充船行三人,并取鄰戶族甘結(jié),如行聯(lián)名保結(jié)。詳報(bào)批示,給與示簿,準(zhǔn)其承充。毋庸輸課,給發(fā)牙帖。凡船只到埠,攬載行戶,詢明該戶及所雇水手姓名住址,并取同幫船戶與在船水手連環(huán)保結(jié)存行,分晰登簿。其無保結(jié)之船,概不許其攬載。客商雇舡開行月日、姓名、籍貫、貨物行囊、船價(jià)、填給舡票。登注循環(huán)簿內(nèi),按月呈繳該州縣査核。”
船行的設(shè)立雖基于商業(yè)貨運(yùn)需求,不過船行負(fù)責(zé)人的遴選,與澳甲(長(zhǎng))一樣,都必須是地方州縣所認(rèn)可的“可靠”之人,并通過這些人實(shí)現(xiàn)對(duì)航運(yùn)船只的具體監(jiān)管,二者實(shí)有異曲同工之處,亦即是規(guī)范船只的管理,這是18世紀(jì)以來航運(yùn)業(yè)發(fā)展的必然趨勢(shì)。另一方面,雖然內(nèi)河澳甲與沿海澳甲在維持航運(yùn)秩序以及協(xié)助船只登記管理方面發(fā)揮作用,但二者之間仍有一定的差別,內(nèi)河澳甲承擔(dān)了地方官府的船只使用的差使。
清代內(nèi)河澳甲的具體施行及發(fā)展,各個(gè)地區(qū)情況并非一致。下文以近年出土的粵東韓江碑刻文獻(xiàn)為主要材料,考察晚清韓江內(nèi)河澳甲的發(fā)展演變。
雖然內(nèi)河澳甲設(shè)立的初衷是為了改善內(nèi)河船政,維持航運(yùn)秩序。不過,澳甲通常由地方州縣選定,與兵役、衙役同為州縣差役,而非船戶自行推選。內(nèi)河澳甲的這一身份導(dǎo)致在實(shí)際的管理過程中,常常會(huì)借機(jī)向船戶勒索。事實(shí)上,地方差役通常在與百姓打交道的過程當(dāng)中以非法的手段收取“例費(fèi)”。雖然針對(duì)衙役、吏員們貪贓懲戒的法律條規(guī)非常完備,但是難以監(jiān)督控制。個(gè)中原因,與清代地方財(cái)政高度集權(quán)有關(guān)。地方政府完全得不到滿足地方行政開銷的費(fèi)用,甚至包括為中央政府征稅和運(yùn)送稅金的費(fèi)用。這迫使各級(jí)地方政府從各種“陋規(guī)”當(dāng)中獲取經(jīng)費(fèi)。以非法的手段謀求酬償。
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如“澳長(zhǎng)籍端勒索,最為船只往來之害,情殊可惡”,“潮郡澳甲舞弊營(yíng)私,久為船戶之害”。據(jù)韓江船戶控訴,澳甲通常借著官府差船的機(jī)會(huì),向雇傭的船只索要額外的錢財(cái),這種情況由來已久。乾隆五十九年(1794),嘉應(yīng)州船戶羅恩發(fā)、大埔縣船戶吳凌云等常年往返于韓江河段的船戶,由于不堪澳甲的侵?jǐn)_,聯(lián)名請(qǐng)求潮州知府裁奪:
緣發(fā)等潮嘉子民,地居僻壤,山多田少,惟賴操舟度活,撐駕各船,希圖賃載貨物。每到埠頭市鎮(zhèn),空船灣泊,多被兵役假名差使勒索大小花紅。□有嘉屬之興、長(zhǎng),潮屬之大埔、豐順、留隍,適遇空船揚(yáng)帆回棹,差使乘風(fēng)坐艇,攔河濫封,許者放,忤者兜,甚至不遂,釀成禍端。即岐嶺之三篷、六篷到彼停泊,該處澳長(zhǎng)勒索免差安班禮錢,自三四百至五六百不等。即大埔之三河名設(shè)對(duì)差,所有船只到彼處,每船勒索規(guī)禮錢二三百文。以至潮城北門、上水、下水各門外,多設(shè)澳長(zhǎng)。每坐無篷小艇,三五成群,或遇高頭、梢馬、湖寮等船,空船灣泊,勒索規(guī)禮錢二百文,稱為“掛號(hào)”、“大揮”名色。稍不遂,即將篙槳抽擱,船行不得。若逢長(zhǎng)差短遣,□百般刁難。更有□害之六篷、三篷,無論空船灣泊,即勒索免差禮銀,重輕不等,許者放,忤者□,尋釁差務(wù),逗留日久,或克扣貼站船價(jià),以至水手乏人,中途趕不及站,害累匪輕,不勝枚舉。
同治五年(1865),大埔縣船戶張格、何忠順等亦不堪澳甲的勒索行徑,“民等撐船營(yíng)生,屢被澳甲勒索,不堪其擾”。“緣順等船只終年在郡城往來,遇有差務(wù),而船差、館甲長(zhǎng)每借海主封條,多方舞弊,用一捉十,有錢則將船釋放,無錢則將船留難。明明當(dāng)差之船,已經(jīng)封足,猶恣意勒索,不飽不休。船戶之受害,實(shí)難言罄。”
雖有嘉慶二年(1797)的禁令在前,但似乎效用有限。同治六年(1866),船戶進(jìn)一步要求永遠(yuǎn)裁革澳甲,設(shè)立船行以取代之。“民等撐船營(yíng)生,屢被澳甲勒索,不堪其擾。迫叩崇階,蒙憲天俯察民困,破除數(shù)十年錮弊,救民水火,垂示□□,心鏡懸河,口碑載道,就示郡城,遵示設(shè)立上河公所,民等愚蠢無知,不堪裁用。議舉大埔縣廩生童纘勛、長(zhǎng)樂縣候補(bǔ)把總?cè)~祿、大埔縣增生邱德光,職員連宣德等為董事。又設(shè)立下河公所,商請(qǐng)海陽縣生員梁鴻運(yùn)、功職趙秀美、許連和等均皆諳練公務(wù),公正勤慎,民等素所深信,堪為局董,所有一切公事,自當(dāng)稟商委員大爺指示遵行。凡有存積公項(xiàng)津貼差使規(guī)條,另單由委員呈電外,伏乞賜準(zhǔn),給發(fā)示諭,俾得開辦。”
潮州府航運(yùn)船只的供應(yīng)差委等由原來的澳甲更換為由船戶自發(fā)組織的“公所”。依照要求,設(shè)立的公所有兩處,以廣濟(jì)橋?yàn)榉纸缇€,分上河公所及下河公所,上河為廣濟(jì)橋往韓江上游方向的大埔、興寧等處,下河為韓江下游等縣船只。各船戶聘請(qǐng)喑練地方事務(wù)的地方士紳(生員、貢生、廩生等)充任局董,處理官府對(duì)于船只的日常差使。“凡遇往來一應(yīng)大小差使,需用船只,統(tǒng)由船局雇備,不準(zhǔn)澳甲干預(yù),所有船局應(yīng)辦事宜,均著遵照新定規(guī)條,妥為辦理。嗣后各船戶等務(wù)宜安分營(yíng)生,奉公守法,遇有應(yīng)當(dāng)差使,不得推諉延誤。”
至此,韓江的內(nèi)河澳甲為公所取代,由公所接替澳甲為官府提供運(yùn)輸服務(wù)。公所的成立與晚清時(shí)期全國(guó)各地普遍設(shè)立行業(yè)公所的趨勢(shì)所暗合。事實(shí)上,內(nèi)河澳甲的裁革,除了與官府之間的差使職能轉(zhuǎn)移外,其原本的監(jiān)管船只及船戶的職能,也隨之被相應(yīng)的政府職能部門所取代,這實(shí)際上反映了晚清時(shí)期航運(yùn)管理的現(xiàn)代化。內(nèi)河澳甲與沿海澳甲,在晚清社會(huì)變遷的時(shí)勢(shì)下,逐漸為形式各樣的航運(yùn)業(yè)公會(huì)所取代,乃至消亡。
四、結(jié)語
澳長(zhǎng)制始于南宋中國(guó)南部沿海地區(qū)抗擊海盜的過程,廣泛施行于廣州與泉州之間的沿海貿(mào)易區(qū),其目的是利用澳長(zhǎng)在地方上的強(qiáng)人角色,切斷船戶、船只與海盜之間的聯(lián)系,同時(shí),也借助于澳長(zhǎng)的軍事武裝力量抗擊海盜。此一融入保甲與民兵政策理念的制度在歷史時(shí)期應(yīng)對(duì)海盜及倭寇的過程當(dāng)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宋代澳長(zhǎng)制的推行范圍主要在福建泉州及廣東廣州之間的海域,其實(shí)質(zhì)為民兵政策,帶有基層防衛(wèi)的性質(zhì),嚴(yán)格說來應(yīng)當(dāng)屬于應(yīng)對(duì)海盜的策略,不能稱之為制度,這種策略是廣東、福建兩地在應(yīng)對(duì)盜賊侵?jǐn)_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澳長(zhǎng)有保衛(wèi)鄉(xiāng)土、抗擊海盜的職責(zé),同時(shí)澳長(zhǎng)也必須擔(dān)負(fù)起對(duì)船戶及船只的監(jiān)管職責(zé),以配合官府的軍事行動(dòng)。明代中后期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倭寇問題,使澳長(zhǎng)制推廣。清時(shí)期澳長(zhǎng)制與基層里甲制度進(jìn)一步結(jié)合,隨著海盜活動(dòng)的式微,澳甲制度的作用主要體現(xiàn)于沿海及內(nèi)河地區(qū)的船只管理上,軍事功能淡化。清代的澳甲制也逐步的職能化。在晚清社會(huì)變遷的時(shí)勢(shì)下,逐漸為形式各樣的航運(yùn)業(yè)公會(huì)所取代,乃至消亡。
注釋:
[1]重要者如楊培娜:《瀕海生計(jì)與王朝秩序——明清閩粵沿海地方社會(huì)變遷研究》(中山大學(xué)2009博士學(xué)位論文,第186~191頁),李堅(jiān):《宋代中國(guó)南部邊疆的海防建置——以潮州為視角》(《宋史研究論叢》2013年),分別就清代澳甲制,宋代澳長(zhǎng)制進(jìn)行討論,不足之處是對(duì)于澳長(zhǎng)制的源流及發(fā)展演變,缺乏一個(gè)完整的考述。
[2][3](宋)鄭興裔:《鄭忠肅奏議遺集》卷上《請(qǐng)置澳長(zhǎng)御海寇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詳見《宋史》卷465《鄭興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593~13595頁。
[4][6](元)脫脫:《宋史》卷191《兵5·鄉(xiāng)兵2》,第4763頁,第4746~4747頁。
[5](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8《福建保伍》,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19頁。
[7]李堅(jiān):《土豪、動(dòng)亂與王朝變遷——宋代閩粵贛邊區(qū)基層社會(huì)的演變》,《韓山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年第4期,第23~29頁。
[8]據(jù)南宋乾道元年(1165)德慶府知州莫廷秀所指:“二廣諸州多與江西按境,江西之民以興販私茶、鹽為業(yè),劫殺平民,而二廣諸州軍兵孱弱,惟賴土豪,號(hào)曰‘統(tǒng)率’者,聚兵保伍以遏絕之”(《宋會(huì)要輯稿》兵1之22);紹熙元年(1190),又有臣僚指出:“嶺南地廣人稀,每歲冬月盜賊尤劇,商旅不敢行于道。臣嘗熟詢其故,蓋由江西、湖南之游手,每至冬間相率入嶺,名曰‘經(jīng)紀(jì)’,皆設(shè)為旅裝,出沒村落,嘯聚險(xiǎn)隘,伺便剽掠。……廣南兵卒寡弱,所恃以御盜者,常藉首領(lǐng),蓋廣南之俗隨方隅為團(tuán),團(tuán)有首領(lǐng),凡遇警則合諸團(tuán)以把截界分。所謂首領(lǐng)者,能因其俗而激用之,誠(chéng)除盜之一助也。”(《宋會(huì)要輯稿》兵13之37)
[9](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8“紹興五年四月戊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471頁。
[10][11][12](清)徐松:《宋會(huì)要輯稿》兵13之2、刑法2之121、食貨28之19。
[13](宋)包恢:《敝帚稿略》卷1《防海寇申省狀(福建提刑)》,《宋集珍本叢刊》第78冊(cè),線裝書局,2004年,第490~494頁;(宋)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7年,第252~253頁。
[14](宋)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7年,第252~253頁。
[15]筆者曾以潮州海防的建置情況進(jìn)行剖析,指出宋代的海防政策實(shí)際上是國(guó)家與地方社會(huì)之間動(dòng)態(tài)的整合。(《宋代中國(guó)南部邊疆的海防建置——以潮州為視角》,《宋史研究論叢》第14輯,保定: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第134~156頁)
[16]具體可參見馬明達(dá):《元朝初期的潮州路》,《潮學(xué)研究》第1輯,汕頭:汕頭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第35~52頁;(日)桑原騭藏著,陳裕菁譯訂:《蒲壽庚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17](明)郭子章:《潮中雜紀(jì)》卷10《國(guó)朝平寇考(上)》,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影印,2003年,第71~72頁。
[18](明)陳天資:《東里志》卷4《公移文》,饒平:饒平縣地方志辦公室編纂委員會(huì)鉛印本,2001年,第163頁。
[19](清)劉抃:《饒平縣志》卷18《藝文》,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影印本,2002年,第195頁。
[20]具體可參考(明)郭子章《潮中雜記》卷五《請(qǐng)社海防參將疏》、《請(qǐng)?jiān)O(shè)沿海水寨疏》、《條陳海禁事宜疏》、《請(qǐng)?jiān)O(shè)南澳副總兵疏》,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影印,2003年,第27~34頁;《東里志》卷4《公移文》相關(guān)篇目,第161~166頁。
[21]《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百八十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條。
[22](明)胡宗憲:《籌海圖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23](明)王在晉:《海防纂要》卷九,明萬歷刻本。
[24](明)曹履泰:《靖海紀(jì)略》卷之四《編造漁舟壯丁示》,臺(tái)北:臺(tái)灣銀行經(jīng)濟(jì)研究室輯:《臺(tái)灣文獻(xiàn)叢刊》第33種。
[25][30][31](清)允祹纂修:《欽定大清會(huì)典則例》卷一百十四《海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6][28](清)黃恩彤:《粵東省例新纂》卷3,轉(zhuǎn)引自《廣東航運(yùn)史》第198頁。
[27](清)金廷烈:《澄海縣志》卷之七《津梁》。
[29]葉顯恩、譚棣華、羅一星:《廣東航運(yùn)史(古代部分)》,第199頁。
[32][34](清)張廷玉:《皇朝文獻(xiàn)通考》卷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3]馬建石、楊育棠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二十《兵津關(guān)津》,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第622頁。
[35]《清高宗實(shí)錄》卷七百七十二,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
[36][39][41]周成紹:《道府憲縣主嚴(yán)禁碑》(嘉慶二年,1798),碑存潮州市博物館。本文所引用碑文均依據(jù)韓山師范學(xué)院潮學(xué)研究院藏碑刻拓片釋讀。
[37]見《粵東案例》手抄本,轉(zhuǎn)引自《廣東航運(yùn)史》第199頁。
[38]見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78~123頁、第333頁。
[40][43][45](清)張銑:《奉道憲碑記》(同治五年,1865),碑存潮州市博物館。
[42][44](清)佚名:《奉府憲華永遠(yuǎn)示禁》(同治五年,1865),碑存潮州市博物館。
[46]馬敏:《官商之間——社會(huì)劇變中的近代紳商》,上海: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251~254頁。
〔責(zé)任編輯 蔡惠茹〕
The Origin and Evolu tion of the“Aojia”
Li Jian
The“Aojia”was an importantmeasure in governing southern China waters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The“Aojia”further combined with the“Lijia”system in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in Qing Dynasty,the boatman and ships compiled closely,and gradually formed a further function;At the same time,the implementation of range from coastalwaters extended to the inland waterway,establishing the inland waterway of the“Aojia”to assist the management of inland river ships.
Aojia,Aozhang,shipmanagement
李堅(jiān)(1981~),男,廣東潮安人,韓山師范學(xué)院潮學(xu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潮州市2013年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規(guī)劃項(xiàng)目《清代韓江渡口研究》階段性成果,項(xiàng)目編號(hào)2013-A-14;韓山師范學(xué)院2012年潮學(xué)研究專項(xiàng)課題《清代韓江的渡口及船政管理》階段性成果之一,項(xiàng)目編號(hào)CS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