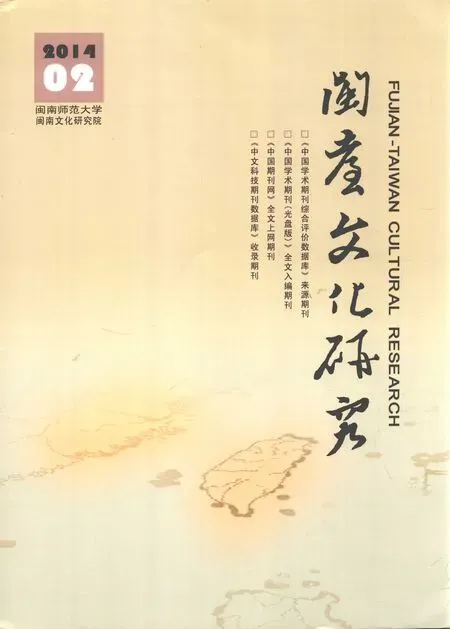陳淳的經(jīng)權(quán)觀發(fā)微
盧有才
(河南工程學(xué)院圖書館,河南鄭州451191)
陳淳的經(jīng)權(quán)觀發(fā)微
盧有才
(河南工程學(xué)院圖書館,河南鄭州451191)
陳淳認為,經(jīng)與權(quán)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聯(lián)系。經(jīng)是日用常行的道理;權(quán)也是正當(dāng)?shù)牡览恚遣怀P械模恰皾?jīng)之所不及者”。用權(quán)的目的是為了讓經(jīng)獲得貫通、融通,權(quán)與經(jīng)實不相悖。用經(jīng)用權(quán)都離不開“義”,義是用經(jīng)用權(quán)的根本準(zhǔn)則。通過用經(jīng)用權(quán)最終達到“中”的目的,實現(xiàn)社會和諧。
陳淳;經(jīng);權(quán);中;義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今福建省漳州市龍文區(qū))北溪人,學(xué)者稱北溪先生。生于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1159),卒于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享年65歲。陳淳是朱熹晚年的高弟,其理學(xué)思想直接繼承朱熹。朱熹多次對人夸贊說:“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陳淳的經(jīng)權(quán)思想頗具特色,在《北溪字義》二十六門中,專辟“經(jīng)權(quán)”一門,對經(jīng)權(quán)關(guān)系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一、經(jīng)、權(quán)內(nèi)涵:“經(jīng)是日用常行道理,權(quán)也是正當(dāng)?shù)览怼?/h2>
何謂“經(jīng)”?《說文解字》:“經(jīng),織,從絲也。”段玉裁注曰:“織之縱絲謂之經(jīng)。必先有經(jīng)而后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jīng)。”“經(jīng)”的原意是指絲織品的縱絲、縱線,引申為根本原則。后來,人們把三綱、五常、六藝這些儒家的道德原則和禮儀規(guī)范稱之為天地之常經(jīng)。因其體現(xiàn)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lǐng)域,具有常住性、常規(guī)性,故而構(gòu)成了人們社會生活中必須遵守的道德原則和行為規(guī)范。
何謂“權(quán)”?《說文解字》:“權(quán),黃華木。從木雚聲。一曰反常。”段玉裁注曰:“《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quán)’。孟子曰:‘執(zhí)中無權(quán),猶執(zhí)一也’。《公羊傳》曰:‘權(quán)者何?權(quán)者反于經(jīng)然后有善者也’。”“權(quán)”的一個重要意思是“反常”,即違反常規(guī),隨機應(yīng)變。《公羊傳》把“權(quán)”理解為“反于經(jīng)然后有善者也”。對此,田豐先生作了如下解釋:“反字有違背翻轉(zhuǎn)之義,如‘小人反是’;又有類推之義,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還有往返回歸之義,如‘自衛(wèi)反魯’,此三義并行不悖,于此處當(dāng)互相發(fā)明。而不可執(zhí)守一‘違背’之義也。”“宋儒其實錯會‘反’字”,僅在“違背”的意義上理解“反”字,這樣,“權(quán)”就成為對經(jīng)的反叛。或者說,權(quán)就是通過違背經(jīng)、打破經(jīng)的常規(guī)性,取得“善”的結(jié)果。朱熹在注《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quán)”時說:“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權(quán),秤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quán),謂能權(quán)輕重,使合義也。’”在程朱看來,“權(quán)”的原意是秤錘,是用來稱量物體而了解它的輕重的,“可與權(quán)”就是能夠衡量輕重、權(quán)衡利弊,使之符合“義”的原則。可見,“權(quán)”的本意是權(quán)衡,引申為權(quán)變,具有靈活性、變動性,是對經(jīng)之常規(guī)性的打破。
陳淳把經(jīng)、權(quán)作為一對哲學(xué)范疇進行研究。他說:“經(jīng)與權(quán)相對,經(jīng)是日用常行道理,權(quán)也是正當(dāng)?shù)览恚强梢猿P校c日用常行底異。”這句話的關(guān)鍵在于“道理”二字。什么是“道理”?首先,陳淳對“道”作了解釋:“道,猶路也。……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dāng)行之理。眾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道”就像路,一個人獨行的不能稱之為路,眾人所共行的才能稱之為路。“道”的根本綱領(lǐng)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處理自然和社會問題所應(yīng)當(dāng)共同遵照執(zhí)行的“理”,也就是眾人共行之路。他強調(diào)說:“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dāng)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道之為道,必須從人們所通行的意義上來理解:它是人們?nèi)粘I钪刑幚碜匀缓蜕鐣栴}所必須共同遵守的當(dāng)然之理,古今人們所共由之路。其次,陳淳對“理”作了解釋:“道與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為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個當(dāng)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zhǔn)則、法則,有個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dāng)合做處便是‘當(dāng)然’,即這恰好,無過些,亦無不及些,便是‘則’。”“道”是從人們所共行之路的意義上理解的,較為寬泛,所以萬古通行之路稱為道;理與道的意思差不多,但區(qū)別還是有的,相對于“道”而言,“理”較為實在,有確定不易的意思,所以萬古不易的法則、準(zhǔn)則稱為“理”。“理”這個萬古不易之則沒有形狀,怎么去認識它呢?陳淳作了說明:“則”是準(zhǔn)則、法則、當(dāng)然;處理問題正確恰當(dāng)、合乎情理,“合做處”便是“當(dāng)然”;做到“恰好處”,無過無不及,就是“則”。簡言之,理就是事物中所包含的當(dāng)然之則,具有確定不易的性質(zhì);據(jù)“當(dāng)然之則”作出剖判、權(quán)衡,做到無過不及,就是“中”。弄清了道、理的涵義,經(jīng)、權(quán)內(nèi)涵就一目了然:“經(jīng)是日用常行道理”顯然是說,“經(jīng)”是人們?nèi)粘I钪泄餐裱漠?dāng)然之則、共行之路;它是萬古通行之道、萬古不易之理。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必須把“經(jīng)”作為當(dāng)然之則,恒常推行,一以貫之;把“經(jīng)”作為共行之路,眾人由之,萬古通行。
“權(quán)也是正當(dāng)?shù)览怼保牵c“經(jīng)”不同,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經(jīng)常推行。為什么呢?陳淳對“權(quán)”作了進一步解釋:“權(quán)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為物,能權(quán)輕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權(quán)。權(quán)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quán)便移來移去,隨物取平。亦猶人之用權(quán)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權(quán)”字的涵義來源于秤錘,秤錘作為一種東西、一種事物,能夠權(quán)衡輕重以取得平衡,故曰“權(quán)”。所謂“權(quán)”,就是變化、變動。秤衡上有衡星、斤兩等不同的標(biāo)志,秤錘隨著物體的輕重在秤衡上移來移去,最終取得平衡,從而知曉物體的輕重。這也就像人們用秤錘和尺度來衡量、測度、揆度事物一樣,通過權(quán)衡取得“中”的效果。可見,陳淳沿襲程朱的說法,以秤錘取義,把“權(quán)”理解為權(quán)衡、權(quán)變,具有靈活變通的性質(zhì),其目的是為了通過權(quán)變達到平衡,取得“中”的效果。“中”是權(quán)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權(quán)”的基本要求是做事合宜。陳淳說:“權(quán),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quán)。天地之常經(jīng)是經(jīng),古今之通義是權(quán)。”簡單地說,權(quán)就是時間、措施的適宜性、恰當(dāng)性,即“時措之宜”。它有兩層涵義:一是“時中便是權(quán)”。“時”是條件,“權(quán)”是方法,“中”是目的。權(quán)就是根據(jù)具體的時間,采取靈活變通的方法,做事合宜、恰當(dāng),達到“中”的目的。二是“古今之通義是權(quán)”。義者宜也,“自文義而言,義者,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即是當(dāng)然而然,無所為而然也。”既然義是根據(jù)天理的要求應(yīng)當(dāng)這樣,當(dāng)然而然,無所為而然,那么,權(quán)就是根據(jù)古今通行的當(dāng)然之則,采取恰當(dāng)措施,做事適宜、合宜。權(quán)與經(jīng)的不同在于:經(jīng)是“天地之常經(jīng)”,亙古不變之則,是常;權(quán)是“古今之通義”,通權(quán)達變之道,是變。
基于上述認識,陳淳對《公羊傳》的“反經(jīng)合道”說提出了質(zhì)疑:“《公羊》謂‘反經(jīng)而合道’,說誤了。既是反經(jīng),焉能合道?”既然《公羊傳》把權(quán)理解為“反經(jīng)”,與經(jīng)相反、相對,違反了經(jīng)的根本原則,或者說違背了“日用常行道理”,怎么能說是合乎道的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反經(jīng)合道”顯然是說錯了!
總之,陳淳認為,經(jīng)是日用常行的道理,權(quán)是“非常行”的正當(dāng)?shù)览恚唤?jīng)是天地之常則,權(quán)是古今之通義;經(jīng)是基本原則,權(quán)是時措之宜;經(jīng)是原則的常住性、常規(guī)性,權(quán)是方法的靈活性、變通性;經(jīng)是常,權(quán)是變。權(quán)變的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平衡,達到“中”的目的。
二、經(jīng)、權(quán)統(tǒng)一:“經(jīng)窮則須用權(quán)以通之”
朱熹嘗以辯證的方法闡發(fā)了經(jīng)權(quán)關(guān)系。首先,經(jīng)、權(quán)相互區(qū)別:“經(jīng)是萬世常行之道,權(quán)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時多。”“經(jīng)”是萬古永存的不變之道,是常行的不易之則;“權(quán)”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而采取的變通方法,是不常用的,“蓋權(quán)是不常用底物事”。其次,經(jīng)、權(quán)相互聯(lián)系:“經(jīng)者,道之常也;權(quán)者,道之變也。道是個統(tǒng)體,貫乎經(jīng)與權(quán)。”“經(jīng)”是道的常住性,“權(quán)”是道的變動性,經(jīng)、權(quán)共處在“道”這個統(tǒng)一體之中。具體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經(jīng)權(quán)相互依存:“只是雖是權(quán),依舊不離那經(jīng),權(quán)只是經(jīng)之變。”權(quán)離不開經(jīng),“權(quán)只是經(jīng)之變”。二是經(jīng)權(quán)相互貫通:“合于權(quán),便是經(jīng)在其中。”只要合乎權(quán),其中就蘊涵著經(jīng)。“權(quán)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dāng)恁地做,故雖異于經(jīng),而實亦經(jīng)也”。權(quán)雖然不同于經(jīng),實際上也就是經(jīng)。三是經(jīng)權(quán)相互轉(zhuǎn)化:“經(jīng)是已定之權(quán),權(quán)是未定之經(jīng)。”權(quán)是為了實現(xiàn)平衡而采取的措施、方法和手段,具有靈活性、多變性、未定性,這些措施在一定條件下通過概括、總結(jié),可以提煉、上升為一般原則固定下來,轉(zhuǎn)化為經(jīng),故曰“經(jīng)是已定之權(quán)”;經(jīng)是已經(jīng)確定的一般原則,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必須化為具體的措施和方法才能推行,而實際情況是復(fù)雜多變的,具體的方法和措施也要隨之變化,必須用權(quán),這樣,已定之經(jīng)在一定條件下就轉(zhuǎn)化為未定之權(quán),故曰“權(quán)是未定之經(jīng)”。經(jīng)與權(quán)的關(guān)系不是絕對的、固定不變的,而是相對的、辯證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zhuǎn)化。
陳淳師承朱熹,進一步發(fā)揮:“經(jīng)所不及,須用權(quán)以通之。然用權(quán)須是地位高方可,非理明義精便差,卻到合用權(quán)處亦看不出。權(quán)雖經(jīng)之所不及,實與經(jīng)不相悖,經(jīng)窮則須用權(quán)以通之。柳宗元謂‘權(quán)者,所以達經(jīng)也’,說得亦好。蓋經(jīng)到那里行不去,非用權(quán)不可濟。”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第一,權(quán)與經(jīng)是統(tǒng)一的。“權(quán)雖經(jīng)之所不及,實與經(jīng)不相悖”,雖然權(quán)是在“經(jīng)之所不及”處才發(fā)揮作用,但是,權(quán)與經(jīng)并不是對立的,而是統(tǒng)一的。這種統(tǒng)一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權(quán)之作用在于通經(jīng)。“經(jīng)所不及,須用權(quán)以通之”,“經(jīng)窮則須用權(quán)以通之”,都是這個意思。就是說,在實際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往往會遇到“經(jīng)窮”而無法推行的時候,固守常經(jīng)已經(jīng)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就必須用“權(quán)”。用權(quán)的目的就是為了使經(jīng)獲得貫通、融通、通達。所以,他贊成柳宗元“權(quán)者,所以達經(jīng)也”的說法。另一方面,權(quán)之作用在于濟經(jīng)。“經(jīng)到那里行不去,非用權(quán)不可濟”,在經(jīng)不能推行的地方,必須用權(quán)來救濟、補充經(jīng)。“權(quán)只是濟經(jīng)之所不及者也”。“權(quán)”的作用就在于救濟、補充經(jīng),在“經(jīng)”不能發(fā)揮作用的時候發(fā)揮作用,完成經(jīng)所未嘗完成的使命。第二,地位高者方可用權(quán)。用權(quán)是有條件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權(quán),只有那些地位高者才能用權(quán)。這里所講的“地位高者”不是指有權(quán)有勢的富貴之人,而是指明白事理、精通大義之人。這些人通曉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掌握社會人倫法則,在認識和修養(yǎng)上都達到了一定的境界,故而能在“經(jīng)所不及”之處,通過用權(quán)來救濟經(jīng),使經(jīng)獲得貫通。如果不明白事理,不精通大義,即使該用權(quán)的地方也看不出來,也不知道用權(quán),所謂“非理明義精便差,卻到合用權(quán)處亦看不出”。
如果仔細琢磨,不難發(fā)現(xiàn):在經(jīng)、權(quán)問題上,陳淳與其師朱熹相比,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強調(diào)了用權(quán)的條件性。用權(quán)是有條件的,離開具體條件,權(quán)變就會成為變詐之術(shù)。一是用權(quán)的客觀條件。“經(jīng)”具有常住性、普適性,處理問題應(yīng)當(dāng)先用經(jīng),而實際情況是復(fù)雜多變的,有時用經(jīng)難以解決實際問題,這就是“經(jīng)所不及處”。此時,只有用權(quán)才能解決問題。“經(jīng)所不及處”構(gòu)成了用權(quán)的客觀條件。二是用權(quán)的主觀條件。不是任何人都能隨意用權(quán),只有在認識和修養(yǎng)上達到一定境界的人方能用權(quán),所謂“地位高方可,非理明義精便差”,“圣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差”。圣人“理明義精”,用權(quán)游刃有余:“圣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nèi)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圣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圣人與天理渾然一體,無絲毫欠缺,貫通內(nèi)外、本末真實無妄。不思而得,“生而知之”;不勉而中,“安而行之”。就像人走路,必須細心照看方能行走路中,否則就會誤偏路邊。圣人則不用看路,自然能行走路中,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此謂契合天道。“地位高者”,聯(lián)系陳淳的思想可知,主要是指“理明義精”者,也就是掌握了自然規(guī)律和社會法則的人,這些人精研事理、深明大義,認識水平和道德修養(yǎng)都達到了極高的境界,所以,合當(dāng)用權(quán)時就能用權(quán)。“理明義精”構(gòu)成了用權(quán)的主觀條件。可見,陳淳關(guān)于用權(quán)的主客觀條件的論述是對朱熹“權(quán)是不得已而用之”思想的進一步明確和深化。
其次,突出了“經(jīng)”的日用常行性。朱熹把“經(jīng)”看成萬世常行之道,強調(diào)它的亙古不變性、至上性:“三綱五常終變不得”;陳淳雖然不否認這一點,但他把“經(jīng)”看成日用常行的道理,強調(diào)“經(jīng)”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適性,把“經(jīng)”從天上拉回人間。凸顯了“經(jīng)”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用性。
再次,指明了“權(quán)”之通經(jīng)作用。朱熹強調(diào),權(quán)“不離那經(jīng)”,甚至明確地說,權(quán)“實亦經(jīng)也”,具有明顯抬高“經(jīng)”之地位的傾向。陳淳則說,“經(jīng)所不及,須用權(quán)以通之”,“經(jīng)窮則須用權(quán)以通之”,宣示了“經(jīng)”亦有無能為力之時,強調(diào)經(jīng)窮權(quán)濟,權(quán)以通經(jīng)。凸現(xiàn)了“權(quán)”之濟經(jīng)、通經(jīng)作用。也就是說,陳淳更看重經(jīng)權(quán)問題的實用性,注重把經(jīng)的原則性與權(quán)的靈活性結(jié)合起來,尋求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進而達到中的目的。
陳淳不僅從理論上闡明了權(quán)以通經(jīng)的問題,而且用具體事例加以論證。他說:“如君臣定位,經(jīng)也。桀紂暴橫,天下視之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quán)也。男女授受不親,此經(jīng)也。嫂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jīng)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jīng)也。佛肸召,子欲往,則權(quán)也。然須圣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差。”陳淳以三個典型范例論證了經(jīng)、權(quán)的辯證統(tǒng)一。其一,商湯滅夏武王伐紂。君臣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各守其分,君為臣綱是天下之常經(jīng),必須遵守;但是,桀紂橫征暴斂,殘暴無度,天下人視之為獨夫,這時,君臣之義已經(jīng)到了盡頭,所以,商湯放桀武王伐紂,就是為了使經(jīng)獲得通達、貫通,這就是以權(quán)通經(jīng)。陳淳在《命》中進一步申述了這一點:“然此等事,又是圣人行權(quán)底事。”武王伐紂這類事,順天應(yīng)人,不僅有“命”的因素,它同時又是圣人用權(quán)的事情。其二,孟子所說的“嫂溺援之以手,權(quán)也”。男女授受不親是人倫綱常,是經(jīng);但是,嫂子溺水了,面臨生命危險,如果不去救援便是豺狼,所以,伸手去救嫂子,也是為了使經(jīng)通達貫通,即行權(quán)、用權(quán)。其三,孔子所講的“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經(jīng);但是,佛肸在中牟叛亂,叫孔子去,孔子想去。子路不悅,認為孔子說話前后矛盾。孔子則認為,“吾其為東周乎”是他內(nèi)心恒久不變的信念,如果能到叛亂的地方去,把自己所倡導(dǎo)的道德觀念貫徹下去,不正是行權(quán)用權(quán)嗎?
總之,陳淳通過據(jù)典引證,理論詮釋,闡明了經(jīng)權(quán)關(guān)系。一方面,經(jīng)與權(quán)之間具有差異性。“經(jīng)是日用常行道理”,“權(quán)也是正當(dāng)?shù)览恚强梢猿P校c日用常行底異”,經(jīng)、權(quán)之間表現(xiàn)出“常行”與“非常行”、常與變的差異;另一方面,經(jīng)與權(quán)之間具有統(tǒng)一性。“權(quán)只是濟經(jīng)之不及者”,“經(jīng)窮須用權(quán)以通之”,權(quán)之濟經(jīng)、通經(jīng)功能得以彰顯。簡言之,經(jīng)、權(quán)之間既對立又統(tǒng)一。
三、權(quán)、中關(guān)系:“知中然后能權(quán),由權(quán)然后得中”
在權(quán)、中關(guān)系上,陳淳同樣展現(xiàn)出辯證思維的特性。他說:“問權(quán)與中何別?曰:知中然后能權(quán),由權(quán)然后得中。中者,理所當(dāng)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quán)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dāng)然,無過不及者也。”這段話十分清晰地闡明了權(quán)、中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
第一,權(quán)與中相互區(qū)別。“中者,理所當(dāng)然而無過不及者也”。在這里,陳淳不是簡單地說“中”就是無過無不及,而是說“中”不僅是“無過不及”而且是“理所當(dāng)然”,根據(jù)事物之理應(yīng)當(dāng)如此。他進一步解釋說:“合當(dāng)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dāng)然而然,便即是中。”“中”是應(yīng)當(dāng)如此,當(dāng)然而然,無過無不及。也就是說,陳淳強調(diào)了“中”是自然和社會的法則,具有客觀性,是人們正確處理問題的依據(jù)。“權(quán)”則與人的主觀性相聯(lián)系:“權(quán)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dāng)然,無過不及者也”。一個“度”字充分體現(xiàn)了“權(quán)”的主觀特性,“度”有揆度、測度、揣度、衡量的意思。權(quán)就是主體根據(jù)實際情況,審慎思考,權(quán)衡利弊,揆度事物之理,從而獲取事物中所蘊含的當(dāng)然之則;依據(jù)當(dāng)然之則裁斷合宜,最終達到無過無不及的目的。概言之,中是目的,權(quán)是方法,用權(quán)是為了達到中。
第二,權(quán)與中相互聯(lián)系。一方面,“知中然后能權(quán)”。“中”是行權(quán)用權(quán)的目的,行權(quán)用權(quán)必須首先知道、了解“中”,然后才能行權(quán)用權(quán);如果不了解“中”,行權(quán)用權(quán)就會失去目標(biāo)和方向,就無法正確地行權(quán)用權(quán),甚至可能導(dǎo)致權(quán)變的濫用。另一方面,“由權(quán)然后得中”。“權(quán)”是達到“中”的手段和方法,只有通過行權(quán)用權(quán),然后才能達到“中”的目的;如果不能正確地行權(quán)用權(quán),“中”的目標(biāo)就無法實現(xiàn)。
總之,“權(quán)”與“中”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聯(lián)系,既對立又統(tǒng)一。“中”是目的,其本質(zhì)是理所當(dāng)然,無過無不及;“權(quán)”是方法,通過采取靈活變通的方法做到無過不及。要實現(xiàn)“中”的目標(biāo),必須知道這一目標(biāo),掌握蘊涵在事物之中的當(dāng)然之理;依當(dāng)然之理進行權(quán)度,裁斷合宜,無過無不及即中的目標(biāo)方能實現(xiàn)。故而“權(quán)”與“中”相互依存,不可分離。離開“中”,權(quán)就失去了目標(biāo)和方向,就無法正確地行權(quán)用權(quán);離開“權(quán)”,就會如孟子所說“執(zhí)中無權(quán),猶執(zhí)一也”,僅僅固執(zhí)地守中,不懂權(quán)變,只能是執(zhí)其一端而不能守中。這樣,就無法達到“中”的目的,取得“中”的效果。
陳淳同樣以歷史事例說明了用權(quán)、守中是極其困難的事情。他說:“天下事到經(jīng)所不及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quán)。且如武后易唐為周,張柬之輩于武后病中扶策中宗出來。胡氏《管見》說武后乃社稷之賊,又是太宗才人,無婦道,當(dāng)正大義,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立其子而殺其母?南軒謂此時當(dāng)別立個賢宗室,不應(yīng)立中宗,他也只見得后來中宗不能負荷,故發(fā)此論。文公謂:南軒之說亦未是,須是身在當(dāng)時,親見得人心事勢是如何。如人拳拳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如何廢得?人心在中宗,才廢便亂。須是就當(dāng)時看得端的,方可權(quán)度。所以用權(quán)極難。”武則天易唐為周,張柬之等人于武則天病中扶持、策立唐中宗為帝,恢復(fù)李唐王朝。就這一歷史事件,宋代的學(xué)者發(fā)表了不同的看法。陳淳以他的經(jīng)權(quán)觀為指導(dǎo),對宋代學(xué)者的評論作出了研判。
其一,胡寅在《致堂讀史管見》中認為,武則天是唐太宗的才人,有失婦道,乃社稷之賊,應(yīng)當(dāng)“正大義”,聲稱根據(jù)唐高祖、唐太宗定立的祖制,應(yīng)該把武則天廢為庶人,并且賜死。陳淳認為,這種說法既有悖于經(jīng),又不合乎權(quán),達不到中的目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用權(quán)。天下哪有立兒子為帝而殺其母的?
其二,張栻(號南軒)認為,不應(yīng)該立中宗為帝,而應(yīng)該另立一個賢德的宗室子弟為帝。陳淳認為,張栻的說法也不對。因為南軒也只是看到后來的唐中宗軟弱無能,不堪重負,難當(dāng)大任,才發(fā)表這種議論。他贊成朱熹的觀點:要想做出正確的判斷,必須身臨其境,親眼見到當(dāng)時的人心所向,了解事情的具體態(tài)勢!如果說當(dāng)時立中宗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人們都懇切地服膺中宗,而中宗又沒有失德,怎么能廢中宗而另立新君呢?既然立中宗是人心所向,如果剛立就廢,必然導(dǎo)致天下大亂。因此,“權(quán)度”必須立足實際,身臨其境,親眼觀察客觀形勢與人心所向,把當(dāng)時的情況弄得清楚明白,才能裁斷合宜。
關(guān)于該不該立唐中宗為帝之事,《北溪字義》里還保存了另一段話:“先生所編《文公竹林精舍語錄》,亦以后來言之,則中宗不可立,以當(dāng)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罪。天下人心皆屬望中宗,高宗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時承乾亦有子,但人心不屬,若卒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最難處,今生數(shù)百年后,只據(jù)史傳所載,不見得當(dāng)時事情,亦難斷定。須是身在當(dāng)時,親見那時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別立宗室;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這段話大概是陳淳的門人王雋所增。先生指陳淳,文公即朱熹。在陳淳所編的《文公竹林精舍語錄》里,詳盡地記述了朱熹的看法。其基本觀點與上述一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朱熹和陳淳認為,歷史上用權(quán)的事例,是否正確、適宜,后人只是根據(jù)史傳的記載進行分析推測,沒有看到當(dāng)時的實際情況,因此,不能盲目地下結(jié)論。正確的做法是:從實際出發(fā),親歷其事,觀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才能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
總之,中是目的,權(quán)是方法。用權(quán)是為了達到“中”,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從實際出發(fā),“須是身在當(dāng)時,親見得人心事勢是如何”,“須是就當(dāng)時看得端的,方可權(quán)度”。因此,用權(quán)不能脫離具體條件,一方面,用權(quán)離不開客觀條件,“天下事到經(jīng)所不及處,實有礙”,才能用權(quán);另一方面,用權(quán)離不開主觀條件,只有“理精義明”者才能用權(quán)。用權(quán)既要結(jié)合實際,又要具備主客觀條件;既要把握客觀形勢,又要看到人心所向。當(dāng)用經(jīng)時則用經(jīng),當(dāng)用權(quán)時則用權(quán),才能作出正確地選擇,做到無過無不及,達到中的目的。
四、經(jīng)、權(quán)準(zhǔn)則:“二者都不可無義”
道是眾人共由之路;理是事物當(dāng)然之則。用經(jīng)、用權(quán)都必須符合“道理”,才能裁斷合宜,也就是合乎“義”。“義”構(gòu)成了用經(jīng)、用權(quán)的的根本準(zhǔn)則。顯然,陳淳繼承了孔子“義之與比”的觀點。什么是“義”?陳淳認為,“義”有三方面內(nèi)涵:第一,“義”是君子路。他說:“才志于義,便入君子路;才志于利,便入小人路。”“志于義”還是“志于利”,意味著走君子路還是走小人路。陳淳對“志”的解釋是:“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里去。”“志”就是全心所向,“有趨向、期必之意”。一旦全心向“義”,便可踏入君子路;一旦全心向“利”,就會誤入小人路。這種說法來源于孔孟。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說:“義,人路也。”“義”是人應(yīng)當(dāng)走的路,只有走人應(yīng)當(dāng)走的路,合乎“義”的要求,才是君子所當(dāng)行的正路。相反,為“利”驅(qū)使,就會誤入歧途,偏離正路滑向小人所走的邪路。第二,“義”是宜之理。陳淳說:“義是宜之理……事物各得其宜乃義之用,而宜之理則在內(nèi)。”義是合宜、適宜的意思,“宜之理”在事物內(nèi)部,事物內(nèi)部的當(dāng)然之則、當(dāng)然之理就是“義”;事物各得其宜是義的作用,是“宜之理”的外在表現(xiàn)。第三,“義”是裁斷合宜。陳淳說:“義就心上論,則是心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后字。裁斷當(dāng)理,然后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dāng)出不當(dāng)出。若要出又要不出,于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如果從人的內(nèi)心意念來說,義是“裁制決斷處”,“宜”則是裁制決斷的結(jié)果,裁斷合理然后得宜。因此,“義”就是裁斷合宜。凡是事情到了眼前,必須剖析判斷,看看可行與否?“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dāng)如此做,不當(dāng)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他援引朱熹的話說,義在人心,就像一把利刃,事物一接觸它,便能分成兩片。如果連是否可行都不能作出剖析判斷,便是人心頑鈍而失去了“義”。比如說,一個人邀我一起出去,便需要分析判斷應(yīng)當(dāng)不應(yīng)當(dāng)出去。如果既要出去又不要出去,“半間半界”,遲疑不決,不能作出正確判斷,還有什么“義”可言?像這種需要裁斷合宜的地方,必須是自己看得透徹分明,知道應(yīng)當(dāng)這樣做,不應(yīng)當(dāng)那樣做,能夠明確區(qū)分可否從違,便是義。他不同意韓愈把“義”說成“行而宜之”,認為“行而宜之”是從外在表現(xiàn)來理解“義”,混淆了內(nèi)在的“宜之理”與外在的義之用,不是把“義”理解為事物內(nèi)部的“宜之理”,而是把“義”看成外在的義之用了!
概而言之,“義”是人之為人所應(yīng)當(dāng)走的君子之路,是事物內(nèi)部的當(dāng)然之理;人們根據(jù)事物內(nèi)部的“宜之理”剖析判斷,裁斷合宜,就是“義”。
基于對“義”的理解,陳淳認為,守經(jīng)、用權(quán)都離不開“義”,都必須以“義”為準(zhǔn)則,“義”字兼經(jīng)、權(quán)而用之。他說:“文中子說:‘權(quán)義舉而皇極立。’說得亦未盡。權(quán)固義精者然后用得不差,然經(jīng)亦無義不得。蓋合當(dāng)用經(jīng)時須用經(jīng),當(dāng)用權(quán)時須用權(quán),度此得宜便是義,便是二者都不可無義。”文中子認為,如果能夠根據(jù)“義”的準(zhǔn)則來用權(quán),就能夠“立皇極”。在陳淳看來,這種說法表達得還不夠完善和充分。用權(quán)固然是對“義”有精深理解的人才能用得不差,然而用經(jīng)也不能離開義。根據(jù)“義”的準(zhǔn)則,應(yīng)當(dāng)用經(jīng)的時候必須用經(jīng),應(yīng)當(dāng)用權(quán)的時候必須用權(quán),權(quán)度這一問題能夠做到合宜、恰當(dāng)就是義。他舉例說:“如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是不當(dāng)用權(quán)而用權(quán)者也。王、魏不死于建成而事太宗,是當(dāng)守經(jīng)而不守經(jīng)者也。自魏晉而下,皆于國統(tǒng)未絕,而欺人孤寡,讬為受禪,皆是當(dāng)用經(jīng)而不用經(jīng),不當(dāng)用權(quán)而用權(quán)者也。又如季札終于固讓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于守經(jīng)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禍之慘,是于用權(quán)中見義不精者也。”在這里,陳淳用歷史事件說明了用經(jīng)、用權(quán)都離不開“義”。其一,唐朝時秦王李世民殺死太子李建成,登上皇帝寶座,這是不應(yīng)當(dāng)用權(quán)的時候而用權(quán)。其二,王珪、魏征原本跟隨太子李建成,玄武門之變后,王珪、魏征不陪李建成去死,反而侍奉唐太宗李世民,這是應(yīng)當(dāng)守經(jīng)的時候不去守經(jīng)。其三,自魏晉而下,都在國家大統(tǒng)未絕的情況下,欺負孤寡弱小,假托“受禪”之名,自立為帝,這些都是應(yīng)當(dāng)用經(jīng)的時候不去用經(jīng),不應(yīng)當(dāng)用權(quán)的時候而去用權(quán)。其四,“季札讓國”,“見義不精”。春秋時吳國的季札由于固執(zhí)讓國而不肯自立,“自亂其宗國”,最終導(dǎo)致吳國被越國所滅,這是在守經(jīng)的過程中對“義”的理解不夠精深準(zhǔn)確,未能在守經(jīng)中見“義”。其五,張柬之等五王扶策唐中宗為帝,使唐朝返回正道,中宗誅殺諸武,卻留下武三思,最終自罹慘禍,這是在用權(quán)的過程中對“義”的理解不夠精深。
上述五種情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合“義”。不當(dāng)用權(quán)而用權(quán),不合“義”;當(dāng)守經(jīng)而不守經(jīng),亦不合“義”;當(dāng)守經(jīng)而不守經(jīng),不當(dāng)用權(quán)而用權(quán),更不合“義”。另一類是“見義不精”。有守經(jīng)而見義不精;有用權(quán)而見義不精。不合義也罷,“見義不精”也罷,都是沒能正確地處理好用經(jīng)、用權(quán)與義之準(zhǔn)則的關(guān)系,在用經(jīng)、用權(quán)的問題上有失偏頗,歸根結(jié)底都是偏離了“義”之準(zhǔn)則,難以達到“中”的目的。一言以蔽之,用經(jīng)、用權(quán)都離不開義。只有對“義”有了精深的理解和準(zhǔn)確的把握,義之與比,當(dāng)用經(jīng)時則用經(jīng),當(dāng)用權(quán)時則用權(quán),“度此得宜便是義”。完全符合“義”,就能做到無過無不及,達到“中”的境界。
綜上所述,陳淳認為,經(jīng)與權(quán)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聯(lián)系。經(jīng)是日用常行的道理;權(quán)也是正當(dāng)?shù)牡览恚豢梢猿P校皺?quán)只是濟經(jīng)之所不及者”,用權(quán)的目的是為了讓經(jīng)獲得貫通、融通,權(quán)與經(jīng)“實不相悖”。用經(jīng)用權(quán)都離不開“義”,義是用經(jīng)用權(quán)的根本準(zhǔn)則。通過用經(jīng)用權(quán)最終達到“中”的目的,實現(xiàn)社會和諧。
注釋:
[1]張加才:《關(guān)于北溪生平研究的幾個問題》,《北方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2002年第2期,26~31頁。
[2][7][8][9][10][11][12][13][14][22][23][24][26][27][29][30][31][32][34][35][36][39][40][41][42][43]陳淳:《北溪字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2009年重印)。附錄1,85頁;51頁;38頁;38頁;41~42頁;51頁;53頁;51頁;51頁;51頁;73頁;51頁;4頁;51頁;20頁;51~52頁;52頁;16頁;15頁;16頁;18頁;19頁;21頁;51頁;52頁。
[3][4]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4頁,第246頁。
[5]田豐:《從“春秋決獄”到“四書升格”:從“反經(jīng)合道”為“權(quán)”透視漢宋學(xué)分野》,《山西師大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2年第3期,85~89頁。
[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2005年重印),第116頁。
[15][16][17][18][19][20]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三)卷三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2004年重印),第989頁;991頁;989頁;994頁;990頁;988頁;989頁。
[25]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二)卷二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2004年重印),第598頁。
[28][33][37]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82頁;37頁;39頁。
[38]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006年重印),第267頁。
〔責(zé)任編輯 吳文文〕
Exp loration of Chen Chun's V iew s on the Constan t Princip le and the Em ergen t Practical Princip le
Lu Youcai
In Chen Chun's opinion,the Constant Principle and the Emergent Practical Principle are both different and related.The Constant Principle is the principle practiced at usual times.The Emergent Practical Principle is also a just principle,but it is not practiced at usual times.It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Constant Principle.The intention of using the Emergent Practical Principle is tomake the Constant Principlemore feasible.The Emergent Practical Principle is not against the Constant Principle.Either the use of the Constant Principle or the use of the Emergent Practical Principle can not be without Justice.Justice is the cardinal principle of the use of the Constant Principle and the Emergent Practical Principle.By the use of the Constant Principle and the Emergent Practical Principle,the purpose of the MiddleWay and social harmony can be achieved ultimately.
Chen Chun,the Constant Principle,the Emergent Practical Principle,the MiddleWay,Justice
盧有才(1964~),男,河南新密人,河南工程學(xué)院圖書館館長,黃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