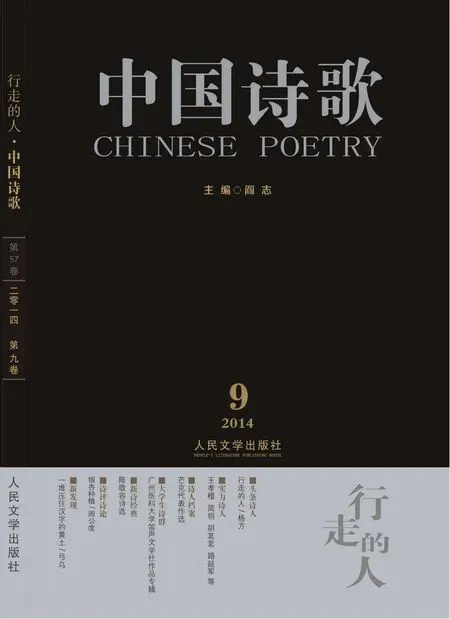詩學觀點
□韓玉/輯
詩學觀點
□韓玉/輯
●曾蒙認為第一個寫出讓人模仿的詩歌的詩人是幸福的,模仿的人卻是不幸的。反過來說,被模仿者亦是不幸的。比如海子,他的死使他的貴族的烏托邦遍布模仿者的詩中,大面積泛濫。盡管海子普及了中國詩歌哲學層面的可能性前景,使我國的詩歌躍上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光輝時代。但是,從結果的層面來分析,大面積無血無肉的虛無的模仿之作,正是結果(模仿)本身傷害了詩歌。海子有一大批言語模仿者,但卻沒有一個像海子一樣以身體祭獻于詩歌的行為模仿者。因此,在靈魂的歷險中,詩人對生命、死亡、信仰、存在、時間等終極關懷命題是無法模仿的。
(《筆記簿:回答與清醒》,《紅巖》,2014年第3期)
●安琪認為現代詩寫作更多的是語言的自覺。即尋找一種有別于過去年代過去詩人的寫作模式,包括詞語的組合,句子的組合,甚至詞組自身組合的反傳統反常規。盡管這種嘗試頗為艱難,造成的直接后果有時會如一些讀者所言的“頭暈目眩”和“百思不得其解”,但這還是值得的。因為詩歌寫作本身就是對既定空間的突破和對未知空間的創造。允許一部分人在傳統的河流中遨游,也應該允許另一部分人自掘河流,前者固然保險,后者因為更加艱難而理應受到更多尊重。
(《與詩歌有關》,《青春》,2014年第3期)
●董迎春認為如果用詩體意識考察當下詩歌寫作,不難發現有兩個派別:一類是以口語、現世、及物、反諷為特征的“非詩”寫作,它充滿著懷疑與虛無的情緒;另一類是以語言、審美、精英、可能作為話語的“詩”的書寫。前者強調易懂、批判的寫作,接近大眾文化;后者是語言本體的、思想可能探索的建構性寫作。用這兩條粗疏的線索歸納當下的詩歌話語,的確有著某種理論褊狹的嫌疑,但是,這兩條寫作傾向卻也有力“標出”當下詩歌的精神性訴求及相異的文化意識。
(《反諷時代的孤寂詩寫——再論海子詩歌精神》,《南方文壇》,2014年第3期)
●姚舟認為在充滿著功利張望和觀念困擾的當代中國文壇上,若說還有如水晶般純粹詩人的存在,則顧城和海子二人可擔此贊譽。在日漸浮華的現代社會里,顧城與海子的詩歌創作卻始終堅持著返身自我、本真投入的美學價值,顧城有著如孩子般純稚的夢幻情緒,海子則是敏感而倔強的生命極限抒寫。顧城用夢構建的童話世界與現實對抗,海子以花營造神性世界來超越現實,在“夢”與“花”這兩種意象中二人抒發了歲月的沉重感及對生命的感悟,唱出了時代的高音。
(《由詩之意象考究顧城與海子的詩歌創作》,《芙蓉》,2014年第3期)
●霍俊明認為新死亡詩派的詩學意義和前所未有的難度和挑戰一同出現。一方面,將死亡的生命詩學有意識地作為詩歌創作的旨歸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一創舉正是因為其更為復雜和更為疼痛和深迥的哲學和詩學成為了中國詩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標系。但另一方面,其難度也是可以想見的。在中國的詩歌精神譜系中抒寫死亡意識和生命觀照的詩人和詩作足以光耀千古。新死亡詩派在有意識地抒寫和發現“新死亡”時都必須意識到與前次的這些相關文本的關聯和差異是什么?
(《漳州詩群五人談》,《福建文學》,2014年第3期)
●黃錦樹認為作為邊緣的小文學系統,馬華新詩太容易受到其他中文系統(或其他系統)的影響,很容易變成附庸。而詩的詩意本身,就是那風格化的陷阱。馬華新詩的現代性或許不在于詩意的自覺,而是反詩意(或反-反詩意)的自覺,對特定模子的反叛。馬華新詩的邊緣性,也即是它自身成立的條件,它的詩意,必須是(反)反詩意,或非詩意。但那并非對詩意的否定,讓語言赤身裸體、私處暴露,而毋寧是發揮詩意自身的否定性——否定性的詩性,經由對詩自身的哲思、對現實的介入、反思歷史,以找到馬華新詩自身的邊緣位置。
(《尋找詩意:大馬新詩史的一個側面考察》,《華文文學》,2014年第2期)
●蘇文健認為閱讀江湖海的詩歌,有兩種聲音特別明晰,第一種是他對詩歌本身的發聲,第二種是他通過詩歌讓無聲的事物得以發聲。這兩種聲音的有效發出有賴于詩人對詩歌藝術本身的自覺追求。詩人作為大自然的歌者,可以直接傳達大自然的天籟之音。他以詞來傳達物的話語,讓人類與大自然進行一種有效的對話互動。詩人通過改變語言(詞語)來改變世界,緩解靈魂的窘境。詩人一生注定與詞語進行不斷的較量,以此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建構自己的“聲音詩學”。分析江湖海詩歌的聲音,可以為我們深入“聲音的詩學”提供重要的入思路徑。
(《聲音的詩學與詩歌的意味——評江湖海詩歌》,《創作與評論》,2014年3月下半月刊)
●朱雄軒認為從詩歌文化發展來看,中西方不少詩人都崇尚自然,賦予了自然力量神秘的色彩,從而促成了自然神秘觀的誕生。自然神秘觀在中西方詩歌發展歷程中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和作用。處于儒家文化領域中的中國詩歌經過時代演變,已經有了一個成熟的系統,誕生了一系列不同類型的詩篇,但“天人合一”等思想貫穿始終。在西方詩歌創作中,自然神秘觀的影響更為深遠,宗教、古希臘神話一直是永恒的主題,在特定時期,詩歌甚至成為了宣揚神學的“吹鼓手”。盡管這一思想遭到了現代文明的抨擊,但其仍為人類詩歌文明的發展和繁榮奠定了基礎,提供了生長的沃土和創作的源泉。
(《小議中西方詩歌中的自然神秘觀》,《芒種》,2014年3月上半月刊)
●張紅波認為肖黛的詩歌很鮮明地體現了她的人生態度:在與都市的喧囂的較量中,從容、淡定、寧靜。詩歌為我們提供了家庭、故鄉兩種途徑,去看待和研究其如何用美去對抗浮躁喧囂對人心的侵襲。她用一個個貌似病態的靈魂,呼喚著一種又一種理想,傳遞著一種又一種對人生、對社會的思索。在她的眼中,廣袤的西部大地、靈動的江南水鄉都值得用飽滿的熱情去訴說。惟獨世人追逐的繁華、喧囂,在詩人這里尋覓不到半點的好感與稱頌。她并非用一種憤世嫉俗的眼光仇視著這些概念。她有的,是一種平靜,平靜的漣漪下,也伏著一絲傷感與抗拒。
(《水的精靈詩的魂——肖黛詩集〈一切與水有關〉風格淺論》,《青海湖》,2014年第9期)
●譚五昌、王琦認為在文學創作中“社會現實”與“想象虛構”之間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在詩歌的創作中,這個問題就表現得更加顯豁,因為詩歌在終極意義上涉及人的心靈幻想,因而天然地需要想象對于現實的超逸與飛升。當下,已有不少詩人不滿足于對現實生活進行平面化的語言復述,而是在面對現實的基礎上,努力開拓詩性的想象空間。武稚、李魯平和李莊三位詩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們立足于現實的土壤中,向天空發出了詩意的召喚,為現實撥動了瑰麗的想象之弦,于現實生活的沉淀與超脫中提煉出了一種在詩歌中想象與現實結合的可能。
(《源于現實之上的詩性想象》,《清明》,2014年第2期)
●江一郎認為靈感能提供給詩人們的,不過是某些思想的火花,其危害性是直接導致他青春期的寫作成天在打磨一點虛假的詩意。一個真正的詩人不會信任靈感,他的寫作更多來自他活著的經驗。經驗遠比靈感持久,也要遼闊。它要求一個詩歌寫作者對生活的認知首先是開掘性地發現,然后以敏銳而鮮活的感覺在想象中創造。經驗才是創造力。
(《札記(創作談)》,《詩潮》,2014年第3期)
●江非認為在詩歌中寫“是”的人往往會在他的作品里實現個人、語言與詩學的三者合一,詩在他們那里是一種對人類存在感的獲取,是一種時代精神語言的創生活動,還是一個人說“我正在”的場所,比如屈原、陶淵明、李白、海子、荷爾德林、蘭波、金斯伯格這樣的詩人。一首詩自從未開始之時,就已經是一個運動。一首詩,在文學上,是一個先前之作、書寫者、寫作者和讀者之間來回運動的語言實體。所以,在這個“在世界之中”和他者存在的意義上,詩更要是一個“是”。詩人要讓自己既在世界之中,也在自己面前和神之跟前。
(《給詩歌一個“是”》,《詩刊》,2014年3月下半月刊)
●辛泊平認為現實遠比我們的文學豐富,文學創作中的任何形式的變形和夸張都不過是矛盾人為化的集中和重組。再變形再夸張的文學,和現實的觸目驚心、匪夷所思相比,都顯得那樣冷靜和平和。我們通過文字和光影看到的不過是現實的影子。他認為在創作中一味地強調詩歌的現實性的做法是危險的,它雖然不同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專制,但卻從某種意義上干涉了詩人的自由。在他看來,真正的現實應該是全方位的、立體式的,它既有那種表現人類苦難、揭示精神困境的宏大敘事,也應有疼痛刻骨銘心的個體述說。
(《我理解的當代詩歌與現實》,《詩選刊》,2014年第3期)
●瓦刀認為詩人是手捧靈魂,讓生命返璞歸真的人。每一個俗世中人都有他相應的位置,詩人是向往和追求真善美的群體,他們時常通過自己獨有的方式濯洗靈魂,其靈魂是干凈的,是敢于示人的。而詩歌就是靈魂撥動語言之弦奏響的生命真音。詩歌來源于生活,來源于詩者的心靈,是一個人對生活和生命等一些外在因素的心靈反應。這種反應應該以一種最原始最質樸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就是詩歌的初始形態,也是我們的“生命的真音”。
(《手捧靈魂返璞歸真——創作小札》,《時代文學》,2014年第3期)
●林雪認為創新并尋找深度是重要的和難能可貴的,也是一個詩人和一部詩集走向獨立和成熟的標志。詩人應該有意在文本中探險,以檢驗自己是否有能力從以往詩歌或光明或黑暗的框囿中,從中國古典和西方文學的強勢圍剿中突圍。當詩人成為一個傾訴者,詩句中的形象注入了詩人自己的智慧。生活是一種宿命,經驗,偶然,邏輯中的突變,而文學卻有著無限的可能。在自己意識到風險,制造出風險后,詩人就能夠做到自己挽救自己。
(《而詩人還將何為?》,《文學界》,2014年3月上旬刊)
●艾士薇、杜青鋼認為里爾克的詩歌創作凝聚了獨具一格的詩學,其詩學致力于對時空關系和物我關系的新思辨。關于時空關系,里爾克主張取消時間、摧毀時間而凸顯空間。他在詩歌創作中試圖建立“時間已然失效的空間世界概念”,以此實現內在空間與外在空間相結合,并超越傳統意義上的時空限制。正是通過對物的凝望和對空間的重視,里爾克促成了物我之間的“深層移情”關系。他將主觀濃郁的物我情感以客觀冷靜的形式加以呈現,揭示了“物”的本質是人類存在的象征,直抵人類存在的本源,并予以詩意的敞開。
(《時空之思與物我之辨——里爾克的詩學透視》,《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2期)
●楊四平認為唐德亮的《驚蟄雷》通過正面的與反面的、歷史的與現實的、中國的與外國的、政客的與詩人的、散文的與韻文的等一系列對比的運用,建構起了全詩縱橫捭闔、開闔有度的整體框架。詩人以對比為邏輯架構,形成藝術張力,在龐大的反思和批判網格中,游刃有余地穿行于中國古代文化史、中國近現代革命史、國外近現代革命史和當代中國現實語境,使得全詩的思想張力和藝術張力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它給予了我們當代詩歌需要恢復處理復雜歷史文化和現實生活的能力的啟示,指引著我們繼續發揮詩歌的啟蒙使命與革命使命。
(《心靈的史詩:新左翼現實主義詩歌的敘事與抒情——評唐德亮的長詩〈驚蟄雷〉》,《文藝理論與批評》,2014年第2期)
●尖·梅達認為詩歌是直通心靈的,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它是直線,最短,直達你的痛或癢,可以深入人們的肉體和靈魂。詩歌,無論是描摹事物還是表達情感,都必須以真實的信仰為本,用精煉的語言,傳達出詩人內心對事物的神秘感覺。詩歌不僅是語言,關鍵是要進入所表達的事物的本身。過多地構造語境,會沖淡事物本身的精神。正如薩特所說的,詞語只是吹過事物表面的風,它只是吹動了事物,但并沒有改變事物。
(《詩之思》,《文藝報》,2014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