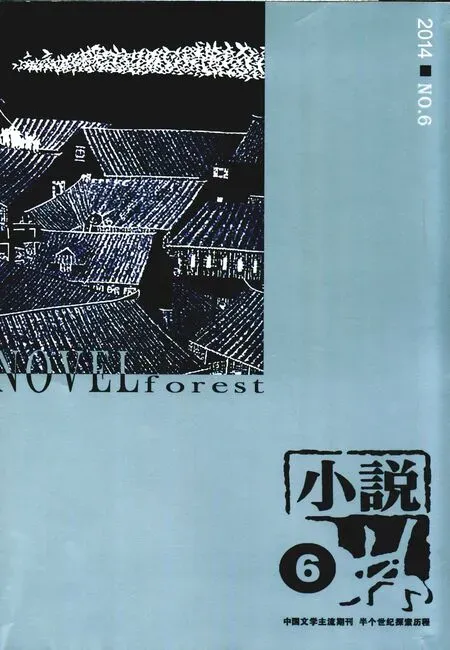警喻微小說三題
警喻微小說三題
陰陽年
天還沒有亮透,父親就把我從被窩里拽出來,把用鐵爐子烤熱的棉襖棉褲遞給我,說就熱乎快穿上。
父親每天都是這樣,早早地從炕上爬起來,端一筐麻茬添進鐵爐子里,把衣服烤熱給我穿。
今天似乎比每天早些,不但因為今天是臘月二十三,小年,更主要的是今天殺年豬。
我穿好了棉襖棉褲,父親就從炕櫥里掏出線麻,他續我搓,不一會兒,三根手指粗細的麻繩搓好了。我知道,這是殺年豬用來綁豬蹄子和豬嘴巴用的。搓完繩子,父親又到柴火垛撅回一把高粱稈,放在地上的瓦盆里,準備用它攪豬血,以防豬血凝結。攪過的豬血,會出現很多血絲,用笊籬撈起,攥凈血水,放進烀肉的酸菜鍋里,這樣的殺豬菜才有味道。然后往豬血里兌些烀肉的老湯,撒些蔥花、花椒、咸鹽,加點蛋清,把弄好的豬血灌進事先洗凈的豬腸里,上鍋一煮,蘸著蒜泥就可吃了。
我已經五年沒有吃過豬肉和血腸了,因為媽媽去世后,我和父親相依為命,我們家就沒養過豬。今年春天,父親用一麻袋玉米從鄰居家換回兩頭豬崽。父親跟我說,今年過年我們也能殺豬了,也能吃血腸了。
于是,我每天都去山上挖野菜,回來用鍋馇好,拌點玉米糠,兩個豬崽氣吹似的長。
于是,我就盼著過年。
父親把一切都準備妥當之后,天已大亮。父親站在豬圏旁看著圈里長得一水水的大肥豬,不知是高興,還是舍不得,淚水在眼圈里直轉轉。我想父親也許是想起了我的媽媽。
媽媽活著的時候,父親總和她吵架。那時,我才七八歲,不知他們為啥吵。后來,隱約聽村里人背后說,我的大姨父曾抱著我媽媽親嘴被我父親撞見了。從那時起,我開始恨媽媽,以至后來媽媽去世我一滳眼淚也沒掉。
剛吃過早飯,殺豬的胡大叔就領著三四個人拎著殺豬刀走進了院里。父親剛從豬圏里趕出一頭,大伙就七手八腳地把豬撂倒,綁上豬蹄和豬嘴,用杠子抬到院子里早就放好的八仙桌上,我急忙從屋里端出接血的瓦盆放在豬頭的下方,胡大叔拿雙筷子插進綁豬嘴的繩子里擰了一下,一只手攥著筷子把豬頭稍稍往起提了提,另一只手操起刀從豬脖腔處插進去,然后,猛地把刀一拔,一股殷紅的鮮血噴濺出來……
父親早把一鍋水燒得翻滾,大伙把豬抬到鍋臺上,用瓢往豬身上潑水,不一會兒,豬就褪好了。
眨眼間,胡大叔就把豬大卸八塊。
灶里架上柈子,鍋里重新添好水,父親選了些肉丟進鍋里,一袋煙工夫,屋里就飄滿了肉香。
父親讓我燒火,他洗了洗手出去了。只一會兒,就把隊長、會計、民兵連長和全隊男勞力領了回來。殺豬請客是我們黑瞎溝屯的習俗,何況我們家五六年沒有殺豬了,總得好好請一頓。
父親把大家讓到屋里,又打發兩個小伙子借桌子板凳,簡直就像我娶媳婦似的,場面弄得挺大。
父親在我身后轉了兩圈,好像下了很大決心似的把我叫到一邊,沉吟了半天,對我說,把你大姨父也叫來吧。
我知道,父親有這樣的決定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我站在那兒沒動。
父親沉默了一會兒,說去吧。
我把大姨父領來時,菜已經上桌,酒已倒滿碗,大伙正吵吵要喝。見我大姨父出現在門口,一下子靜了下來。
父親迎上來說,來啦。
大姨父含糊地應著。
這時,隊長站起來,招呼著,來,來,坐這里。
大姨父就坐在了隊長旁邊。
父親說,大伙喝吧。
大伙這才緩過神兒來,吵吵嚷嚷地喝起酒來。
唯獨大姨父不吱聲,只悶頭喝酒。
酒過三巡,大姨父突然從凳子上摔倒在了地上,嘴里的哈喇子淌了出來。
大伙一下子就蒙了。
隊長急忙讓車老板子套車,送大姨父去公社衛生院。車剛出屯子沒走上二里地,大姨父就停止了呼吸。據大隊衛生所的大夫說,大姨父是死于突發性腦溢血。
隊長說,人死了不能回村子,就停放在村頭吧。
大姨父的兒子,我的兩姨哥哥滿堂子不肯,非要拉我們家去,埋在屋里不可。
對于大姨父的死,滿堂子簡直是瘋了。爬上我家房頂,把大黃紙壓在房脊上……
隊長好說歹說,答應大姨父發喪的費用由我家承擔,拿不出錢就用豬頂。
滿堂子就把我家僅剩的一頭豬趕到了他家。這才答應在村頭搭起了靈棚,把尸首停放在那兒了。
那天夜里,我居然夢見了媽媽,這是我第一次在夢里見到媽媽。媽媽穿件紅襖,滿臉喜色,正忙著往門上貼福字兒。
我在哭喊媽媽的聲中醒來。
醒來的我,臉上已掛滿了淚水。
我把夢中的情形告訴了父親。父親撫摩著我的頭嘆了口氣說,雖然說夢都是反的,陰間陽間都一樣,你媽那邊肯定也忙著過年哩。
天要下雨
這幾天,天總陰沉沉的,就像父親臉上不愉快的神色。
臨去生產隊干活時,父親囑咐我多抱些柴火回來,怕是要下雨了。可是我一連準備了兩天柴火,這雨也沒下。
我站在門口,望著天,就看見趙嬸著急把火地來了。此時,仍然陰沉的父親正忙著做晚飯。
趙嬸到了,父親露出些許的微笑,對我說,燒火。就領著趙嬸去了里屋。
趙嬸這幾天常來我家,每次來都神神秘秘的。我不知道她找父親有啥事兒。鍋燒開了,趙嬸還沒出來。
我就好奇地走到門口,聽到趙嬸嘀嘀咕咕地說,那咋整,這事你得掂量好。
父親嘆了口氣,沒再言語。
趙嬸是婦女隊長,東鄰西舍的事她都知道,該管不該管的她都管。趙嬸辦事很公道,在我們黑瞎溝屯很有威信。
趙嬸走后,父親端著飯碗一直沒吱聲,只是沒滋沒味兒地吃著。
父親這幾天情緒一直很低落,常常拿東忘西。
有天晚上,兩姨哥哥滿堂子來了。滿堂子臉色很難看,繞過我直奔里屋拽著父親的脖領子問,咋的,你是不是覺著害我們家不夠慘?
高中對于學生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階段,數學對于學生而言也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需要老師們重視數學情感教育,為學生們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
父親怯懦地說,不是,真的不是。
滿堂子說,你把我爹喝死了,還惦念起我媽啦?是,我爹跟我小姨有沒有事,這是你們的事兒,你別動我媽的歪心眼兒。
大姨夫死后,雖然我還拿滿堂子當作很親很近的姨哥,可他卻拿父親和我當仇人。
父親滿臉難色,是你媽托他趙嬸來說的,我也沒應允。
滿堂子撒開父親,照你這么說,我媽是上趕著你了?你做夢吧你,就你這破家,窮得叮當響,這日子咋過?
父親說,我知道,我不配。
知道就好。滿堂子說完轉身走了,走的時候,好像還瞪了我一眼。
其實,姨媽對我們挺好,媽媽去世后,姨媽常給我們爺倆做鞋穿,夾的棉的供著。有時還來我家給我們洗洗衣服,拾掇拾掇屋子。她對父親說,她干這些活計都是為我,不能讓我沒人管。那一刻,我一直都認為,姨媽就是親媽。
有一次,我病了。倒在炕上蒙上被子還冷得直打牙巴骨。
姨媽來了,用酒泡紅花,在我的額頭、前后心、手心腳心上搓著,朦朧中我以為是媽媽,就拽著姨媽的手哭喊著媽媽。這一喊就把姨媽的淚喊了下來,她抱起我喃喃地說,沒娘的孩子苦啊!
父親嘆道,屋里沒女人的日子是不好過!
大姨說,沒男人的日子也難。
父親又自責道,都怨我,那年殺豬,我不該找大姐夫來,他要不喝悶酒,死不了。我這腸子都悔青了。
姨媽許久才說,那不怪你,是他到壽了。
我把姨媽當成自己的媽媽,可我知道她畢竟不是我的親媽。
趙嬸開始張羅父親和大姨倆人的事,這一張羅,就把這事整大了。
滿堂子整天在家鬧,連勸說他的媳婦都罵。事情公開了,姨媽也就不藏著掖著了。大姨說,滿堂子,你大了,你也是有兒女的人,離開我,你們也能過。你姨弟還小,我幫他拉扯一把。
滿堂子哀嘆著,薅自己的頭發,在地上撒潑。
姨媽來到我家,跟我父親說,這個家,里里外外都得你手到,啥事都得自己扛著。我妹子活著時又不讓你省心,你心里苦啊!姨媽摩挲我的頭說,這事兒就定了,咱倆搭伙把孩子拉扯大,這孩子跟我不生分。
父親說,難啊!滿堂子驢驢豁豁的,我不想讓你們娘倆鬧別扭。
姨媽說,這事兒,你別管。你想沒,你要有個天災病業的孩子連飯都吃不上。
父親說,大姨子嫁妹夫,這也不是個曲子。
姨媽說,別說這沒用的,人親不?親就嫁了。我妹子說不定在那邊都跟人家過上了呢。
聽了這話,父親不再言語了。
幾天后,趙嬸和滿堂子的媳婦把姨媽送過來,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在我家喝了頓酒,姨媽成了我的親媽。
那天,唯獨滿堂子沒來。
那天,天真的飄起了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可是我的心里卻是一片晴空,父親也一定是這樣,樂顛顛地往屋里抱柴火。
三十多年過去了,有一個事情一直讓我想不明白,我不知道,將來他們走的那天,會和誰埋在一起?
那一年,我十一歲
二嬸走了。
二嬸結婚不到三年就走了。
二嬸走的時候瘦得就剩一把骨頭。
我站在二嬸的棺槨前默默地立著,我知道二嬸是抑郁成疾走的。因為就在二嬸即將成為我二嬸的頭天晚上,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至她后來一直生活在擔驚受怕中。
在黑瞎溝屯,不論誰家辦喜事,至少要預備兩天酒席,頭一天叫偏席,第二天拜堂成親叫正席。偏席那天晚上,老親少友擠在我家的土屋里喝酒。那時,我才八歲。我對喝酒當然不感興趣,就抓了把肉丸子坐在窗外的小凳子上,就著朦朦朧朧的月色吃著。
東院就是我那沒過門的二嬸家,我們兩家就一墻之隔。說是墻,只不過是半米不到的干打壘土墻,我常爬過墻頭去她家玩。其實,二嬸的心上人不是我二叔,是村子東頭的二牤子。我常常見二牤子去她家幫著干活,二嬸和二牤子有說有笑的總也嘮不完。倆人正好著呢,我二叔從中插了一杠子,硬是用一頭老母豬、四百塊錢,還有幾塊碎花布料送給了我二嬸他爹,就把我二嬸撬來了。后來,她就成了我的二嬸。
我正享受著肉丸子的美味,就見三斜楞推開房門里倒歪斜地去房后的柴草垛旁撒尿。
三斜楞是個光棍。一個人吃飽了,連狗都不用喂。誰家有個大事小情,他腦袋削個尖往前湊。常常喝得跟頭把式,五迷三道的。
不一會兒,就聽房后有爭吵聲,我好奇地跑過去。見聽三斜楞說,見面分一半,我趕上了,不能白趕,你要不從,我就在明天拜堂時把這事兒抖摟出去。
我見二嬸和二牤子哆哆嗦嗦地跪在三斜楞的腳下,苦苦地求饒。三斜楞一把薅起二嬸,強行地把她攬在懷里……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就知道三斜楞是在欺負二嬸,就順手抄起木棒翻過土墻砸在了三斜楞的后腦勺上,三斜楞連聲也沒吭就倒在了地上。
二嬸把我抱在懷里嚶嚶地哭。
二嬸和二牤子走后,我跑回屋里說,三斜楞喝多了,倒在房后起不來了。
大伙七手八腳地把三斜楞抬回到他家,三斜楞睜開眼睛,摸摸后腦勺子,問我這是咋啦?
大伙說他喝多了,摔倒在地上了。
三斜楞只覺得后腦勺子疼,好像什么事兒也記不起來了。
過門那天,二嬸哭得死去活來。拜堂時兩眼紅腫著,一直盯著大門口,看上去非常恐懼,生怕有啥事兒發生。晚上鬧洞房,屋里擠滿了人,大伙起著哄,捉弄二叔二嬸,二叔跟他們瘋著,二嬸臉像葡萄水坐在炕沿邊一聲不吱。二嬸見我進去,急忙抓把糖塞進我的兜里,還擠著笑在我的臉上輕輕地捏了一下。
幾天后,三斜楞來到我家說找二叔喝酒。二嬸很緊張,死死地拽著二叔不撒手。三斜楞淫蕩地盯著二嬸,說我只想喝點酒。
二嬸不敢看他,把頭深深地埋在二叔的懷里。
三斜楞走后,二叔很不高興地倒在炕上生起了悶氣。二嬸一直心神不寧地坐他身邊。
有天早晨,二叔趕著馬車去公社給隊里拉化肥,二叔剛走,三斜楞就來了。塞給我一塊糖,摸著我的頭嬉笑著打發我到外面玩。二嬸喊我不要走,可我看看手里的糖,還是推門跑掉了。
剛到門外,屋里就傳來聲嘶力竭的大叫,我急著跑回屋,見三斜楞捂著襠部嗷嗷地叫著,二嬸披頭散發地哆嗦著,小衫的扣子全掉了。二嬸哭夠了,把小衫塞進灶坑里燒了。這是第二年的春天,那年我九歲。
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從山上遛鳥蛋回來,剛走到山下,見三斜楞拖著二嬸往山上撈,三斜楞說就一回,就一回,你要不答應,我就把你和二牤子的事告訴你男人。二嬸一邊掙著一邊叫著。
我知道三斜楞說的男人是我二叔。我就高喊,二嬸!二嬸!
我這一喊還真管用,嚇得三斜楞跑進了山里。
這是我十歲那年的夏天。
后來,二叔和二嬸總吵架。可每次二嬸都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只是嚶嚶地哭泣。
再后來,二嬸病倒了。倒在炕上的二嬸臉色煞白,大口大口地吐血。
二嬸死后的那一夜,二叔的頭發全白了。
我在給二嬸燒紙時,捜尋著這模模糊糊的零散記憶。
我不明白這么年輕的二嬸怎么會憂郁而死。
二叔拉起哀傷的我,拍著我的頭說,記著,娶媳婦一定要娶個兩廂情愿的。
那一年,我十一歲。
警喻,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哈爾濱市作家協會副秘書長。曾在《北方文學》《章回小說》《小說林》《百花園》《歲月》《短篇小說》《文學報》《短小說》《中華傳奇》《天池》《延安文學》《小小說月報》等報刊發表中短小小說三百余篇。四十余篇作品被選入各類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