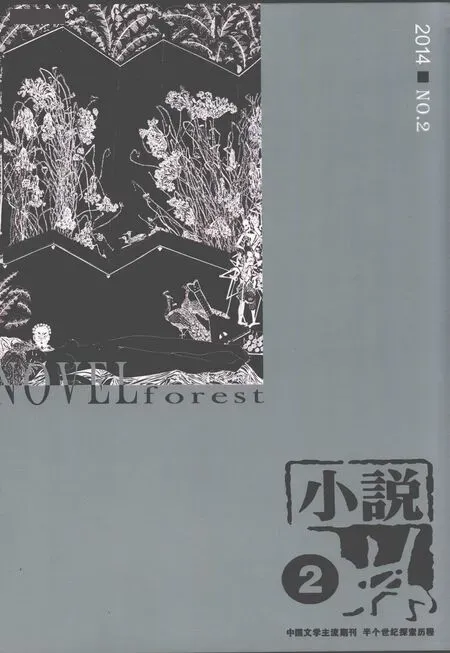拉什迪:在文本內外
◎武 歆
拉什迪:在文本內外
◎武 歆
坦誠地講,初始知道薩爾曼·拉什迪,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因為文學之外的事情:1989年他因為出版小說《撒旦詩篇》,牽扯到宗教問題,在伊斯蘭世界引發劇烈動蕩,被認為這部小說侮辱了伊斯蘭教,隨后被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宣布拉什迪“死亡”——也就是說,所有的穆斯林教徒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以神圣的宗教名義,可以用任何方式殺死他,并能得到千萬美元的獎賞,而且這個宗教命令將無限期的存在。從此,拉什迪被迫開始了“地下生活”,并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銷聲匿跡,人間蒸發。
很多年以后,細想閱讀拉什迪的前因后果,誠實地講,除了文學的原因,當然還有文學之外的好奇心理。
大約三年前,在寧夏銀川的異常疏朗的夜晚,一位頗有實力的“70后”作家,在和我交流閱讀心得時,情緒激動地向我講起拉什迪,講起拉什迪獲得布克獎和為拉什迪獲得巨大世界聲譽的小說《午夜之子》。我深知,在西方或者說在世界,假如說諾貝爾文學獎更具有“大眾意義”,那么布克獎具有的,是完全的真正的“文學意義”。從寧夏回來,正好定居英國的詩人楊煉來津,他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我們無話不談,當然只是限于文學領域。我急切地問起拉什迪在英國的情況。楊煉告訴我,最近這些年,拉什迪已經逐漸開始“正常生活”,他在英國一些文學活動場合中多次見過拉什迪。我站立起來,急忙追問拉什迪現在是什么精神狀態。楊煉笑著說,非常沉靜。
我對拉什迪更是陡升“興趣”,畢竟他被“宗教通緝”許多年,過著多年警方保護的地下生活,其保護費每年高達一百六十萬美元。多年如此非正常的生活狀態,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壓力,卻還能依舊“非常沉靜”,這讓我對于拉什迪的興趣逐漸攀升——正是這文本內外的持久的雙重原因,“神秘”的拉什迪,這才開始真正地“闖進”我的閱讀世界里。
我把閱讀的靶心,首先對準了拉什迪獲得文壇地位并且獲得了英國布克獎的小說《午夜之子》。但有意思的是,卻買不到這本書。關于這個問題,順便多說一句:在中國國內有一個怪現象,外國作家的代表作特別不好買。比如楊煉極力向我推薦的奈保爾的《印度:受傷的文明》,我花了半年的時間才買到。原因何在?真是“洛陽紙貴”嗎?不得而知。
因為急于想要閱讀拉什迪,所以我只好選擇了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羞恥》——應該說,這是一次退讓的閱讀,一次“無奈”的閱讀。如今想來,當我三年前拿起《羞恥》這本小說時,那時我并不知道,我將要開始的,會是一場漫長的閱讀對峙,就如同不久前重新閱讀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的《修道院紀事》一樣艱難。都說挑戰寫作難度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其實挑戰閱讀難度,更是一件無比艱難的事情。
但在三年時間里,我就像一個馬拉松的跑者一樣,還是斷續地耐心地把《羞恥》讀了下去。
應該如何用最簡短的話語來描述《羞恥》這部長篇小說,這讓我真的很是為難。很多年以前,在一次與中學生交流閱讀感受時,記得一位中學生問我,怎樣的作品才是一部好小說?記得我當時說,用一句話能夠概括的或是用很多句話都不能概括的,這兩種情形的小說,都應該算是好小說——拉什迪的小說《羞恥》,卻是具備了這兩種情形。
先說第一種情形。也就是一句話概括:“非理性的宗教和政治暴力是導致社會的羞恥以及無恥的根源,并且《羞恥》巧妙地結合了歷史、藝術、語言、政治及宗教,描寫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創建及其失敗的過程。”
這就是“一句話”概述的《羞恥》。想想看吧,這包容了那么多的訊息,無論哪一條拿出來,都是一個體積很大的龐然大物,別說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十部或是一百部,似乎都無法容量。
那么,要是用許多話描述《羞恥》呢?顯然,這就要從“文本之外”撤退到“文本之內”了。
應該說,拉什迪的敘述語言,并沒有特別值得我們欣喜的地方,因為:他沒有海明威的簡潔,也沒有普魯斯特的冗長;沒有愛德華·P·瓊斯的沉穩,也沒有胡安·魯爾福的輕靈精致……拉什迪的語言,堅硬而快速,理智而清醒,盡管也有大段的敘述,也有短促的小節,但無論哪種形式呈現,他從來都沒有柔媚過,即使描寫情感細節時,也依舊還是堅硬、板正,帶著砂紙的粗粒。那一刻似乎你能看到拉什迪那張沒有表情的臉正在審視他的文字。
拉什迪的小說,假如單看某一段落,似乎不像小說,有點兒像非常理性的哲學闡述,有時似乎又像詞典,他會為一個人的姓名而做幾百字的詞典式的解釋。那么,形成如此風格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與他的經歷有關。
拉什迪是移民作家。他出生在印度,成長于巴基斯坦,最后定居倫敦。不斷地遷徙,多種文化的侵襲和灌溉,以及生活環境的不斷變化,導致他必須不斷地適應新的環境,不斷地調整內心的情緒。如此的經歷,勢必影響到他的創作上,影響到他小說的敘述之中。
記得前年我去江西贛南采訪,在瑞金的那些簡陋的房屋前,每個房屋的上面,都釘有顯赫的木牌,有的是“中央蘇維埃銀行”,有的是“最高法院”,有的是“糧食部”,有的是“郵政局”……也就是說,在當年贛南的那個偏遠的山村里,革命的蘇維埃政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那些政府部門,早在中國革命的開始階段,就已經初步形成了,就已經開始運轉了,只不過規模大小而已。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在那段艱苦的歲月里,在那個不起眼的小山村里,已經開始操練管理共和國的經驗。
在與贛南一位文化學者聊天中,那位學者說,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以及進入陜北之前,已經在贛南待了十多年,顯然受到了當地民俗文化的重要影響。他舉例說,贛南文化其實就是客家文化,而客家其實就是中國的“吉卜賽”,客家人不斷地遷徙,所以中國革命在最初的那段時期,潛移默化地受到了客家文化的影響,文化學者讓我大膽地設想一下,后來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運用嫻熟的“運動戰”,是不是就是當年受到客家文化影響的產物呢?我不敢如此認定,但聽上去,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拉什迪的那種敘述粗狂而又龐雜的背后的細膩和真誠,莫非也是受到了動蕩不安的移民經歷的影響?
世界上許多有成就的作家,似乎都是移民作家,拉什迪是這樣,奈保爾也是這樣。奈保爾祖籍印度,出生于特立尼達,最后定居英國倫敦。奈保爾的著名大散文《印度:受傷的文明》,雖然許多時候,他在抒寫印度知識分子的同時,也用大量的筆墨,抒寫了印度平民的普通生活,寫他們的艱辛、保守、茫然和無知,但字里行間卻是沒有一點兒歧視,沒有一點兒俯視感,而是平等地、心痛地去追究產生這種問題的歷史原因。我們能夠看出來,在每一個字句里面,都飽含著奈保爾對本民族的向往與熱愛。
拉什迪和奈保爾一樣,我們在他的《羞恥》的文字表面上,盡管能夠看到滴血的嘲諷,對人的內心瘋狂的針砭,但是在文字背后,卻又能看出他的心痛、不安。
“溫暖”隱藏在“尖銳”背后,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溫暖呢?這需要讀者緊密地與作家配合,需要認真地潛入到作品的精神內核中,“拷問出潔白,然后再拷問出潔白下面的齷齪,最后才是找到齷齪下面真正的潔白”。
美國《紐約時報》曾經評論《羞恥》說“如果不是被看作小說,而是被看作不易分類的作品,可能更有助于欣賞”。的確如此,三年前,當我帶著“讀故事”的心態開始閱讀《羞恥》時,卻是遇到了巨大的障礙,幾乎讀不下去,而當我受到《紐約時報》評論家的啟發之后,重新轉換角度,立刻便有了讀下去的興趣,那些曾經折磨我的枯燥的文字,頓時熠熠生輝起來,仿佛碎亂的珍珠,被一根精神的細繩藝術地串聯起來。
如今想來,拉什迪的這種“散亂的寫法”,莫非受到他不斷變換生活環境的影響?這只是我的猜測和推斷。因為,這就像曾經是戰地記者和拳擊手的海明威,因為經歷的緣故,所以他才能創造出來“電報式寫法”的作品《白象似的群山》;而因為患哮喘病、常年躺在床上的普魯斯特,所以才能寫出多卷本的意識流的《追憶似水年華》。
作家的經歷以及生活狀態,常常能夠烙印在他的作品之上。而遷徙的移民生活,常常是把粗莽袒露在外的,猶如弱小的刺猬,而藏在內心里的,則是柔軟。只有如此,才能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生存下來。這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本能,而這種本能又會成為移民作家的作品外殼。
“敘述混亂”的《羞恥》,也與它的敘事相吻合——是一個關于編造的、虛構的國家的故事。正是因為有了這兩個重要的詞匯:“編造和虛構”,所以一切都正常起來。這也就讓我們不難理解書中許多的“不可思議”,尤其是關于國家的暴力。
在寫這篇小文時,正是“棱鏡門事件”響徹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時候,正是那個叫“斯諾登”的戴眼鏡的美國青年“攪亂世界”的時候,世界上所有人都在猜測這個文靜的“前美國特工”下一站去向何處?當滿載著一百多名記者的飛機降落在哈瓦那機場的時候,笑呵呵的機長面對電視鏡頭,用手指著身后的飛機,興奮地說“機上全是記者”。這時,我突然想到了拉什迪的《羞恥》,想到了英國《衛報》評論《羞恥》時說的“這部小說的主題是羞恥和無恥,這兩者都來自于現代歷史的暴力”。我們再向深處思考,“棱鏡門事件”難道不是“現代歷史暴力”的多重解讀嗎?
我開始逐漸發現《羞恥》的魅力,或者說“與現實生活對應”的魅力。是的,它的魅力,還能有另一種解讀,那就是這部小說,還可稱為“政治小說”。這讓我想到了“政治小說”的另一部代表作: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寫于1948年的傳世之作《1984》。
《1984》同樣虛構了一個國家——“歐亞國”(隱喻前蘇聯)。這部“反烏托邦、反極權的政治諷喻小說”,用文學語言——在作品出版四十一年之后,真實生活中的蘇聯真的解體——完成了他的政治預言,而這一切僅僅相差了五年。
那么,同樣又被譽為“政治小說”的拉什迪的《羞恥》呢?我以為,《羞恥》的作用,在于給“當下”(這是一個現代進行時的“當下”)找到一面鏡子,當下幾乎所有的“羞恥和無恥”的事情,都能在拉什迪的小說《羞恥》中找到某種對應——這似乎要比奧威爾的《1984》更具有震撼力。
前面說過,《羞恥》是一部“一句話能夠概述和許多話都不能概述的小說”,“一句話概述”已經說了,那么“許多話都不能概述”又是什么呢?于是,這回到文本之內的問題,又開始變得越發艱難了起來。我不知道抒寫者拉什迪該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反正我要在這字數有限的篇章里,簡明扼要說出來,猶比推著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怎么辦,只能把“許多話”修正為“幾句話”——我只能做一個“偷奸耍滑”的人,否則我將會把自己置放在浩瀚的海洋之中,最后只能被拉什迪的澎湃的巨浪淹死。
那幾句話是什么呢?
拉什迪在這個虛構的國家里,把人的自由生活比喻為“猶如動物園里動物的偽自由”,而這種偽自由,通過一位已經做了十八年鰥夫的沙克爾先生還有他的三個女兒的日常生活,細碎而又夸張地呈現出來。也就是從沙克爾先生臨終之前,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門窗全都關上,不讓他聽到窗外“帝國主義者的音樂”,而窗外是哪里呢?是外來殖民者紳士們的聚居區——金色酒店。小說也就是從這里開始,“亂石飛舞”般地講述了社會上眾多人士的無恥生活,還有社會上的眾多的丑惡現象。拉什迪在他塑造的近百個人物中,每個人都區別于同類,但又具有相同的丑惡。而這一切的根源,就是“非理性的宗教和政治暴力”,同時他也隱晦地指出來,帝國主義者才是無恥的最終根源。
閱讀拉什迪的《羞恥》,真的不能把它當作小說來讀,而應該作為一部社會詞典來讀,當我掩卷之后,我仿佛看見平靜嚴肅的拉什迪的面容背后,那翻江倒海一樣的內心波瀾。我想,這也只能是拉什迪所寫,只能是一個背負著巨大精神壓力的作家之作品。
《羞恥》之奇幻、神話、宗教乃至口傳文學的多重藝術風格,噴薄般的敘事,在近似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風格之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的書房的窗外,是北方七月潮濕而又霧蒙的天空。假如要是天氣晴朗的話,我能看到海河邊高聳的高樓,可是現在什么都看不見。只有一片白霧。
南方在下雨,北方也在下雨。我看著《羞恥》,心里在想,遙遠的拉什迪,你現在做什么?
作者簡介:武歆,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陜北紅事》、《密語者》、《樹雨》、《延安愛情》、《重慶愛情》、《天津愛情》等九部,中短篇小說集《諾言》,散文集《習慣塵囂》等,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說,共計五百萬字。小說被各種期刊轉載,并有作品改編成電視劇、廣播劇等。文學創作一級,專業作家,天津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