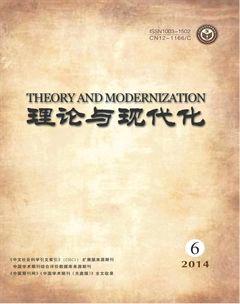解釋學轉向:價值與論爭
王偉
摘 要:關于意義生產問題,羅蒂提出用“解釋學”來取代“認識論”的策略。這一解釋學轉向主張把事物置于意義之網中進行考察,破除了意義擁有不變本質的神話。它在學界引發了強烈共鳴,但也招致頗多微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與羅蒂同屬新實用主義陣營的舒斯特曼做出了長篇批駁,但它實際上并不成立,又重新墮入傳統的基礎主義窠臼。
關鍵詞: 羅蒂;解釋學轉向;舒斯特曼;論爭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4)06-0016-05
人們應該還能記得理查德·羅蒂的震撼性看法:語言是偶然的,語言既不表征現實(反映論),也不表現心靈(表現說),不同的語匯只是適合我們不同目的的工具。意義也是如此,在羅蒂看來,任何事物所具有的意義都不是出自其內在的本質或本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意義的偶然性問題”構成了羅蒂著作中“倍加關注的一個方面”。[1]
一
所謂“認識論”是哲學的核心,“它是一種不同于各門科學的理論,因為它是各門科學的‘基礎。”[2]羅蒂批評這種找尋基礎的做法,因為它總是與某種人力之外的東西相聯,而且還意味著限制——因為所有的表象都必須憑借最終的本質來衡量。他提出用解釋學來取代認識論的策略以避免對不變本質、永恒基礎空洞的追求。但解釋學不愿填補認識論撤除之后所留下的那個空缺,因為它對認識論先前的目標根本就沒有興趣。“解釋學把種種話語之間的關系看作某一可能的談話中各線索的關系,這種談話不以統一著諸說話者的約束性模式為前提,但在談話中彼此達成一致的希望絕不消失,只要談話持續下去。這并不是一致發現在先存在的共同基礎的希望,而只是達成一致的希望,或至少是達成刺激性的、富于成效的不一致的希望。”[2](299)解釋學關心的是具體的對話中所包含的諸種復雜的關系糾結、諸種不同話語之間的相互交流或抗衡。這種對話并沒有什么先在的基礎可以依靠,當然,對話的結果也不需要拿去跟那個基礎進行比對。盡管如此,對話仍然能夠達成一致或共識,但它絕非認識論框架下那種作為共同基礎征候或表象的一致。
在羅蒂看來,整個社會科學都不可能是與價值無涉的、而是詮釋學的,因為“將一種語言中‘評價性的術語分離開來,并把它們的不在場作為一門學科或一種理論具有‘科學特征的一個標準,這種提議是不可能行得通的。”[3]我們使用的任何語匯都不可能晶瑩剔透,而是潛藏著人類意識的編碼,因此,要讓一種描述做到完全客觀與中立是不可能的。實際上,社會科學的詮釋學化都服務于一個共同的目的——幫助人們解決社會問題。因此,成為解釋的不是說掌握了某種特殊的方法,而是說盡可能尋找某種可能會有所助益的語匯來達成特定的目標。羅蒂征引駱賓諾(Paul Rabinow)與薩利文(William M. Sullivan)“解釋始于一種假定,即意義之網構成了人類的存在”的觀點并加以闡述。這里的構成不是物理意義上的,而是說“X構成Y”可以理解為假如沒有足夠關于X的知識我們就無法理解Y。在這個意義上,即便是化石也仍然會陷入意義的網絡中。因為只有將某些化石與其它的化石進行比較才可確定它歸屬于化石家族,否則的話它就只能是巖石。就是說,化石是由這些化石跟那些化石之間的關系,加上古生物學家對它們關系的描述這三者間的關系網絡構成。羅蒂得出的結論是“任何東西,在被用于研究的目的時,都是由意義之網所構成的。”[3](224)這當然不是說作為物理現象存在的化石是由語匯構成的,而是說化石之所以具有意義是因為它處于多種關系項交合形成的意義網絡中的結果。
邁克爾·默里(M.Murray)對從認識論到闡釋學的轉向十分欣賞,他認為《哲學與自然之鏡》“集中收集了對近代哲學所做的有力批判,特別是批判了認識論試圖使自己成為根本科學和思想文化的最高法庭的夢幻”。也可以說,這是他之所以稱贊這部著作“杰出”的最重要原因。[4]但卡林內斯庫認為羅蒂沿著這條路徑又走得太遠了,“以至于主張一旦傳統認識論的那些非歷史(ahistory)假定被證明沒有現實‘根基,并因此站不住腳時,認識論本身除了成為闡釋學的一種形式外別無選擇。”在羅蒂反本質主義邏輯的進逼下,這的確就是認識論無可選擇的歷史命運,而這也顯示出它原本就是闡釋或表述的一種形式,不過是在風云際會之時被神圣化罷了。如其所言,“這一意義上的闡釋學觀念回到了尼采對唯心主義與實證主義(我們想到他的名言‘事實即闡釋)的批判,也回到了海德格爾的激進歷史主義。”[5]另外,拉比諾也批評說:“羅蒂的敘述盡管有著難以抵擋的毀滅性力量——但卻由于它沒能解釋認識論的轉變在西方社會中是如何發生的——在羅蒂看來,它就像伽利略的科學那樣,就那么發生了——或者由于它沒能看到知識在解放和啟發對話之外的作用,而顯得缺乏說服力。”應該說,羅蒂的論述還主要限于哲學領域,而且還是較為抽象的理論表述,但這并未減少它對社會科學其他領域的波及與震撼。這里的沒有解釋“如何”而說服力不夠的判斷其實是與福柯的思想做一比較后得出的:“對于福柯而言,表述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偶然出現在哲學中,隨后對思想進行了三百年統治的問題。通過對秩序、真理和主體的獨特關注,它與范圍廣泛的、異質的然而又是相互關聯的社會和政治實踐相聯系,這些實踐建構了現代世界。于是,福柯就在這種意義上與羅蒂相區別:即前者把哲學觀念當作對話或哲學之中的社會實踐,而不是機緣巧合來對待。”[6]羅蒂的關系主義已經告訴人們他所說的偶然與機緣實則是對歷史現場感的張揚,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他所贊賞的弗洛伊德境界——機緣決定命運。很可惜,“我們都忘記了,實際上與我們生命相關的任何事情均是或然的,從產生我們的精子和卵子的相遇開始”。[7]因此,盡管羅蒂沒有像福柯那樣深入社會實踐開展自己的研究——如果說這是羅蒂無法掩飾的缺陷的話,那也是理論家個人的興趣所致,然而,“機緣巧合”與“社會實踐”在精神上可以契合。
二
引人關注的是,與羅蒂同屬新實用主義陣營的舒斯特曼卻對解釋學轉向作出了長篇大論——他在《實用主義美學》這部著作中專門列出“解釋之下”一章——的辯駁。他認為解釋學轉向是“解釋學普遍主義”(hermeneutic universalism),其核心是反對基礎主義或本質主義的透明事實、絕對真理等。而解釋學普遍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在他看來是正確的,因為他們成功地證明了所有解釋都是非基礎的,可以變更的,而且往往攜帶著偏見。然而,他們錯在由此得出“所有理解都是解釋”(all understanding is interpretation)的結論,錯在“將非基礎的等同于解釋的”。這些錯誤“妨礙整體主義者采取一種更解放的實用主義視界,這種實用主義視界(我將論證)能夠有力地在理解和解釋之間作出區分而又不認可基礎主義。這種實用主義更激進地承認非解釋的現實、經驗和理解已經是透視的、有成見的和可以改變的——簡而言之,為非基礎地給予的。”[8]也就是說,與那些解釋學普遍主義者不同的是,舒斯特曼主張區分理解與解釋這兩個詞,被區分出的那些不是解釋的理解同樣也是非基礎性的。這些對他而言可以凸顯自己作為“整體主義者”(holist)“更解放”或“更激進”的“實用主義視界”。既然他也認同解釋學轉向的反本質主義做法,又標榜自己才是更為激進者,因此這就給人以他才是激進反本質主義者的印象。這就與他以“激進”批評羅蒂的反本質主義形成了有趣的對比。他認為理解與解釋之間的區分并不是嚴格的本體論區分,它們可以共享同一對象,關鍵在于兩者間“某些功能上的區別,是在實用主義上有助益的和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其自身可以被有益地說明。”[8](160)問題是,如果同一事物的理解與解釋僅僅是功能上的差異,那么,是否有必要專立一個理解的名目?它又能否徹底地與解釋區分開?又是什么將解釋與非解釋理解劃出界限?舒斯特曼從解釋學普遍主義論證的六個方面來進行詳細說明,從而試圖回應這些質疑。
先看第一個論證,它的前提是“由于任何公認的事實或真的理解都可以被解釋所修正或取代,因此,它不能享有比解釋更高的認識論地位;而解釋則是典型地可以改變的和不可窮盡的。”由此推論,“由于理解在認識論上并不優于解釋,因此,它與解釋完全沒有什么不同。”再由此進一步推論,“由于所有解釋是可以改變的,所有理解也是可以改變的,因此,所有理解都是解釋。”舒斯特曼認為上述推論“一旦被公式化”就“顯然是(實際上可悲的)荒謬的”。這似乎意味著這些推論如果不公式化就是正確的,但他并未透露這又該是怎樣的情形。而且,他所總結的以上三步看似謹嚴的推論對解釋學普遍主義既沒必要也不合乎實情。僅就羅蒂來說,他就不是如舒斯特曼這樣還在什么“認識論”的問題框架之內討論問題,因為羅蒂對這種追尋最終基礎的做法根本提不起興致。因此,羅蒂所言的所有意義或理解都是闡釋就不是如舒斯特曼所說的那樣被推導出來的,而是意在強調意義產生于話語網絡。舒斯特曼認為人們之所以樂于接受以上推論其實是因為“我們將所有可以改變的和局部的理解比作解釋,好像真正的理解本身從來不能被修改或擴展,好像理解不得不被解釋去修改”。這種批評其實是空穴來風,因為對那些被他批評的解釋學普遍主義者而言,又哪里會有什么“真正的理解”呢?又哪里有什么必要在“可以改變的和局部的理解”與“真正的理解”之間作硬性切分呢?因此,當舒斯特曼嚴厲質問“為什么要作出這種嚴格苛求的假定”時,他與羅蒂們唱著同一首歌。多少有些讓人意外的是,既然是批評解釋學普遍主義者,那就應該在它的這個論證下列出其理由,而舒斯特曼緊跟著給出的卻是“傳統的理由是:理解(像它的同源詞真理和事實一樣)自身被定義為與‘純粹解釋相對的不可改變的東西。”顯而易見的是,舒斯特曼行文的邏輯掉鏈子了,這就使他鏗鏘有力的指責全部做了無用功。“如果我們通過否定任何理解都是不可改變的而放棄基礎主義,那么,可改變的理解的觀念,就變得可能和真正必要了。一旦我們認識到這個觀念,就不必去推斷:僅僅因為解釋是可以改變的,因此,所有理解必須是解釋。但是,解釋學普遍主義者作出這種推斷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了對基礎主義將非解釋的理解與不變的、基礎的真理連接起來的不情愿的、不相稱的依賴。”[8](165-166)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舒斯特曼并沒意識到被他批判的解釋學普遍主義者進行的解釋學轉向并不是靠“推斷”,而是跳出“認識論”的視域做了再描述。恰恰是舒斯特曼自己執迷于“非解釋的理解”,從而與本質主義情緣再續。這種不自覺的做法同樣體現在他對解釋學普遍主義第二個論證的述評中。舒斯特曼完全接受這一論證的前提——所有理解、所有活動都是局部的與透視的,他的疑問是如何由此得出所有理解都是解釋。他再一次重返傳統基礎主義的框架中:“在那里解釋標志著人類理解的局部的、有視界的和多元方式的領域,它在本質上相對于那些將事物作為真正是單一的、可窮盡的和絕對的東西去把握的理想理解。正因為反對那種單一和完全理解的可能性與可理解性(像內哈瑪斯和伽達默爾正確地從事的那樣),普遍主義者推論出所有理解因此被還原為解釋。”就是說,基礎主義設定了“理想理解”這個標準的、必然的、完全真實的答案,而“解釋”則是所有非基礎的理解形式的收容站。舒斯特曼認同伽達默爾對基礎主義的批判,但他認為“我們應該再一次認識到:一旦我們從基礎主義學說中解放出來,就沒有必要接受它的范疇。因此,沒有必要否定真的理解自身可以是有視界的局部的和多元的,因而沒有理由得出結論:由于所有理解必須是有視界的,因此它們也必須是解釋的。”[8](167)讓人生疑的是,那些被批判的解釋學普遍主義者接受了基礎主義的什么范疇呢?如果說是“解釋”的話,那它早已在羅蒂等人那里被賦予了新的意涵:所有可能的解釋都是平等的,它們再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理想理解需要去符合。而且,舒斯特曼本人不也在使用“解釋”這一范疇嗎?關鍵的問題不在于采用了哪一個范疇,而在于給予了它怎樣的內涵。如其所言,的確沒有必要否定“真的理解”的局部性,這恰好證明了它們都是特定解釋的產物,而不是導向舒斯特曼邏輯顛倒的相反結論。
第三個論證與第二個立足點相同,但舒斯特曼由此引出的側重點不一。他認為所有理解都決非中立而是包含著偏見這一點距離所有理解都是解釋“只有很小的一步”。而究竟是否跨出這一步就成為他這個“更謹慎的實用主義者”與那幫“主要的大陸解釋學家如尼采和伽達默爾”之間的分歧點。他也認可理解與解釋一樣總受動機激發、有偏見,然而,“為什么這會使得理解總是解釋”?“除非我們假定只有解釋可以是有成見的,而(前解釋的)理解或經驗則可以完全沒有成見,否則就不能充分地得出這個結論。”[8](168)解釋學普遍主義者自然不會接受這種假定,在他們眼里沒有必要機械地把理解分成“前解釋的”與解釋的,它們本為一物。
第四個論證是因為所有理解都有選擇性,舒斯特曼對此也無異議,但他認為并非所有選擇的理解都是解釋的。“如果理解的選擇既不是有意識的,也不是有意的,而是前反省和即刻的,我們就沒有理由將那種選擇或作為結果而發生的理解視為解釋,因為解釋通常意味著某些有意的或至少是有意識的思考,而理解則不必有。我們能夠根本不用思考某物就能理解它;但要解釋某物我們則需要思考它。”問題是,這里“前反省”與“即刻的”選擇是“理解”,還是一種人的本能反應抑或經驗?當他把這個質疑的理由與維特根斯坦對看—作(seeing-as)討論相提并論時,答案更傾向于后者。他認為維特根斯坦把“看”與“解釋”區分開來:前者是一種“狀態”,而后者則是“去思想、去做某事”。[8](169-170)其實,在維特根斯坦那里,這種區分不過是“‘看的兩種用法”,而且,看與解釋兩者也不是沒有聯系,因為維特根斯坦指出“看”可以不必“想”,但有某種“經驗”也就“在思想”著“所看”。[9]
第五個論證是所有感知和理解包含做某事,舒斯特曼坦言自己完全接受這個前提,但否定這必然使它們總是包含解釋。他認為這一推論暗含著如下前提:“所有對思想具有認識論價值或意義的‘做事,它們自身已經是思想的事了。因此,任何感知的主動選擇和建構,必須已經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有意的選擇,一個包含解釋的決定。這種將所有主動的、選擇的和構成的理解力與主動的、選擇的和構成的解釋理智同化合并,正是我要反對的前提。理解可以不用解釋的參與而主動地構成和選擇,就像行為可以沒有思想或理智的參與而有聰明智慧一樣。”[8](170)舒斯特曼對解釋學普遍主義者的描述不妥,對思想具有“意義”(羅蒂已經棄置了“認識論” )的“做事”與“思想的事”明顯是兩碼事,它實際上是動作與表述之間的差別。羅蒂們突出的是,如果想要使得某一“做事”或者動作具有意義的話就必須把它放置于話語的網絡中。舒斯特曼把兩者的淆亂強加于人并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推論,有著邏輯硬傷的前提還會導出可信的結論么?所以,“理解”竟能大搖大擺地脫離了“解釋”的視線。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行為”竟然可以拋棄“思想”的參與而能坐擁智慧。問題是,如果沒有思想的介入,又憑借什么斷定它是智慧?這與第六個論證直接相關,即在大陸與英美都流行的語言學轉向。“不僅所有理解而且所有經驗都是解釋的,因為二者都不可避免地是語言的—— 一個被羅蒂、德里達和一大批解釋學普遍主義者所認可的結論。”[8](171)盡管有如此之多的理論家秉持此論,但舒斯特曼仍然滿懷信心地從兩個方向進行挑戰,從而斷定其“缺乏說服力”。
其一,應該追問下述觀念:語言的理解總是通過意義及句法規則對約定符號的解碼或解釋。他認為“對語言的駕馭”并非完全如此,因為維特根斯坦提供的另一個模式顯示:它還“(至少部分地)是一種對姿勢的智力習性的駕馭,一種對有效參與一種生活形式中的反應的駕馭”。[8](172)不過,維特根斯坦曾經舉過的看到一只兔子而驚呼的例子恰恰證明這種“反應”其實也是“思想”或解釋。駕馭語言的確是包含“對姿勢的智力習性的駕馭”,但維特根斯坦談及這一點時并非將其視為一種模式,而是學習語言的一個方法或階段。因為他認為教小孩學說話用的是原始形式,“靠的不是解釋或定義,而是訓練”。[9](6)而且,兒童通過學習逐漸掌握了由一批詞匯組成的語言系統,它制約著兒童的理解、解釋與想象。其二,舒斯特曼退一步說,縱然承認語言理解必定總是解釋也不能就此得出所有理解都是解釋的結論。他以為這里不可或缺一個前提:所有理解經驗與有意義的經驗都是“語言經驗” 。從邏輯上說,舒斯特曼只需證明還有非語言的經驗即可鳴金收兵:“身體的意識或理解形式似乎是當然存在的,它們在本質上是非語言的,并在實際上藐視語言描繪,雖然它們可以以某種方式適宜于經過語言。”問題在于,身體的感覺要想成為“經驗”能夠離開語言(的解釋)嗎?當舒斯特曼接著舉舞蹈的例子時,他對這一點的忽視就顯露無遺:我們可以通過脊骨與肌肉的感覺“就能本能地理解一個動作或造型的意義與正確性”,而根本不需要將其“翻譯成概念化的語言術語”。[8](173)那么,單靠本能就能知道什么是“舞蹈”嗎?這種特殊的能力又來自哪里?真的跟語言術語了無瓜葛嗎?我們觀看舞蹈時確實不需要喋喋不休地用枯燥的術語進行解釋,似乎憑借我們的身體感覺就足以判斷優劣高下。但不應忘記:我們的感覺來自語言的規訓,是語言形塑了我們的舞蹈感知。追其根本,舒斯特曼反對語言學轉向是為其“身體美學”張本:“我們哲學家未能看到這一點,因為我們是脫離肉體的談論—頭腦(talking-heads),我們認可和使之合法化的惟一經驗形式就是語言:思考、談論、寫作。但是,如果沒有前反省的、非語言的經驗和理解的沒有清楚說出的背景,無論是我們還是公認為塑造我們的語言都不能幸存。”[8](174-175)人類誕生之前自然界就存在著,但它只有進入語言之網中才能獲得意義。它們可以說是語言的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一用語言去談論就與之脫離。自然界如此,所謂非語言的肉體經驗也是如此。
舒斯特曼最后還談到了自己為何一定要在理解與解釋之間劃界的三點理由:理解給解釋提供“意義—給予”參照,又提供意義—給予的基地,三是為普通理解經驗的合法性或價值進行辯護。放在解釋學的視域中,這些說辭都很牽強,因為能給解釋提供參照或基地的仍然是解釋,只是它們的層次、角度等存在差異罷了。而且,解釋學的轉向本身就是為了破除認識論對某一解釋的專斷,自然也會顧及到普通的理解經驗。舒斯特曼還很擔心:假如沒有解釋就無法理解事物的話,又該怎樣理解解釋自身呢?解釋不就在不斷被解釋的過程中“以至無窮”了嗎?所以,他呼吁“解釋必須最終依賴某種先行的理解”,依賴某種“不是解釋”的東西。這樣的底線或定位顯示了舒斯特曼對傳統意義理論有意或無意的守護。然而,后結構主義的睿見告訴我們:語言遠非經典結構主義所說得那般穩定,它不能簡單地看作一個定義清晰界限分明的結構,而應將其視作一張蔓延到無邊無際的網。讓人惋惜的是,舒斯特曼對此中真意并未明了。但既然自視為一個有時比羅蒂更要激進的反本質主義者,他沒有忘記再三強調理解與解釋的區分是“功能上”或“關系上”的而非“本體論上”的。矛盾的是,他又認為那個作為最后依靠的“不是解釋”——“先行的和基礎的理解”——卻又“可以已經是先行解釋的產物,雖然現在它是被當下直接把握住的東西。”[8](177-178)這不又明明白白承認了那個所謂“不是解釋”的家伙還是“解釋”了嗎?同時不也承認了直接的經驗也是解釋嗎?所以,對舒斯特曼來說,與其哀嘆羅蒂因為“殘余的語言本質主義”而使其“有前途的‘美學轉向精華盡失”,①[8](406)不如認真思索與解釋學普遍主義者連篇累牘的爭辯究竟能否成立。
注釋:
① 羅蒂贊成戴維森對語言的看法,既非“化約式”又非“擴張式”:“他并不(像有些分析哲學家那樣)想要對‘真理或‘意向性或‘指涉等語意概念提出化約式的定義;他也不像海德格爾那樣,企圖使語言成為像上帝一樣的東西,使人類成為只是從語言衍生出來的東西。誠如德里達警告我們的,這樣把語言加以神化,其實只是觀念論把意識加以神化的翻版而已。”(見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第21頁)顯然,羅蒂在這里對海德格爾的語言本質主義進行了批判。
參考文獻:
[1]〔英〕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M].張衛東,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11.
[2]〔美〕理查德·羅蒂.哲學與自然之鏡[M].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24.
[3]羅蒂文選[M].孫偉平,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220.
[4]〔美〕邁克爾·默里.美國現代藝術哲學的新潮流——解釋學和消解哲學[A].裘曉宇譯.汝信主編.現代外國哲學(9)[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8.
[5]〔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M].顧愛彬,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291.
[6]〔美〕保羅·拉比諾.表述就是社會事實——人類學中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A].趙旭東譯.馬戎,周星主編.21世紀:文化自覺與跨文化對話(一)[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485-486.
[7]〔奧〕弗洛伊德.論文學與藝術[M].常宏,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182.
[8]〔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實用主義美學[M].彭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64-165.
[9]〔英〕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M].陳嘉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99-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