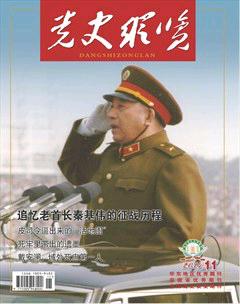宋玉凡的非凡經歷
陳大斌


宋玉凡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鄉村基層干部,一輩子沒離開過家鄉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符離農村。他雖官位低微,卻經歷過一些歷史性事件。
宋玉凡出生于當地一個貧寒農家,“土改”中入黨,合作化運動中被提拔為“脫產干部”。在實行“責任田”那段時間,曾任符離區委委員,但更多時間在該區王樓村任職,先是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后擔任劃小了的王樓公社黨委書記。
1961年春天,符離區開始實行“責任田”,大家都興奮異常,全力推行。但“責任田”只實行了一年就奉命糾正,區委的干部們都想不通。3月中旬的一天,時任中共符離區委書記的武念茲召開區委擴大會議,傳達省委改正“責任田”的決定。會場上氣氛凝重,討論時人人沉默不語。冷場好一會兒,只見宋玉凡站起來“開了頭炮”。他一開口就讓大伙兒大吃一驚:他提出,立馬派人上北京向毛主席反映情況!
宋玉凡提出這樣的建議,不是一時沖動,而是日思夜想拿定的主意。他不緊不慢地向大伙兒說:改正“責任田”的命令是新省委下的。可他們新來乍到,怎么會急著干這件事?我猜想,這是執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又為啥要改正“責任田”呢?我看主要是有的領導人不了解下情。所以,咱們先不忙說怎么改正“責任田”,最當緊的是立馬派人上北京,當面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實際情況。毛主席他老人家最講實事求是,若是他了解“責任田”對發展生產的好處,知道老百姓這么喜歡“責任田”,就一定會讓咱們繼續干下去!
此言一出,馬上就有人響應,要求區委即刻派人進京。可派誰去呢?有人說,主意是老宋出的,要去就老宋去。老宋說:“讓我去我就去。咱們這里的實際情況,實行‘責任田后的變化,老百姓的心思,我都了解。見了毛主席我就仔細對他老人家拉拉。”
有人擔心地問,要是毛主席不同意咱們的意見呢?宋玉凡說,那就據理力爭。我也敢當面把咱們的意見仔細給他老人家匯報匯報。
這邊大家伙兒說得熱烈,那邊武念茲則陷入了深思:這個辦法行嗎?進了北京就一定能見到毛主席嗎?再說,真的有機會見到毛主席,誰能保證他不緊張、激動?結果把應當報告的情況說個七零八落,那不就糟了嗎?真要向毛主席反映情況,申述意見,不如坐下來認認真真寫封信,把咱們這里的實際情況、“責任田”的好處、群眾的要求,都充分寫出來。
武念茲把自己的想法一說出來,大家紛紛表示這樣更妥當。于是,武念茲決定,由他帶頭,區委全體委員自愿簽名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信。這就是日后惹下滔天大禍的符離區委全體同志上毛澤東“萬言書”!
后來這封信遭到批判。在區委會議上,武念茲說,這封信是我提議寫的,又由我主持幾次修改寫出來的。這個檢討應該我來做;上級要給紀律處分,也該處分我這個“首惡”分子,其他同志都是脅從者,按政策可以“不問”。他還沒說完,宋玉凡就嚷起來!這事不能讓書記一人頂缸!如若開初沒有我出主意上北京見毛主席,也就不會有后來的這封信!要說“首惡”,我才是真正的“首惡”,要處分也應處分我。開除黨籍,回家種地我都認了!可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們一門心思要讓老百姓吃上飽飯。這怎么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
不久后,省、地、縣三級組成聯合調查組,來符離調查“萬言書”的“出籠”經過。宋玉凡在接受調查時直截了當地說,“責任田”沒有錯!他還請求調查組批準王樓公社繼續實行“責任田”。他說,讓一個公社實行,錯了也翻不了社會主義的天。調查組嚴厲批駁他的“謬論”。宋玉凡則針鋒相對,說謬論不謬論也不能光憑你個人說,“責任田”里莊稼擺在那里,社員家里的余糧擺在那里呢。你們一天到晚高喊集體好,從五幾年辦合作社時就講“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讓社員過吃面包喝牛奶的日子。過去這么多年了,你們去弄出一個靠集體生產讓社員吃面包、喝牛奶的典型來,哪怕是一個小隊也好啊!調查組氣急敗壞,說宋玉凡是個頑固分子,蠻不講理,堅持錯誤,死不悔改。
1962年6月,鄧子恢看了符離區委的“萬言書”后,派張其瑞為組長的調查組來宿縣農村調查“責任田”,王樓公社王樓大隊是調查點之一。而宋玉凡當時正是王樓公社的黨委書記。
張其瑞等人來到王樓公社做實地調查時,宋玉凡提供一切條件讓調查組廣泛接觸社員干部,充分了解當地實際情況,同時敞開心胸向他們講了實行“責任田”前后的切身感受。他說實行“責任田”不只是增產點糧食,更重要的是使農村集體經濟中從合作化以來多年一直無法解決的一系列“老大難”問題得到解決,是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最簡便易行的辦法!張其瑞調查組在王樓看到的聽到的,使他們對包產到戶“責任田”有了正確的了解。調查結束后,他在《安徽省宿縣王樓公社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情況調查》中說,責任田有力地解決了集體農業發展中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評工記分、農活質量不高,公私爭肥爭勞力,社員集體生產中出勤不出力,不積極勞動生產等痼疾,有效地調動起社員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生產發展。
中央農村工作部調查組在王樓公社的調查報告,已成為中國農業改革歷史上的一份重要歷史文獻資料。這份報告所列事實及闡述的重要觀點,可以說與宋玉凡在王樓公社的實踐及思考有著直接關聯。
以上這兩個方面表現出宋玉凡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從實際出發,堅決捍衛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作風,實在讓人欽佩!
2002年春天,筆者在符離區王樓鄉期間再次拜訪了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
老人耳背,談話要大聲對著他耳朵喊。但他頭腦清楚,說起合作化、公社化和“大躍進”那段經歷,仍然是記憶清晰,激情滿懷。
如今,宋玉凡在宿縣發生的那些重大歷史性事件中的表現,已引起黨史、地方史研究者的重視,而最讓鄉親們感念的“政績”,還是他擔任王樓村領導時實行的“陰陽田”。
所謂“陰陽田”,是在合作化過程中,在給社員劃自留地時,千方百計給農民多留點耕地。宋玉凡說這是給老百姓留下一條保命的活路。王樓實行的也是集體經濟,但老百姓自己耕種的“私地”不比集體耕地少多少。這種明公暗私的辦法被稱為“陰陽田”。它與全國各地的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都不相同,這是宋玉凡一手創造出來的一種獨特的土辦法。
為了了解“陰陽田”,我與宋玉凡有一次長談。正是這次談話讓我真正認識了宋玉凡。
我們的這次談話就像是拉家常。他說,我們這個地方窮,保證人人吃飽飯就是件天大的事。不讓一家人挨餓,這是每個當家人最起碼的責任。成立了高級社之后,農戶的土地牲口都歸了“大堆”,幾十戶、上百戶人家一起干活過日子。一個社的社長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大家長。你要帶好這幾十、幾百戶人家種好地,讓人人吃飽肚子,這容易嗎?后來王樓鄉又辦了高級合作社,一下子成立近千戶的大社!好幾個村莊,幾千口子男女老少,就靠合作社養活了。當社長的肩上責任可就大了。當時人們忙著敲鑼打鼓,呼喊著“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點燈不用油,犁地不用牛”,好像好日子就在眼前。可我打心眼兒里疑惑。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幾畝地,牲口還是那幾口牲口,地里還是種著小麥、雜糧,只說聲合作化,地里就能多打糧食?那好日子就來了?
宋玉凡說,當時我就想,這么大的家業,這么多人的日子,管家的可得多個心眼,得留點后路。不是為自己,而是為這幾百上千戶的人家留條后路。當時高級社章程規定可以給社員劃“小園地”種蔬菜。我們這一帶有些矮山淺溝,地面較廣,耕地比較多。我就在自留地上做文章。上級規定每人一分自留地,我就偷偷地再加上半畝。當時有人說,種菜要那么多地干啥?我說,農民有誰會怕地多?不種菜不會種糧食?又有人說了,合作社生產發展了,還愁沒有糧食?我聽了這話嚇了一大跳。一個當干部的,沒有一點防災的心,這還了得!我問他,你咋知道有了合作社就年年風調雨順,季季豐收?若有了災荒怎么辦?幾百口人,嘴連在一起有幾丈長。那么大個窟窿,見天得多少吃物才填得滿?多給社員一點地,讓他們種點糧食,一旦遇上災荒不至于挨餓!當時有些年輕人聽了就笑話說老宋是小農的窮日子過慣了,腦子過死,目光太短。可我覺得這才是農家過日子的正道。
宋玉凡接著說,合作社頭一年莊稼種得并不好,大伙都說,集體化優越,可我知道,我們農業社當年并沒有比單干時多打糧食。看來社員光靠合作社這一頭不行。1958年春天,我就來了個“憨大膽”,讓社員各家各戶自己刨荒地,自種自收全歸自己。這年麥季又是歉收,我就再大點膽子,把沒有種上的集體耕地劃給每家一畝,規定每戶只要給大隊交100斤山芋干子,余下的出產全歸自己。可是地剛分了不久,1958年9月就來了人民公社化。當時符離是一個大公社,王樓村只是一個大隊。分了地的事,要不要向公社報告?一報告就得將地收回歸公,大隊幾個干部經過一番密商之后,宋玉凡拍板決定:這事得隱瞞下來;分了的地也不能收回,收了糧食還是按事先的規定,每畝交給大隊100斤山芋干子,余下的全歸社員自己。
宋玉凡感嘆道,干了一輩子農村工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幾年。那叫什么日子啊!一聲“大躍進”、公社化,農村工作、農家日子就全亂了套。到處“大兵團”作戰,賽著吹牛皮,家門口的地都荒了,還吹“大豐收”。我真的不明白,地里沒打下糧食,當干部的自己真的就一點不害怕嗎?幾百戶幾千戶社員缺了糧食,那得出多大的事?“大躍進”開始后,我還是抱定老主意,讓社員盡力多刨荒地,凡集體沒種的地,不管生荒、熟荒,誰刨出地來就歸誰,誰種出糧食歸誰收。幾年下來,王樓村家家都開了不少地,都存上了點糧食。1959年冬天大災荒一起,鄰村鄰社鄰隊都病餓死了一些人,我們王樓大隊就沒餓死人。符離公社(后改為區)老書記武念茲讓我拿出點糧食急救。我們拉了幾車山芋干子送過去。
宋玉凡這一手自作主張的“土政策”,在關鍵時刻救了一方百姓性命,至今當地人都忘不了。
* * *
其實,宋玉凡能有這樣一番作為,并不是他有多高的思想理論水平,更不是對后來的大災荒有什么先知先覺的預見能力。他出身于農家,與廣大農民心心相通,他從農民的樸素認識出發,懷疑“大呼隆”集體化能不能搞好生產,養活這么多社員。他遵照農家儲糧備荒的古訓,按照莊稼人過窮日子的常例,給社員們留下一條“后路”。堅持從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實際出發,對農民的命運負責,這是一個農村基層干部最為可貴的品德!
(責任編輯:吳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