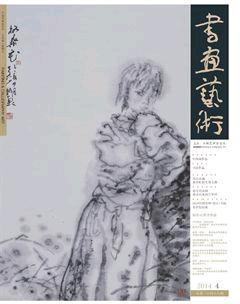2014中國(guó)蘇州(吳江)書(shū)法史講壇綜述
編者按 “2014中國(guó)蘇州(吳江)書(shū)法史講壇”于7月18-21日在太湖之濱的平望古鎮(zhèn)隆重舉辦。來(lái)自海內(nèi)外的書(shū)法史研究專(zhuān)家,眾多知名大學(xué)的在讀碩士、博士研究生,主辦、承辦單位領(lǐng)導(dǎo),全國(guó)多家書(shū)法專(zhuān)業(yè)媒體記者等近200人出席了本次講壇。本屆書(shū)法史講壇由中國(guó)書(shū)法家協(xié)會(huì)、江蘇省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huì)、蘇州市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huì)、吳江區(qū)人民政府共同主辦,蘇州市書(shū)法家協(xié)會(huì)、吳江區(qū)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huì)共同承辦。中國(guó)書(shū)法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江蘇省文聯(lián)副主席、東南大學(xué)博士生導(dǎo)師言恭達(dá),中國(guó)文聯(lián)書(shū)法藝術(shù)中心主任、中國(guó)書(shū)法家協(xié)會(huì)學(xué)術(shù)委員會(huì)副主任劉恒,蘇州市文聯(lián)主席、黨組書(shū)記成從武,中共吳江區(qū)委常委、宣傳部部長(zhǎng)周志芳,中國(guó)書(shū)法家協(xié)會(huì)隸書(shū)委員會(huì)副主任、蘇州市書(shū)法家協(xié)會(huì)主席、蘇州大學(xué)博士生導(dǎo)師華人德,中國(guó)書(shū)法家協(xié)會(huì)學(xué)術(shù)委員、江蘇省書(shū)法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蘇州市丈聯(lián)副主席王偉林,吳江區(qū)丈聯(lián)主席孫俊良等出席了18日上午的開(kāi)幕式。
中國(guó)蘇州書(shū)法史講壇重在培養(yǎng)書(shū)法研究的高層次后備人才,因此每屆均邀請(qǐng)五位國(guó)內(nèi)外知名的書(shū)法史研究專(zhuān)家,有針對(duì)性地為國(guó)內(nèi)書(shū)法史方向在讀博士、碩士研究生、年輕學(xué)者以及書(shū)法愛(ài)好者開(kāi)設(shè)五場(chǎng)高水平的學(xué)術(shù)講座。本次講壇同前三屆(2008-2010)一樣,特設(shè)50個(gè)資助名額,為這些青年學(xué)子提供講壇期間的食宿費(fèi)用。為保證演講的質(zhì)量,讓專(zhuān)家們有充足的時(shí)間闡述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每位專(zhuān)家演講半天。全部演講結(jié)束后,組委會(huì)還安排半天讓五位導(dǎo)師與全體學(xué)員進(jìn)行問(wèn)答式互動(dòng)交流,釋疑解惑,使講壇成為難得的書(shū)法研究的學(xué)術(shù)盛宴。
7月18日上午,美國(guó)波士頓大學(xué)終身教授白謙慎先生作了首場(chǎng)演講。他的演講內(nèi)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題是“吳大澂和文人文化的現(xiàn)代命運(yùn)”。白先生對(duì)晚清士大夫所處的時(shí)代和他們的主要文化活動(dòng)進(jìn)行了鳥(niǎo)瞰式的概括,并向?qū)W員們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研究課題。這部分演講包括下列內(nèi)容:一,吳大澂的生平和他所處的時(shí)代;二,吳大澂與晚清地緣政治;三,吳大澂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四,文人和書(shū)法;五,繪畫(huà)和晚清官員的業(yè)余時(shí)間;六,晚清官員的收藏活動(dòng);七,印章和古文字研究;七,拓片和晚清的知識(shí)生活;八,官員們的藝術(shù)家幕僚;九,吳大澂和西學(xué);十,吳大澂和中國(guó)文人文化的現(xiàn)代命運(yùn)。可以說(shuō),這部分滴講內(nèi)容是白謙慎先生為他近十余年來(lái)的吳大澂研究所做的概述。他所涉及的歷史時(shí)期大約在1850年至1890年,亦即鴉片戰(zhàn)爭(zhēng)后至甲午戰(zhàn)爭(zhēng)前,圍繞著晚清名宦吳大澂(1835年-1902年)及其師友,分析晚清政府高官的文化藝術(shù)活動(dòng),為人們提供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最后那一兩代的士大夫的文化生活的具體圖像,并為我們了解中國(guó)精英文化在二十世紀(jì)發(fā)生的歷史性變化提供一個(gè)可靠的觀察點(diǎn)。白謙慎先生在演講中說(shuō),“我之所以選擇吳大澂,是因?yàn)閰谴鬂钤谝粋€(gè)至關(guān)重要的歷史時(shí)期,來(lái)自一個(gè)在政治和文化上都舉足輕重的地區(qū)——蘇州,而且他所為官的地區(qū)在當(dāng)時(shí)的地緣政治中都有著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他的師友中有許多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他參與了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我希望通過(guò)吳大澂和他的友人來(lái)觀察中國(guó)歷史上最后那一兩代士大夫的文化生活,當(dāng)然我所說(shuō)的‘文化生活包括了藝術(shù)活動(dòng)和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兩者又密切不可分。”
與第一部分的概括性的介紹不同,白謙慎先生演講的第二部分“晚清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書(shū)法”是十分細(xì)致的個(gè)案研究。白謙慎先生以晚清一些政府官具的日記和信札為基本史料,對(duì)他們?nèi)粘I钪械臅?shū)法活動(dòng)做了十分具體的研究,向人們展示晚清的官員如何對(duì)待書(shū)法,花多少時(shí)間寫(xiě)書(shū)法,寫(xiě)多少書(shū)法,這些書(shū)法又是怎樣使用的。這部分演講包括以下內(nèi)容:一,晚清官員的日課及其相關(guān)活動(dòng);二,應(yīng)酬書(shū)法的主要形式和數(shù)量;三,人口增加對(duì)應(yīng)酬書(shū)法的影響;四,提高書(shū)寫(xiě)效率的種種策略;五,為什么書(shū)法扇面和對(duì)聯(lián)這樣流行;六,晚清官員不賣(mài)字;七,特殊的禮品經(jīng)濟(jì)——索書(shū)。在演講中,白謙慎先生指出,晚清的許多高官雖然繁忙,但依然堅(jiān)持練字。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書(shū)法的應(yīng)酬量很大,而最為流行的書(shū)法形式是對(duì)聯(lián)和扇面,最多產(chǎn)的書(shū)法家,如何紹基,居然一天能寫(xiě)幾十副甚至過(guò)百副對(duì)聯(lián)。由于書(shū)寫(xiě)量大,又要保證質(zhì)量,官員們想盡辦法提高書(shū)寫(xiě)效率,譬如,買(mǎi)墨汁,制作磨墨機(jī),正文和落款不同時(shí)寫(xiě),請(qǐng)人代筆等等。白謙慎先生還特別指出,晚清官員雖然寫(xiě)字很多,但通常在為官期間不賣(mài)字。正因?yàn)闆](méi)有市場(chǎng)價(jià)格,索書(shū)的現(xiàn)象很普遍,構(gòu)成了中國(guó)藝術(shù)中特有的“禮品經(jīng)濟(jì)”。
7月18日下午,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教授黃悖先生作了題為《明代仿書(shū)創(chuàng)作模式的運(yùn)用與特征——從祝允明到董其昌的仿書(shū)討論》的演講。黃惇先生首先為聽(tīng)眾解釋“仿”的概念,他說(shuō),“仿”這一詞語(yǔ)在中國(guó)藝術(shù)中出現(xiàn)很早。在書(shū)畫(huà)語(yǔ)境中有時(shí)引申為臨摹和學(xué)習(xí)。早在宋代的文獻(xiàn)中,我們便可尋覓到仿書(shū)的痕跡。當(dāng)然這與后世出現(xiàn)的書(shū)家仿書(shū)創(chuàng)作模式,并非一回事。元明時(shí),經(jīng)畫(huà)家的實(shí)踐,“仿”逐漸轉(zhuǎn)化為一種創(chuàng)作模式。這種仿作,與書(shū)畫(huà)中的臨摹手段有別,即與以學(xué)習(xí)和復(fù)制為目的的書(shū)寫(xiě)不同。臨和摹是必須有具體范本為前提的,仿作則大抵只須和古人作品的風(fēng)格對(duì)應(yīng),而不必和具體內(nèi)容對(duì)應(yīng)。明代吳門(mén)書(shū)畫(huà)家以沈周、文徵明為代表,在他們的山水畫(huà)中,開(kāi)始廣泛地運(yùn)用“仿”的創(chuàng)作手段,并在題跋中多有表述,但在書(shū)作中卻鮮有提及。通過(guò)仔細(xì)考察吳門(mén)書(shū)派代表書(shū)家文徵明、祝允明、陳淳、王寵、文彭等人的有關(guān)作品后,黃悖先生認(rèn)為,仿書(shū)也許在吳門(mén)書(shū)家中已經(jīng)存在,但并不為多數(shù)書(shū)家所運(yùn)用和接受,當(dāng)時(shí)并不作仿書(shū)看,更不將仿書(shū)作為作品的名稱(chēng),未能將仿書(shū)轉(zhuǎn)化成常態(tài)的創(chuàng)作手段。萬(wàn)歷時(shí)代的董其昌,受吳門(mén)山水畫(huà)家影響,不僅在山水畫(huà)中大量使用“仿”的創(chuàng)作模式,而且積極將之使用于書(shū)法創(chuàng)作,并從觀念上清晰地表達(dá)出來(lái),將“仿”的手段放大。在董其昌看來(lái),臨也好,仿也罷,所得當(dāng)在離合之間,而追求的則是神采。骨肉形骸可以?huà)仐墸匾氖莻€(gè)性的顯現(xiàn)。以此觀察仿書(shū)的特征,則用“妙在能合、神在能離”的不似之似表達(dá)最為貼切。此外,董其昌對(duì)于仿書(shū)表現(xiàn)出極高的自覺(jué)性。一方面,董其昌將畫(huà)題直接標(biāo)明仿作,顯然開(kāi)始影響了同代書(shū)畫(huà)家和后輩菩錄者。另一方面,董其昌用他大膽的實(shí)踐和理論闡釋將仿作主動(dòng)從山水畫(huà)延伸至?xí)ㄉ希⒍鄻?biāo)明于作品上。在仿書(shū)的踐行中,“不似之似”、“神似”等審美觀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由于董其昌自覺(jué)運(yùn)用這種新的創(chuàng)作手段,使他的仿書(shū)作品更加鮮明地表達(dá)了個(gè)性,因而對(duì)晚明書(shū)法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從仿畫(huà)到仿書(shū),作為創(chuàng)作模式大體手法是相同的,因?yàn)槊鞔霈F(xiàn)的仿書(shū)手法正源于仿畫(huà)。從嘉靖四年祝允明寫(xiě)《十九首卷》,到隆慶六年的文彭《十九首卷》,再到董其昌寫(xiě)于萬(wàn)歷三十八年年《十九首卷》,這近百年中仿書(shū)創(chuàng)作模式借鑒于仿畫(huà),從隱晦、偶一戲之到以此直抒胸臆的發(fā)展,大約發(fā)生于吳門(mén)書(shū)家而發(fā)揚(yáng)光大于董其昌。兼書(shū)畫(huà)一身的作者,在長(zhǎng)期實(shí)踐中,從偶一戲之,轉(zhuǎn)化為自覺(jué)地運(yùn)用,遂使這種手段在董其昌之后蔚然成風(fēng)。
黃惇先生最后指出,仿書(shū)在明代的出現(xiàn),是傳統(tǒng)創(chuàng)作模式上的突破和創(chuàng)造,在書(shū)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涉及當(dāng)時(shí)書(shū)家對(duì)經(jīng)典解讀的變化、對(duì)個(gè)性的認(rèn)識(shí)加強(qiáng)、對(duì)創(chuàng)作觀念的進(jìn)一步自覺(jué)等一系列問(wèn)題。這些變化乃時(shí)代使然,因?yàn)閺膮情T(mén)派到董其昌為核心的云間派,由于社會(huì)思潮的變化——從前后七子的復(fù)古思潮到公安派的“獨(dú)抒性靈”思想的風(fēng)靡,促使個(gè)性在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得到極大的釋放。
7月19日上午,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zhǎng)、研究員何傳馨先生作了《書(shū)為心畫(huà)——宋元明書(shū)法名跡研究舉例》的演講。何先生列舉了趙孟頫、沈周、乾隆三位書(shū)家的例子,具體分析了他們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三位書(shū)家的身份分別是王室后裔、平民和皇帝。關(guān)于趙孟頫,何先生主要對(duì)他的《禊帖源流》進(jìn)行了梳理與解讀。禊帖即《蘭亭序》,南宋時(shí)期關(guān)于《蘭亭序》墨跡流傳、臨本及石刻本鑒藏等,討論十分熱烈。趙孟頫的《禊帖源流》卷,書(shū)于至元26年(1289年),根據(jù)友人野翁所抄姜夔《蘭亭考》,以精秀小楷抄寫(xiě)成卷,全文1600余字,扼要的梳理出由真跡到定武石刻本的脈絡(luò),是印證南宋時(shí)熱衷蘭亭研究的重要文獻(xiàn),也是探討趙早年承襲王羲之書(shū)法傳統(tǒng)的重要例子。此外,作為宋室王孫,初上大都任職蒙元朝廷,此卷又是趙孟頫連結(jié)江南故鄉(xiāng)親友的憑據(jù),最初的受贈(zèng)者野翁推測(cè)即是活動(dòng)于杭州文藝圈的詩(shī)友張季野。繼而何先生又對(duì)沈周所書(shū)的《落花詩(shī)》進(jìn)行了賞析。沈周晚年有感于年華逝去,陸續(xù)作了數(shù)十首《落花詩(shī)》,詩(shī)意圍繞在春天已逝、繁華盛景不再、凋零殘落的花瓣,象征人生暮年由盛轉(zhuǎn)衰的景況。詩(shī)中或?qū)崒?xiě)繁花落盡,或虛擬于人與事物;繁花落盡,青春不再,觸動(dòng)了詩(shī)人的感興,吟詠之余,并轉(zhuǎn)化為圖畫(huà)與書(shū)法。82歲的《落花圖并詩(shī)》卷書(shū)幅落花詩(shī)十首,是目前僅見(jiàn)的傳世真跡,書(shū)法渾融天成,含蓄內(nèi)斂,筆墨勁健而不失溫潤(rùn),為晚年人書(shū)俱老之作。何先生對(duì)于沈周賦落花詩(shī)的因緣、初作的時(shí)間以及本卷詩(shī)與書(shū)法,均作了細(xì)致的品味與獨(dú)到的分析。他最后談到了乾隆皇帝的書(shū)法志業(yè)。乾隆皇帝繼承祖父康熙皇帝與父親雍正皇帝所建立的龐大帝國(guó),也繼續(xù)滿(mǎn)族統(tǒng)治漢人的文化政策,對(duì)儒家傳統(tǒng)文化極力推重,尤其重視人文教養(yǎng)中書(shū)法藝術(shù)的提升與實(shí)踐。乾隆帝在位期間,積極搜求歷代書(shū)法名跡,拓展皇家收藏。他在處理朝政之暇,或出巡各地,駐蹕行宮的旅途中,以?xún)?nèi)府所藏為范本,透過(guò)一再的臨寫(xiě),試圖超越古跡的外在形象,直接掌握師法對(duì)象的內(nèi)在神韻。乾隆帝自少年、登極至退位,與書(shū)法相關(guān)的活動(dòng)極為豐富,也有前后一致的延續(xù)性。從相關(guān)事跡來(lái)看,“臨書(shū)”是他主要的書(shū)法實(shí)踐方式,透過(guò)臨書(shū),一方面是書(shū)法的學(xué)習(xí),增進(jìn)書(shū)法技能,另一方面將臨書(shū)的對(duì)象作為完成書(shū)寫(xiě)作品的媒介,滿(mǎn)足書(shū)法成就的方便途徑。因此內(nèi)府的收藏、乾隆帝的品味與臨書(shū)作為形成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因素。
7月20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學(xué)藝術(shù)系系主任、教授莫家良先生作了《從北山堂收藏談中國(guó)書(shū)法史的若干問(wèn)題》的演講。莫先生首先介紹了“北山堂”利榮森先生的收藏以及香港中文大學(xué)文物館正在舉辦的“北山汲古:中國(guó)書(shū)法”展覽的籌備及圖錄的編撰情況,他特別指出,香港中文大學(xué)藝術(shù)系藝術(shù)史專(zhuān)業(yè)的研究生共同參與了圖錄條目的撰寫(xiě),這對(duì)學(xué)生是一個(gè)很好的訓(xùn)練。莫先生的報(bào)告分為三個(gè)部分。第一部分主題是“書(shū)法與傳承”,他首先以南宋皇室書(shū)法為例,高宗書(shū)法先學(xué)黃庭堅(jiān)、米芾,后回歸古典,經(jīng)隋僧智永上溯王羲之,終建立了典雅圓融的個(gè)人書(shū)風(fēng)。此書(shū)風(fēng)在南宋初年流行于宮廷,成為南宋帝后的家族書(shū)風(fēng)。高宗的吳皇后練得一手酷似高宗的書(shū)法,傳世高宗的《御書(shū)石經(jīng)》,相傳便有吳皇后的代筆。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雖非高宗之子,但其書(shū)法亦緊隨高宗,而且相似之處,幾可亂真。到宋寧宗時(shí)已是第四代,但高宗的影響依然可見(jiàn)。寧宗的傳世書(shū)跡甚罕,其中為楊皇后生辰所書(shū)的一幀七言詩(shī),有“丙子”(1261)御印,尤為珍貴。就書(shū)藝而論,寧宗此書(shū)并非上乘之作,筆法既不精熟,結(jié)字亦嫌生硬,但閑和端雅的氣息,始終離不開(kāi)高宗以來(lái)的家風(fēng)。楊皇后的書(shū)法亦類(lèi)寧宗,但技巧更佳,其圓雅清潤(rùn)之處,更能體現(xiàn)高宗的家族傳統(tǒng)。他隨后又以吳奕寫(xiě)給伯父吳寬的尺牘冊(cè)頁(yè)為例,說(shuō)明吳奕在書(shū)法傳承上受到伯父的影響,將蘇東坡的風(fēng)格視為代表家族傳統(tǒng)的書(shū)風(fēng)。米漢雯的行書(shū)詩(shī)又是一例,無(wú)論用筆結(jié)體,以至整體俊健清邁之勢(shì),皆遠(yuǎn)接其同宗祖先米芾。莫先生指出,由于師法古人是臨池學(xué)書(shū)的不二法門(mén),故重現(xiàn)大師風(fēng)格、繼承經(jīng)典傳統(tǒng)是中國(guó)書(shū)法衍變的常規(guī)。第二部分主題是“書(shū)法與人品”,莫先生強(qiáng)調(diào)書(shū)跡的流傳并非只取決于筆墨的工拙,更在于書(shū)家人格的高低。他以王寵傳世的一紙借券為例,說(shuō)明這一尺幅短小的尋常之物,只是王寵向友人袁褒借銀五十兩的憑據(jù),雖無(wú)文辭之美,但由明至清流傳教百年,經(jīng)歷數(shù)名藏家之手,幾番裝池,題詠書(shū)跋者數(shù)十人,如此為世所珍,重要原因在于王寵為人稱(chēng)許的形象,正說(shuō)明書(shū)以人重的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第三部分主題是“書(shū)法與生活”。他列舉了以下例子:婁堅(jiān)的《草書(shū)自書(shū)詩(shī)》為煩悶中書(shū)以自?shī)剩惶祈樦摹缎袝?shū)后赤壁賦》是督師海上兵過(guò)家書(shū)與兒子的遣興之作;王文冶的《行書(shū)快雨堂偶然書(shū)》是應(yīng)友人以素冊(cè)索書(shū)而寫(xiě);而萬(wàn)經(jīng)的《隸書(shū)舒元輿牡丹賦》則是為友人宋犖的樂(lè)春園而精心書(shū)寫(xiě)。這些都反映出古人于不同情景下的作書(shū)情況。另有《武林勝集》,此卷見(jiàn)證了白埏、張楧、鄧文原、有在、仇遠(yuǎn)、鮮于摳、俞伯奇等文人于杭州以北宋盛次仲詩(shī)句“飛入園林總是春”為韻而各賦五言詩(shī)的風(fēng)雅,反映出文學(xué)唱和與書(shū)法生活不可分。
7月20日下午,浙江大學(xué)藝術(shù)與考古中心主任、教授繆哲先生作《重訪(fǎng)樓閣:關(guān)于漢畫(huà)像樓閣拜謁主題的再認(rèn)識(shí)》的演講。漢代藝術(shù)研究所稱(chēng)的“樓閣拜謁圖”,是東漢魯中南祠堂畫(huà)像最重要的主題;其建筑的性質(zhì)與主題的含義,自上世紀(jì)初以來(lái),便是學(xué)者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繆哲先生的報(bào)告分為三個(gè)部分:第一部分從形式分析的角度,論證“樓閣拜謁圖”中的建筑并不是今昕共稱(chēng)的“樓閣”,而是一前一后兩座建筑。他首先歸納了漢代可居建筑的主要類(lèi)型,即宮殿、宮署、與住宅(兼及樓),以及漢代人所賦予四者的禮儀或意識(shí)形態(tài)含義。如宮殿可分為前殿和后宮,是君權(quán)的象征;官府分為聽(tīng)事和官舍,屬于功能空間;私人住宅分為堂和內(nèi),屬于生活空間;樓是建筑的附屬性設(shè)施。前兩種建筑以性別加以分隔,后兩種無(wú)性別分隔。他繼而總結(jié)了漢代藝術(shù)中建筑表現(xiàn)的主要類(lèi)型,即平面圖型、描繪型與圖符型;以此為基礎(chǔ),他推斷“樓閣拜謁”之建筑屬于圖符類(lèi)型,其刻畫(huà)的建筑為前后殿/室,而非畫(huà)面呈現(xiàn)的樓閣。繆先生認(rèn)為昕謂“樓閣”,應(yīng)是由闕、堂(前殿或聽(tīng)事)、與內(nèi)(后宮或官舍)等標(biāo)志性建筑所構(gòu)成的一意義圖符。第二部分把“樓閣拜謁”主題復(fù)原于魯中南的兩組代表性祠堂——孝堂山祠與武氏祠,通過(guò)對(duì)同祠其他畫(huà)像主題的分析,論證兩組祠堂中與“樓閣拜謁”并出的其他主題所表達(dá)的,都是漢代——尤其東漢——皇家的意識(shí)形態(tài),或漢帝國(guó)的意識(shí)形態(tài)。譬如孝堂山祠中“大王鹵簿”主題通過(guò)大王鑾駕一黃門(mén)鼓車(chē)一執(zhí)節(jié)奉引車(chē)等圖像來(lái)表現(xiàn);“大王有師”主題通過(guò)孔子師老子圖像來(lái)表現(xiàn),對(duì)應(yīng)于漢代經(jīng)學(xué)背景中的“王者有師”;“大王有輔”主題通過(guò)周公輔成王圖像來(lái)表現(xiàn),對(duì)應(yīng)于漢代經(jīng)學(xué)背景中的“帝王有輔”。以此證明“樓閣拜謁”主題所表達(dá)的,也同為漢帝國(guó)的藝術(shù)形態(tài)。在這個(gè)脈絡(luò)下,最后討論“樓閣”一側(cè)的大樹(shù)圖,結(jié)論是此圖最初或是紀(jì)念“光武中興”的。第三部分探討了此類(lèi)主題是如何從漢帝國(guó)的首都洛陽(yáng)流傳于魯中南民間的。他提示了以下幾點(diǎn):1東漢諸侯王70%以上分封于魯中南及附近;2其中魯王強(qiáng)(靈光殿主人)生死皆行天子禮;3東平王蒼被明帝、章帝稱(chēng)為周公,死行天子禮;4魯中南民間的畫(huà)像石主題,經(jīng)此可上溯洛陽(yáng)的漢帝國(guó)藝術(shù)。樓閣拜謁即其一。
7月20日上午是互動(dòng)環(huán)節(jié),導(dǎo)師們和學(xué)員就書(shū)法史研究展開(kāi)對(duì)話(huà),對(duì)學(xué)員的提問(wèn)一一給予解答。中國(guó)書(shū)協(xié)培訓(xùn)中心教授、蘇州市書(shū)協(xié)顧問(wèn)葛鴻楨先生主持了本次講壇。廣州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祁小春先生、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教授薛龍春先生也參加了講壇并與學(xué)員交流。作為本次論壇的學(xué)術(shù)主持,蘇州大學(xué)研究館員、博士生導(dǎo)師華人德先生在每位導(dǎo)師講座以后,都會(huì)講一些他的體會(huì),言簡(jiǎn)意賅,發(fā)人深思。在導(dǎo)師與學(xué)員互動(dòng)環(huán)節(jié)結(jié)束之后,依照慣例,他對(duì)本次論壇進(jìn)行了學(xué)術(shù)總結(jié)。他在總結(jié)中說(shuō),“本次講壇繼續(xù)堅(jiān)持平等、務(wù)實(shí)、陽(yáng)光的會(huì)風(fēng),對(duì)所有邀請(qǐng)的嘉賓一視同仁,不講排場(chǎng)。這次講課的地方環(huán)境很安靜,很幽雅,就像古代的書(shū)院一樣,大家同吃同在一起講授,一起交流,也是我們所夢(mèng)想的古代書(shū)院的授課狀態(tài)。這次有兩位導(dǎo)師,他們經(jīng)過(guò)自己展覽的實(shí)踐得出來(lái)研究的成果和新的體會(huì),對(duì)同學(xué)們啟發(fā)很大。現(xiàn)在我們有些同志比不上海外的(包括臺(tái)灣)的同行,我們的展覽只為作者服務(wù)而不是為觀眾服務(wù)。今后在全國(guó)書(shū)法展覽的時(shí)候應(yīng)該做些牌子說(shuō)明作者創(chuàng)作的心態(tài)和狀況,這方面的工作像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和香港中文大學(xué),做得非常仔細(xì),我們要把這套方法引進(jìn)內(nèi)地。繆哲老師的講座內(nèi)容非常新穎,開(kāi)闊了我們的視野。白謙慎老師和黃悖老師雖多次為大家講授,但每次都是講授他們不同的研究成果,非常專(zhuān)業(yè),視角獨(dú)到。蘇州這個(gè)講壇影響很大,其高端的學(xué)術(shù)追求、開(kāi)放的學(xué)術(shù)視野與自由的研討氣氛贏得了海內(nèi)外書(shū)學(xué)界與文化界的一致好評(píng),其培養(yǎng)當(dāng)代書(shū)法研究人才的新模式得到了書(shū)法界的普遍贊譽(yù)。中國(guó)書(shū)協(xié)、江蘇省文聯(lián)、蘇州市文聯(lián)、吳江市政府等單位以及劉恒、白謙慎等領(lǐng)導(dǎo)與專(zhuān)家的熱情鼓勵(lì)與大力支持下,講壇取得了圓滿(mǎn)的成功。我們力求把講壇辦成當(dāng)前書(shū)法藝術(shù)理論研究和學(xué)術(shù)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載體,發(fā)揮它對(duì)于培養(yǎng)書(shū)學(xué)研究后備人才、推動(dòng)書(shū)法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重大作用,并且希望能夠持續(xù)地辦下去,使其真正成為中國(guó)書(shū)法的學(xué)術(shù)品牌。”
(易齋、谷安、陳道義、逢成華、張恨無(wú)、毛秋瑾、王學(xué)雷、盧月龍、何鵬、朱駿益參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