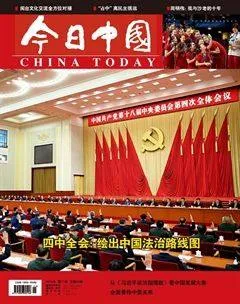中美關系新契機
朱鋒
2014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北京舉行。這不僅是一年一度亞太經合組織的盛事,也是亞太區域政治中最搏人眼球的熱點。作為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中規模最為龐大和出席規格最高的首腦會議,從1993年第一屆APEC西雅圖峰會舉行以來,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一直都是促進成員國政治溝通、推進區域合作進程深入的重要場合。2014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格外引人注目,原因之一就是此次會議能否為目前緊張的中美關系、中日關系帶來積極影響,并對未來幾年的亞太區域局勢走向產生大的影響。
“習奧會”:從桑尼藍(Sunnyland)到北京
2013年6月7-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桑尼藍舉行非正式首腦會議。雙方輕車簡從,在兩天的時間內花了8個小時對兩國關系、區域和全球政治議題舉行了深入、坦率地交流和對話,達成了增進合作、相互諒解和彼此密切政策溝通與協調的“桑尼藍首腦共識”。習近平主席在對話中,向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要求在兩國關系中實現“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奧巴馬總統呼應習主席的提議,強調美國愿意與中國一起建設兩國間的“新型合作模式”。
加州會談之后,中美關系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積極進展,例如,雙方在朝鮮核問題上的合作確實在不斷加強,但中美關系整體上卻遇到了更大的挑戰。2013年11月23日,中國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這是中國依據國際慣例加強國土防御和國家安全預警的重要舉措。在東亞主要國家中,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的時間最晚、有關防空識別區措施也比較穩健。然而,對美國來說,由于從二戰以后一直都享有在西太平洋的空中和海上霸權,習慣于美國方式的“自由航行”,面對來自中國的防空識別區決定反應過激,認為這是中國有意在西太平洋挑戰美國的空域主導地位。美國五角大樓甚至恫言,這是中國“旨在改變亞太安全秩序現狀”的挑釁行動。11月26日,美國從本土派出兩架B52戰略轟炸機長途疾進,進入東海防空識別區以示抗議。美國還聯合日本,拒絕承認中國宣布設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
進入2014年以來,中美緊張關系繼續升溫。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拉塞爾在2月5日的國會聽證會上,公開指責中國的南海政策。他不僅向中國施壓“九段線”問題,更是強調中國在南海的一系列所謂“單邊行動”造成了南海局勢動蕩。在南海領土主權爭議問題上,美國作為“域外大國”,將自己的政策從“不進入、不表態”轉向了“全面介入和干預”的政策,支持和縱容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東盟國家,想要達到牽制中國的正當、合法的南海維權行動,阻止中國按照“歷史權利”和國際海洋法享有南海島嶼及相關海域主權權利的目的。南海爭議成為了中美對立的一個新的爆發點。
在東海問題上,奧巴馬政府依據日美同盟關系所界定的東盟責任,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在釣魚島領土和主權爭議問題上力挺日本。2014年4月23-25日奧巴馬總統在訪問日本期間,公開承諾美日同盟將幫助日本協防釣魚島,美日軍事同盟協調不斷增強。4月28日,奧巴馬總統在訪問菲律賓期間,在馬尼拉簽署了《美菲十年防務協定》,將在菲律賓開設新的軍事基地,擴大在菲律賓的美軍軍事存在。奧巴馬2014年4月的東亞四國之行,“繞著中國轉”。美國端出的一系列新的軍事姿態和簽署的新的防務協定,在繼續推進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之余,也努力在亞太區域外交中對中國擺出“狠勁”。其對華“戰略警告”的含義十分明顯。
2014年6月30日舉行的香格里拉亞洲防務對話中,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不顧外交禮儀,在講話中用了冗長的篇幅公開指責中國,和應邀發表主旨演講的日本首相“一唱一和”。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參加香格里拉對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不得不奮起反駁。2014年香格里拉亞洲防務對話本來應該就亞太海洋安全議題、區域防務合作問題,以及應對再度猖獗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勢力問題進行坦誠交流,卻最終變成了中、美、日大打“口水仗”的對話。
除了在一系列區域安全事務問題上打壓中國之外,美國還在新疆、西藏、香港等一系列中國內政問題上對華說三道四、指手劃腳。在經貿議題上,美國也不斷攻擊中國的經濟調控政策,指責中國有意在“惡化”中國國內的投資環境。2014年8月初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雖然中美之間取得了30多項共識,但會晤的氣氛和融洽程度顯然是近年來最差的一次。習近平主席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克里時語重心長地表示,希望美國朋友在處理美中關系時能夠“向前看”。
中美關系持續緊張“事出有因”
2013年11月以來中美關系的持續緊張,有著諸多現實的因素。首先,奧巴馬政府面對此起彼伏的國際安全熱點問題的襲擾,唯恐在中國政策上表現軟弱。因此,繼續推行2011年以來美國既定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鎖定中國作為美國全球戰略轉型的“頭號目標”這一近年來美國亞太戰略的重大調整,是最主要的原因。
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說到底,就是要依據中國崛起的實力現實來調整美國全球的戰略部署和戰略重點,提升亞太政策和中國政策中應對中國作為最主要的“競爭者”的緊迫性,避免美國的全球戰略存在繼續受到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拖累、確保美國可以更有效、更及時地“盯防、牽制”中國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核心不僅是在亞太地區范圍內加強同盟體系、擴大防務合作和戰略伙伴關系,更重要的是,美國要在外交和戰略上利用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復雜的地區安全影響,支持和鼓勵在海洋領土爭議、安全關注等問題上和中國有競爭性的國家,強勢提升美國制衡中國的外交和軍事力度,以便實現既要有能力在軍事上威懾中國,又要獲得亞太地區內國家的支持,從而削弱中國的外交和政治影響。這一戰略的核心,當然是要確保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地位。
和2011年以前相比,目前的美國對華政策已經有了三個方面的顯著調整:一是在心理上,唯恐中國會認定“美國衰落”,因而將美國的軟弱無力視為是中國實行戰略擴張的機會。因此,美國需要將中國正常、合理的維權行動一概視為是中國“企圖在謀求利用美國力量收縮轉而進行中國式的戰略擴張”。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維權行動,在美國眼中,都成為中國想要“改變現狀”的行動。二是在心態上,美國認為中國越來越咄咄逼人,越來越不把美國放在“眼里”。美國需要通過力量、意志和決心,讓中國承認和接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避免中國戰略影響力的擴大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政治和戰略利益。為此,美國國內的中國政策討論,出現了對華“警惕性越來越高”、分析的視野和角度“越來越不友好”的變化。三是隨著中國的崛起,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確實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變化。如何衡量彼此的能力、意圖和政策目標問題上,中美關系需要隨著兩國力量對比的新變化而進行新的調試和磨合。例如,美國在對中國海上和空中抵近偵查的問題上,很典型地反應了美國對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不斷上升的戰略焦慮。近年來,美國對華抵近偵查一年達到500次以上,這不僅是一種赤裸裸的對中國國家軍事機密的頻繁窺視,也反應了美國對華軍事敵意的顯著上升。中國適時地對美國抵近偵查的空中攔截,是中國軍方捍衛國防尊嚴的必要舉措。然而,美方的抵近偵查和中國的空中攔截必然加劇中美關系的緊張,也推升了中美發生事故性軍事沖突的可能性。
讓兩國領袖坐下來好好談
不管有多少爭議,中美兩國關系都是21世紀全球政治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也注定是重要而又復雜的關系。冷戰結束20多年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中美關系需要管控分歧、穩定局面,就需要高層政治接觸和對話,需要兩國領導人之間坦誠、務實和建設性的交流。一年一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事實上已經證明是中美兩國領導人直接對話的重要機制。1993年西雅圖APEC首腦峰會中,當時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首腦峰會,就對中美關系走出1989年之后的政治僵局發揮了重要作用。2013年的APEC印尼峰會,奧巴馬總統因為國內財政預算僵局而無法成行,中美之間也失去了首腦會晤的良機。
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習近平和奧巴馬再度舉行會晤。我們殷切地希望,中美兩國領導人能夠繼續談下去。正如習主席曾說過的那樣,“太平洋足夠寬廣,裝得下中美兩個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