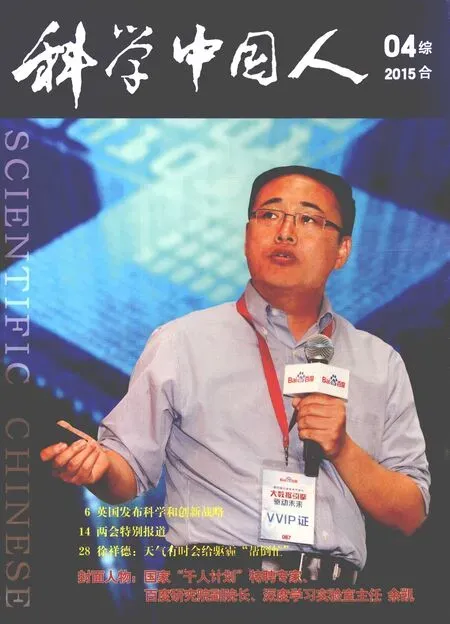基于土地利用/覆蓋變化的黃河源頭區土地管理研究
祁佳麗
(青海民族大學,青海西寧810007)
1 引言
在我國,土地利用/土地覆蓋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兩類地區,即“熱點地區”和“生態脆弱、敏感區”。“生態脆弱、敏感區”一般是指對外界干擾和環境變化反應敏感,自身生態系統組成結構穩定性較差,抵抗外在干擾和維持自身穩定的能力較弱,易于發生生態退化且自我修復能力較弱、恢復時間較長的區域。“生態脆弱、敏感區”主要集中在生態脆弱、物種多樣、生態系統易變、自然資源相對較豐富的重點生態保護和治理地區,例如國家自然保護區和省級自然保護區。
2 研究區域、技術路線及指標體系
2.1研究區域概況
黃河源頭區行政區劃涉及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瑪多縣、玉樹藏族自治州的曲麻萊縣和稱多縣。該區域是“中華母親河”黃河的發源地,河流、湖泊眾多,雪山連綿,是黃河水資源的主要來源地之一,被稱為黃河的“水塔”。黃河發源于青海省巴顏喀拉山的約古宗列盆地,學術界較集中和權威的認識是,黃河源頭區系指位于青海省瑪多縣多石峽以上的黃河河源集水范圍,大致介于N33°56′~35°51′,E95°55′~98°40′。地勢西高東低,海拔在4200米至5200米之間。該區域內湖泊眾多,基本為湖盆、低山以及寬谷為主的地貌組合。植被覆蓋以高寒草甸和高山草原為主,局部地區以灘地和沼澤為主。草地是黃河源頭區最主要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蓋類型,而人工用地面積較少。土壤基本是以高山草甸土為主,小范圍地區是以沼澤地為主。
2.2技術路線
主要技術流程為:①影像準備,包括遙感影像的收集、預處理、圖像鑲嵌、融合等;②野外調查;③建立判讀標志庫;④進行人機交互目視屏幕解譯;⑤進行解譯結果的修整驗證;⑥計算土地利用轉移矩陣;⑦分析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狀況。(見圖1)
2.3土地利用/土地覆蓋分類體系
根據全國生態遙感監測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分類體系,確定了黃河源頭區土地分類與土地覆蓋專題的分類系統。主要根據土地的自然生態、利用屬性和覆蓋特征,共分為5個土地利用/土地覆蓋類型。
黃河源頭區遙感監測土地利用/土地覆蓋分類體系及含義(見附表1)

附表1黃河源頭區遙感監測土地利用/土地覆蓋分類體系及含義

4 5 6水域城鄉、工礦、居民用地未利用土地指天然陸地水域和水利設施用地指城鄉居民點及縣鎮以外的工礦、交通等用地目前還未利用的土地、包括難利用的土地
3 研究結果
3.1土地利用/覆蓋現狀
通過遙感監測,得到黃河源頭區土地利用/土地覆蓋現狀數據,結果表明:2011年林地面積占黃河源頭區總面積的2.01%;草地面積占黃河源頭區總面積的75.24%;水域面積占黃河源頭區總面積的4.33%;人工用地面積占黃河源頭區總面積的0.04%;未利用土地面積占黃河源頭區總面積的18.38%,其中沙地面積占未利用土地總面積的1.90%;無耕地用地。
草地是黃河源頭區最主要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蓋類型,占黃河源頭區總面積的75.24%,其中高覆蓋度草地占草地總面積的47.14%;中覆蓋度草地占草地總面積的20.13%;低覆蓋度草地占草地總面積的32.73%。2011年黃河源頭區土地利用/土地覆蓋比例見圖2、2011年黃河源頭區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見圖3)
3.2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計算
根據史培軍等的研究,在ArcGIS軟件的支持下,經過2008年、2011年兩年矢量層的融合、疊置分析,計算得到黃河源頭區土地利用轉換矩陣。
從表中可看出,林地主要轉變為草地、未利用土地;草地轉變為未利用土地、林地、水域;水域轉變為草地和未利用地;人工用地主要轉變為水域、草地;未利用地主要轉變為草地。2008~2011年黃河源頭區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見表2)

表2 2008~2011年黃河源頭區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4 進一步優化土地管理對策
4.1設置獨立縣級土地管理機構
黃河源頭區的瑪多縣目前在機構設置方面存在問題,即瑪多縣國土、環保及水利共3個機構還未分家。雖然瑪多縣地廣人稀,機構合并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整合管理資源,但負責專門管理土地資源的機構的缺失,造成土地管理的不健全。從公共管理學理論來說,無法達到“權責一致”。
設置獨立的瑪多縣土地管理據,有利于發揮管理人員的作用,提高管理功效,實現土地管理的目標。在今后工作中,應致力于設置瑪多縣土地管理機構,完善其內部各個組織管理部門,招錄專業土地管理人員進行該區域土地管理工作。
4.2完善土地監管責任制度
目前黃河源頭區各縣土地管理機構的職責較多,但在管理職能的運作中,存在較多問題,包括工作計劃編制、組織工作開展、控制作用等方面都存在問題。應該進一步明確縣級土地監管責任,各縣級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林業部門、環保部門、交通公路部門等都要做好自身監管工作,共同推進土地科學管理。
4.3提高縣級土地管理人員素質
提高土地管理人員素質,一般是提高其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建議在每年的招錄考試中,嚴格制定錄用條件。雖然瑪多縣、稱多縣、曲麻萊縣土地管理人員每年都是經過省直單位招考,經過筆試、面試等環節,選拔進入單位工作,但整體業務水平還是欠佳,建議進一步加入專業考試,選拔一批技術過硬、水平較強的干部從事土地管理工作。另外就是加強在崗人員的再培養。不僅從技術層面出發,還要考慮其思想道德認識的提高。通過省外或省內技術培訓、業務
4.4加強土地管理,科學制定管理措施
科學管理,不僅是指土地資源的保護,還要把閑置的土地資源利用起來,要充分考慮藏族傳統生計對土地管理起到的積極作用,進而制定與其相契合的土地管理機制。針對一些惡性的人為干擾活動,例如,盜獵、無節制的采礦、盜挖珍貴藥材等行為,必須嚴厲懲處。為了對犯罪行為的懲處更為準確和公正,需要賦予牧民監督權和控告權。如此一來,已有的保護法規才能真正付諸實用。通過政策扶持引導后續產業的發展,這一舉措的意義不僅表現在牧民退牧還草后的生計問題,還體現在生態移民方面。
[1]HJ/T 192-2006,生態環境狀況評價技術規范(試行)[S].
[2]葉國文.土地政策的政治邏輯[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吳健平.區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蓋遙感調查[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4]黃杏元,馬勁松,湯勤.地理信息系統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卓瑪措.青海地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6]李龍浩.土地問題的制度分析:以政府行為為研究視角[M].北京:地質出版社,2007.
[7]于興修,楊桂山.中國土地管理現狀與問題[J].地理科學進展,2002,21(1):51-57.
[8]王廣華,張麗君.信息技術在土地管理中的應用[J].國土資源情報,2006,25(6):94-101.
[9]張金屯,邱揚,鄭鳳英.景觀格局的數量研究方法[J].山地學報,2000,18(4):346-352.
[10]史培軍,陳晉,潘耀忠.深圳市土地利用變化機制分析[J].地理學報,2000,55(2):151-160.
[11]顧朝林.北京市土地利用/覆蓋變化機制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1999,14(4):307-312.
[12]陳國慧.基于GIS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2006
[13]黃鵬.我國土地利用和管理形勢政策分析研究[D].南京:河海大學,2007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