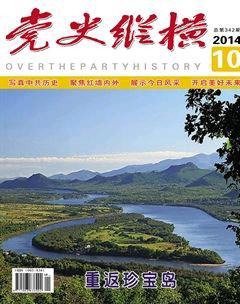突如其來的張國燾批判
孫果達
西安事變余波未消,中共中央突然開始了對張國燾的批判。
中共中央的警惕
要理解對張國燾的批判,首先就必須研究當時中共中央究竟有沒有已經意識到蘇聯在西路軍與西安事變中的叵測心懷。答案是肯定的,事實證據如下:
其一,中共中央到陜北后派鄧發出使莫斯科所做的匯報,以及最初致共產國際的電報中者陂口實匯報了情況與計劃,尤其還匯報了張學良要求入黨的機密,可見當時毫無戒心。但當共產國際奇怪地拒絕張學良入黨時,中共中央的疑竇顯然已起,證據就是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給斯大林的信中竟然對中共中央與張學良自8月中旬后迅速發展的緊密關系毫無所知,表明中共中央當時已經有所警覺而完全中止了有關的匯報。
其二,11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含蓄地指責對紅軍的軍援計劃之荒唐時,疑竇顯然已經加劇。
其三,5天后,即11月13日,中共中央突然決定南下并同日通知共產國際:“現擬第一步從慶陽、鎮原、合水南下,占領平涼、涇川、長武、分州、正寧、寧縣等戰略機動地區。”電報顯示紅軍似乎即將從慶陽一線大規模南下,實際上紅軍幾乎全部主力隱蔽在慶陽等地區以北的必經之路山城堡四周,靜候胡宗南部是否真會如期從背后襲來。中共中央顯然要檢驗南下信息是否已經泄漏。
其四,兩天后,即11月15日,蔣介石果真開始直接指揮胡宗南所部向紅軍背后急進。20日,毛澤東連續急電彭德懷:“蔣介石令胡軍向定邊、鹽池急進。”
其五,21日,在蔣介石催促下,孤軍深入的胡宗南部一個多旅進入山城堡,當即遭到紅軍的圍殲。“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線后撤,國民黨軍對陜甘寧根據地的進攻,實際被停止。”
驗證的結果雖然令人震驚,但當時要確認究竟何處泄密卻絕非易事。不過,中共中央就此有了必要的精神準備。這就合理解釋了為何西安事變一發生毛澤東立刻就能毫不猶豫地公開采取與斯大林相左的立場,并得到周恩來的全力支持。但是,當西安事變后中共中央面臨與蔣介石的新一輪談判時,又必須得到蘇聯的支持。因此,不僅讓蘇聯,還必須讓蔣介石也以為中共中央對其幕后交易一無所知就成為當務之急。
批判張國燾的突如其來
1937年年初,中共中央突然開始批判張國燾。程中原所著的《張聞天傳》說:“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進駐延安后,即在中央內部開始對張國燾錯誤的批判。張國燾不得不在2月6日寫了檢討《從現在來看過去》。”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暗濤洶涌,西路軍又岌岌可危之際突然發動全黨全軍對張國燾的批判,看似忙中添亂、自亂陣腳,實是迫不得已、刻不容緩。原因很簡單,追究西路軍失敗責任引起的激烈爭論已經涉及蘇聯的軍援。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當時延安有種說法:“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準,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還認為西路軍“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于人,轉移目標,將對外轉到對內。”這種把莫斯科軍援、西路軍與“蔣氏圍剿”相聯系的爭論如進一步觸及西安事變,其后果可想而知。因為蘇聯的軍援說是幫助紅軍對抗蔣介石,但在西安事變中卻全力支持蔣介石。只要簡單地把兩者聯系起來,蘇聯態度的孰真孰假就一目了然,西路軍的遭遇與“誘發蔣氏圍剿”的原因也就可能水落石出。這種局面一旦出現,必將不可避免地出現災難性的連鎖反應,其后果之嚴重將難以估量。因此,中共中央必須先發制人以控制責任追究的導向,立即鎖定西路軍失敗的責任者,讓蘇聯迅速淡出視野,張國燾顯然是最合適的人選。
2月27日,凱豐已經寫就了包含14部分內容的大批判文章:“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洋洋數萬言其實只有一句特別關鍵:“在二、四方面軍到達甘南時,當時的西北局決定北上會合一方面軍,國燾也可以不執行西北局的決定,私自改變為向西開進。”這段文字應該是對張國燾必須為西路軍失敗負責的含蓄表達。用張國燾的話來說就是“西路軍的失敗,他們更認為是證據確鑿的證明。”
中共中央對張國燾批判的突然一是違背原先的決定。中共中央對張國燾的態度在1936年夏致王明的“第一號電報”已經明確。電報概括了張國燾另立中央等錯誤,也指出“張國燾同志開始改變自己的立場”,最后表示“現在我們正在竭力爭取在堅持原則政策的基礎上同他和解,以便團結成一個整體,爭取成立西北國防政府,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更高的階段。”更要指出的是,就在1936年12月1日,也就是對張國燾展開大批判的前一個月,毛澤東還專門批評彭德懷對張國燾的態度不夠尊重:“兩星期前批評國燾一電,昨日整頓紀律一電,原則上完全正確,但在措詞上有一二句頗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請留意及之。”當時西路軍已經危急,但電報中的“國燾”稱謂依然頗有親切之意,尤其彭德懷的電報僅僅一二句“措詞”有些“刺目”,毛澤東都認為“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要求彭德懷日后“留意”。毛澤東的這一態度與中共中央希望團結張國燾的決定完全一致。因此,如非事出無奈,中共中央怎么可能在迫切需要全黨全軍團結一致時,突然形成違背決定又不顧事實共識的大舉批判張國燾?
二是共產國際反對。在批判張國燾前夕,中共中央特地向共產國際發出第64號電報進行請示,并且要求在一天內答復,卻遭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反對。季米特洛夫在收到中共中央1936年6月26目的“第一號電報”后,曾于7月初向斯大林請示了三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關于中共中央書記處多數成員與其個別成員張國燾之間的分歧”。季米特洛夫顯然認為中共中央與張國燾的矛盾只是“分歧”,因此在得知要對張國燾展開批判時,立即于3月22目,即批判張國燾的延安會議召開的前一天回電:“對你們第64號電答復如下:我們沒有十分準確的情報能夠使我們對張國燾問題作出明確的表態。我們不相信,為了黨的利益必須像你們所做的那樣來審查西路軍的地位問題。(“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于莫斯科,絕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一書的原注:指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西路軍,中共中央企圖將其失敗的責任加在張國燾頭上。)我們認為,無論如何現在不宜就張國燾以前的錯誤作出專門決議并就此展開討論。要千方百計避免激化黨內關系和派別斗爭,時局要求團結黨和紅軍的一切力量來對付敵人,并有必要準備齊心協力地反對無論來自何方的對紅軍的打擊。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應該客觀加以研究,吸取相應的教訓,并采取適當的措施來幫助和保存這支部隊的力量。請將這一點告知全體政治局委員。建議今后不要再讓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實際上面對已成既成事實的這類問題,這一點從你們要求在一天內作出答復就可以看出來。”這份電報起碼說明了三個問題:一是“第64號”電報正式告知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已經形成共識:張國燾必須對西路軍的失敗負責;二是共產國際反對立即“就張國燾以前的錯誤”下結論,認為西路軍的失敗不該由張國燾負責;三是共產國際反對中共中央在關鍵時刻“激化黨內關系和派別斗爭”,并且先斬后奏。共產國際當然不會意識到,批判張國燾將對中共中央保持、發展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關系起何等重要的作用。
三是速戰速決。中共中央沒有理會共產國際3月22目的電報,于3月23日至3月31日在延安舉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決議正式確認張國燾必須對西路軍的失敗負責:“西路軍向甘北前進和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張國燾的“草原密電”問題。應該說,毛澤東所言非虛,但與西路軍失敗的責任無關,此時舊事重提,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方便給張國燾定罪,因為沒有猛料,顯然就難以服眾。決議最后強調:“中央更號召全黨同志,同張國燾路線做堅決斗爭,在這一斗爭中教育全黨同志,如何在各種環境下堅決不動搖的為布爾扎維克的路線而奮斗到底。只有共產國際與中央路線的勝利,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徹底的最后的勝利。”決議把張國燾與西路軍的失敗直接掛上了鉤,同時突出表明了中共中央對蘇聯與共產國際“堅決不動搖”的信任。
當時西路軍尚在苦戰。據《毛澤東年譜》記載:“3月27日,為解救西路軍危局,同張聞天、秦邦憲、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西路軍情況萬分緊張,他們東進西進都成不可能,有被消滅危險。”西路軍尚未最后失敗,失敗的責任者卻必須確定,因為與此同時,周恩來到杭州開始正式與蔣介石直接會談。這一相呼應的時間節點應該不是巧合。
中共中央隨后在全黨全軍展開對張國燾的大批判,專門印發了“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其中有一章的標題是“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宣告最后的破產”,對西路軍的失敗做了這樣的總結:“全國紅軍會合后國燾同志私自調動部隊渡過黃河,向甘西退卻,同樣說明了國燾同志直至到達中央前還是沒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國革命的損失,而同時也證明與宣告張國燾路線的最后破產。”
決議為西路軍失敗的責任一錘定音,隨后的大討論不僅杜絕了黨內的公開爭論,也杜絕了對蘇聯軍援可能產生的懷疑。同時,決議與大討論不僅體現了對蘇聯與共產國際的信任與擁護,以利于修復西安事變中與蘇聯分歧公開的裂痕,更體現了中共中央似乎絲毫沒有察覺到蘇聯版的“慕尼黑”。
四是中央領導層的態度各異。張國燾是這樣回憶延安會議的:“這個會議當時雖是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名義召開,但實際上多數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任弼時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羅瑞卿、莫文驊等主要當事人都沒有參加,參加會議的二十多人,多是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張國燾同時還評價了不少領導人:“西路軍失敗的原因雖然沒有定論,但毛澤東、張聞天都利用這一失敗事件,發動反張國燾的斗爭。”“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周恩來從未斗爭過我,因此我們見面照舊談天說地,凱豐這時似也不完全同意毛澤東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談天,似乎要沖淡一下前此對我的不客氣。”“林伯渠當時采持平態度”,董必武“事實上緩和了這個斗爭”。“林彪也擺出他那校長的姿態,表現置身事外的樣子,不公開卷入斗爭漩渦。其他中共要人們,則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大約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澤東率領著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來訪我,我們相見握手問候。他們滿面笑容,贊揚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件難決的事特來請教。我也答禮甚恭,表示有勞各位大駕。”張國燾的評價不論是否客觀,卻也反映了中央領導層對非常時期還展開黨內斗爭多少有些不解:要張國燾對西路軍的失敗負責畢竟有失公允;要清算張國燾以往的錯誤又何必只爭朝夕。確實,當時中共領導層不可能理解必須迅速為西路軍失敗定性的重大意義,真正了解內情的只能是極少數幾個核心。
批判張國燾的擔綱者
張聞天罕見地作為黨內斗爭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人,尤其要把西路軍失敗的不實之罪強加給張國燾確實令人難以理解。如此反常的歷史事實,其中必有隱情。
張聞天是延安會議的主持者與主講者,《張聞天傳》說:“在會上,張聞天從理論上比較系統地批判了張國燾反黨反中央的種種謬論和他的錯誤路線的退卻和軍閥主義的實質。毛澤東、凱豐、朱德、賀龍等也都在會上作了深刻的批判。”張聞天的長篇總結發言對張國燾路線做了概括:“第一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是軍閥土匪主義,第三是反黨反中央的派別主義。”還提出了“處理張國燾錯誤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如前所述,此時周恩來正在杭州與蔣介石開始會談。
1937年11月18日至24日,延安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大會,繼續進行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張聞天作了長篇總結:“他運用唯物辯證法和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深刻地駁斥了張國燾為自己錯誤辯護的種種謬論和遁詞。指出:退卻路線、軍閥主義與反黨反中央,是國燾路線的三位一體。”此時,臨行時見過斯大林的王明正在從莫斯科回延安的途中,而毛澤東數天前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特別強調“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張聞天傳》說:“張聞天于1938年6月7日寫的《讀了‘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之后》是分析、批判最為深刻有力的一篇。”張聞天在這篇上萬字的大文章中認為:“他的錯誤路線有三個組成部分”:“是他的腐朽的機會主義”;“是他的自私自利的極端個人主義”;“是他的口是心非,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兩面三刀的惡根性”。
以上事實表明,當時張聞天作為黨的總書記,自始至終而且全力以赴領導了對張國燾的批判。張國燾在回憶中也往往把張聞天與毛澤東相提并論。令人奇怪的是,盡管批判張國燾的起因就是為了追究他對西路軍失敗的責任,但無論是張聞天還是毛澤東,在批判張國燾時都對此只字不提。這一事實正好證明,張聞天完全知道急于批判張國燾的原因其實與西路軍的失敗根本無關。在王明到延安前后,張聞天更加強了對張國燾批判的領導,以免王明心中生疑。王明積極參與了西路軍與西安事變,他突然回國難保沒有秘密考察的使命,張聞天不得不高度謹慎與警惕。或許,這就是當時毛澤東盡管在西安事變中與張聞天的分歧重大而依然稱其為“明君”的真正原因,以含蓄地贊揚張聞天作為黨的總書記在關鍵時刻立場堅定責無旁貸,能夠洞察大局深明大義。
應該說,張國燾另立中央的錯誤是客觀存在的。但理解了當時不得不以西路軍失敗的責任為由開展對張國燾的批判,也就理解了此后中共中央為何對張國燾的出走持出人意料的寬容態度。據歷史當事人在《黨的文獻》上撰文回憶:1938年“4月17日晚11點前后,胡宗南第八戰區司令部的一伙特務開著兩輛汽車停在張住的太平洋飯店樓下,幾個人沖到了二樓。這時負責跟著張國燾的只有我一人,吳志堅同志有事出去了。幾個便衣特務進房來二話沒說把我死死抱住,其他幾個特務搶走了張國燾。我一面掙脫一面喊道:‘你們要干什么?為什么搶走我們的張副主席,我要向你們的上面去抗議。有一個家伙歪著腦袋得意洋洋地說:‘上面,這就是受上面的指令干的。然后特務們把張國燾接上汽車后吹了聲口哨,從江漢關輪渡過江到武昌去了。”周恩來說:“我們要盡量爭取他,他若是不肯晦改,不愿回頭,你就是用繩子捆住他,他也不會跟著我們走。”“4月下旬,張的老婆楊子烈及一歲多的男孩從延安被送到漢口,按組織上的指示,我將他們送到了張國燾那里。”
當時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團結一致嚴肅嚴厲追究張國燾對西路軍的責任,也許使得蘇聯,當然包括蔣介石不得不信,因此松了口氣,也放下了心,不僅使得國共和談能夠順利進行,更使得中共中央能夠繼續保持與蘇聯極其重要的雙邊關系。
對張國燾決議的形成,標志著歷史從蘇聯聯蔣政策在中國引起的西路軍、西安事變等連鎖反應告一段落。對張國燾批判的本身,表明中共中央已經意識到了蘇聯這柄雙刃劍,并由此開始高度保持不露聲色又心領神會的警惕。毛澤東在此歷史的驚濤駭浪中令人心悅誠服的政治智慧和膽略勇氣,也為其隨后真正成為全黨全軍的領導核心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