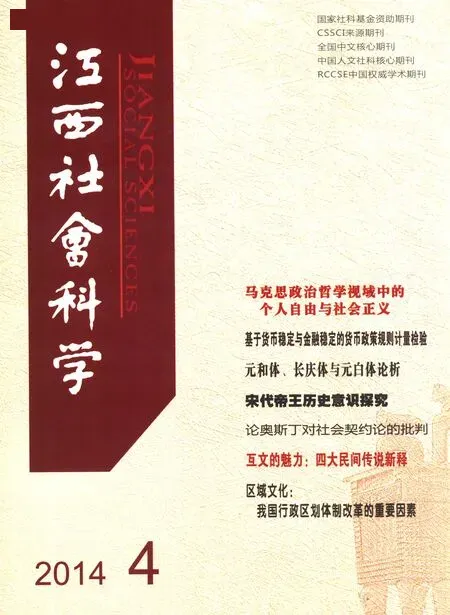晚清邊村社會秩序構建中的甲頭制度——以土默特地區為例
■許慧君 喬 鵬
晚清時期山陜等地的破產農民、軍隊叛卒、內地手工業者,不愿繼續在內地生活,很多人選擇了邊疆地區。土默特地處中國北部邊疆,經歷了三次移民高潮,“第一個高峰在康熙到乾隆時期,這一高峰持續時間較長;第二個高峰發生在咸豐時期,這一個高峰持續時間較短,第三個高峰期發生在光緒至民國初年”[1],所以形成了一個邊村社會。
所謂“邊村”,“邊”指邊疆、邊陲。但“邊”也存在由外向內轉換的問題,即從“邊外”到“邊內”。清朝之前,這里都屬于邊外地區,從清朝開始,土默特雖屬邊疆,卻已開始內地化。所謂“村”,為定居聚落的代表。從明朝時的板升,到清朝的村社,都是漢人移民進入帶來的產物。此外,“村”還代表著與聚落相關的一整套村社組織,它不僅存在于內地民人之中,而且逐漸于邊陲中發展起來。從“邊”到“村”的過程,是農業逐步取代牧業的過程,也是“邊村社會”的形成過程。本文將研究范圍限定為整個土默特地區的鄉村,希望可以分析土默特地區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社會的形成脈絡和社會秩序建構。
土默特地區在移民大量進入之前,社會階級結構很簡單,主要分為蒙古貴族、平民和奴隸。移民的進入,改變了土默特原有的社會結構,在轉變過程中,由于觀念和經濟沖突而產生了種種糾紛矛盾。這些糾紛矛盾對土默特社會造成了重大沖擊,打破了土默特社會的正常秩序,土默特原有的盟旗制管理體制必須對此做出應對。
在土默特檔案館中存有大量清朝至近代關于土默特地區的檔案,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珍貴的民間糾紛案件的原始狀紙和官府判詞。各種民間力量、基層組織的身影在這些案件中若隱若現,筆者有幸對這些檔案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整理,現試圖通過土默特基層社會組織甲頭的形成及功能等的分析,探討土默特邊村社會的形成。
清代歸化城都統(后為副都統)衙門的公文檔案,相對較為完整,主要以兩種方式存在:一部分為保存于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檔案館的檔案資料,另一部分為《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巴彥塔拉盟史料集成·土默特特別旗之部》。事實上這兩部分公文都是清朝土默特都統與中央理藩院、綏遠將軍及各道廳衙門之間的往來文件。清朝時這些檔案文件保存于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民國時期保存仍比較完整。1942 年日軍占領內蒙古期間,偽蒙疆學院的教授江實從這批檔案中挑選了30 多箱帶走,剩余部分此后歷經劫難,殘余部分最后集中到土默特左旗檔案館。江實從這批檔案中選擇了287 份影印出版為《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巴彥塔拉盟史料集成·土默特特別旗之部》一書。
這些公文包括滿、漢、蒙三種文字檔案,其中清朝部分的檔案從雍正年間至民國初年(民國年間檔案正在整理中)。三種公文總數為15 993件,其中漢文有4803件,滿文10 374件(其中1980件已譯),蒙文816件(637件已譯)。漢文部分主要為土默特都統與山西巡撫、歸綏道廳衙門之間的往來文書及眾多漢人狀紙,整理者按軍事、行政、人事、政法、土地、財經、生產、外交、氣象、旅商、備臺、文教、房地契、圖表16類進行分類。其中除房地契類有1000多件外,政法類內容豐富,有800多件,土地類相關檔案也有500多件。滿文部分主要是都統衙門呈理藩院和將軍衙門文書,其中已譯為漢文的可分為:內政類的禮儀、職官項,財政中的賑濟、礦務、貿易、賦稅項,法律中的盜馬、民事糾紛、逃犯、修訂法律等項,軍務中的訓練、防務、軍需、臺站關口、賞罰撫恤項,文化類,宗教類,外交類。蒙文以家譜、召廟香火地畝冊、圖冊等為主。
這些檔案材料中包含著許多一般資料極少涉及的珍貴信息,例如檔案中出現的關于土默特地區甲頭、會社組織的事例。土默特社會最重要的地方力量在地方社會中究竟發揮了何種作用,向來少人論及。事實上甲頭以及其他地方基層組織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正是土默特社會形成過程的曲折反映。
一、土默特地區的保甲制度
“本省在清初時代,內地漢人出口多務農或經商,始而春來秋歸,繼則稍稍落戶,當時統稱為寄民。戶口漫無稽考,后以開地漸廣,寄民稍多,雍正年間,始有編甲之法。”[2](卷26,保甲團防)為何土默特地區在雍正年間開始編甲之法,一者在于“寄民稍多”,由此產生的糾紛矛盾增多,編設甲頭進行管理成為迫在眉睫之事。與此同時,查閱雍正年間檔案文獻,就可以發現,從雍正年間開始,朝廷嚴飭力行保甲,認為畸零村落、邊疆少數民族皆可編入保甲。可見,土默特地區保甲的實行,是清政府面對當地民人移入產生的種種問題,調整自身制度體系,將內地廣泛實行的保甲制度試行于邊疆地區的結果。
清廷最初設立甲頭的目的是管理內地移民,“雍正年間(1723—1735 年)開始,清廷在寄民中設立牌甲,將姓名、籍貫注冊,逐年查核”[3](P433),“在雍正年間,寄民尚少之時,僅止設立牌甲已足稽查邊氓”[4](卷6《田賦》,P14),故初期甲頭只存在于內地民人之中,管理民人內部事務,并對民人與當地蒙族之間產生的糾紛進行調節。隨著土默特地區蒙族逐漸定居,開始從事農業,在蒙族中也產生了甲頭,筆者所見關于蒙古甲頭的最早記錄是乾隆四十年(1775)關于蒙古甲頭爾林慶的記載[5],這也是對原有蒙族管理體系的一種修補調適。
甲頭的設立基本按村莊進行,一村設一甲頭,個別村莊設有蒙、漢兩個甲頭。甲頭具體以何種方式任命未見記載,但不需經過官府似乎無疑。有內地民人輪充甲頭的記載,且甲頭多“種地營生”[6],可能甲頭是由內地民人中稍有家產者輪任。存在“代管”情況,即在特殊情形下,一個甲頭可管理兩個村莊的事務。如乾隆四十六年,某人為“查漢溝代管當鋪溝甲頭”[7]。土默特地區的蒙甲頭和漢甲頭,分別由當地的蒙族和內地民人擔任,管理各自事務。如乾隆四十年,土默特某村分別存在蒙甲頭爾林慶和漢甲頭王天爵[5]。而上級政府有命令發布時,也會分別曉諭村中蒙漢甲頭,如道光三十年(1850),“諭飭聶圪圖村蒙漢甲頭等,將闔村蒙民人等所打之草捆點明數目,暫存公所”[8]。
乾隆、嘉慶時期,因“蒙古地方民人寄居者,日益繁多,賢愚難辯”,朝廷多次重申“將所居民人逐一稽考數日,擇其善良者立為鄉長、總甲、牌頭”[9](卷978,P16879)。光緒年間,“民物繁庶,情勢與前大別”[2](卷26,保甲團防),土默特地區的甲頭成為村眾共同推選出來應付官府之職。“蓋其始固嘗認真一時,積久遂不復深求”,“各村鎮年久沿襲其名,莫解其義,設一人或二人以為支應官差者,名曰甲頭”[2](卷26,保甲團防)。“而其制實彷于編甲,迨后僅殘留甲之一名詞”,名稱雖與清政府設定的保甲制中之甲有相似之處,實質卻已有了根本改變[2](卷26,保甲團防)。甲頭的設定既不按“合十戶為一牌,設一牌長。合十牌為一甲,設一甲長”,而是一村設一甲頭,其性質也從最初的一個管理內地民人的職位變為內地民人“支應官差”之職。這中間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是我們興趣所在。
甲長、牌頭的設置辦法是,“合十戶為一牌,設一牌長。合十牌為一甲,設一甲長。彼時村民零落,多為聯合數小村莊始可編為一甲”[2](卷26,保甲團防)。“各廳編造保甲門牌冊籍,每屆冬月,差查一次,其冊首注村名、距廳治里數,及甲長姓名與戶口總數。次注各牌長姓名及每十戶男女名口總數,第一甲至第十牌終,再注第二甲,此其編造之大略也。”[2](卷26,保甲團防)“每堡設牌頭4名,總甲1名。”[10](戶部保甲)光緒十年民人入籍之時,對保甲制度的規定又有了變化,“1883年(光緒九年),山西巡撫奏準,于次年按糧戶(種地納糧者)、業戶(置有房產種有田地者)、寄戶(無業不常居住者)編立戶籍,將各戶編入街、村、牌、甲之內,分別由街長、村長、牌長、甲長督察之。以上三等之外,凡里甲不具保結者即驅逐之”[3](P433)。總甲、牌頭“專司稽查。有蹤跡可疑之人報官究辦,遞回原籍”[11](P462)。鄉長、總甲、牌頭重要職責之一是每年春秋二季具并無容留匪類甘結存案,“如有作奸犯科者,將該鄉長等一并分別治罪”[11](P462)。檔案中大量所見,都為甲頭活動(參見表1),關于“牌頭”、“鄉長”、“保長”的記載很少。可見,土默特地區的保甲制度具有地方特殊性。相比較內地廣泛實行的保甲制度,土默特地區保甲制度中缺失“保長”、“牌長”的聲音,基本只有甲頭一種聲音。面對地方實際,政府調整了制度規定以適應當地情況,維護帝國秩序。
二、土默特地區的甲頭之職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甲頭的職能各不相同。甲頭成立初期主要執行政府規定的一些職能,例如具結甘結、出庭作證、發醫調治犯人等。無論蒙、漢甲頭,都常常要被傳出庭,協助調查。如乾隆四十年,衙門在調查一件土地糾紛案件的時候,明確要求村漢甲頭王天爵、蒙甲頭爾林慶參與調查[5]。被發配來的犯人有何病癥,當地甲頭都要報告上級部門。例如乾隆四十九年左右,保長某和甲長某報告,有發遣犯人某因身染傷暑病癥,需要發醫調治,請求派人前來治療[12]。與于甘結的例子很多,每年甲頭都要與于甘結,保證本村并無內地逃人(清朝政府嚴厲禁止內地人逃往蒙古,要求當地甲頭每年檢查,向政府匯報有無內地逃人)。乾隆四十年左右,二十家村的甲頭胡作圣與于甘結,保證該村并無隱匿內地逃人[13]。甲頭在執行這些職能過程中與當地民人接觸有限,對當地社會影響也有限。

表1 土默特檔案中所見清朝土默特地區甲頭列表

續表
甲頭的第二個重要職能是參與民間糾紛的解決,維護社會治安。宣統年間曾任歸化城副都統的三多曾說:“徵之如蒙古地方……杭嘉之間豫之民寄居其地,或百余年,然土客攘耕,每每釀成巨案,是爭斗易起于畦町,況外駐防情形既與京旗不同,而東南田地又比西北缺少……”也認為與內地相比,土默特地區更易于發生各種民間糾紛[14](《宣統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條陳蒙古事宜摺》)。因此,甲頭成為處理民間糾紛的最主要力量。如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八的盜牛案中,丟失牛只的告狀人稱:“小的認獲皮頭,并將不認識姓名二人俱交給該村蒙古甲頭必力貢、漢甲頭崔姓看守,理合稟明拘究。”[3](P478)。同年發生在蘇家村的一件盜竊案中,張順是蘇家村甲頭,當某人丟了牛后,“該犯在村外野地行竊牛只,并未偷拉回村,甲頭張順無從考察,請免置議”,從該例中可以看到,甲頭負責稽查村中盜匪,但他只負責村中發生的案件,而不負責村中人的行為,即村中人在外犯罪作案,甲頭并不需負責。并且張順在公堂上稱,失主“并沒通知小的”[15]。這也從反面說明,失主在丟失東西之后呈報甲頭,屬于正常程序,為法律所許可、也已得到民眾普遍認同,甲頭在當地為官方形象的代表。同年,查漢溝代管當鋪溝甲頭某,聽說村中有人打架,“趕緊趕去調解”,并把其中一人綁起來,阻止他們繼續爭斗[7]。58 歲的忻州人某充當村甲頭時,晚上他已經休息,村里忽然發生爭斗,村人都要趕去把他叫醒處理[16]。以上事例都證明,乾隆年間村中發生糾紛,由甲頭負責協調。
乾隆四十六年的盜牛案還說明,本設于內地民人之中的甲頭出現于蒙族村莊中后,也要負責處理蒙族中種種矛盾糾紛,此為甲頭制度逐漸適應形勢變化自身所作調適,而這種調適也適應了當地社會的變化。大量民人進入土默特地區后,當地蒙族牧民除少數繼續從事傳統畜牧業外,大多拿起鋤頭向漢族學習耕耘稼穡,由牧民變為農民。但正所謂“旗丁食租衣稅二百余年,一旦責令躬耕誠非易事”[14],社會轉變之時,不僅蒙人與民人矛盾多,發生在蒙族農民之間的糾紛也多,正由于甲頭的協調處理而使得社會處于穩定之中。
甲頭的基本職能即參與解決社會矛盾糾紛,這個基本職能隨著內地民人的大量涌入和土默特社會的日益變遷而相應發生著緩慢調適變化。伴隨著土默特社會各種力量的逐漸變遷,甲頭職能也相應變遷,在光緒末年時達到了某種程度的相對穩定。
甲頭的第三個職能是參與村中社會事務的處理,例如土地糾紛,這一功能在清朝末期尤為凸顯。光緒十年,清政府正式同意民人在土默特地區落籍,這一政策標志著,移民在土默特地區有了自己的合法地位,管理民人的甲頭的職責范圍和性質也相應發生根本變化。
從嘉慶到光緒,清朝逐漸走向沒落,康乾時期移入土默特地區的內地民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逐漸富裕起來,從最初租種蒙民土地,變為將蒙族土地購為己有。這就引起許多失去土地的蒙民不滿,這種不滿情緒通過各種渠道表現出來,引起當地社會震蕩。埋墳成為當地社會矛盾的導火索之一。試看道光八年(1828)的一則檔案:“劉永魁籍隸山西,來土默特河爾土默特營子佃種蒙古地畝,盤剝獲利有年,巴牙爾臺曾借劉永魁東錢一百九十吊,屢經逼討,巴牙爾臺將園地六畝,熟地十五畝當給劉永魁,尚欠東錢七十吊,無奈以應收租項當給折欠,因爾懷恨,后向劉永魁之弟劉永元借錢,復被劉永魁攔阻,不為借給,巴牙爾臺益為忿恨,適劉永魁父母先后亡故,因蒙古地方向來不準民人葬墳,劉永魁暫租蒙古隙地,于上年三月十二日埋葬之后”,巴牙爾臺邀素與劉不睦之人“去刨劉永魁父母墳塚”,并最終將劉永魁父母尸身刨揚①。此案結尾,負責處理的松筠一再強調:“查向來蒙古地方不準民人葬墳,應札飭所屬府州各縣,出示曉諭,佃戶商人各以劉永魁為戒,嗣后其有亡故者,仍前浮厝,或代量力送回原籍埋葬,違者治以應得之罪,并行文住居民人之各扎薩克,一體知照。”要求仍按照朝廷規定辦事。這個問題并未獲得根本解決,內地民人和當地蒙族之間的矛盾一直隱含于社會內部。
內地民人進入土默特地區后,主要以租種蒙族土地為生,發生土地糾紛在所難免。在官府進行處理之前,民間社會由甲頭協調矛盾雙方。乾隆八年,由于土默特地區土地占有極不均勻,朝廷重新調整分配了土地,按照實有人口,每口給地一頃,名為戶口地。規定戶口地不得典租、出賣,凡典賣者一律收回充公。但現實情況基本是,民間出租典賣照樣,租典方式有活約、活租、永租三種。活約地為定有年限,到期取贖之地;活租地為年限無定,錢到取贖之地;永租地為永遠耕種,許退不許奪之地,實際已經相當于賣地,但前兩種租約都可贖取。出典土地的,可分為兩種人,一種為達官貴族,為了滿足自己大肆揮霍的要求,將手中土地出典換取現銀。另一種為貧窮蒙民,這也是出典土地的絕大多數,由于有緊急需要,或因要當差打仗無暇耕作,不得不出典自己名下的戶口地。光緒三十一年,“朱紅計子租種小的家地四十一畝,雖有長支伊租錢八十三千五百文,本系短租活約。小的向該朱紅計子私下理論,經該村甲會處辦,令伊與小的退地十畝,因小的要拔(即“撥”之誤——作者)好地,伊與退給賴地,因此該甲會推手不辦”[3](P481)。從該案中可見,當時出典土地的現象非常普遍,甚至公然為出典土地糾紛而告上公堂,當時基層官府已默許了出租戶口地。從文中還可得知,當時的土地出租后,要退回時只需退足畝數即可,并不要求一定歸還原地畝。村甲會當時負責處理民間土地問題,而村民也承認甲頭的處斷,他們已成為村民輿論所承認的合法的決斷力量。
此外,甲頭也負責處理一些社會其他事務,例如入社問題。光緒二十四年,領催格海呈稱:“近日村中甲頭張六九、會首趙德明等向小的言說,托府主出諭,由各村捐辦義務,勒令小的入社,隨同伊等攤辦襟差。”“小的與甲會理較,而伊等以稟明托廳,拘鎖到衙門責打管押,那時看你入社不入,說完揚常而去。”[17]該社本為民人組織,漢族甲頭卻要求蒙族加入該社,可見漢甲頭所管理的已不限于民人,對當地蒙族也有了指揮權。甲頭職能本為處理社會糾紛、維護社會治安,會社之事為會首負責,但該案中甲頭所為早已超出其本身的職責范圍,開始參與當地社會的多種社會事務。光緒朝時,甲頭職能隨著民人的增多逐漸改變,職責范圍增寬,權力增大,在當地社會權威地位逐漸樹立。
三、甲頭在當地社會秩序中的地位
甲頭本是官府為統治內地移入民人而設立的,但設立之后,“所造冊籍,陳陳相因,年終廳冊匯報藩司而已”,“年僅以依樣葫蘆之冊籍,奉行故事耳”。而內地民人數量不斷增加,力量逐漸增大。制度的變遷不能與社會現實相適應,二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于是社會內部民人中間,需要一套新的制度對其進行管理。甲頭的性質逐漸轉變,官方色彩減弱,主要負責應付官府差役、代表村莊與政府進行接觸,成為村莊代表。甲頭完成了性質的徹底轉變,成為重要的地方勢力之一。
前述甲頭創立初期,在當地社會中主要執行維持社會治安的職能,在村民中的威信有限。在少數情況下,清初的甲頭也會為了村莊利益與其他勢力對抗。
從光緒十年內地民人在土默特落籍開始,甲頭的性質逐漸發生變化,首先表現為盡力保護村民。如,光緒二十一年,臺吉②阿彥爾札那、喇嘛扎木牙從烏里雅蘇臺馱攬廣泰魁皮貨,十月初九日至城北蜈蚣壩上時,被賊偷去駱駝一只和駱駝馱的羊皮一百張。兩人跟蹤駝印找尋,找到東五速圖村的時候,發現駝印不見。遂到村中要求甲頭成二套子協助找尋,成二套子滿口應允。但此后再無音訊,并不認真幫助查找。臺吉認為成二套子“任意推諉,詭言支吾,意存肯得已可概見”。歸化城兵司為此將成二套子傳來訊問,成二套子供:“同村蒙古六德子平素為盜,并有回民海明福子前賠過福義永失貨駝只”[18],“懇傳同本村會首衛順漢子查找失物”,但他的態度還是很消極,聲稱“不期有著”。土默特地區最早出現的是行商,即以駱駝等工具販運貨物,在歸化城和大青山后等地進行流動貿易。從本案可見,光緒年間土默特地區的商業逐漸發達,從事商業貿易的人日益增多,甚至臺吉和喇嘛都已加入行商。該案本為甲頭所負責之事,但成二套子卻要求會首協助查找失物,可見二者關系密切,在某種程度上二者職能已經混淆,甲頭和會首共同合作,處理社會事務,維系社會秩序。從成二套子對官府詢問的態度可見,他對發生的事情早已心中有數,但之所以直到官府介入都不追查,目的在于盡力保護犯罪者。從村民的角度來看,成二套子是站在村民一方的,此時他具有村民保護者的意義。甲頭敢在官府詢問的時候說“不期有著”,說明此時甲頭對官府的依賴性關系已經減弱,相對官府,甲頭與民眾之間關系更為密切。
甲頭也極力維護本村利益。光緒二十二年,距城70里后紅岱村發生一起民事糾紛:
七月二十九日,有小的本村之蒙古人老滿家紅前往新營子村看戲,不知伊等與本村民人王姓一戶有何嫌隙,就在戲場之中,伊兩家互相爭毆。根九子那時亦在新營子村看戲,見伊兩造相毆,念在同村,向前攔勸,將伊等各勸回村。不料于日落時,根九子同本族弟兄五六人亦相隨回家,走至前紅岱村南麻田地畔,突出甲頭王蘭套子等十數余人,各執鐮刀木棒,在麻地埋伏。不容根九子等分說,任意詈罵,且王蘭套子喝令肆行亂毆,將根九子并伊族弟兄四
五人俱毆有傷痕。……[19]
如果只根據呈控人所報,我們無從猜測,為何王蘭套子要糾集眾人毆打與其無關的外村人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蘭套子可以糾集村中眾人,說明王蘭套子在村中有很高威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村中集會演戲之時,竟然有外村人攪鬧會場(不管他們是否有意),作為甲頭的王蘭套子可能是對于有人在村中集會的重要場合鬧事不滿,所以帶人毆打鬧事之人,雖然王蘭套子的方式值得商榷,但他為村莊著想的態度表明,他和村莊是一體的,村莊利益受到侵害,他會出面維護。這同前期看到的甲頭只是作為官府的雇員,并沒將村莊利益當作切身利益的情況完全不同。
光緒末年,甲頭已代表村民整體利益,為維護全體村民利益,可以與個別大戶對簿公堂:
具呈人新舊甲會蒙古合同民人王存等,年歲不同,為鯨吞借谷,苦害村眾,乞恩拘究,今斷追給原積之谷以濟眾民事。緣小的等村于光緒二十六年適遇荒年,村眾饑餓難度,懇請伊參領祈借倉谷四十余石,給散村眾度命。……該連明應恃富不仁,強橫惡霸,鯨吞積谷,苦害村眾。……
具呈人蒙古合同 民人王存年歲不同住兩施格氣村
鯨吞積谷人連明應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日[20]
連明應為村中大戶,在村中沒有集體谷倉之時,以一己之力自建谷倉。但是,該大戶卻為富不仁,災荒之年不但不借給村民谷物度荒,甚至將官府救災之谷糶賣肥己。對官府命令尚且“強橫硬抗,違斷不遵”,其在村中狂妄之態可見。甲會為了全體村民利益,多次要求連明應歸還借谷,散給村眾,在多次討要無著的情況下,將其告上公堂。此時甲會完全代表全村利益。
甲頭維護村莊利益、村民利益,逐漸得到當地民眾承認,成為地方權威。如:
具呈人納參領兼佐領下蒙古恩受,年二十九歲,住城東蘇計村,距城九十里。為屢欠租銀,抗不償給,祈恩飭寧遠廳查卷,地歸蒙古,以免失落無著事。緣小的等先人七戶蒙古戶口地二十二頃余,租給民人花戶承種,每年寧遠經征租銀三十二兩,交給小的等七戶分散。迨至光緒十年,花戶報退八頃有余不堪耕種,每年應得租銀無幾,以致眾蒙古赤貧如洗。又至二十八年,花戶棄地逃走,遺留地五頃六畝,現在小的等承種。荒蕪者多耕種者少,寧遠至今應征九頃有余,地租銀花戶分交,不能短欠,小的等更不能見租。現在荒撫(同“蕪”——著者),不堪耕種,逃亡絕戶,短欠舊租,該廳原差勒逼,向甲、會討要。此租與甲、會無涉,將二個甲、會勒拿管押在班,祈懇憲天飭寧廳將九頃有余地原歸蒙古,將甲、會開放還家。……施行。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21]。
蒙古戶口地分給蒙民后,多租給民戶,時日一長,蒙戶常常將自己的土地典賣給民人。故清政府規定,由政府出面,將部分戶口地租給民人,民人將租銀上交政府,再由政府分給每戶蒙民。從乾隆四年開始,土默特蒙民巴特馬孟克等七戶地畝招民人墾種,征租解交歸化城都統查收,再轉給巴特馬孟克等。例中的恩受即為巴特馬孟克之后人。從最初的順利招墾,到光緒年間的“花戶棄地逃走”,當地土壤質量已大大降低,蒙民的地租銀也不能順利得到。土地被遺棄,地租無著,官員即向該村甲、會討要。此時的朝廷和甲、會已完全是對立的兩方。朝廷將甲頭和民眾視為當然的一體,租地戶交不出地稅,既管押甲、會在班。而民眾也似乎將甲、會視為自己一方。看到年節將近,感到“將甲、會管押,小的矢難安然”。此時的甲會和民眾的關系比以前更加密切,而甲會和官府的關系則更加疏遠,甚至對立。
涉及村莊與官府交涉事宜時,作為地方代表,甲頭會出面與官府交涉,如宣統二年(1910),廣化寺圪斯貴八十一并海流樹、太寬店子、廟爾溝等十四村蒙古領催、甲頭圓孟多爾圖、納遜、阿育什等聯名稟懇,請求政府暫停開采周圍山中之礦藏,原因是會“破壞風水”,且認為“廣化寺系奉歷憲明文斷歸之山廠,而阻攔不令挖窯是必然之勢”[22]。
甲頭由于壟斷官府與村莊之間聯系而具有某種特權,因而有某些利用職權損公肥私的行為。而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甲頭在當地已經具有很大特權,成為當地權威力量之一。光緒二十年,住歸化城西(今呼和浩特)十里倒拉土木村的佐領諾孟德力格爾與侄子依力圪曾發生土地糾紛,“依力圪曾恃其充當佛廟甲頭之勢,勾結本村少年無知之蒙古,到地逞強兇阻,不容耕種”[23]。光緒二十四年,領催格海呈控甲頭張六九、會首趙德明等聲稱托府主出諭,由各村捐辦義務,令其入社。格海與甲會理較,而甲會以“稟明托廳,拘鎖到衙門責打管押,那時看你入社不入”回答,說完揚長而去[17]。此時的甲、會,更加類似村中惡霸的形象,可見當時的甲、會職權已大,否則甲、會無法借甲頭之勢作威作福。再如,光緒三十一年,乃痛村崇壽寺屬下俗徒孟保,因為爭水澆地發生糾紛,被黑水泉子村領催二換、伊兄披甲面換子等毆打,并“將孟保下部納傷,導致孟保傷重身死”[24]。按照清朝法律,發生命案是要報告官府的。但二換和面換非但沒有報告官府,而且“買通闔村甲、會蒙民十余人辦理”,和事主違法私了。當孟保表兄聞訊前去詢問的時候,面換、二換不但不認錯,反而變本加厲,指使人毆打孟保的表兄。這三份材料反映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即甲頭在當地具有很大權威,是構成當地社會的重要支柱之一。
四、結語
甲頭為官府設立之職,在解決移入民人之糾紛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職能也集中在解決已發生的糾紛案件中。民人大量進入土默特,從而與當地蒙人在使用資源、宗教信仰等方面都產生了矛盾,使社會發生振蕩。當地原有的社會機制無法很好地解決這些沖突矛盾,需要一種新的制度處理種種矛盾糾紛,維護社會正常運轉。對此,清政府將推行于全國的保甲制也應用到土默特地區。試圖通過設立保長、牌頭、甲長,將各家各戶嚴格按牌甲編制,穩定當地社會。但土默特地區在民人初入之時,“或五六十里始見一村,或一里數村,一村僅兩三家居住”,內地保甲制在當地實行頗多窒難之處。適應當地現實,保甲制進行調適,保長、牌長基本未發揮作用,主要由甲頭管理社會事務,“保甲”制在土默特地區實為“甲頭”制度。
土默特地區本為蒙族游牧之地,內地民人的大量進入,使得該地由游牧社會變為一個“邊村社會”。促成這種變化的內在動力和機制正是幾種合力的共同作用。保甲制度無疑是合力之一。土默特社會原有的八旗制度不能完全解決民人進入引發的各種問題,構建和改變地方秩序體系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邊村社會”的形成過程。在新的秩序體系建立過程中,構成當地社會勢力網絡的甲頭在社會沖突中不斷進行調適,和其他力量逐漸形成了新的秩序體系。甲頭本為官府設立以管理民人之組織,而且隨著土默特蒙族受民人影響逐漸定居,在蒙人內部也出現了甲頭,作用基本和民人甲頭相同。甲頭雖為官府設立,但到光緒朝之后,甲頭與官方聯系日益減少,逐漸發展成為代表民間力量的地方勢力。
注釋:
①據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檔案129655 號。
②俺答汗系黃金家族,其后裔均可稱為臺吉。入清后,俄木布被廢,其親近支派亦被貶為庶人,保留臺吉名號的只有數支。臺吉分屬左右翼,有職者僅有二等臺吉2員,四等臺吉2 員。
[1]王衛東.1648—1937年綏遠地區移民與社會變遷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1.
[2]綏遠通志稿[Z].民國抄本.
[3]土默特志[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4](清)劉鴻逵.歸化城廳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
[5]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5,卷宗號1187.
[6]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140.
[7]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177.
[8]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5,卷宗號2002.
[9]昆岡,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Z].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
[10]大清會典[M].臺北:臺北文海出版社,1995.
[11]土默特志·理藩院則例[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12]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169.
[13]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151.
[14](清)三多.歸化奏議[Z].清宣統間抄本.
[15]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176.
[16]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180.
[17]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5,卷宗號2213.
[18]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581.
[19]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587.
[20]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732.
[21]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5,卷宗號2313.
[22]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7,卷宗號152.
[23]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5,卷宗號2166.
[24]土默特清代檔案[Z].全宗號80,目錄號4,卷宗號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