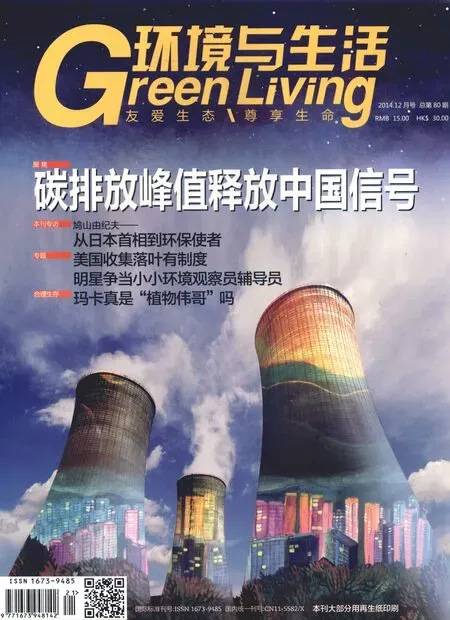專家解讀“碳排放峰值”中國發出清晰政策信號
◎本刊記者 朱艷
中國和美國是目前全球兩個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約占全球總排放的42%。11月12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兩國共同發表了一份《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引起世人關注。聲明中,美國首次承諾到2025年,溫室氣體排放較2005年整體下降26%~28%。中國也首次提出到2030年左右碳排放達到峰值,并將于2030年把非化石能源消耗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這是中國首次釋放2030年左右碳排放達到峰值的信息。


我國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利用占能源利用總量的20%,這和我國的核能開發利用進度有關。
作為一個嚴重依賴化石能源、尚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中國依據哪些數據做出這個2030年左右碳排放達到峰值的預測?這份聯合聲明對中國來說具有什么意義?2014年11月20日,《環境與生活》雜志就此采訪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處的專家王克博士。
減排是中國的自覺要求
所謂碳排放峰值,是指通過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大值。它能反映出能源的最大消耗量。達到碳排放峰值,就意味著往后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加或逐漸消減。
王克博士對《環境與生活》解釋說,中國在此時提出2030年左右達到碳排放峰值,有兩個重要背景。一是中國乃《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國,根據2013年華沙“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決定,各締約國需在2015年第一季度宣布各自的溫室氣體減排貢獻,也就是行動目標,中國當然不能例外。
截至2014年10月,歐盟的28個成員國已經承諾到2030年,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40%的溫室氣體排放。此時恰逢APEC會議,中國作為東道主和美國通過兩國元首峰會發表聯合聲明,更能體現兩國的減排決心。“事實上,全球兩個最大碳排放國的承諾,把過去5年來5次全球氣候變化大會試圖談妥的事給談成了。盡管美國的排放量少于中國,居全球第二位,但經濟總量是全球第一,如果美國不設定目標,中國就更難做。”
王克認為,中國此次明確提出碳排放峰值時間目標,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背景,就是當前我國霧霾問題嚴重,引起民眾廣泛關注,治理大氣污染,進一步壓縮煤炭用量勢在必行。“幾年前是別的國家要求我們做,現在是我們自覺要這么做。”王克坦言。
美國加州“全球生態足跡網絡”首席執行官蘇珊·伯恩斯聽到這個消息也對《環境與生活》記者說,中美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能聯合承諾碳減排目標,令人非常欣喜!這將對其他保持觀望態度的國家具有促進作用,將對環境產生深刻影響。

中國明確提出碳排放峰值時間目標,原因之一是當前我國霧霾問題嚴重,治理大氣,進一步壓縮煤炭用量勢在必行。
與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峰值同步
在目前這樣嚴峻的環境形勢下,把我國的碳排放峰值設定在2030年左右,依據是什么呢?11月25日,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與行動2014年度報告”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透露,確定這個時間點的方案,是經過了一年半到兩年的論證。
解振華強調,表述中有“左右”這個詞,可以更科學、更客觀。因為現在距離2030年還有16年,這16年中會面臨經濟社會發展、能源等很多不確定性的問題,確定一個非常準確的時間或者數字,實際上并不科學。“比如,發達國家承諾的2020年之前達到的目標,因為2008年出現了金融危機,實現不了。發達國家曾承諾在2020年之前提供1000億美元,支持非發達國家減排,現在不行了,發達國家說出不了這個錢,因為本國經濟困難。”
值得一提的是,11月5日,中國社科院-國家氣象局氣候變化經濟學模擬聯合實驗室發布了第六本氣候變化綠皮書——《應對氣候變化報告訴2014:科學認知與政治爭鋒》,書中提出,中國的碳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出現。
這份綠皮書對我國工業化進程進行了分析與預測,認為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總體上處于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階段,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業部門將于2020年前后實現產量峰值。在低碳情景下,工業部門總排放將在2025年~2030年之間達到峰值。
城鎮化也是影響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城市建設對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品的潛在需求巨大,未來城鎮化的發展對我國碳排放峰值的實現會帶來巨大挑戰。根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約在城鎮化率為70%左右的階段出現。綠皮書稱,2013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53.73%,預計達到70%大約還需要15年,以此可以推斷,中國的人均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現在2030年左右。
王克也說,“根據各方面的統計,到2030年左右,我國工業化進程、城市化進程都接近頂峰,風能、太陽能、核能等新能源的建設也差不多能替代部分化石能源。”
核能利用納入減排目標
據了解,2013年我國已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累計下降28.56%,相當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億噸。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2013年底已經達到9.8%,接近10%。而且今年9月份之前,國內煤炭消費量首次呈下降趨勢,“這可能和大的經濟環境有關,但也從理論上說明我們能控制煤炭的使用量。”

到2030年左右,我國風能、太陽能、核能等新能源的建設,差不多能替代部分化石能源。
王克告訴《環境與生活》,由于中國的能源消費中,有超過70%來自煤炭,擁有數以百計的新燃煤發電機組,是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碳排放國的重要原因,“再怎么控制,我國煤炭的使用量也會比發達國家高,發達國家希望我們2015年達到峰值,但是根據我們自己的實際情況,權衡一下,提出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
我國之所以承諾2030年非化石能源利用達到能源利用總量的20%,王克認為這和我國的核能開發利用進度有關系,“核電廠的建設周期長,一般建成發電需要10年左右。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事故,使得我國核能整體開發進度耽誤了兩三年時間,原先計劃的2010至2020年的核能發展目標很難實現。照這樣看來,我國2020年的碳減排目標不能指望核能有大貢獻,而2030年的目標是考慮了核能利用的。”
給企業發展指明方向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國際合作部負責人張曉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指出,如果要實現占比20%的目標,非化石能源需要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這意味著我國每年新增8至10億千瓦核電、太陽能、風電的裝機容量,這個數值相當于我國目前的煤電裝機總量。所以可以想象,要實現“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總量的20%”確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未來的碳排放無論是在強度還是總量控制上都有難度,但王克認為,對我國來說,2030年的目標非常有意義,因為碳排放峰值的提出透出了清晰的政策信號,給企業投資提供了方向,“因為能源的改革和升級都需要過程,這個信號可以讓更多資金流向這個領域。”

我國工業化進程總體處于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業部門將于2020年前后實現產量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