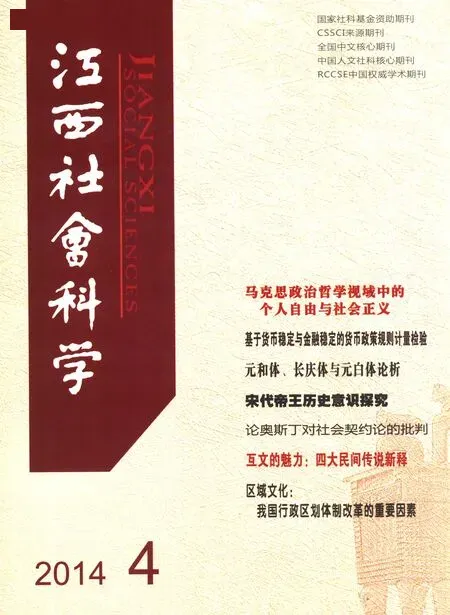論王夫之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詩(shī)學(xué)的繼承與超越
■石朝輝
一
蔡元培在《中國(guó)倫理學(xué)史》中說:“評(píng)定詩(shī)古文辭,恒以載道述德眷懷君父為優(yōu)點(diǎn),是美學(xué)亦范圍于倫理也。”[1](P2)中國(guó)古代詩(shī)學(xué)的傳統(tǒng)中,倫理與詩(shī)學(xué)具有同一性,從先秦我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產(chǎn)生開始,詩(shī)學(xué)與倫理之間就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jìn),不斷豐富。
依據(jù)現(xiàn)有文獻(xiàn)資料來看,《尚書·堯典》中“詩(shī)言志,歌永言”應(yīng)該是最早的詩(shī)學(xué)理論之一,其所注重的正是文學(xué)的功用性。先秦時(shí)期儒家提出一系列理論都有意識(shí)地把教化與詩(shī)學(xué)結(jié)合在一起。“盡善盡美”、“文質(zhì)彬彬”要求政治內(nèi)容和藝術(shù)形式的統(tǒng)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思無邪”追求中和之美;“興于詩(shī)、立于禮、成于樂”要求文學(xué)由政治生活來決定其地位;“興觀群怨”要求文學(xué)為禮樂服務(wù),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社會(huì)作用。儒家思想都從“教化”的倫理道德的角度出發(fā)規(guī)范藝術(shù),使得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在產(chǎn)生之初就與倫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倫理觀念甚至對(duì)詩(shī)學(xué)審美起著直接的引導(dǎo)作用,要求詩(shī)樂必須符合道德倫理的社會(huì)要求,否則是不合適的。
漢代自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之后,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作用更是得到了充分發(fā)揮。《毛詩(shī)序》雖然也對(duì)文學(xué)中的某些方面提出了積極論述,但是其核心目的還是詩(shī)的教化作用:“故正得失,動(dòng)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shī)。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fēng)俗。”[2](P63)明確提出了情感不能任意抒寫,而必須由禮義予以節(jié)制。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guó)文學(xué)自覺的時(shí)代,但是詩(shī)學(xué)理論還是沒有完全走出原有的傳統(tǒng)。曹丕《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jīng)國(guó)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強(qiáng)調(diào)文章的重要性和社會(huì)功用。劉勰直接在《文心雕龍》中把“原道”、“征圣”、“宗經(jīng)”列為“文之樞紐”,無論是“道”還是“圣”、“經(jīng)”都是以儒家思想為出發(fā)點(diǎn),其還認(rèn)為各類文體都應(yīng)該以圣人的經(jīng)典為榜樣,使得詩(shī)學(xué)和倫理的同一達(dá)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
從唐代到宋元時(shí)期,中國(guó)文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兩條明顯不同的道路:一是政教作用的強(qiáng)化,另一是審美意識(shí)的深化。但作為詩(shī)學(xué)和倫理共同作用下的文學(xué)理論還是依然得到了整個(gè)社會(huì)的提倡。唐初陳子昂提出詩(shī)歌需要有“興寄”和“風(fēng)骨”,重新要求詩(shī)文再次回歸內(nèi)容和形式上的統(tǒng)一,文學(xué)應(yīng)該反映社會(huì)政治的內(nèi)容。中唐新樂府運(yùn)動(dòng)的代表人物白居易直接用“文章合為時(shí)而著,歌詩(shī)合為事而作”來說明文章詩(shī)歌必須為時(shí)事政治而創(chuàng)作,“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要充分發(fā)揮“補(bǔ)察時(shí)政,泄導(dǎo)人情”的作用。古文運(yùn)動(dòng)更是掀起了一場(chǎng)宣揚(yáng)儒家思想的文風(fēng)改革運(yùn)動(dòng),提倡文以明道。到了宋代儒學(xué)有新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理學(xué),其代表人物周敦頤、程頤分別倡導(dǎo)“文以載道”、“作文害道”,朱熹在此基礎(chǔ)上把“道文合一”作為重要的詩(shī)學(xué)理論。
二
明清時(shí)代是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的總結(jié)時(shí)期,詩(shī)學(xué)中的兩大重要觀念——教化與審美更是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王夫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duì)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進(jìn)行了重新審視,其理論正是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詩(shī)學(xué)的繼承和超越。這主要表現(xiàn)在依然沿用原有的觀念、范疇、概念,重視詩(shī)性和倫理的同一;但是在闡釋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范疇時(shí),又不時(shí)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試圖用一種全新的視角來賦予新的意義,以下具體從其中幾個(gè)具有代表性的范疇概念入手,展開分析。
(一)詩(shī)言志與詩(shī)緣情
朱自清稱“詩(shī)言志”是中國(guó)詩(shī)歌理論的“開山綱領(lǐng)”。王夫之論詩(shī)依然還是從詩(shī)言志出發(fā),另一方面其詩(shī)言志的意義卻發(fā)生了改變。
王夫之認(rèn)為:“詩(shī)言志,非言意也……心之所期為者,志也;念之所覬得者,意也。”[3](P325)在言志中,引入了“意”的概念,心里所期待的是志,是人生對(duì)既定目標(biāo)或理想的追求,但是非分的希望或企圖則會(huì)成為意,不應(yīng)該是詩(shī)歌所要表現(xiàn)的內(nèi)容。王夫之還對(duì)“志”進(jìn)行了補(bǔ)充闡釋:“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4](P439)這一段話雖然論述文學(xué)作品,實(shí)際上也是對(duì)于詩(shī)歌中“志”的要求,也就是說無論個(gè)人的道德修養(yǎng)還是個(gè)人的情感抒發(fā)都必須從自己出發(fā),外物只有受到了個(gè)人情感的觸發(fā)才能被呈現(xiàn),同樣的情感,在不同的人身上會(huì)展示出不一樣的表現(xiàn),詩(shī)言志的“志”也應(yīng)該是“己志”,而非脫離自我的表達(dá),不能因?yàn)椤把灾尽倍鲆暳嗽?shī)歌獨(dú)有的藝術(shù)特征。雖說言“己志”,但是王夫之實(shí)際上進(jìn)行了一種轉(zhuǎn)換,因?yàn)樵谒磥恚词故恰凹褐尽币残枰獏^(qū)別對(duì)待。
王夫之對(duì)“志”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一是立志。“入學(xué)之士,尚志為先”,一個(gè)人無論從事什么事業(yè),都把“立志”為第一要?jiǎng)?wù),有了具體的追求理想和目標(biāo),堅(jiān)定不移的努力,才有可能成就其功績(jī)。王夫之對(duì)具體“立志”的內(nèi)容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立大志,“以身任天下”之“無私之志”,只有這樣才能符合仁義道德,才能“寵不驚而辱不屈”、“生死當(dāng)前而不變”,才能實(shí)現(xiàn)“身可辱,生可損,國(guó)可亡,而志不可奪”的境界。二是正志。王夫之的正志指用道德規(guī)范來培養(yǎng)人的情操、意志,使其符合封建倫理思想的要求,“教者尤以正志為本”,只有樹立堅(jiān)定的志向,才能“志正而后可治其意”,從而真正實(shí)現(xiàn)理智對(duì)于情感的節(jié)制和約束。胡家祥在《志:中國(guó)哲學(xué)的重要范疇》一文中說:“從人的社會(huì)性生存方面看,志作為人道、性理的負(fù)載者,既是個(gè)體與群體親合的心靈紐帶,又是保持個(gè)體相對(duì)獨(dú)立而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柱石。”[5](P41)王夫之詩(shī)論中的“志”正是兩者的結(jié)合,既沒有脫離儒家倫理的限制,又沒有完全背離詩(shī)歌本身應(yīng)該具有的特征。王夫之還進(jìn)一步把《尚書·舜典》的思想發(fā)揮為:“以詩(shī)言志而志不滯……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盡天下之貞淫而皆有之。圣人從內(nèi)而治之,則詳于辨志;從外而治之,則審于授律。內(nèi)治者,慎獨(dú)之事,禮之則也;外治者,樂發(fā)之事,樂之用也。”[6](P251)志必須進(jìn)行宣發(fā)、表達(dá),而不能“滯”于人心,但“志”有“貞淫”的區(qū)別,必須“治志”,具體可以通過“外治”與“內(nèi)治”兩種途徑實(shí)現(xiàn)。“內(nèi)治”主要通過禮來實(shí)現(xiàn),是“慎獨(dú)之事”,面對(duì)自我如何保持本心、本性,面對(duì)外界,如何不為外物誘惑,在內(nèi)心才能見功夫。“外治”則通過音樂的形式得以實(shí)現(xiàn)。總之,志需要不斷磨煉、鍛造,才能實(shí)現(xiàn)真正意義的“詩(shī)言志”。
雖然志能成為詩(shī)歌的言說對(duì)象,但是由志到詩(shī)的過程中還必須經(jīng)由一個(gè)重要的因素:“‘詩(shī)言志,歌永言’,非志即為詩(shī),言即為歌也。或可以興,或不可以興,其樞機(jī)在此。”[7](P897)可否“興”成為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標(biāo)準(zhǔn),并不是任何志、言都可以成為詩(shī),關(guān)鍵在于“興”的存在。只有具有感發(fā)人心、飽含情感的詩(shī)歌才是真正的詩(shī)歌,而那種缺乏興發(fā)狀態(tài)的詩(shī)歌無法引發(fā)作者的創(chuàng)作激情,更不用說觸動(dòng)讀者的內(nèi)心情感了。
與詩(shī)言志具有同樣重要地位的詩(shī)歌本體論思想是詩(shī)緣情。王夫之主張?jiān)姼钁?yīng)以情為本:“詩(shī)以道情,‘道’之為言‘路’也。詩(shī)之所至,情無不至;情之所至,詩(shī)以之至。”[8](P689)從本體論而言,“情”是詩(shī)歌需要表達(dá)的對(duì)象,情感貫穿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全過程,從情開始,觸動(dòng)心靈,誘發(fā)表達(dá)的激情,詩(shī)歌不能離開情,情感是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中的核心因素。情感與詩(shī)歌之間并不能完全等同,王夫之具體通過性情的方式來進(jìn)行調(diào)和,即“詩(shī)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關(guān)于王夫之性情關(guān)系的研究已經(jīng)很多,這里不再重復(fù),僅看性與情之間的相互作用,性如何引導(dǎo)情進(jìn)入詩(shī)歌言說的領(lǐng)域。王夫之認(rèn)為要以性正情,循情定性,強(qiáng)調(diào)以性主情。性和情之間也存在順序的問題,“以性主情”,情才能夠得到很好表現(xiàn)。王夫之認(rèn)為:“君子之于情也,必有所節(jié),節(jié)情而用,性得其正,天地之理得矣。”[9](P591)性情本源于正,這不是隨意獲得的,也不能任意改變,更不能替代,需要有效地把情規(guī)范在性的引導(dǎo)之下。情可以有著各種不同的表現(xiàn)狀態(tài),但都不能離開性,性必須要有效主情,正情,而且這個(gè)作用不能替代和改變,所以說“循情而可以定性也”。王夫之有意識(shí)地通過“正”、“主”的方式把兩者統(tǒng)一在一起,這可以說是對(duì)于情性關(guān)系的總結(jié)。正是在這樣深入分析的基礎(chǔ)之上,王夫之詩(shī)學(xué)中的情也得到了更多的規(guī)范,即使言情也是不同于明代文論家的情,是受到了倫理道德約束的情,是道性之情。
王夫之通過“志”與“情”的不同要求,使得原本兩個(gè)獨(dú)立的理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既對(duì)傳統(tǒng)倫理詩(shī)學(xué)中的詩(shī)言志、文以載道進(jìn)行了繼承,但是又具有一種新的活力。
(二)溫柔敦厚與思無邪
溫柔敦厚最早出現(xiàn)在《禮記·經(jīng)解篇》:“為人也溫柔敦厚,《詩(shī)》教也……”指人的言行舉止、興趣愛好,性格溫和寬厚,后逐漸引申為詩(shī)歌的表現(xiàn)手法。“溫,謂顏色溫潤(rùn);柔,謂情性和柔。《詩(shī)》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shī)》教也。”[10](P1609-1610)再后來逐漸演變?yōu)槿寮覄?chuàng)作、批評(píng)的標(biāo)準(zhǔn),更是儒家詩(shī)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藝術(shù)原則。王夫之在《禮記章句》中對(duì)這一思想進(jìn)行了強(qiáng)調(diào)和發(fā)揮:“‘溫柔’,情之和也;‘敦厚’,情之固也。……立教之道盡于六經(jīng),為君師者以此為教,俾學(xué)者馴習(xí)而涵泳之,則變化氣質(zhì)以成其材之效有如此矣。”[11](P1172-1173)從另一個(gè)角度重新闡釋了溫柔敦厚的含義,強(qiáng)調(diào)其與情密切相關(guān)的兩個(gè)特征:一是和,一是固。這兩個(gè)特征也成為王夫之詩(shī)學(xué)理論對(duì)于中國(guó)倫理詩(shī)學(xué)的繼承與超越的具體表現(xiàn)。
王夫之在《說文廣義》中具體解釋了“和”字的意思:“凡相應(yīng)者通謂之和。相應(yīng)則協(xié)于中,心與理相應(yīng),道與事相應(yīng),文與情相應(yīng),己與物相應(yīng),無不愜合,故為天下之達(dá)道。”[12](P294)在王夫之詩(shī)學(xué)中,各種言說對(duì)象之間,都盡可能地以一體的性狀出現(xiàn),比如:情景、情理、性情、情物、己物等等。“情景名為二,而實(shí)不可離”,“理密情深”、“實(shí)則天理、人情,元無二致”,“發(fā)乎情,止乎理”,“失己,則物無與依”……這些論述有效地說明了“和”在王夫之詩(shī)學(xué)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情之和正是溫柔的表述。
固主要指情感的堅(jiān)定、長(zhǎng)久,也指情感的內(nèi)在持續(xù)性作用。王夫之作為明代遺民的身份選擇本身就是個(gè)人情感、意志堅(jiān)定和能力的表現(xiàn)。趙園在《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中也說:“‘遺民’以特殊情境,將士的角色內(nèi)容呈示了。……‘遺’本是對(duì)孤獨(dú)的選擇,當(dāng)其成為群體行為時(shí),真正孤孑的,只能是其中的杰出者,其人既拒絕順民身份,又不認(rèn)同于‘遺民社會(huì)’的一套概念、觀念,不茍同于這社會(huì)的自我界說、詮釋,其難以納入‘類’的描述,是不待言說的。”[13](P262-265)王夫之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堅(jiān)持“固”、堅(jiān)持貞,也決定了其詩(shī)學(xué)理論的傾向。他的詩(shī)學(xué)中一方面試圖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進(jìn)行總結(jié),但是另一方面又以儒家詩(shī)學(xué)為其堅(jiān)持的核心。無論經(jīng)歷怎樣改變,社會(huì)歷史如何變化發(fā)展,王夫之始終有著無法改變的信仰,其詩(shī)學(xué)思想建立在哲學(xué)思想上,自然不可能完全擺脫倫理詩(shī)學(xué)的影子,只能是在某種意義上對(duì)這些思想進(jìn)行補(bǔ)充、修訂。這也是為何其詩(shī)學(xué)中的情永遠(yuǎn)有著一個(gè)更高意義的抽象概念——性、理、禮等的限制和約束的原因。在詩(shī)學(xué)中還表現(xiàn)在詩(shī)歌與其他體裁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藝術(shù)典范的推崇等等,而且這些觀念可能有別于同時(shí)代的思想家,但是他依然保持自我的那一份執(zhí)著。王夫之從詩(shī)經(jīng)引申為六經(jīng),指出為君師者應(yīng)以六經(jīng)為教學(xué)內(nèi)容,使學(xué)習(xí)的人熟習(xí)它并深入領(lǐng)會(huì)其含義,那么自然其氣質(zhì)就會(huì)得到提升;教育者得到六經(jīng)的精意,引導(dǎo)學(xué)習(xí)之人達(dá)到中正規(guī)矩的境界,那么整個(gè)社會(huì)都會(huì)達(dá)到至善的境界,風(fēng)俗自然而然變得完美,異端邪說都不會(huì)得以出現(xiàn)和禍亂社會(huì)。
與《詩(shī)經(jīng)》有關(guān)的另一個(gè)重要詩(shī)學(xué)思想是“思無邪”。《論語》中孔子提出:“詩(shī)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這一思想概括了《詩(shī)經(jīng)》情感的重要特征,后世對(duì)這一觀點(diǎn)有多種解釋。朱熹《四書集注》認(rèn)為:詩(shī)可以勸善止惡,其作用都在使人情性歸正,然而詩(shī)的語言是細(xì)微婉曲的,而且都是因個(gè)別的事而發(fā),能夠直接指出詩(shī)使人“歸正”這種共同屬性,沒有像孔子“思無邪”這樣明白到家的,這句話足以概括詩(shī)的共同意義。劉寶楠《論語正義》也認(rèn)為,詩(shī)或勸善,或止惡,都是要使人“歸于正”,孔子“思無邪”這句話足以概括這一點(diǎn)。
王夫之認(rèn)為:“《詩(shī)》雖貞淫具在,學(xué)《詩(shī)》者當(dāng)以‘思無邪’一語為學(xué)而取益之,要重在一思字。《詩(shī)》之所詠,皆思致也。其貞正者,由一念之正,纏綿悱惻,以盡天理民彝,則身修家齊,以底于化行俗美。其邪者,由一念之妄,留連泛濫,以極乎淫蕩狂逞,而至于辱身賤行,敗國(guó)亡家。知‘思無邪’則慎思以閑邪,三百篇皆興觀之實(shí)學(xué)也。”[14](P166-167)他從一個(gè)全新的視角分析,把“思無邪”的言說對(duì)象由《詩(shī)經(jīng)》這一文本轉(zhuǎn)到了讀者,認(rèn)為《詩(shī)經(jīng)》“貞淫具在”,有貞情也有淫情,重要的是讀者在閱讀《詩(shī)經(jīng)》時(shí)的“思”。這是對(duì)于藝術(shù)作品的一種獨(dú)特的理解和領(lǐng)悟,可能出現(xiàn)兩個(gè)方面:一是“一念之正”,那么即使是抒發(fā)纏綿悱惻的感情也可以盡可能地展示天理人倫,給人帶來審美享受和熏陶,也能讓人領(lǐng)悟到儒家倫理道德的益處。另一種是“一念之妄”,則會(huì)“情至則淫,情盡則變”,導(dǎo)致泛濫、淫蕩、狂妄驕逞,甚至可能做出卑劣的行為,出現(xiàn)敗國(guó)亡家的危險(xiǎn)。當(dāng)面對(duì)《詩(shī)經(jīng)》時(shí),讀者必須有意識(shí)地約束自己的情感,避免被淫情、惉滯之情,私情,悁急之情、矯情、不道之情、太過之情等各種不利的情感所左右,而是要以理性精神來匡正、節(jié)制、整治、協(xié)調(diào)情,“《詩(shī)》者,所以蕩滌惉滯而安天下于有余者也”[3](P326),這樣《詩(shī)經(jīng)》的審美作用才真正得以實(shí)現(xiàn)。王夫之從讀者的角度進(jìn)行論述,使得“思無邪”獲得了新的意義。每一個(gè)閱讀者必須具有“自正之情”來區(qū)別貞淫,通過這種方式改變?nèi)说男郧椋瑥亩鴮?shí)現(xiàn)《詩(shī)經(jīng)》真正的功能。
(三)興觀群怨
《論語·陽(yáng)貨》中提出了興觀群怨:“子曰:‘小子何莫學(xué)夫詩(shī)?詩(shī)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yuǎn)之事君;多識(shí)于鳥獸草木之名。’”[15](P185)這一思想逐漸成為中國(guó)詩(shī)學(xué)的重要范疇。蕭?cǎi)Y說:“自孔子出此語以來,響應(yīng)者代不乏人,但以詮義之開拓、運(yùn)用之廣泛而言,當(dāng)首推船山。此一概念于船山詩(shī)學(xué)意義之重大,亦非比尋常。”[16](P135-136)
第一,王夫之把這四者作為一個(gè)整體,而統(tǒng)一的核心是“情”。“詩(shī)之泳游以體情,可以興矣;褒刺以立義,可以觀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含其情而不盡于言,可以怨矣。”[17](P915)“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18](P808)情是這四者的內(nèi)核,王夫之直接以四情來概括興觀群怨,興觀群怨是情的表達(dá)形式,情貫穿興觀群怨始終。沒有情,就不能有效地興,無法觀,不能群,更難以怨,四情無處不在,無所不包。人在四情中,游刃有余,沒有情感也就沒有詩(shī)歌創(chuàng)作,更無所謂審美感受、審美欣賞。
第二,興觀群怨之間的相互作用。“于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于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18](P808)從興開始,因?yàn)闆]有興就不會(huì)有詩(shī)歌的創(chuàng)作,興為詩(shī)歌創(chuàng)作提供了可能性。通過觀自然,對(duì)于外在之物的全面了解,使得興更為深入;而觀的內(nèi)容也可以成為興的對(duì)象,這樣觀會(huì)更具審查性。通過群,大家一起切磋交流,能夠有效地達(dá)到怨的目的,怨使“群”之中的情感更加真摯。“可以興觀者即可以群怨”,興觀和群怨之間相互聯(lián)系。王夫之還認(rèn)為:“得其扢鼓舞之意則‘可以興’,得其推見至隱之深則‘可以觀’,得其溫柔正直之致則‘可以群’,得其悱惻纏綿之情則‘可以怨’。……‘可以’者,可以此而又可以彼也,不當(dāng)分貼《詩(shī)》篇。”[14](P259-260)《詩(shī)經(jīng)》中的篇目并不一定如前人所言每一篇或興或觀或群或怨,而是可以相互對(duì)照,既可能興,也可能觀,也可能群,也可能怨。這四者之間沒有嚴(yán)格的界限,存在可以游動(dòng)的可能性,這也使得對(duì)于詩(shī)歌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都有了更為廣闊的空間,而不會(huì)被束縛在某一特定的創(chuàng)作目的中,這樣才有助于更好地發(fā)揮詩(shī)歌功用,否則就會(huì)“拘于象數(shù)”、無法達(dá)到“詩(shī)之用廣”的作用。
第三,王夫之也強(qiáng)調(diào)興觀群怨的適度問題。他認(rèn)為:“群而貞,怨而節(jié),盡己與人之道,盡于是矣,事父事君以此,可以寡過,推以行之,天下無非中正和平之節(jié),故不可以不學(xué)。”[19](P316-317)“貞”、“節(jié)”、“中正和平”是儒家詩(shī)學(xué)思想的體現(xiàn)。在進(jìn)行情感宣泄的時(shí)候,不能肆無忌憚,應(yīng)有所節(jié)制、含蓄委婉,從而實(shí)現(xiàn)中正和平的狀態(tài)。“可以群者,非狎笑也。可以怨者,非詛咒也。不知此者,直不可以語詩(shī)。”[8](P540)群怨不可過度,強(qiáng)調(diào)節(jié)制地抒發(fā)、宣泄情感。只有平情才適合詩(shī)歌的表達(dá),“平情說出,群怨皆宜”,“攝興觀群怨于一爐錘”,才是風(fēng)雅的表現(xiàn)。王夫之尤其還強(qiáng)調(diào)表現(xiàn)怨的時(shí)候不能過度,不能謾罵,反對(duì)情感過于直露的詩(shī)歌。“長(zhǎng)慶人徒用謾罵,不但詩(shī)教無存,且使生當(dāng)大中后直不敢作一字。”[7](P976)他還批判司馬遷的“怨毒之情”太過:“馬遷以刑余無諫諍之責(zé),后事而摘毫毛之過,微文而深中之,怨毒之情也。”[3](P456)他貶斥杜甫詩(shī)歌中的情緒過于直白的表達(dá),因?yàn)榍楦杏绕涫窃骨椋^于尖銳完全不符合“怨而節(jié)”的標(biāo)準(zhǔn)。怨是國(guó)家治理中的消極因素,王夫之就用“貞于情者怨而不傷”來對(duì)怨進(jìn)行協(xié)調(diào),強(qiáng)調(diào)“怨而貞”,實(shí)現(xiàn)兩者之間的統(tǒng)一。總之,王夫之對(duì)于興觀群怨的反復(fù)論述,最終目的是“可以興觀群怨者即可以事君父,忠孝善惡之本,而歆于善惡以定其情,子臣之極致也”[17](P915)。無論他如何強(qiáng)調(diào)詩(shī)的重要性,情的重要性,還是沒有能夠跳出儒家倫理道德的規(guī)范。
以上僅僅選取了王夫之詩(shī)學(xué)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進(jìn)行分析,雖然我們分別論述了各個(gè)概念的繼承和超越,但其實(shí)它們各自之間并不是彼此獨(dú)立,而是整合在王夫之對(duì)于傳統(tǒng)儒家詩(shī)學(xué)主要觀念、思路、話語的言說中。王夫之依據(jù)自己的言說方式把這些概念統(tǒng)籌在一起,實(shí)現(xiàn)了內(nèi)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現(xiàn)實(shí)世界和理想世界、詩(shī)歌創(chuàng)作和詩(shī)歌欣賞的統(tǒng)一,各個(gè)范疇概念之間也有了連接的可能性,不再割裂。這才是真正意義上對(duì)于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詩(shī)學(xué)的繼承和超越,既重視詩(shī)性和倫理的同一,又發(fā)揮新的內(nèi)涵。
三
明末清初是一個(gè)天崩地裂、“地坼天乖”的時(shí)期,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思想上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變化,王夫之的一生經(jīng)歷了兩個(gè)歷史朝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
明王朝后期新的經(jīng)濟(jì)因素出現(xiàn),社會(huì)矛盾激化,政治危機(jī)加劇和民族矛盾惡化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引發(fā)了明王朝的動(dòng)蕩,李自成領(lǐng)導(dǎo)的農(nóng)民起義直接導(dǎo)致了明王朝的滅亡,這都沖擊、震撼著王夫之的思想。他一直希望上層階級(jí)能夠關(guān)心民生疾苦,緩和階層矛盾,但都無法改變現(xiàn)狀。從清朝建立開始,滿族統(tǒng)治者對(duì)漢族人民實(shí)行了各種殘酷的政治手段和壓迫,外族的統(tǒng)治也讓王夫之的思想感情產(chǎn)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始終堅(jiān)持自己既定的理想和信念,自始至終都以明朝遺民自居。
在文化領(lǐng)域,晚明時(shí)期的文化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文化語境。理學(xué)已經(jīng)逐漸走向衰敗,心學(xué)也出現(xiàn)分化,禪學(xué)之風(fēng)興盛,文藝思想也醞釀著更為激烈的變化。李贄的“童心說”、袁宏道的“性靈說”給文壇帶來了新的生機(jī)活力的同時(shí),也引發(fā)了新的問題。他們過分強(qiáng)調(diào)本心、情感的重要,導(dǎo)致明代后期情感的過分張揚(yáng),擺脫了道德倫理、政治思想的束縛,走向了另外一個(gè)極端。王夫之正是處在思想震撼、文化多樣的語境中,因而一方面必然對(duì)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反思、整合,另一方面又有所發(fā)展和突破。
除了社會(huì)歷史原因之外,個(gè)人原因也是王夫之能夠?qū)χ袊?guó)傳統(tǒng)倫理詩(shī)學(xué)進(jìn)行繼承和超越的重要因素。王夫之自小有著良好的家學(xué)傳統(tǒng),受到父親、叔父等人的啟蒙和教育,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學(xué)術(shù)基礎(chǔ),同時(shí)在人格修養(yǎng)、道德情操方面也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王夫之本人廣泛涉獵了古代經(jīng)典著作,勤奮好學(xué)、善于思考,即使人生道路坎坷,也從未停止過寫作,用自己獨(dú)到的解讀,表達(dá)人生理念,學(xué)術(shù)性的思考也被賦予了選擇的意義。王夫之并非僅僅局限于理論思考,他也參加了革命實(shí)踐活動(dòng),雖然都以失敗而告終,卻直接促成了他思想的轉(zhuǎn)變。王夫之最終選擇著書立說作為實(shí)現(xiàn)人生理想和目標(biāo)的方式,是他一步一步不斷經(jīng)歷實(shí)踐的結(jié)果,即使在面臨各種人生考驗(yàn)、挫折和風(fēng)險(xiǎn)的時(shí)候,他都從未改變過自己的信念。
王夫之生活的歷史文化語境和個(gè)人的選擇成就了其“懷貞”的一生,這其中既有可能性,也有其必然性。王夫之的人生選擇也決定了他的詩(shī)學(xué)思想的闡釋道路。一方面有著對(duì)于傳統(tǒng)文化、儒家思想的堅(jiān)持,無論時(shí)代如何變化,都無法動(dòng)搖這一信仰;另一方面新的歷史發(fā)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新的變化,必然會(huì)給思想家?guī)沓絺鹘y(tǒng)的可能。他正是在這種語境下,有效地把時(shí)代因素和個(gè)人因素結(jié)合起來,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詩(shī)學(xué)中的某些因素有所繼承,但同時(shí)又能進(jìn)行超越。
[1]蔡元培.中國(guó)倫理學(xué)史[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
[2]毛詩(shī)序[A].中國(guó)歷代文論選(第一冊(cè))[C].郭紹虞,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清)王夫之.詩(shī)廣傳[A].船山全書(第三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4](清)王夫之.讀通鑒論[A].船山全書(第十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5]胡家祥.志:中國(guó)哲學(xué)的重要范疇[J].江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6,(8).
[6](清)王夫之.尚書引義[A].船山全書(第二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7](清)王夫之.唐詩(shī)評(píng)選[A].船山全書(第十四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8](清)王夫之.古詩(shī)評(píng)選[A].船山全書(第十四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9](清)王夫之.周易外傳鏡銓(下)[M].陳玉森,陳憲猷,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
[10](清)王夫之.禮記正義[A].十三經(jīng)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1](清)王夫之.禮記章句[A].船山全書(第四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12](清)王夫之.說文廣義[A].船山全書(第九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13]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4](清)王夫之.四書箋解[A].船山全書(第六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15]論語譯注[M].楊伯峻,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16]蕭?cǎi)Y.抒情傳統(tǒng)與中國(guó)思想——王夫之詩(shī)學(xué)發(fā)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清)王夫之.四書訓(xùn)義(上)[A].船山全書(第七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18](清)王夫之.姜齋詩(shī)話[A].船山全書(第十五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
[19](清)王夫之.張子正蒙注[A].船山全書(第十二冊(cè))[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