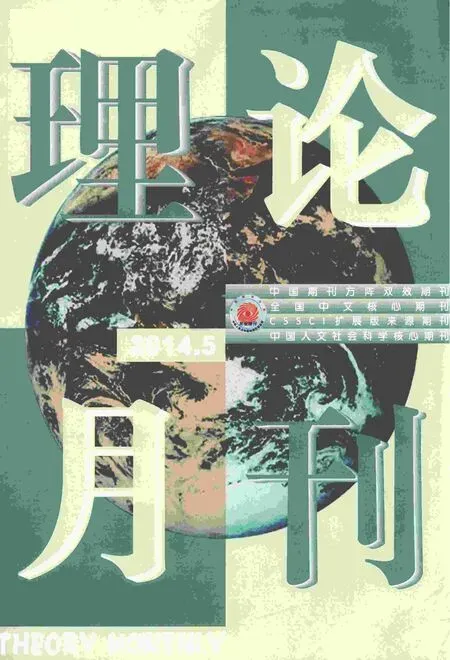論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
程 皓
(西南政法大學 法學院,四川 綿陽 621010)
一、引言
按照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劃分,人類社會迄今已經經歷了三個主要的發展階段,即從最初的農業化社會階段,漸次過渡到工業化社會階段,再逐步邁入當前的生態化社會階段。在當前的生態化社會階段,由于面臨著工業化社會階段所遺留的諸多問題,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已成為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而人類也正在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生態社會對傳統法律提出了挑戰,因為它已經難以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現實。正如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人類的法律必須重新制訂,以使人類活動能與不變的、唯一的自然法保持協調一致。[1]這種變革被稱為法律生態化,即將保護自然環境、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以及防治環境污染的內容注入傳統法律之中,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目標。
在漫長的古代社會,我國的法律制度一直是“諸法合體”、“重刑輕民”,缺乏產生專利制度的社會環境。1944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公布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專利法,但是在戰爭環境下,這部法律并沒有在大陸地區全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專利制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得到重視,致使技術發明無法獲得應有的法律保護,直至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才在各種內外壓力之下重新開始研究建立專利制度的必要性。1985年4月,經過歷時五年的24次修改,新中國首部專利法才得以頒布實施,并在歷經1992年、2000年、2008年三次修訂后,一直沿用至今。專利法的頒布與實施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成為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2]2011年,中國年度專利申請總量已經居于世界領先地位。①提供商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最近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中國的專利申請總量在2011年超過日本和美國,居世界第一。參見國家知識產權局規劃發展司2010年專利統計公報。同年,中國的經濟總量也超過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3]
遺憾的是,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帶給我們的不僅僅只是福音。相反,由于我國超常規的發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高污染和高自然資源消耗實現的,從而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甚至影響到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得不反思傳統專利法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缺失,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對專利法實行生態化改革的相關建議。
二、專利法生態化改革的理論基礎
(一)專利法生態化改革的倫理學基礎
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念認為,人類作為地球的主宰者,在自然界處于中心地位,理所當然應當成為唯一的倫理主體和道德代言人,人類的價值評價和道德地位無疑也應當優越于自然界的任何其他物種。根據這樣一種邏輯,人類有權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毫無節制地向自然索取,無視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存在價值,把自身的發展進步建立在對自然資源掠奪性開發利用的前提和基礎之上,而不需要因此而付出任何代價。這種價值觀具有明顯的反自然性質,已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引入了絕境。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日益加劇, 以動物權利/解放論 (Animal Liberation/Right Theory)、 生物中心論 (Biocentrism)、 生態中心論(Ecocentrism)和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等為代表的非人類中心主義(Anti-Anthropocentric)倫理學對人類中心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所有這些努力的結果,終于使人們基本達成這樣的共識,即人類僅僅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之一,自然界權利主體和道德共同體的范圍應當包括人類、動物、植物和所有生命共同體,甚至還需進一步拓展至土地、山脈、河流、乃至整個生態系統。
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大自然也應當擁有權利,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應當被納為道德范疇,由一定的倫理原則來制約和調整。[4]這場變革把人類由大自然的主宰變為普通公民,摒棄了狹隘的人類中心論,確立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觀念,為專利法生態化改革提供了倫理學基礎。
(二)專利法生態化改革的經濟學基礎
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Kenneth Boulding)在1960年代正式提出了生態經濟學的概念,這是生態學和經濟學相互交叉、相互滲透、有機結合形成的新興邊緣學科。它也被公認為是專利法生態化改革的經濟學基礎。
生態經濟學認為,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生態與經濟的矛盾已成為當代社會發展中的一對基本矛盾。根據這一認識,人類應當深刻反思現行的經濟增長模式,重新定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并與自然界締結新的契約。人類應當努力尋找一種能夠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全新經濟增長方式,這種方式就被稱之為生態經濟,基本特征是采用新的具有更高生產力水平的“綠色技術”,注重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作為新的生產力的代表,生態經濟將推動人類社會從工業社會逐漸向生態化社會轉化,其基本要求是:在遵循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同時,也要遵循自然界的生態平衡規律;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將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作為基本要求,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注重保護生態環境。[1]
(三)專利法生態化改革的法理學基礎
生態本位主義的法律觀是專利法生態化改革的法理學基礎。傳統的法律觀是與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念相適應的,把人類看做自然界的主宰者,任何其他物種都被視為人類可以隨意役使的對象。即使法律規定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也是著眼于人類的功利主義立場。
和傳統的法律觀不同,生態本位主義法律觀認為生物擁有內在價值,作為一個不斷進化的生態系統,人類只是大自然的后來加入者之一。大自然的價值在人類出現之前早已經存在,因此自然應當具有獨立的權利和價值,而不僅僅是人類的權利客體和價值評價對象。[5]生態本位主義法律觀強調以生態利益為本位,人類與自然應當和諧共處,要求“法律制度應圍繞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而精心設計,既要體現人的權利,也要反映生態自然的權利”。[6]同時,生態本位主義法律觀主張人類應當順應自然規律,尊重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在不破壞生物圈生態平衡的前提下,遵守最適合條件可持續獲得利益的原則。當代人、尚未出生的后代人和世界上其他生物都應當被納入法律規范的范疇之內,當代人需要為后代人肩負起維護生態環境的歷史義務,而不能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損害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應當追求人類與自然生態之間的共存共榮。
三、專利法生態化改革的作用機制
“法律是功能性的”,專利法同樣也不例外。正如法學家達維德所說:“現代社會有一種以法為手段來組織和改革社會的新趨勢,法已不再被看作單純的解決糾紛的手段,而逐漸被公民們甚至法學家們視為可用以創造新型社會的工具。”為了阻止生態環境的繼續惡化,對“綠色技術”的大力研發和廣泛應用已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共識。①綠色技術〔GreenTechnology),又稱生態技術(Eco-Technology),通常指能夠節約資源、避免或減少環境污染的技術。綠色技術的發展需要通過經濟利益來加以誘導,而經濟利益的終極體現是個人產權。從法律功能上看,專利法通過授予發明人專利權,使其在一定期限內擁有對其發明的獨占權,這同樣也是實現綠色技術利益產權化的主要制度。因此,專利法將有能力通過生態化的改革,對綠色技術的研發、傳播和應用施加影響,進而發揮對生態環境保護的積極作用。
(一)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將有利于激勵綠色技術研發
專利法對發明創造的激勵功能,是通過授予專利權人在一定期限內的排他獨占權利來實現的。[7]憑借這種獨占權,專利權人可以通過轉讓或實施生產取得經濟利益,收回投資,這樣才有繼續進行開發的積極性。這種激勵能有效地挖掘技術發明人的智力潛能,積極推動其創造出更為豐富的技術成果。
以往的經驗表明,如果一項技術發明考慮了生態環境保護因素,通常會增大發明難度,并大幅增加未來技術轉變為商品的成本。現行專利法并未將符合生態環境保護要求作為授予專利的必要條件之一,這就導致技術發明人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會以犧牲環境利益作為代價。
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將把生態環境保護因素與專利授予條件聯系起來,通過外在強制力量規避新技術可能帶來的環境惡化風險。既然不符合環保要求的技術將不能被授予專利,技術發明人將不得不在創造過程中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取向,進而轉向對綠色技術的關注,從而激勵綠色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并增加社會對綠色技術的認同。
(二)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將有利于促進綠色技術傳播
技術的公開是專利制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專利法要求受專利保護的技術成果內容要以專利文獻的方式向社會公開,這就使得技術成果得以迅速傳播,大大加快了技術的擴散,方便了公眾對技術的獲取。研究人員在進行技術開發之前,能充分利用專利文獻了解到該技術領域的最新動向,從而有效避免了重復研究和資源浪費。據W IPO的一項研究表明,全世界有超過九成的發明創造信息都是通過專利文獻被首先披露出來的。有效地運用專利文獻,不僅能提高研究起點,還能夠節約大約40%的科研經費和超過60%的開發時間。[8]
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將使更多的綠色技術內容寫入專利文獻,促使研究人員更加關注綠色環保技術,加速綠色技術的傳播與擴散。通過專利文獻的傳播方式,一項綠色技術創新將有可能帶動一批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新技術產生,甚至改變該領域內的整體技術創新模式。
(三)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將有利于推廣綠色技術的應用
一般來說,技術成果只有在市場上得到推廣和應用,才能為專利權人帶來經濟效益。因此,專利權人自始至終都以市場需求為目標,盡力推廣和實施其專利技術。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將綠色技術列為法律優先認可和保護的對象,積極鼓勵專利權人將先進的綠色技術專利應用到生產實踐之中去,將有助于推動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9]
此外,在保護專利權人利益的同時,專利法也注重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①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4條、第5條。因為預見到專利權人的私人利益如果過度膨脹將有可能會損害公共利益,從而無法實現專利制度的公共目標,專利法事實上一直在努力尋求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將使綠色技術專利在生態環境惡化的特殊情況下有可能被強制許可使用,從而在應用綠色技術專利保護公共利益方面有法可依,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防止生態破壞的作用。
四、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方向
TRIPS協議中規定的環保例外權,是生態環境保護觀念在國際公約中的發展趨勢的集中體現。②參見TRIPS協議第27條。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TRIPS協議和其他國際公約的相關規定理應成為我國專利法生態化改革的指導方向。遺憾的是,盡管被多次修改,我國專利法對有關生態環境保護內容的規定仍然籠統且缺乏針對性,更缺少相應的執行措施,從保護理念和方法上都不能達到技術環保的要求。生態環境是人類的生存基礎,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生態導向的專利制度。基于此,對專利法進行生態化改革已經成為中國法制發展的迫切需要。
(一)專利法立法宗旨的生態化改革
專利法的立法宗旨決定了實施專利制度所要達到的目標,是統領專利法的靈魂。依據專利法第1條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專利法以功利性為基本價值取向,其立法宗旨主要是通過實施專利制度,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實現經濟快速發展。這樣的立法宗旨,過分強調經濟利益至上,將不可避免地忽略環境利益,明顯已經無法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專利法立法宗旨的生態化改革,需要賦予專利法新的使命和責任,使其具有生態性和前瞻性,改變過去單純追求經濟利益的目標,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協調發展作為最終目標。在法律規定上,將促進科技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結合起來,將專利權的法律保護置于環境的承載力和人類道德所允許的范圍以內,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二)專利審查制度的生態化改革
我國現行專利法規定,對授予專利的發明和實用新型應當審查其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這長期以來一直被公認為專利審查的標準。③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22條。但是,正如前文已經論述的那樣,這種標準體系將可能使發明者在從事技術發明過程中不顧及其生態環境影響。專利審查制度的生態化改革,對上述標準提出了質疑,認為應當將環保性(Greenness)作為一個新的標準引入專利制度,從而鼓勵發明出綠色的產品和工藝。
反對者認為,專利法的職責是鼓勵、促進技術創新,無法勝任區別創新技術是否環保。[10]“對新技術的道德評價應依據現實證據,而不能憑借所謂的可能的危險的預測,以免因此損害發明人的合法權益”。[11]對專利技術的環保性審查應該由農業、衛生、科技等其他部門來負責,而且應當發生在該技術進入實質應用階段以后。這種說法看似有理,但令人遺憾的是,事實上采用后端控制的方法將無法避免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歷史上發達國家曾走過“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盡管在這一過程中消耗了大量的物力財力,但仍然不能改變污染的事實,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銳減等等環境問題。因此,發展中國家應當汲取教訓,采用事先控制的方法,防患于未然,從源頭上遏制有害技術的應用,這比花費時間和資源再去救治更為有效。
對環保性標準的審查,關鍵在于如何界定環保性。根據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關于生態效益的界定,環保性應包括以下方面,即減少產品和服務的材料消耗、減少產品和服務的能量消耗、減少有毒物的排放、增加材料的再循環利用、盡可能使用可再生的能源、增加產品的耐用性、增強產品的服務強度等。[12]雖然制度設計者事先不可能完全界定環保性的內涵,但三百多年來,專利制度已成功促進了新的和有用技術的進步,這是因為專利審查建立在相對標準的基礎上。因此,和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一樣,我們無需預先界定環保性的完整內涵,仍然可通過新的專利申請與先前發明的比較,個案審查發明創造的環保性,以達到環保審查的目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借鑒英國等國的先進做法,對符合綠色技術的專利申請,可以嘗試開辟綠色通道,縮短審查程序,提供更為便捷的審查服務。
(三)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的生態化改革
根據我國專利法的規定,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時,或者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國家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①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49條。此外,專利法還有基于專利權濫用、藥品專利和從屬專利的強制許可制度。②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48條、第50條、第51條。但是,這些強制許可制度的內容均未直接反映生態環境保護要求,環境利益并未明確被納入到專利法規定的公共利益之中,這給環境利益使用強制許可制度造成了法律困難。TRIPS協議也未對“公共利益”作出明確規定,而是允許各國根據其國情來決定“公共利益”的內容和范圍。③參見TRIPS協議第8條。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術及資金有限,應充分利用TRIPS協議預留的制度空間,吸收國際上其他國家的一些經驗和做法,完善我國的強制許可制度。
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的生態化改革的具體做法是,將環境保護目的明確規定為“公共利益”的一種,以此來彌補現行強制許可制度沒有關于為了環境保護的需要,可以對綠色技術實施強制許可規定的缺失。當我國基于環境保護的目的,需要實施強制許可時,上述規定將有助于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五、結語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們帶來幸福還是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要實現科學技術與生態環境的共同進步和協調發展,法律的保障作用至關重要。人類已經邁入生態化社會階段,法律的生態化改革亦是大勢所趨。[13]因此,專利法——作為鼓勵科學技術發展的最重要法律之一,同樣也要進行生態化改革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作為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最快,同時環境污染也是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中國專利法的生態化改革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中國第一部專利法頒布至今,中國專利制度的建立還不到70年時間,其間屢受非議、甚至長期被廢止。面對來自外部世界的法律改革壓力,我們長期處在被動接受的不利地位,難以在知識產權法制發展的國際舞臺上發揮出一個大國應有的作用。生態化改革是世界各國專利法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應當把握住這次機會,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在推動中國專利法律體系向前發展的同時,在世界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1]曹明德.生態法的理論基礎[J].法學研究,2002,(5):104.
[2]何東明.和諧社會視野下共贏性國際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構建[J].河北法學,2009,(4):197.
[3]成都晚報.2010年度經濟總量中國首次超過日本.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10121/12529291562.Shtm l.首次訪問時間:2011-01-21.
[4]鄒彩霞.生態自然權宣言[J].河北法學,2010,(10):63.
[5]〔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大自然的價值以及人對大自然的義務[M].楊進通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45.
[6]陳泉生.可持續發展與法律變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54.
[7]劉宇暉.論專利強制許可制度[J].河北法學,2010,(4):106.
[8]江鎮華.怎樣檢索中外專利文獻[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1.120.
[9]錢琨,潘雄鋒.專利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及實證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38.
[10]Micheal A.Gollin.Driving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ies for a Dynamic World[M].2008:334-335.
[11]崔國斌.基因技術的專利保護和利益分享[A].知識產權文叢:第三卷 [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271.
[12]萬志前,鄭友德.知識產權制度生態化重構初探[J].法學評論,2010,(1):49.
[13]李靜云,王世進.生態補償法律機制研究[J].河北法學,2007,(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