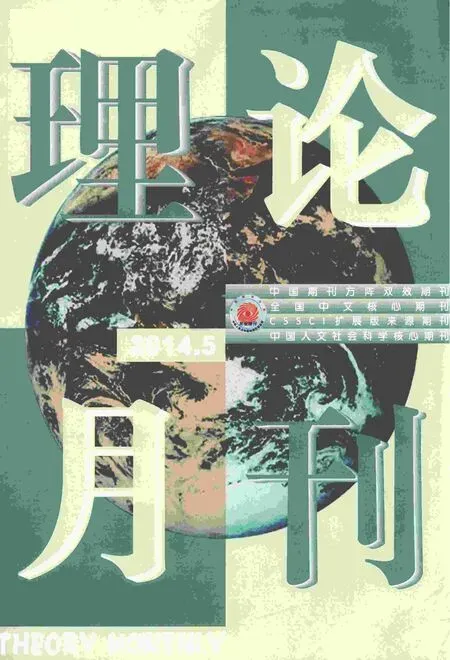當下中國社會民意的概念、特征與形態分析
張 強
(長沙理工大學 文法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6)
這是一個眾聲喧嘩、民意鼎盛的年代。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民意,即民眾作為一個集合體的意見表達,從未像今天這般炙手可熱和地位崇隆。民意,引領著政府進取和社會發展的方向,無可爭辯地成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之一,政府公共政策的制訂、政治人物的雄韜偉略,無不以民意為依歸。當然,在很多時候,民意也被異化為一種工具,被各種利益集團反復地利用,以達到各自的目的。無論如何,在當下中國社會,民意已經上升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標志著權威主義時代無可挽回地式微,以及一個雖仍顯粗礪卻生機勃勃的大眾時代的降臨。
然而,在這個言必稱民意的時代,一個令人遺憾的問題是,我們對于民意的認知事實上并不透徹,甚至完全不甚了了。我們對于這個經常脫口而出的詞匯,所持有的理解常常是抽象而模糊的,是大而無當和缺乏內涵的。一定程度上,這種對于民意的膚淺體認,妨害公共理性的涵養,更阻礙國家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因此,透視和辨析民意及其表現出來的各種表征,顯得必要又迫切。
一、民意的概念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里系統而又富有創見地闡述了民意的概念。按照盧梭的分析,民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公意;一種是眾意。公意是絕大部分或全體民眾的共同意志;而眾意則是個體的意志和團體的意志,二者可以合稱為個別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或主權的意志,這一意志無論對被看作是全體的國家而言,還是對被看作是全體的一部分的政府而言,都是公意。”[1]“公意永遠是公正的,而且永遠以公共利益為依歸。”[2]“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以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并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由此可見,盧梭對公意的推崇。
而另一方面,盧梭則對眾意持有某種程度上的負面解讀:“個別意志由于它的本性就總是傾向于偏私,而公意則總是偏向于平等。”[4]“公意與眾意經常有很大差別,公意只著眼于公共的利益,而眾意則著眼于私人利益,眾意只是個別意志的總和,但是除掉這些個別意志間正負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則剩下的仍然是公意。”[5]
盧梭對于民意的概念性界定,最值得珍視的一點是,將民意細分為多數人的意見和少數派的意見,二者或有沖突,但都在民意概念的統攝之下。這對于我們系統而健全地理解民意,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國內一些學者對于民意概念的界定,往往是從盧梭“公意”的角度去闡發,而忽視了從盧梭“眾意”的角度去觀照。
比如:程世壽:“民意是人民意識、精神、愿望和意志的總和,作為社會真理的坐標,是判定社會問題真理性的尺度。”[6]吳順長:“民意不單單是人民范疇中某個群體或某個個體的政治主張和思想愿望,而是人民這個集合體的意向趨勢,它所反映的總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共同意志。”[7]
分析國內部分學者對于民意的定義可以看出,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盧梭民意概念中的一個方面,即公意,當作了民意內涵的全部。而且在他們的定義中,也假定民意天然地具有正義性和合法性,是毋庸置疑和無可辯駁的,是鐵板一塊和集體行動的。但事實上,這樣的概念恐怕與民意的全部復雜性并不吻合,其間甚至有不可小覷的抵牾。
筆者傾向于認為,應該從一個整全性的角度,充分體察民意本身的全部復雜性與難以參透性,既要看到民意的主流,也要看到民意的各種支流,二者的有機結合才算是民意的全部。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嘗試給民意下這樣的定義:民意即公民基于自身的觀點、立場和態度所表達的社會意見與社會愿望的總和,它是個體意見和群體意見、顯性意見與隱形意見、主流意見與非主流意見,正義意見與非正義意見的激蕩、雜糅與融匯。這樣一種概念性定義的開創性在于:其一,以“公民”作為民意表達主體,強調其權利性與異質性,而不再以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人民”作為想當然的表達主體;其二,將民意視為一種發散型的網狀結構,強調其層次性、多元性與動態性,而不再將民意視為一種單箭頭的、先驗的線性結構。筆者以為,這樣一種概念更加符合現實與民意真相。
必須予以澄清的是,民意并不代表真理本身,它并具備真理性或者神性,不排除民意在某些情境下帶有瑕疵甚至謬誤。民意中的少數派,無論怎樣都值得予以恰當地尊重,因為它們也是民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越是少數派的意見,越需要我們另眼相待。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文明社會的責任。
二、當下中國社會民意的時代特征
當下的中國正值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狂飆突進的同時,也充滿諸多矛盾與糾結。反映在民意上,就是一邊是激情澎湃,一邊是哀怨叢生。時而悲觀,時而樂觀;時而堅強,時而脆弱;時而迷惘,時而清晰,常常呈現出社會轉型期基于特殊國情的一些明顯的時代特征:
1.“混沌—迷惑”性
事實上,盡管在我們的公共輿論中充斥著“民意”這樣的字眼,但恐怕沒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民意是什么、民意的真正訴求又是什么。就像人民這一概念一樣,我們在使用民意這一概念的時候,也往往是在抽象的意義上使用它,缺乏對其的精確界定與清晰表達。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民意都是復雜多樣的,很多時候也是沒有方向感的,尤其是在中國當下社會,當整個國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民意自然不可能是鮮明清晰和完全有跡可循的。在很多情況下,它是曖昧的、混沌的,需要仔細摸索和辨析的。
舉例來說,以雅安地震后,身陷尷尬的中國紅十字會為例:一面是名譽掃地、臭名昭著、遭世人唾棄;而另外一面則是收到5.66億元捐贈款物,占所有捐款的53%以上。由此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合理卻又不合理的結論:中國紅十字會的惡濁形象似乎并沒有影響人們對它的信任度。由此我們也不得不反思,中國紅十字會真的已經名譽掃地、被善良的人們棄之如敝屣了嗎?
對此,青年時評家曹林先生在一篇評論中寫道:“網絡上一邊倒地對紅十字會喊‘滾’和‘捐你妹’,現實中的人們并不一定就都不信任紅會了;網絡上一邊倒地反對水價上漲,其實現實中很多人是能理性地意識到資源性產品漲價的必要性;網絡上一邊倒地支持政府各種限購,現實中投票卻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結果;網絡上一邊倒地反對政府取消長假,換個平臺進行的民調結果卻完全不同;網絡上提起拆遷都是一片受害者的罵聲,現實中很多人卻寄望于拆遷改變自己的居住環境;網絡上提起“高房價”好像人人都咬牙切齒,現實中很多有房者都期待房價上漲房產增值……”。[8]
顯然,民意是混沌的,甚至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虛假性和難以捉摸性。背后則反映出人們對于一些社會問題缺乏堅定而自洽的立場,處于猶疑彷徨的狀態,甚至人們自身也不知道該采取何種立場才是正確的,體現出一定的隨意性與盲目性,如此這般,都導致了民意的混沌。
2.“多元—層次”性
民意絕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鐵板一塊和通往一個方向,事實上民意是一個復雜多元、多方向、立體而豐滿的網狀結構,它遠遠不是一條“單向度的直線”的意象所能概括的。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同社會階層與利益群體不斷涌現。而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導致民意的多元化。人們基于不同的立場和利益取向,展開或溫和或激烈的辯論,以期壓倒對方的立場與利益,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與價值期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下的中國社會,隨著政治文明的演化以及媒體技術的空前發達,為不同民意的表達提供了廣闊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除了一些特定的敏感話題,人們可以借助各種平臺,比較充分而自由地表達自己對社會問題的意見和觀點,形成了一個紛繁蕪雜而又生機勃勃的多元民意場。
此外,民意也是分層的。大體來講,民意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個體民意、群體民意與整體民意。梁漱溟先生曾說,“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的機會,多少感情要求被抑壓,被抹殺。”[9]世易時移,現在不同以往,現在的公民個體勇于、敢于和善于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們構成一個個微弱卻尊貴的個體民意,成為民意的最廣泛的基礎性要素。
群體民意也在成長,隨著政治對社會的松綁,眾多民間自治組織獲得了快速發育成熟的機會。各種行業協會、公民組織、公益組織、社團組織紛紛建立和發展,它們的意見成為民意的重要組成部分。
整體民意,只是一種理想性的民意。事實上,很難出現籠罩性的全體性民意,總有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見,這是人性以及社會的復雜性決定的。著名學者劉建明認為,“把70%視為民意量度的臨界點,反映了人口比例的絕對優勢,無疑具有民意的品位。”[10]這似乎意味著,只要在統計學意義上超過70%的民眾認同某一種觀點或意見,就可以稱之為整體民意。
3.“外強—內脆”性
當代中國,民意的確是一種耀眼的價值。任何人都無法忽視民意的存在及其強大的影響力。在官方的表達口徑中,民意甚至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合法性,成為政治正當性的重要資源。江澤民曾經說過,“及時、準確地反映社情民意,積極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多做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安定人心的工作,努力為黨和政府排憂解難。”[11]胡錦濤也曾經說過,“各級領導干部要自覺貫徹群眾路線、切實轉變作風,多做順民意、解民憂、得民心的實事,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12]習近平同志更是在多個場合反復提及民意的重要性。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就著重提到,“要從人民偉大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辦好順民意、解民憂、惠民生的實事,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13]
在網絡民意場上,我們更是可以輕易便能體會到民意的喧囂及其強悍的影響力。多少貪官是被民意送上法庭的,多少冤案是在民意的壓力下沉冤昭雪的,多少善政是在民意的壓力下慢慢出臺的,歷歷在目,數不勝數。
然而,在一派繁榮而強大的民意表象之下,我們也不難窺見和感受民意的脆弱與無力。民意不是萬能的,民意不能改變的事情要遠遠多于它能改變的事情,即使它改變的事情,也多是個案,遠遠不能改變整體形勢與格局。民意把一個貪官送入了囚籠,但還有無數的貪官前腐后繼;民意讓一個冤案大白于天下,但還有很多的類似案例隱藏在鐵幕背后;民意讓一個善政浮現于公共領域,但還有更多的惡政揮之不去;民意或許能改變個案,但不能改變全部;民意或有助于一時,但無力裨益于長遠。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民意千呼萬喚,但終究無法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民意望穿秋水,但一次次折戟沉沙;廢黜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民意已經過河,官方卻還在摸石頭。凡此種種,無不證明民意的脆弱性。
4.“撕裂—對抗”性
基于不同立場與利益的民意,自然會產生辯論和爭執。在某些尖銳問題上,甚至會產生民意的撕裂,以至于激化成意見和行為的對抗。
當代中國社會,呈現出諸多方面的分裂:階層分裂、城鄉分裂、貧富分裂、精英與大眾的分裂等等。這些形式的分裂,都會反映到民意的分殊與對抗上面。
比如關于“異地高考”的問題,就撕裂為兩種截然相反又激烈沖突的民意。支持異地高考的民意認為,異地高考是一項不可褫奪的權利,它涉及教育公平與對外地人口的基本尊重,以憲法和教育法的名義,異地高考無論在現實中會遭遇多少困難,都必須堅決執行。
但反對異地高考的民意則認為,如果徹底放開異地高考,北上廣等教育發達的城市將不堪承受,洶涌而來的外地人口將徹底擾亂這些地區的教育秩序,分割當地原住民的本也不足的教育資源,此外異地高考還極有可能導致浩浩蕩蕩的高考移民,負面后果巨大,在目前狀況下不具備實行的條件。
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意見嚴重對立。在具有標本意義的“占海特事件”中,甚至引發街頭對抗。2012年10月25日,支持異地高考的標志性人物占海特及其支持者在上海大沽路100號上海教委,與意見對立組織“守護者聯盟”發生沖突,最終以占海特父親被警方拘留而收場。由此可見,雙方意見分歧之難以調和。
民意的撕裂和對抗首先造成的是一個劣質的輿論場和民意場,在這里人們基于立場而區分敵我,沉溺于單方面意見的表達與自我認同之中,并且傾向于強化既有的意見和觀點,隨時準備去征服別人,最終陷入難以溝通的偏執之中。這樣的民意場中缺乏共識達成的條件和氛圍,缺乏溫和、理性和建設性的討論空間,民意的撕裂和對抗,造成并加劇社會的撕裂和對抗,對轉型中國而言,這是非常遺憾的一幕。
三、當下中國社會民意的基本形態
1.顯性民意與隱性民意的統一
顯性民意,即公開的民意,是公民借助各種平臺,公開表達出來的觀點和意見。現階段,公民表達意見的平臺和管道有很多,比如新聞媒體(傳統媒體、新媒體、自媒體)、代議制平臺(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信訪體制、民間自治組織、民意調查機構等等。
民意通過上述管道而得到彰顯,呈現在官方以及全體人民面前,成為政府制訂公共政策的依據,也成為不同民意辯論、篩選和整合的前提。現代中國社會,早已不是一個萬馬齊喑的社會,官方應該充分鼓勵民意的表達,暢通民意表達的渠道,及時呼應民意的吁求,只有如此才能贏得民意的信任。
當然,在中國還存在一種隱性民意形態。隱性民意的形成和存在,或者是因為公民缺乏表達的意愿和能力,或者是因為缺乏表達的渠道和平臺,又或者是因為民意表達的成本和風險太高,以至于不得不三緘其口、靜觀其變。隱性民意雖然沒有顯性化為公共輿論,但它猶如暗潮洶涌,更值得當政者關切與回應。
事實上,真實而完整的民意,是顯性民意和隱性民意的結合體,前者作為一種高調的民意,需要被看見和聆聽,而后者雖然沉潛低調,但卻具有更加沉郁頓挫的力量,更應被發現和體察,以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全面性和深入性。
2.強勢民意與弱勢民意的統一
中國社會存在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因而也就存在強勢民意和弱勢民意。一般而言,強勢群體具備更高的智識水準,掌握更多的表達與傳播平臺,擁有更強大的左右公共政策的能力,遂成為強勢民意。反之,則成為弱勢民意。
強勢或者弱勢民意的形成,與歷史、傳統、財富、權力、地位、地緣、真理、良知、教育水平、公民素養等因素息息相關,是多種因素綜合而成的產物。而且極具相對性和更迭性,在合適的條件和土壤下,強勢民意和弱勢民意會在不經意間迅速完成轉換。
一般而言,強勢民意如下:城市民意、富人民意、原住民民意、網絡民意、主流民意、正義民意、集團性民意等等。相對的,則屬于弱勢民意:農村民意、窮人民意、外來人口民意、線下民意、非主流民意、非正義民意、分散性民意等等。
強勢民意與弱勢民意之間的轉換是微妙而迅捷的,以前段時間農夫山泉與京華時報的爭執為例,以前者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為分水嶺,民意輿情的轉換就相當值得玩味:在這起已被定名為“華山之爭”的論戰中,2013年5月6日下午3時被證明是個民意反戈的節點,在那之前,京華時報總體占據上風,雖然諸多媒體同行都不再擁有持續追問的熱情,但至少還算是靜觀其變;但在農夫山泉召開新聞發布會之后,輿情明顯發生偏轉,更多為農夫山泉鳴不平的聲音冒了出來,一些媒體同行甚至已經開始拆臺,拆京華時報的臺。在微博上,在民間,甚至響徹著陰謀論的聲音,農夫山泉被當成了遭到神秘權力打壓的無辜者,而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同情。一些微博大V,像周立波甚至公開表示支持農夫山泉,周有3000多萬粉絲,他的號召力對輿情的影響不可小覷。
3.正義民意與非正義民意的統一
民意并不代表正義本身。人群的復雜性、利益的多元性,決定了所謂的整全性民意永遠都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民意即殘缺。因此,民意事實上不可能代表正義本身,民意也有可能是非正義的,事實上,常常存在這樣的可能。
某種意義上,民意不代表正義這樣的判斷,簡直是一個常識。在中日釣魚島風波引發的一些城市的“打砸搶”行為,難道沒有民意慫恿的痕跡?在著名歌唱家李雙江之子李天一案中,人們對這位未成年少年喪失分寸的口誅筆伐,難道不是民意高燒的結果?如麥迪遜所說,“在雅典的6000人公民大會上,即使每個人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也只可能是一群暴徒的大會。”[14]
我們要充分警惕民意的負外部性,尤其在極端環境下,民意滑向民粹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后果是相當嚴重的。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其名著《烏合之眾》中亦有值得我們省思的論斷。他說,“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情感;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15]又說,“從一定意義上說,群體就像個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經暫時擱置。”[16]
我們當然不能抹煞民意所代表的正義含量,它是我們的力量源泉以及所有合法性的基礎。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充分體認民意非正義的一面,使我們既尊敬民意又不迷信民意,依靠民意又獨立于民意,這樣不管是我們個人還是整個社會,才能永遠保持審慎、謙卑、克制與理性。
4.主流民意與非主流民意的統一
主流與非主流仍然是相對的。不妨試著下一個定義:主流民意,就是那種相對多數的、相對正統的、相對穩定的民意。主流民意,與絕對無關,只與相對有關。它甚至都不意味正義和正確本身,它也只是民意之一種。
在缺乏科學有效的民意評價工具與體制之前,所謂“主流民意”經常陷入自說自話的局面。問題在于主流民意該怎么測算,誰有權力做出判斷?主流的就一定是對的嗎?非主流的就一定是錯的嗎?都未必。
正如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所寫的那樣,“科學的民意調查只要一天得不到充分發展,主流民意就仍是一個 ‘隱身人’,永遠是沉默的大多數,發不出自己的聲音。”[17]重要的也許不是誰贏得了主流民意,而是任何民意都值得傾聽,不要以為非主流民意就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甚至必須要鏟除而后快的。
四、結語
民意是一個迷人的字眼。隨著政治文明的進步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見證民意作為一種價值在當今的崇高地位。從權力神圣到民意神圣,是一個轉型社會努力掘進的結果,是無數仁人志士付出勇氣和行動的結果。
然而,我們也要冷靜地看到,民意崇高,是它所代表的價值的崇高;民意神圣,是它所代表的精神的神圣。民意本身則是復雜而難以琢磨的,當我們從現實層面論及以及使用民意概念為我們服務時,我們得秉持十二分的謙卑和審慎,去對民意進行抽絲剝繭地理解和詮釋。
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民意,既有一種普世性的民意特征,也有著基于特殊國情的特殊民意特征。一方面,轉型期民意有著深刻的積極作用,但也有著完全不可小視的負面進攻性。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從善如流,支持和皈依正面民意,阻止、引導和改變負面民意,促進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
[1][2][3][4][5]〔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0,79,21,32,3.
[6]程世壽.公共輿論學[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14.
[7]吳順長.民意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7.
[8]曹林.別在被放大的網絡輿情中誤讀中國[N].中國青年報,2013-05-03(A2).
[9]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259.
[10]劉建明.穿越輿論隧道:社會力學的若干定律[M].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171.
[11]江澤民.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黨員負責人會上的講話[N].新華社,2001-03-03.
[12]胡錦濤.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研究進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N].新華社,2010-09-29.
[13]習近平.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N].新華社,2012-11-19.
[14]王怡.網絡民意與失控的陪審團[J].百姓,2004,(02):60.
[15][16]〔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M].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36,48.
[17]李梁.主流民意是一個隱身人[N].南方周末,2009-0514(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