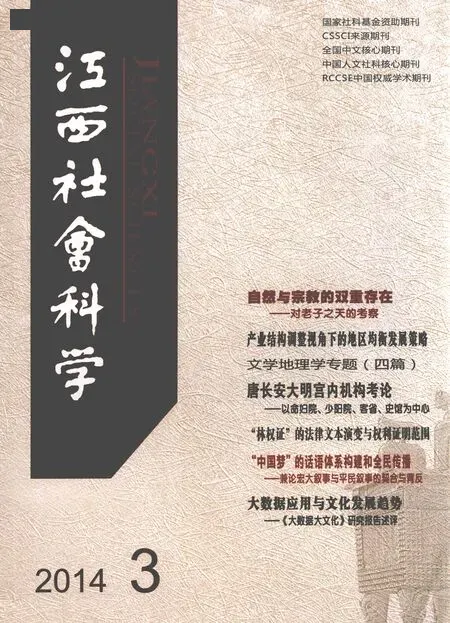“復生”母題的文化探析
■張 艷
“復生”母題與“變形”母題從發生的機制來講實屬同源,但又有明確的界限:“一個人、一個動物或物體改變了自身的形狀并以另一種新的形狀出現,我們稱之為變形;但如果一個生物在這兩個階段之間死去,我們便稱之為復活。”[1](P309)這里指出了“復活”與“變形”之間的區別,即“復活”中有“死去”這一環節存在,且復生是生命原體的復活。當然,界限有時也并不明顯,如顓頊在復生的過程中就出現了“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的現象,即顓頊在復生的過程里曾短暫呈現出變形為魚的狀態。當然比較起來,同樣是實現生命的不朽,復生比變形體現了人類在更高層次上的期望,畢竟這是生命本體的復活。
一、先秦:原始信仰里的復生母題
最早的死而復生的記載出現在《山海經·大荒西經》:“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及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有學者指出:“顓頊死即復蘇的神話,蓋即象征草木冬枯春生,昆蟲冬蟄春蠕的寓言。”[2](P33)《海外西經》載:“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文化人類學家也認為刑天、夏耕之尸等以原身復生是對農作物“生長——收割——再生長”的生命歷程的模仿。刑天操干戚以舞隱含了古代祭祀谷靈的儀式,刑天被“斬首”則是模擬稻谷收割方式,是神話中一種隱喻的文化行為。這一神話故事的內涵即借自然生生不息的意象表達對生命永恒的渴望。在原始初民看來,萬物皆為一體,人的生命與自然的循環交替一樣是周而復始的,有無窮流轉的可能。在這種神話思維的運作之下,“死亡”這一現象之于“復生”反而是成就生命的又一契機。因此《海外北經》里還出現了一個“無啟國”的傳說:“其人穴居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盡管現實中的自然法則是“人死不能復生”,但這種體驗在最初的認知里還不足以顛覆初民的生命觀。何況當原體復活被意識到很難實現時,又有“變形”的情節作為補充,共同支撐起原始人類的生命信仰。
原始人類對永生的信仰,背后是以靈魂不滅的理念為支撐的。靈魂按其本質來說是虛無的,在初民的意識里卻是生命和思想之根本;它是虛幻的,卻顯示出支配的力量。靈魂也被認為具有可以分離和不死的特質,即使生命形式出現短暫的改變也只意味著靈魂出現位移而并非消亡。從后來的文學史發展可以看出,關于靈魂的這一概念不僅支撐了原始時代復生神話的存在,還為復生情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理論發展的空間。
信仰的堅定使得復生的情節在崇尚實錄的史書里也有體現,如《左傳》里關于人被殺六日后復蘇的記載。戰國《古文周書》中載有這樣一段故事:“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置而大戮……’”大意是講越姬偷去姜后所生王子,三月后越姬死去,在冥中受到先王斥責,七天后越姬復活,恐懼之下只得自承罪行。這一復生的情節里已經出現了死后世界的描述。與此相類似的還有秦簡《墓主記》中的故事:丹自殺后被埋葬,三年后由地下“司命使”送返人間。這一故事“反映了秦人的樂生心態和當時人們的鬼神觀念”[3](P239),《墓主記》里還有對鬼神和祭祀的記載,引發了李學勤對于丹的職業屬于巫覡一類的猜測。可見,隨著蒙昧時代的逝去,復生的原始信仰非但并未消失,還與秦漢之際流行的巫術、鬼神思想相結合,成為那個時代人們情感的寄托所在,“死而復生”的情節內容也開始有了細節和情境的擴充。
二、魏晉:宗教影響下的復生母題
佛教的傳入帶來了更多關于生死的傳說與更多世界、空間的存在,佛教的因果論、因緣觀等和道教重視修道、長生的意念結合,再加上原始的鬼神論,很快就實現了信仰上的通融,占據了思想意識的主動。在宗教的影響下,魏晉六朝時期“死而復生”的故事大量涌現。這一時期“復生”故事大致呈現以下特點。
從內容上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鬼吏索命有誤,后改正放人回生;一類是因情復活,如《搜神記》中“王道平”、“河間郡男女”等條目。前者強調幽冥世界、神靈權威,借鬼神力量行懲惡勸善的目的;后者則是想象奇特的敘事文學。復生的方式也分兩類:一是借助于外力復生,如李娥的故事;一類是自我復生,如“戴洋復生”、“史姁”等篇目。從情節來看,結構相當完整,并有細節充實,不同于之前的簡略記述。李娥復生的故事里還附帶述及了亡魂劉伯文在冥中托她捎信的情節。從描寫來看,作者對死后的世界刻畫也漸漸清晰:有城池巷陌、官吏群眾等人事物理,也有親情倫理等意識,井然有序一如地上世界。就死而復生的過程而言,敘述相當完整,主人公由生入死屢經奇歷,死而復生后又能傳情達意且具備占卜預制的異能。這里對復生后的異能的渲染,既可以說是一種宗教宣傳,也可以看出對遠古神話的繼承。遠古神話里復生所代表的是生命的新機,此處的死而復生作為生命的奇跡也由此具備了一定的地位和權威,成為神秘世界的發言人。
有些死而復生的記載,如人氣絕后復蘇的描寫,站在今人的科學立場來看,是那個時代醫學水平不發達的緣故以致暈厥復蘇被誤認為是死而復生。但這類傳說在作家筆下又經發揚,如寫漢宮宮女于百年后從冢中復活等故事則很明顯超出了常理。這種非理性的表達方式正是宗教文學的特點。以《幽明錄》“趙泰”條為例,趙泰死后復蘇,自述被帶入地獄勘問生前善惡的經歷及期間地獄所見種種果報、贖罪之事,后以其生前未曾作惡被遣還陽世。有些故事里還寫到道教符箓厭劾等法術,死而復生故事成了宣揚宗教信仰的工具。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故事此后并未因教化意識濃厚而被揚棄,相反,對于地獄的渲染在唐代以后的小說里都是敘事的重心,足見集體意識的深潛和文學因襲的厚重。
魏晉時期的“復生”故事所體現的情感傾向和民族心理當然不限于宗教的層面。如《搜神記》中“河間郡男女”、“胡粉女子”等條目講述的是男女之間的傾心相愛。這里復活故事的重點已經不再是通過生死來表現幽冥世界和勸懲意識,而是借生生死死這一曲折的過程來展現愛情的忠貞。所謂“實謂精誠貫于天地,而獲感應如此”,“感應”只是情節的發展結果,而故事突出的是情節過程中的“精誠”。從敘事的角度來看,這類作品敘事完整、情態宛然,即使有著對鬼神觀的表達卻也并不刻意,而是將之轉為一種樸素的審美觀放在愛憎悲歡里自然體現。既有早期人們對生的渴求的表達,也有文明時代里對現實的認識和熱愛,尊重生命、珍惜生存,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后代作家也由此而受到啟發,在此基礎上創作出了很多經典之作。
三、唐宋:世俗理念里的復生母題
“唐朝的崇道佞佛,是志怪小說發展的思想基礎,但也不可低估六朝志怪小說傳統的深刻影響。”[4](P160)六朝志怪對于唐代文學的影響是深刻的。就復生故事來說,唐代小說幾乎全盤繼承了魏晉六朝文學的特征。就故事內容而言,基本也是兩大類:一類是側重宗教敘事,以復活宣揚果報;一類是用復活表現現實內容。然而繼承之中又有發展。
在前一類敘事里,佛教觀念的體現更加廣泛,如對殺生、報應等情節的描寫;對于主人公游歷地府的過程,描繪也更加詳盡。同時隨著佛經大量被翻譯,人們對佛教的體悟也漸深。因此唐代小說里描寫幽冥世界較之魏晉又有進步,不是為渲染宗教神秘感,而是以此為背景對照鮮明的現實人生,表達積極的人生追求。唐代復生故事里常出現有道士等助人起死回生的情節,他們憑借法力可與鬼神相爭并取得勝利,最終迫使冥使放回死者。當時的一些有名望的道士,如葉法善、仇嘉福等都出現在復生的故事里。他們的角色接近于早期故事中的“司命”,能力卻又過之。早期的“司命”放回死者是對誤拘、誤錄錯誤的糾正,而《廣異記》“仇嘉福”條故事則是表現道士運用道教法術改變天命救回死者,這里體現出人類對于自我命運的超強信心和積極態度。這種積極態度首先源于信仰的堅定,正如恩斯特·卡西爾曾經所指出的,在原始思維中,人對生命的感情曾經強烈到否定死亡這個事實的地步。死亡并不是必然的一種自然現象,而是“取決于個別的和偶然的原因,是巫術、魔法或其他人的不利影響所導致的”[5](P107)。而在幽冥世界的觀念深入人心之后,人們對于死亡的排斥不再表現為否定死亡而是表現為對復生的爭取,而在尋求對抗自然法則的方法上,巫術、法術所能施加的影響便受到格外重視。積極的人生態度同時也是時代氛圍的體現。本來,就中國的傳統而言,儒家強調“未知生,焉知死”,正視生命、回避死亡;道家更是修道煉丹以求長生不朽。而以唐代國力之強盛,唐人積極的生命態度自不待言。故而在魏晉作品里幽冥世界體現的是毋庸置疑的權威性,在唐宋作品里即使是陰司判官也表現出對人間的積極向往:“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忻慶。吾雖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鄭會》)
后一類的故事里則體現了唐代文人的“好奇”之心,寄托著文人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復活故事本身就具備奇異感,何況主人公神游四方的經歷是對生活和思想的極大突破想象,這中間能夠更好地被寄寓文人自身的思考。無論是中國本土信仰里的地府還是佛教宣傳里的地獄,都是人的想象的產物。但如果說魏晉時期的復生故事里對神秘世界的現實映射還是一種不自覺或半自覺的行為的話,那么唐代借地獄影射社會則是完全的自覺。如敦煌保存的唐代寫本《唐太宗入冥記》寫唐太宗利用權力與人情為自己謀取還生,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此外,寫兩性情感的內容在復生的故事里始終占有相當的比例。唐人小說里為愛情而復生的故事較之魏晉作品更加浪漫華彩,如《崔護》篇寫邂逅相遇、兩情悅慕,較之魏晉“胡粉女子”的故事,無論是意境還是情節都更勝一籌。其他作品如《齊推女》、《薛昭傳》寫女子的復生、結婚、生子,過程無異常人,這種美好的結局無疑是時代開明的產物。然而此類故事發展到宋代,女子為情還魂的結局則多以悲劇告終。以《夷堅志》為例,《吳小員外》、《鄂州南市女》等作品里寫女子復生來追隨心上人卻遭到堅拒,不得不再次離開人世。這種傾向體現出傳統倫理在宋代之后漸趨保守,而在對勸懲意識的表現上更顯得過于生硬和冷酷。
四、明清:藝術創造里的復生母題
明清之際出現了一些有著較高水平的小說創作,復生故事從情節到內容都受到小說家的重視被采用在作品構架中。其中有部分作品的創作仍著眼于對宗教教義的宣揚,且這類宣傳并非是出于官方意志而仍是源于人們虔誠的信念。如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中即有大量“復生”的記載。雖然這些復生故事涉及的社會內容相當豐富,作者卻將這類故事落腳于宗教和倫理的規勸上。對此我們不能完全歸結于紀昀本人的封建意識濃厚。事實上紀昀本人對此是有過理性思考的。如受清代考據之風的影響,紀昀對“復生”這一現象作過考證。《如是我聞》里對《左傳·宣公八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的記載,紀昀即言“或由縊殺杖殺,故能復活”。對于張天錫復活之事,紀昀認為這與《史記·扁鵲列傳》里所記載虢國太子的故事一樣,其“死亡”只是尸蹶病,經過治療乃得蘇醒。只是醫學水平有限,世人誤以為是死后復生。然而這類理性思考始終不敵宗教影響下復生信仰的分量。故《閱微草堂筆記》一書始終不脫善惡相抵,“冤家債主,須得本人是也”的宗教意識。宗教意識的深潛在大學者紀昀那里尚不能免,至于其他作品中對復生的情節描寫則因襲痕跡更濃。如《后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圓夢》等書“或借神人,或用定魂丹,把紅樓冤魂一個個從墳墓棺中請出來,往往是為了證因果、償恩怨、彰盛世,因此描寫大同小異,情節索然無味”[6](P430),情節之蒼白甚至不具備宗教說理的價值,只是無意識的一種模仿。
而在另外一些作品里,有著古老意義的復生故事完全成了一種藝術形式被作家運用在作品的敘事架構里。如瞿佑《剪燈新話》中《令狐生冥夢錄》篇、《聊齋志異》中《席方平》篇等,皆是借復生的故事框架來映射現實。傳統復生故事里所宣揚的宗教意義在這里也受到質疑和批判,烏老因家人大作佛事得以死而復生。令狐生因譴責冥吏貪贓枉法而被招入地獄。作品由此感喟:“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覆盆。貧者何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惡都無報,多積黃金遺子孫!”席方平赴地獄鳴冤,歷經數次死生才得以積冤昭雪,父子還陽。這里復活的情節已不是故事的核心,而鋪敘死生之間的經歷才是作品的寫作意圖所在。隨著藝術虛構越來越突出,復生的情節也更加繁復,作品篇幅因此更顯宏大。如《牡丹亭》里女子還魂的故事在前朝文言小說和民間話本里已長期流傳,但在湯顯祖的筆下則賦予這個古老的故事以全新的境界。所謂:“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古代復生故事在這里已完全從說教轉為寄情,是借助主人公超越陰陽兩重世界的阻隔的歷程,表達對愛情的禮贊,表現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堅定。
在對復生的情節進行藝術再創造的同時,這一故事情節所蘊含的文化內容也隨之呈現新的意義。如《西游記》中的孫悟空抹去生死簿一段:“把猴屬之類,但有名者,一概勾之。”然后聲稱:“了帳!了帳!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同樣是靠自身法力起死回生,這里既沒有對宗教法術的渲染,也無倫理道德的牽制,將之前所有復生故事里人類的主動行為發揚到淋漓盡致。以幽默戲謔的情調消解掉死亡這一沉重命題,可謂是文化傳統里的精神奇葩。再如李汝珍的《鏡花緣》,其中第十六回特別提到《山海經》里曾出現的“無啟國”:“彼國之人,活了又死,死了又活,從不見少。他們雖知死后還能重生,素于名利心腸倒是雪淡。他因人生在世終有一死,縱讓爭名奪利,富貴極頂,及至‘無常’一到,如同一夢,全化烏有。雖說死后還能復生,但經百余年之久,時遷世變,物改人非,今昔情形,又迥不同,一經活轉,另是一番世界,少不得又要在那名利場中努力一番。及至略略有點意思,不知不覺,卻又年已古稀,冥官又來相邀。細細想去,仍是一場春夢。因此他們國中凡有人死了叫作‘睡覺’,那活在世上的叫作‘做夢’。他把生死看得透徹,名利之心也就淡了。至于強求妄為,更是未有之事。”這里講述無繼國的人對待生命有著“方生方死”的豁達,死而復生于此倒更像是寓言般的存在,用來反襯出名利的虛無縹緲,這番論述對死而復生這個古老命題來講是新的詮釋。
五、復生情節與民族文化心理
黑格爾曾說過:“每種藝術作品都屬于它的時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環境,依存于特定的歷史和其他的觀念和目的。”[7](P346)復生的情節被后世所重視并在文學史上頻繁出現也絕非偶然。
首先,復生的情節架構有著很大的生成空間。中國古代小說發源于史書記載,因此重實錄而輕虛構。而復生的故事在敘述中必然涉及對冥府這一與人間相對存在的世界的虛構,因此復生的情節架構擴大了小說的敘事空間,便于安排豐富的內容。在復生的故事里,不僅有不同空間的平行存在,又有不同的格局安排,如人物的借尸還魂往往又關聯了另外一個系統的人事。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明清之際復生小說的敘事結構呈現相當的規模,而描摹也豐富細致許多。與空間格局相對應的是時間格局,復生故事在敘事上有生前——死后——回轉三個階段上的遞進,擴大了小說的表現力。
“復生”的情節結構里體現的是民族的審美觀。復生的故事體現為一個生——死——再生的循環過程,而回環往復既是中國古代小說的形式特點,也是文化特點。大量出現的死而復生之作,從表面看體現的是靈魂不滅的古老信仰,其實質卻是對民族深層文化心理的綜合傳達。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現世性、人間性的特征。儒家所講的“五福”①之中即強調有“壽”才談得上康寧,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也還是要在現世人間里完成的,因此天堂雖有卻還是要還陽。至于道教本就是追求生命不朽的,如老子之所謂“長生久視之道”,對于普通人而言,更是不僅求不死,且追求人間之樂。生理上求長,心理上求安,時間在國人的意識里則近似于停滯。而“復生”的情節“通過賦予時間以循環方向的辦法來消除時間的不可逆性”[8](P89-90)。一切事物均可周而復始,一切事物也都只是同一原型的重復,這正契合了中國傳統的哲學觀——循環觀。所謂“道者,反之動”、“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等。這種哲學觀體現在文學里則表現為回環往復的結構和理念,“復生”故事里無論是寫現實抗爭還是浪漫想象最終都被統攝在循環理念之下。
“復生”的故事在長期的發展中由于承載了過多的原始信仰和宗教理念的內容以致形成了固定的模式,這種模式又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內容的開拓。因此“復生”的故事直到唐宋時期仍大量用于傳道說教,與小說史上其他文學母題的發展并不同步。在明清之際作為小說的敘事結構模式被大量采用后,其作為文學的意義才得到彰顯,從而對古典小說的敘事產生了較大影響。丹納說過:“文學作品既不是一種單純的想象游戲,也不是狂人頭腦的孤立思想,而是時代風尚的副本,是某種思想的表征。”[9](P27)從文學作品中可以追溯幾百年來人類的感覺和思想的方式。綜合考察“復生”這一綿延不絕數千載的情節所表現出人們對于生活與生命的思考,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藝術產物,對于我們了解古人的行為方式、藝術的構成演變有著重要的意義。
注釋:
①《書·洪范》:“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1](美)史蒂斯·湯普森.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M].鄭海,等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2]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3]沈頌金.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4]侯忠義.隋唐五代小說[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5](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6]吳光正.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和母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7](德)黑格爾.美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8](美)艾利亞德.永恒回歸的神話[M].紐約:萬神殿書局(Pantheon Books), 1954.
[9](法)丹納.英國文學史導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