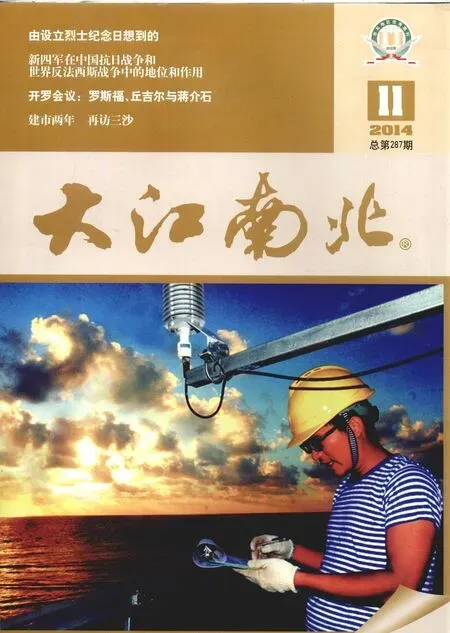對日大反攻前的準備
□劉亨云
(編輯 韓鴻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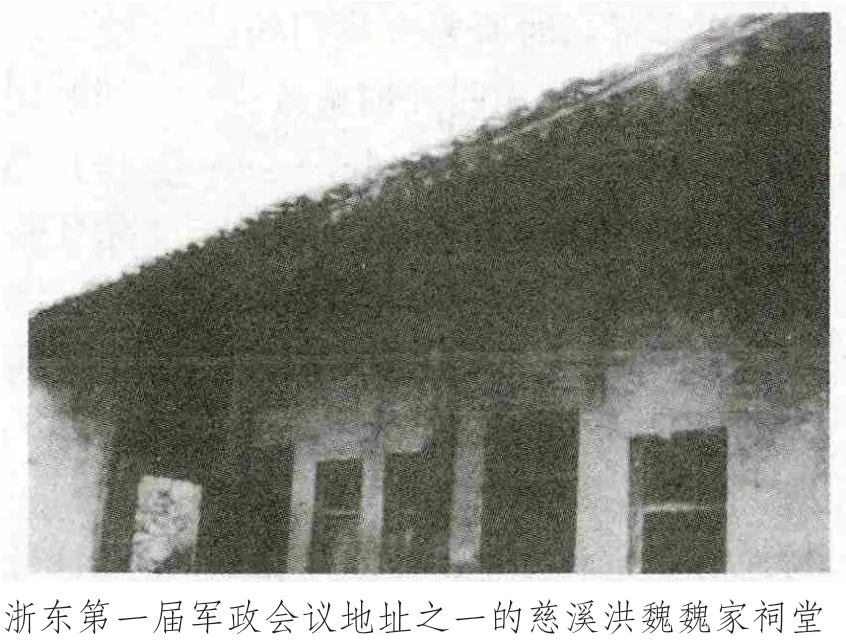
編者的話:為了從思想上、組織上作好對日大反攻的準備,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70年前,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召開了為期42天的第一屆軍政會議,并在會后開展了大量的工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東游擊縱隊》一書對此段歷史作了詳細的介紹。本刊予以摘編發表。作者劉亨云(1913年~1992年),江西貴溪縣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野戰軍第1縱隊3師師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浙東第一屆軍政會議,于1944年9月25日在慈北洪魏隆重開幕。浦東、金蕭等邊遠地區和海防大隊,也都派了自己的領導同志前來參加。出席會議的軍政干部代表共100余人。
六七月間,洪魏及其鄰近的東埠頭等地,還是我軍與日偽軍頻繁交戰的地區,如今已成了三北根據地的中心。八月上半月和九月上半月,我們在這里先后召開了全縱隊的后勤工作會議、組織工作會議和宣教工作會議。這三次會議的規模都不小,部隊多少天不動窩,周圍據點中的日偽軍豈有不知。寧靜的早晨,他們站在高高的碉堡上,甚至還能聽到我們的軍號聲呢!但敵人也對我無可奈何。
軍政會議總共開了42天,直到11月5日才勝利結束。會議的大部分,都是在洪魏開的,移駐四明山區袁馬繼續召開,那已經是會議的后期了。正如譚啟龍在會議的開幕式上所說的:“我們浙東部隊從開始創立至今都是處在與敵偽反動派的殘酷斗爭中,由于斗爭頻繁,過去,沒有很安全的環境可以允許我們來開這樣的大會。”這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有條件開這樣的大會了。可以想象,我們的縱隊領導機關,在敵偽控制很嚴的三北,駐扎一地達數十天之久,且又集中了那么多的領導干部,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會議上,倘若不是形勢對我空前有利,那是辦不到的。同時,它也說明了這次會議的重要,是一次從思想上、組織上作好大反攻準備的會議。
這時的形勢確實是令人鼓舞的。在歐洲戰場,希特勒德國已臨近滅亡。在太平洋戰場,日軍早已被迫轉入防御,盟國軍隊正在日益迫近中國海岸,全面反攻階段的到來,業已為期不遠。日軍為了挽救他們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危機,重新發動了對國民黨戰場的進攻,一直深入到了貴州,完成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計劃,占領了華中、華南的大片國土。但是,敵后抗日的力量也有新的發展,進入了再上升的時期。我八路軍、新四軍,在敵進我進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挺進到日軍新占領地區,開辟了許多新的游擊根據地,并開始了局部的反攻。
相比之下,我們浙東敵后抗日力量的再上升時期來得晚了一些。可是,我們畢竟也已經度過了前一段時間所遇到的重大困難,“達到了今天比較穩定的局面”。隨著盟軍已步步逼近我國海岸線,浙東地區的戰略地位顯得更加重要了。區黨委和縱隊領導在大會期間,一再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充分地認識這一點,清醒地看到日軍在完全失敗以前,對于滬杭甬三角地帶及其沿海地區的控制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敵我之間的斗爭只會更加尖銳,而不會緩和。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繼續鞏固與發展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堅持浙東抗戰……配合盟軍反攻敵人,奪取滬杭甬等大城市,解放東南數千萬同胞”。
正是為了完成上述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積極迎接大反攻的到來,會議自始至終貫徹了延安整風的精神,開成了一次“團結自己,提高自己”的大會。誠如新四軍軍部當時所要求我們的:“真正做到團結無間并徹底改進自己的領導方法與作風……每個人放下包袱,以高度的原則性,深刻檢討自己的缺點與錯誤,虛心接受人家對自己的批評,以治病救人的精神來幫助人家,部隊干部與干部,外來干部與地方干部,老干部與新干部,均必須革除一切宗派主義、本位主義的毛病,求得親密無間。”為什么這樣強調團結的重要呢?因為這是兩年多來被浙東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實踐所一再證明了的,我們內部的親密團結,是克敵制勝、戰勝困難的法寶。
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對于浙東敵后以往的斗爭,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們在來電中說,“你們建立和發展了浙東根據地。在敵人‘清鄉’、‘掃蕩’中,在反頑自衛戰爭困難環境下,堅持浙東敵后斗爭,發動和組織廣大人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部隊從數百人發展到數千人,威脅著上海、杭州、寧波等大城市,控制著重要的海岸,所有這些,證明你們的努力是獲得巨大成績的。”
黨中央、毛主席在收到大會發去的致敬電以后,給大會發來電報,要求通過大會100多名代表告訴浙東敵后廣大軍民:“你們的努力是獲得巨大成績的”,“望你們努力殺敵,發展武裝部隊,擴大解放區”,“準備配合盟軍驅逐日寇”。
這使得全體同志受到莫大鼓舞。
軍政大會以后,部隊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整訓。在此期間,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曾兩次發布“開展部隊大練兵的指示”;區黨委也于11月15日作出了相應的決定,號召全體指戰員“爭取一切時間和可能,加緊整訓部隊,提高部隊戰斗力,以迎接新的光榮任務”。
作為縱隊的參謀長,組織部隊練兵,提高廣大戰士的軍事技能,提高各級指揮員的軍事素質,是一個一刻也不能忽視的重要任務。對此,同志們在首屆軍政大會上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批評。大家認為,過去在軍事上有一個重要缺點,就是沒有抓緊一切機會練兵,“我們的兵不精”。是的,從我的思想上來說,往往強調戰斗頻繁、部隊長期分散、缺少整塊的時間和相對安定的環境等等,認為很難搞什么訓練。這當然是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很不全面。無數的事實促使我們思索:為什么在有些戰斗中,部隊的傷亡過大,又為什么在不少戰斗中,彈藥消耗較大,殺傷敵人卻不很多。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我們的戰斗技術較差,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同志們批評縱隊司令部不重視軍事訓練是很對的。根據訓練前的測驗,許多人不曉得什么是射擊瞄準中的“三點成一線”;不會扔手榴彈的,也不是少數幾個人,敢扔卻扔不遠、扔不準的,為數更多。有的連隊,投彈達30米以上的只有8人,有的連隊,投彈平均距離僅23.4米。論刺殺技術,那就更差了。
這次整訓,對于縱隊領導來說,那是下了決心的。無論從思想上、組織上和物質上都作了較為充分的準備。
我們部隊是11月上旬從三北移駐四明山梁弄地區的。稍事安頓,便于15日召開了干部和黨員大會,由何司令作了大練兵的動員。緊接著,縱隊政治部制定和公布了《戰斗英雄與模范工作者條件及獎勵辦法》,并號召大家在練兵中開展立功創模活動。從組織上來說,自上而下,都建立了以黨的總支委員會、支部委員會為核心的領導小組,并在《戰斗報》上明文公布了縱隊司令部、政治部和各支隊以及縱隊直屬部隊的黨總支、黨支部成員的名單,以此加強各級黨組織對練兵的領導,并取得群眾監督。各部隊還就地取材、因陋就簡地制作了必要的練兵器材,開辟了練兵場地。
這次練兵,共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在練兵中,貫徹了以技術為主、戰術為輔的訓練方針,在戰術訓練上突出了山地攻防,堅持了群眾路線和軍事民主,強調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要求首長親自動手,創造典型,全面推廣。這樣,一個群眾性的冬季練兵運動,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
那時,主要是訓練射擊、投彈、刺殺、土工作業四大技術。“打槍要打得百發百中,手榴彈要扔得又遠又準,刺殺要使敵人無法招架,土工作業又快又好”,這成了指戰員們自覺地行動口號。他們結合自身的戰斗實踐深深體會到:“革命部隊的勇敢精神很好,打起仗來猛打猛沖猛追,就是戰斗本領還不高,‘三猛’加‘四高’,仗仗能打好。”
沒有真刀真槍,要提高四大技術也是很困難的。我們縱隊的幾個領導人一起給后勤部兵工廠的同志寫信,要求他們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制造更多的武器彈藥支援前線。他們回信說:“戰斗部隊已經掀起了‘整訓熱潮’,我們要以‘生產熱潮’來和戰斗部隊展開革命的競賽”,“只要原料和人工問題能夠適當解決,部隊所需的子彈、手榴彈、槍榴彈、地雷,我們可以保證供應,而且還要不斷提高質量,使每一顆子彈、每一顆手榴彈都能發揮高度的威力”。他們所寫的不是一封普普通通的回信,而是全廠130多個軍工人員的誓言。
說起這個兵工廠,我是去過幾次的。工廠座落在一條叫做白龍潭的偏僻山溝里。真是簡陋得很啊!但在那時候,我們已經把可以調動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都集中到兵工廠里來了;凡是他們提出的要求,只要我們能夠辦得到的,總是竭盡全力地去辦。就拿兵工廠的主任林邦許(林克光)來說,那是由三門縣地下黨組織特地挑選來的。這同志是個大學生,懂得機械,也有一些化學知識。副主任朱連根同志,是個老鉗工,早在1941年,便是黨領導的浦東部隊的修械所所長了,他不但有熟練的技術,還有豐富的領導軍工生產的經驗。從諸暨請來的四個老師傅,專門負責澆注手榴彈鐵殼。
今天說起來,簡直難以叫人相信。兵工廠所需的原料,大到機床、火藥、鋼鐵,小到木炭和風箱中所需的雞毛,統統都是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援和部隊的繳獲來解決的。沒有引擎,就從擊毀的日軍汽車中拆卸,由群眾把它抬進山溝。缺乏鋼鐵,群眾捐獻破銅爛鐵,并到杭甬公路兩側,搜尋早年被丟棄的鋼軌,多少人為此下河入水,摸的摸,抬的抬。山區人民缺糧食,生活貧困,很少養雞,連雞毛也很難找到。三北的群眾得知這一情況后,便收集了很多雞毛,派專人送到兵工廠。至于地下黨同志,為了從上海等大城市運來必需的機械、儀器和原料,更是歷盡了艱險。
正是這樣一個由修械所逐漸發展起來的山溝兵工廠,到了1944年冬季大練兵的時候,已經能夠自己制造手榴彈、子彈、地雷和三角刺刀了,為部隊開展實槍實彈的練兵,提供了有力的保證,為提高部隊的戰斗力,作出了重要貢獻。后來,我們的兵工廠還造出了迫擊炮彈。令人難忘的是,當他們造出第一枚炮彈時,由于受到設備和技術條件的限制,彈體不很光滑,留有一些細小的砂眼。結果,在四明山區徐鮑附近試射時,炮彈打出炮口不遠便自行爆炸了,當場炸死炸傷兵工廠支部書記等七人。同志們含著眼淚總結了這一血的教訓,又經過刻苦的鉆研,終于造出合格的炮彈,源源送往戰斗部隊。
正如兵工廠同志所說的,這是一場革命的挑應戰和革命的競賽。各戰斗部隊在練兵中,也涌現了眾多的不怕困難,苦學苦練的動人事例,產生了數以百計的“神槍手”、“榴彈大王”和“刺殺英雄”。
這次練兵,確實體現了群策群力、同心同德的精神。同志們上山砍柴做木樁,自搓草繩做鐵絲網。在自己動手開辟的操場上,鞍馬、天橋、獨木橋、壁障、碉堡、沙坑,一應懼全,看上去還真有點樣子呢。練習射擊所需的沙袋、三角架、靶子,全是土造的。依靠指戰員的才智,我們還自己制造了瞄準具。
從縱隊司令部各科到各級參謀人員,無不全力投入練兵,他們制定訓練計劃,編寫教材,下部隊了解訓練情況,及時總結先進經驗,集中群眾智慧攻克難點。政治工作人員,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練兵場,還開展了群眾性的宣傳鼓動和文化娛樂工作。而且他們也都同軍事指揮員一樣,嚴格要求自己,既做好本職工作,也苦練四大技術,提高作戰本領。三個多月的練兵,對于游擊部隊來說,是很長的時間,但這100多個日日夜夜,又是非常緊張的。我親眼看到,許多同志在整訓中反比行軍作戰時更為消瘦。部隊軍政素質的提高,無不凝結著干部的心血。
在那些日子里,我走到哪里,哪里的干部都要向我“討救兵”。救什么?就是要我去批評批評那些“不顧死活”,“不曉得疲勞”的干部戰士。那時,干部碰在一起,不是研究怎樣保持部隊持久的練兵熱情,而是怎樣想辦法勸大家休息,保證大家有充足的睡眠時間。我批評了,也勸說了,但不起作用。他們說,“參謀長,不是要迎接大反攻嗎?譚政委講話,要求我們不許有一分鐘時間的浪費,要提高一百二十倍的工作精神,你怎么叫我們休息呀?”這樣的干部戰士,實在是太可愛了。
同志們在練兵中進步很快。我看司令部掛著的表格上,標志四大技術進步的紅箭頭,每天都在上升。有一天,我趕去三支隊,參加他們舉行的墻報展覽和排球比賽。不是要我勸同志們注意休息嗎?我看三支隊的這個辦法很好,開展文娛活動,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可是,走去一看,看墻報展覽的人和看排球賽的人都不多,卻在另外的地方圍了很多的人。原來,這里正在舉行持槍瞄準的比賽。那架勢也確實好看,各中隊選派出來的代表,足有幾十個。幾十個人排成一列,一個個舉槍直立。黑黝黝的槍管,紅亮的槍托在太陽下閃閃發光,無倚無托、三四公斤重的步槍,在他們的手上不顫不晃,就像托著根輕巧的木棍似的。五分鐘過去了,不見一個人放下槍來。在場的人,誰沒有見過持槍瞄準,誰又不是練了多少次,當兵的看當兵的,有什么好看呢?但是,場子上靜得很,沒有一個人亂動,連咳嗽的聲音也沒有。
七分鐘過去了,八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才看到有幾個人陸續放下槍來。慢慢地,就只剩下一個人還舉著槍了。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計時看表的人也來到了他的身后。比賽結果,3連6班戰士顏岳云同志奪得了第一名,瞄準時間,達到十五分鐘。我還特地湊上去,挨到他的胸前聽了聽,他的呼吸一點也不急促。這可是真本領!南宋的愛國名將岳飛有個兒子叫岳云,是個很會打仗的小將,我們的這個同志去了姓,也叫岳云,這豈不是很巧!直到這時,場子上才爆發出一片呼叫聲和鼓掌聲,弄得排球賽也沒人看了。
缺乏攻堅的技能,這也是我們的一個薄弱環節。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還不可能把提高攻堅能力作為軍事訓練的一項重要內容,但也作過一些努力。例如,通過反復鉆研,我們曾經把兩門迫擊炮改制為“平射炮”,在50米左右的距離內,可以直接瞄準,摧毀碉堡。后來,在討伐田岫山的許岙戰斗中,發揮了作用。“轟轟”幾炮,碉堡里的敵人慌了,說是“不得了啦,三五支隊有鋼炮了”,促使敵人進一步動搖。
總之,這次練兵,對于以后討田戰役的勝利,對于奪取浙東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都起了明顯的作用。
浙東首屆軍政會議以后,我們的敵軍工作和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也有了明顯的加強。
- 大江南北的其它文章
- ">"刀筆一線通"——記"將軍書畫家"景在平
- 連續受賄11年年均斂財百余萬——蘇州黃承風受賄案追蹤
- “最美”鄉村醫生沈如斌
- 誠信兒子替父還債
- 為國從戎生死以 清風兩袖一支筆——懷念我的大表哥顧正均
- 建市兩年 再訪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