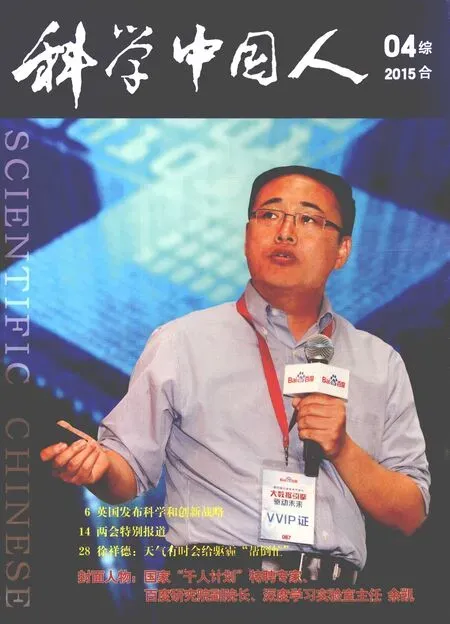規劃在務實 平凡見真知——記中國工程院院士、城市規劃師鄒德慈
本刊記者 黃雪霜
少年鄒德慈:踏實鋪路 “功夫在平時”
1934年,上海。鄒德慈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祖父給他起了“德慈”這么一個富含深厚底蘊的名字,希望他能德慈兼備。
生在舊社會,長在舊社會。戰火紛飛的年代,其中經歷的艱辛磨難自不必細說。鄒德慈十歲那年父親去世。是他的母親,一個堅強、知性的女人,靠著擔任小學英文教師不高的收入,在動亂時代獨立支撐起這個家,只希望他們兄妹倆能夠順利長大成人,用功讀書。
在這樣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鄒德慈,從小就學會自強自立,刻苦努力。與天資極為聰穎的人不同,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極普通”的人,因而很早就知道踏實為學的道理。他笑言得益于自己當時個子偏小,常被老師安排在前排聽講,所以養成了平時集中精力聽講,用心做好筆記,課后認真做好作業的習慣。讀書階段一直到大學畢業,每逢考試,他都極少開“夜車”臨時抱佛腳。
日積月累,細水長流,鄒德慈在求學過程中深刻地體會到了一步一個腳印,將基礎扎實扎牢的的好處。而這些體驗其實并不只是簡單的讀書之道,也蘊含著博大的做人、做事之道,貫穿在他之后科學生涯中,成為指引他從一個成功邁向另一個成功的“墊腳石”。
伴隨著新中國傳來的第一聲啼鳴,鄒德慈在之后也迎來了人生的跨越。1951年,在新中國百業待興,百廢待舉,醞釀蓬勃發展新機的時刻,涌入到建設祖國的熱流中,他成功考取同濟大學土木工程系城市規劃專業,成為新中國早期這一專業的學習者。1952年恰逢全國進行院系調整,同濟大學在這一時期聚集了一大批建筑方面的大家,名師薈萃,師資雄厚。鄒德慈幸運地成為了時代的寵兒,在這一段青年成長最關鍵的時期,他盡情地沐浴在各名家大師的“春風”中,聆聽他們字字璣珠的教誨,學習了大量專業的基礎知識,且開始嘗試著運用踐行,為他長期在規劃領域開展工作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大二那年,鄒德慈通過自行積累,參閱外國文獻,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寫出一篇《城市綠化》的小論文,發表在上海《新民晚報》上。這件“小事”在他不凡的規劃之路中,雖然只能算是一小步,但意義不同尋常,可以說是他作為一名在校大學生勇敢實踐的第一步,也是他長達60年規劃生涯中一個起點。
漫漫人生路,可以采擷的片段何止一點半點。
作為一名生在舊社會,長在新中國磨礪時期的親歷者,青少年時期的鄒德慈深刻體會中國從一個任憑列強欺凌、千瘡百孔的積貧積弱之國,到翻身做主成為一個鼎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國的不易。涌入到新世界的創造洪流中,他將“以踏實鋪路,肯干務實”的良好習慣放置到之后60年的規劃生涯中,走出了一條不平凡的規劃之路……
60年規劃生涯剪影:肩負使命 如履薄冰
這位八十歲老人的身后,承載著太多新中國城市規劃發展大大小小的歷史瞬間:20世紀50~60年代主持和參加了重點新工業城市的總體規劃;80年代后參加天津震后重建規劃及指導三峽工程淹沒城鎮遷建規劃等;近十多年參加和主持了30多個重要科技咨詢項目,包括首都總體規劃、上海發展戰略研討等。
“如果讓我總結做這些規劃項目的特點,我認為是有兩條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不墨守陳規。”鄒德慈如是總結。正如他所說:“規劃設計,手上攥著的是國家、人民的錢,事關國家安康,百姓樂業。”因而每走一步,他都小心謹慎,如履薄冰;每做一個決定,都力爭思慮周全,結合實際。
“要錢”的項目——三峽工程淹沒城鎮遷建規劃
1955年,鄒德慈從同濟大學畢業,分配到國家城建總局城市設計院(中規院前身)工作,開始了他與中規院“剪不斷”的淵源。雖然期間因為文革,他先后輾轉到大慶“蹲點”,再從干校“畢業”被分配到交通部第一航務工程設計院,一干就是8年,終于1979年被調回中規院。
十幾年的磨難和歷練,鄒德慈用他的隱忍畫出了一個圓,終點即是起點,機遇總是留給有所準備的人,“重操舊業”后幾年,他與“三峽工程”不期而遇——
1982年,受長江流域辦公室(長辦)的委托,他參與三峽工程可研報告的“移民遷建”部分,直接分管和指導這個項目。
三峽工程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歷程里“最宏偉的工程之一”,投資規模巨大。為順利完成這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業,整個三峽水庫庫區淹沒城鎮14座(縣以上),加上農村被淹人口,移民總數量近百萬。如何將這么多的移民順利遷移出庫區,并妥善安置他們,成為事關三峽工程成敗的“決定性”要素之一。如此大規模的遷移在當時世界水庫建設史里是罕見的,沒有經驗可循,沒有史例可鑒。
這項重任落在了中規院肩上,在歷時一年多的工作過程中,鄒德慈帶領中規院項目成員圍繞淹沒城鎮開展了遷建選址、規劃設計、投資估算等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工作,這是一種“非常規”的規劃工作,方法從任務中來,標準從實際出發,一切參照過去僅有的一點經驗而定。
當時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按照過去水利部所執行的補償標準與三峽實際需要大有偏差,庫區老百姓照此補償沒法遷移。通過大量深入實地的考察調研,他們為項目制定了一套特定的“統一技術措施”,提出了一套標準的城鎮移民遷建指標,這一指標大大超過了水利部的預期,起初水利部并不愿接受,但后來經過反復校核論證最終予以了認可,并最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
回顧這一歷程,鄒德慈笑稱三峽項目是他“多向國家要錢了”,當時遷建所需要的資金占到總工程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他很肯定地說這是必要的,是經過大量調研結合實際需要的做法。20多年后三峽工程的建設實踐最終也證實了這一研究成果的科學性。
“省錢”的項目——陜西安康縣城災后重建
陜西安康市地處“秦頭楚尾”,南依大巴山北坡,北靠秦嶺主脊,一條漢江穿流而過,構成“兩山夾一川(江)”的自然地貌。隨著勤勞祖先的繁衍發展,長期形成了濃郁的安康漢水文化。
1983年7月31日,一個不能忘卻的記憶:一場洪峰流量為3400m3/秒的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淹沒了安康老城,綜合損失4億元和870人不幸遇難的慘痛代價,讓這座城市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唯一被洪水沖毀的地級城市,震驚國內外。于是,“7.31”這個特殊代號,成了安康人永不磨滅的情感記憶,成了安康城永載史冊的災難符號。時值秋后,隆冬在即,災后重建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
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幾乎所有的災后重建規劃都是中規院完成的。因此,中規院在相關方面累積了一定的經驗。因此,安康災后重建規劃的重擔再一次落到了他們肩上。面對幾萬人無家可歸,物資匱乏,時間緊迫等一系列難題,鄒德慈及項目組成員首要面臨一個艱難的抉擇:當時有兩個方案,一個是遷到原址高地“塬上”進行城市重建;一個是在原址上重建。兩個方案前者看似是一個長遠的方案,后者有再次面臨災難的危險,因而當時的省規劃院更傾向于前者。但鄒德慈及其項目組成員通過細致調研決定力排眾議采用后一方案。
為什么放棄一個看似長遠的方案采取一個“短視”的做法?鄒德慈有自己的一番見解:首先“遠水解不了近渴”,遷到新址重建至少要花一年時間,當時物資匱乏,眼看著快要進入寒冬,幾萬居民居無定所;二是塬上地質是大孔性土壤,遇到水后容易軟化降低承受能力,作為地基不是很安全;三是當時安康上游正在建一個水電站,水壩建成后可以抵擋住一些洪水,減輕洪災壓力;四是安康原先有舊的城墻,何不將其加固提高當成防洪堤來用?這不失為一個巧妙靈活的方法。
“當時爭論很激烈,理論上原址遭到淹沒,遷址新建搬過去后可以‘一勞永逸’,但除了一系列安全等復雜因素之外,首先它就解決不了當前困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把道理倒過來看:不能只求長遠的合理,但是過不去當前這么一個難關。所以說在很多實際規劃設計里,首先要考慮更符合實際的做法,而不是符合你的理想。”
30年過去,事實證明安康原址重建的合理性。它不僅解決了當時的困難,而且后來上游水電站完建,起到一定攔洪作用。安康舊城得以繼續維系著以前圍水而居的效果,漢江的水路交通仍然絡繹不絕……
原址重建為國家節約了經費,鄒德慈笑稱這是一個“為國家省了錢的項目”,但“省錢”抑或是“花錢”,凡事都是從實際需要出發,得有根有據。轉眼30年過去,當時正在當年的規劃師如今已經搖身變為白發蒼蒼、耋耄之年的老人,但他依然還很關心安康,遇上有什么大災大難,他會盯著看這座古城有沒有頂住災難,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一切都還好。“我個人比較滿意,看來是做對了,城市規劃不同于一般的工程設計,前面需要大量調研。所以遇事最好不要教條,單從理論出發,還是結合實際進行研究……”
中國著名建筑規劃大師吳良鏞曾經這樣說過“一個真正的建筑大師,不是看他是否設計出了像埃菲爾鐵塔一樣流傳百世的經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讓自己國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與吳老一樣,鄒德慈走過的60年規劃人生始終站在普通老百姓、國家的實際需要去運籌帷幄,各種細節控于心間,不管是選擇從實際出發還是打破常規,靈活應變,他的規劃只為一個最簡單、最純粹的訴求:肩負民之重任,因而如履薄冰。
規劃管理人生:鄒院長的“五子”及整頓院風
1986~1996年,鄒德慈被任命為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任期11個年頭。
11年披荊斬棘,11年磨礪成長,從一名技術人員到成為一名普得團隊贊譽的一院之長,鄒德慈自是經歷了一番刻苦琢磨,酸甜苦辣在心間。
“當時中規院恢復組建沒幾年,使它盡快成長發展是我們這一代規劃人的責任”,鄒德慈如是說,正因肩負使命重任,他義無反顧、盡心盡力地踏上這條管理之路。
也許是出于一名規劃師的職業習慣,鄒德慈的管理之路一路走來也力求綜合考慮全局,運籌帷幄,仔細布局……當院長后,“雜事纏身”,他將各種問題歸結為“五子”,包括票子、房子、孩子、位子等。“票子”即錢,是一院維系發展之根本,所以鄒德慈當時帶領規劃院全體員工想盡辦法多拿到項目,爭取為員工多謀福利;“位子”即崗位,一個大院五百多號人,大大小小的職務如何分配才能實現各司其職,人盡其才,鄒德慈下了一番功夫;房子顧名思義,當時還沒進行房改,單位負責給員工安置住房,因為數量有限,如何公平分配使得大家都滿意也是一件大事;除此之外,他還將關注的目光也聚集到每位職工的孩子問題上,經常幫助他們處理孩子上學、托管等雜事,雖然他沒有職責和義務做這些事情,但職工的“后顧之憂”鄒德慈都愿意盡力去幫忙解決,難怪有人笑稱當他的部下是件“極幸福的事”。如此“五子登科”,鋪就了一條特別有序的管理之路。
在鄒德慈院長任上,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倡導的“院風”。見證了新中國成長歷史的他對共產黨三大作風所煥發的蓬勃生命力有著切身體會。擔任院長后,他認為一個歷史悠久的規劃設計院也應該有自己“精神之魂”即作風。綜合考慮規劃院的實際特色,他最終提出了中規院的“院風”——求實的精神、活躍的思想、嚴謹的作風,并最終在部里通過。
對于這三大“院風”,鄒德慈有自己的一番解讀:首先,城市規劃特別要講“求實”,因為城市規劃的特點是要對未來做一定的預測和設計,規劃的圖紙和文件,都是描述未來的,所以既不能過份保守,不敢想不敢做,也不能脫離實際,浮夸虛漲;“活躍”,主要是指思想。針對的是城市規劃的另一種傾向,即容易固步自封,思想僵化跟不上客觀世界發生的變化,所以提倡思維要活躍,不斷接受新知識新技術;“嚴謹”,指的是科學的作風。“我們在圖上‘指點江山,縱橫千里’,一動筆就是幾個甚至幾十個平方公里,俗語有云‘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所以嚴謹的作風相當必要……”
現如今,30多年過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依然秉持著當年立下的這一“院風”,在中國規劃設計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枝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從一名純粹的技術人員到成為一名管理者,一路走來,在中國規劃設計領域,他除了摘得一項項規劃成果之外,還帶出了一支專業隊伍里的強勁團隊,一個又一個規劃戰線上的精英人才。更為難得的是,他留下了一個行業從業人員可以秉之自度的精神標尺,而這些,才是推動我們國家規劃設計行業不斷創新前行的無窮源泉。
莫道桑榆晚 為霞尚滿天
1996年以后,年過花甲的鄒德慈不再擔任行政職務,雖已到退休年齡,但他一天都沒有停止過工作,主要集中在技術方面。
2003年,他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時年69歲。回憶起這段經歷,他笑言這是他專業生涯的又一個里程標志,當年他全無負擔,抱著如果沒被選上就回家安度晚年的那份淡然(中規院規定70歲以上不再回聘),沒想到順利入選。而這次當選也促使他開始踐行起“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信念,此后每天奔波忙碌于國家行業領域各重要事務,如今算來已10年整。
就像他在當選院士的時候所說:“我不認為自己是權威,因為城市規劃沒有權威。城市規劃‘看似淺顯’,因為它貼近生活,誰都可以說三道四,‘評頭論足’,但它又很‘精深’,深在它的綜合性和復雜性。一個人很難具有如此全面的知識和經驗,去窮盡它的真諦。現在我感到自己又進入了專業歷程的一個新的階段,還有很多新的知識需要學習,許多新的經驗需要體驗,必須活到老,學到老,學一輩子……”
“活到老,學到老”,他做到了。10年間,他一直活躍在我們國家規劃設計領域第一線,為國家在相關專業領域里獻計獻策,并擔任中規院學術顧問等職。除此之外繼續“潤花著果”著書立作,總結經驗留給后者。但凡國家在規劃領域發生了哪些事情,他都愿意參與其中,參與討論,并提出一些建議。“中國城市應預防過度發展”“避免千城一律”……諸如此類的言論經常出現在各大媒體上。在參與的過程中,他也不斷提高著自己的知識和理念。
當院士之后,鄒德慈陸續擔任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南京大學、重慶大學等校的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先后帶出了不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現在,他自己有一個工作室,屬于中規院里的一個小的機構,工作室的一應事務都圍繞他運轉。
“我不把工作帶到休息時間中。”對于自己的工作節奏,鄒德慈保持一貫的實在,這位剛過80大壽的院士盡力展示著自己的平凡生活,每天盡力保持按點上下班,書畫、音樂都還喜歡,可是談不上愛好。閑下來就看看電視,最近央視有檔很火的文化綜藝節目《中國漢字聽寫大會》,鄒老也是“鐵桿粉絲”,對節目里青少年的表現他很是敬佩,他笑著說自己也會經常暗地里掂量:“要我來還真是拿不到冠軍……”
工作還在進行,鄒德慈一貫的踏實、實在也將延續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