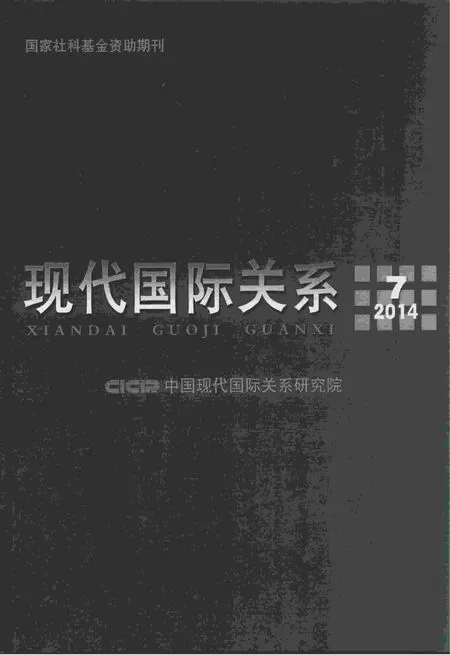如何認識國際秩序(體系)及其轉型?
林利民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吳興佐、黃昭宇、沈碧蓮、孫成昊)
什么是國際秩序?趙曉春教授將之定義為“國際體系內的成員為了維系國際體系的穩定與正常運轉,協調、處理各種國際事務而確立的準則、規范以及與之相應的保障機制、決策程序、議事規則等”;蔡拓教授將之定義為“國家行為體在國際交往與互動中所形成的特定的規范、制度、格局與體系”;袁鵬教授則將之定義為“通過主要國家的斗爭與協調而形成的規范重大國際行為的原則、機制的總和”。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秦亞青教授總結說:“國際秩序大約有三種類型,即權力秩序、規則秩序、規則關系混合型秩序”。他進而把這三種類型的國際秩序具體分為“五種形態”,包括單極主導型、兩極對抗型、兩極合作型、多邊協調型、松散多邊協商型(即關系規則混合類)。這些認識或定義無疑集中并代表中國最高層次的國際政治學者們有關國際秩序問題的最新看法,具有理論創新意義。
綜而論之,討論國際秩序不能脫離權力(及權力互動)、規則(準則、原則、規范)以及建立在權力、規則基礎上的機制。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會如此。
按照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以及中國國際政治學界一直以來大體接受的觀點,近代以來世界經歷了四次國際秩序(體系)轉型,每一次國際秩序轉型都涉及權力、規則及機制的調整與變化。其中第一次是由“無序”向威斯特伐利亞秩序(體系)的“有序”轉型;第二次是由威斯特伐利亞秩序(體系)向維也納秩序(體系)轉型;第三次是由維也納秩序(體系)向凡爾賽-華盛頓秩序(體系)轉型;第四次是由凡爾賽-華盛頓秩序(體系)向雅爾塔秩序(體系)轉型。一些西方學者認為,蘇聯解體、華約解散、東歐集體“倒戈”、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后,世界進入“單極時刻”,國際秩序由雅爾塔秩序(體系)轉型為單極秩序(體系)。如果這一觀點成立,則近代以來的國際秩序(體系)在前四次轉型之外,還有一個第五次轉型,即由雅爾塔秩序(體系)向單極秩序(體系)轉型。當前國際秩序(體系)正面臨新的轉型。按傳統國際政治邏輯和思維慣性,這將是國際秩序(體系)的第五次轉型(也可能是第六次——如果“單極秩序(體系)論”成立的話)。
問題討論至此:是否存在一個獨立的單極秩序(體系)以及是否存在一個從雅爾塔秩序(體系)向單極秩序(體系)的第五次國際秩序轉型?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概念與內涵之間是否存在本質區別?以及本次討論會為什么重點討論國際秩序而不是直指國際體系?等等,這些并非簡單的學理問題,而是關系到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理論話語,以及關系到如何認識未來國際秩序(體系)轉型的基本問題。
通常情況下,國際政治學界有一種混用、最少是不嚴格區分“秩序”與“體系”概念的傾向。然而,二者是有本質差異的。“體系”更真實、更具體、更強調權力及其作用。在“體系”概念中,規則、機制等只是權力的附屬物,而“秩序”較虛、較口語化、較“形而上”,更強調國際關系的運行狀態及權力與國際規范、機制等的綜合政治后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有可能存在五次或六次國際體系轉型,但肯定不存在五次或六次國際秩序轉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秩序)與維也納體系(秩序)只是歐洲體系(秩序),由歐洲主要國家確立的國際規范、機制只在歐洲有效,而在非歐世界,這些規則并未普遍適用。如“主權不可侵犯”原則,當時就只適用于歐洲國家處理其內部紛爭,歐洲人對非歐國家從來就未遵守過這一原則。因此,由前兩個體系及其規則、機制所確立的國際秩序不過是歐洲秩序,而非全球秩序,后二者是分裂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有較多的全球性成份,但其本質上仍然是歐洲體系、西方體系,其確立的規則、機制仍未平等、公平地通用于全球,仍然主要體現西方大國的權力、意志。因此,從非西方國家的立場觀察,前三個國際體系本質上是西方體系、由其規范的國際秩序是一種西方秩序,那時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國際秩序轉型。
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秩序轉型是建立在二戰及其政治成果基礎上的,奠基于雅爾塔體系的戰后國際秩序具有真正的全球性。其中,雖然美蘇仍然玩大國權力游戲,但權力作用范圍在收縮,規則、機制對國際秩序塑造以及規范國際關系運行的作用增大,并不斷增大、不斷擠壓大國權力的空間。《聯合國憲章》、《核不擴散條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都體現了戰后普遍性國際規范的作用增大;聯合國及其各附屬機構的成功運行、中國在美國不樂意的情形下被“黑人兄弟抬進聯合國”、以及美國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除名等,則體現了戰后國際機制的作用增大,體現了國際公平、進步。這是此前任何一種國際體系(秩序)中都不曾有的新現象。
雖然蘇聯解體導致雅爾塔體系解體,隨之出現了“單極時刻”,但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礎及其成果并未因此而削弱。相反,冷戰后大國權力進一步削弱,美國對世界影響力、控制力直線下降就是證明。與此同時,冷戰后聯合國及其他一些國際機制的功能以及各種國際規范的作用繼續增強,如“維和”作用增大、阻止美國打敘利亞等。雅爾塔體系解體后或許確實存在過單極體系、“單極時刻”,卻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單極秩序。雅爾塔體系或者所謂單極體系,都只能納入二戰后國際秩序的藍子里才能認清其成功與失敗。
總之,觀察未來國際秩序及其轉型,包括其轉型方向、性質及其方式,仍不能不以考察權力、規范、機制三要素為出發點。未來國際秩序轉型中,權力因素的影響進一步縮小,國際規范、國際機制的作用不斷增大將是基本趨勢、是國際潮流,任何人、任何國家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明乎此,作為國際影響力、塑造力不斷增大,國際利益不斷增大的崛起中大國,中國一方面要繼續增強綜合國力,另一方面又要慎用增長中的國際權勢、慎玩“權力游戲”,要在國際規范與國際機制改造、塑造過程中,在推動戰后國際秩序向21世紀國際新秩序轉型這一國際議程中,堅持戰后國際秩序中的合理成份,并不斷與時俱進,確保主動權、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