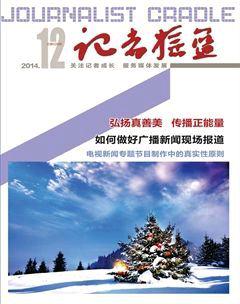新聞報道如何避免產生負面效應
徐艷輝
“不怕耳光,怕曝光;不怕通報,怕見報……”這句順口溜詮釋了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但是,新聞記者在報道時,就算堅持了新聞的真實性和深入采訪的精神,如果選材不當或者尺度掌握得不好,也會產生負面效應。明明是一個正面報道,卻沒有達到正面的效果,好心辦了壞事的情況也是存在的。所以記者在進行新聞報道時,也要考慮得全面一些,在凸顯正能量的同時,也要注意避免產生負面效應。
監督性報道尤其是具有破窗性新聞題材,要注意報道的角度。新聞監督,顧名思義,是通過報道進行曝光和揭露,抨擊時弊、抑惡揚善,以達到對其進行制約的目的。監督性報道,是老百姓非常喜聞樂見的,也是非常能體現媒體輿論監督作用的。但是如果把握不好,不但起不到監督作用,也會適得其反。
比如對亂建的報道、小開荒的報道,就要突出整治結果。亂建這是城市建設中的“腫瘤”,不但影響居民的正常生活環境,對市容市貌也會產生不良影響。在很多居民小區,居民對亂建都是深惡痛絕,希望職能部門能夠加大力度進行治理。現實情況卻是很多亂建都是很長時間以前遺留下來的,那時候老百姓意識不強,職能部門監督不到位,所以就成了歷史遺留問題,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再想治理,就很難著手了。對這樣的亂建問題進行報道就要謹慎進行。如果只報現象不報結果,或者壓根就沒有和職能部門溝通,沒有治理舉措就進行報道,那就起不到監督作用,反而會給其他人提供效仿的范例。所以對這樣題材的報道就要突出治理結果。記者在報道《亂建治理,需要重磅出擊》中就是采取了一追到底的報道方式。對亂建現象只是輕描淡寫似的帶過,重點報道了記者協調職能部門對亂建予以拆除的過程和結果。為了有這樣的結果,記者多次協調職能部門,并采取了跟蹤的報道方式,一方面突出了媒體的監督職能,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人的亂建想法。
對小開荒式的報道也是如此,有人把小開荒比喻成小區里的“牛皮癬”,具有很大的“傳染性”。報道得好,就會起到一定的教育意義,報道得不好,就會讓他人肆無忌憚地開荒種地,所以對這類題材的報道一定要突出整治,既然報道了,就要追究到底。
對正面人物的報道,要注意其所處的環境,也要選好尺度,不要夸大其詞。對正面人物進行報道一直是媒體在對人物報道時采用的主旋律,主要是想通過寫人物的先進事跡,反映出人物的先進思想,使之成為社會的共同財富。但是如果不考慮人物所處的環境,不考慮大局,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一位記者為了突出殘疾人自食其力的精神,報道了一位殘疾人沿街擺攤、供孩子讀書的事跡。對人物本身無可厚非,自食其力,不給社會帶來負擔,這種精神是值得頌揚的。可是這位記者卻忘記了殘疾人擺攤的環境,她是占道經營,應該屬于執法部門執法的對象,如果照顧了她,就影響了以后的執法工作,如果不照顧,又違背了媒體報道的初衷。所以對人物報道,要考慮其所處的生存環境。另外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在寫作時切不可把先進人物絕對化,寫人敘事力求言真意切,恰如其分。
對案件性新聞報道,不要透露作案、破案的細節。有些記者在對公安機關偵破案件的報道中,為了增強報道效果,把案件敘述得很詳盡,并且把作案手段也和盤托出,這樣的報道是很有聲色,但是報道之后,會讓一些人效仿,起到“教唆”的作用,結果一篇新聞報道卻成了反面教材。所以對這類新聞題材進行報道時不要過多講述細節,也要避免出現特別血腥、恐怖的畫面,以免對公眾造成不良影響。
不讓報道走向物質化、娛樂化。一些網絡媒體常常出現炫富的報道題材,在報道時還出現了“高富帥”的字眼,這樣的報道將公眾引向什么樣的方向呢?看到這樣的報道,公眾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心理呢?是嫌貧嫉富,還是心理失衡呢?新聞媒體采用這樣的題材進行報道沒有任何意義。
有些媒體充分利用了媒體的娛樂功能,開創了娛樂版面,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有的媒體過分利用了受眾的娛樂心理特點,不遺余力地推銷其“娛樂”產品,從中獲取利潤。有些新聞媒體為了吸引人的眼球,對一些影視明星的私生活也大肆報道,除了增加公眾茶余飯后的談資之外沒有任何正面意義,反而還會給一些青少年造成不良的影響。
新聞記者也要與時俱進,提高自己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素養。新聞報道要起到良好的教化作用,起到正面的宣傳效果,記者本身也要不斷提高自己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素養。所謂“身正影子才不會斜”。如果記者本身的世界觀就有問題,怎么會讓報道去宣傳正能量呢?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新聞報道,都能側面反映出寫作者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所以記者也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記者在采訪的時候,除了要堅持真實性和客觀性之外,也要多問一個“為什么”,增加報道的深度和廣度,這樣的新聞報道產生負效應的機會也才會更小。
總之,一篇良好的新聞報道一定要宣傳正能量,同時要具有“三維”或者“四維”的視角。在橫向上要有廣度,在縱向上要有深度,還要講究立體感,要有維度,要經得起推敲,這樣的報道才會更加全面具體,才不會背道而馳。■
(作者單位:本溪廣播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