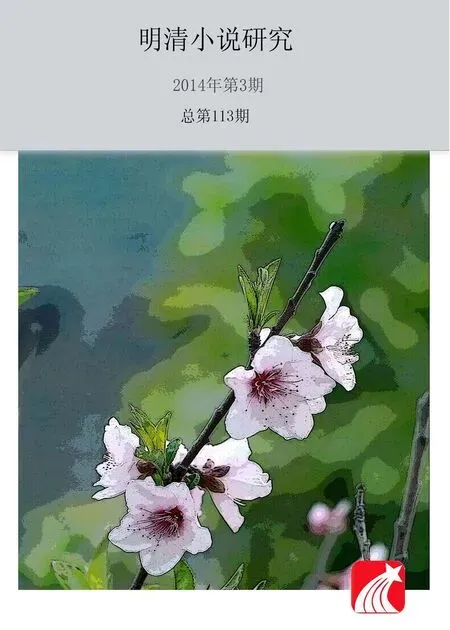順治十年李漁蘇北之行考述
··
順治十年李漁蘇北之行考述
·陳曉峰·
《南通范氏詩文世家·范國祿卷》中所收七律《次韻答李漁》,可考作于順治九年,詩中披露了李漁其時飽受長舌交構(gòu),與范國祿相訂移家通州,并對自己未來的小說、戲曲創(chuàng)作躊躇滿志、信心滿懷;所收《漕撫大司馬沈公狼山水操恭紀二十四韻》,披露了李漁曾與通州交游觀摩狼山水兵實戰(zhàn)演習,并聯(lián)句紀盛。詩中所涉李漁在通州的十多位交游皆可考辨。順治十年李漁的蘇北之行以通州、如皋為中心,更廣及揚州、泰州等地,此行對其后來的《無聲戲》小說創(chuàng)作頗有影響。
李漁 通州 揚州 交游 《無聲戲》
李漁出生于江蘇如皋①。清順治十年癸巳,李漁43歲時有蘇北之行,他重返出生地如皋,漫游通州(今南通),與當?shù)毓偌澪娜嗽娋平挥危污檹V及揚州、泰州等地。關(guān)于此次李漁的蘇北之行,以往所憑系年資料僅見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中所載:清順治十年(1653),“浙江李漁到南通訪范國祿、凌錄(木道)等,同泛舟芙蓉池,國祿作紀事詩”②。筆者新近翻檢《南通范氏詩文世家·范國祿卷》等文獻,發(fā)現(xiàn)了若干則與李漁此行相關(guān)的資料,其中以范氏《次韻答李漁》七律對李漁生平事跡的了解尤有裨益。本文試圖通過新舊資料的細致辨析,考察順治十年李漁蘇北之行的交游活動和交游對象,并進而探討此行對其《無聲戲》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
一、李漁通州交游的新資料
筆者從《南通范氏詩文世家·范國祿卷》及地方文獻中發(fā)現(xiàn)的李漁通州交游資料為二詩一評。二詩為李漁著述之外,他人別集中最早出現(xiàn)且標識明確時間的李漁交游材料。茲引錄如下,必要者結(jié)合李漁生平事跡予以考辨:
一是《漕撫大司馬沈公狼山水操恭紀二十四韻》,詩曰:
創(chuàng)業(yè)戎功懋,承平武備弛。先王雖耀德,殷國鼎 暇日豈忘危?開府兼司馬,喜越 行臺駐海涯。獻俘方戢眾,范國祐 善后復陳師。調(diào)度嫻敦琢,李漁 憑陵任指麾。將能優(yōu)戰(zhàn)略,吳彥國 士盡習軍儀。受甲蒼頭擁,姚咸 懸牙卿子隨。鍵橐須次第,僧寂光 營衛(wèi)趁提撕。同力搖波岳,凌錄 含威奮虎羆。大人貞則吉,吳生 三捷奏何私?部署衡夷險,楊麓 張皇振鼓鼙。船依山作壘,范國祿 水映日揚旗。斥堠俄傳警,楊時暹 聲援肯后期?中軍常不動,殷國鼎 四角每相維。茀茀從公氣,喜越 桓桓敵愾資。少焉驚電發(fā),范國祐 忽爾訝魚麗。簇聚螽蝗起,李漁 游迴鵝鸛移。接鋒看格斗,吳彥國 陷陣惜紛披。姚咸 鯨浪翻如雪,僧寂光 狼煙裊似絲。五成交七變,凌錄 六合出三奇。批亢崇奔命,吳生 秉虛戒失宜。鳴金知不黷,范國祿 稅介示無差。并受敉寧賞,楊麓 同歌《常武》詩。僧寂光 觀兵原用逷,伏莽敢潛窺?楊時暹
詩題后注:“時癸巳土賊平后。”③可知該詩記述的是順治十年癸巳李漁在通州與范國祿、范國祐、殷國鼎、喜越、吳彥國、姚咸、凌錄、楊麓、楊時暹等人觀摩的狼山水兵操練演習。康熙《通州志》卷十五《遺事》中錄有平土賊事:“順治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土寇竊發(fā),知州錢國琦、守備韓可桂剿滅之。”④是年,通州周應魁、王鼎在北鄉(xiāng)聚眾起事,發(fā)展到3000余人,圍攻通城,后為當政擊潰。
詩題中漕撫沈公即沈文奎,字清遠,浙江會稽人。少寄育外家王氏,因其姓。清趙弘恩等撰《江南通志》中《職官志》曰:“總漕部院自前明以來駐節(jié)淮安,以便趲運,國朝因之。順治六年裁去鳳撫,歸總漕,兼理巡撫事。”因總漕兼理撫事,故有“漕撫”一稱。沈文奎,“順治二年任”,“順治十年再任”⑤。通州三面巨浸,視為金湯門戶。《通州直隸州志》載:“(明)成祖永樂中置水操軍,以都御史督之,自九江以抵蘇松通泰。凡地方緩急、寇盜鹽徒出沒,聽調(diào)兵禽捕。”順治三年,“置副將一員,守備三員,把總六員,兵一千二百名”。注:“內(nèi)左營守備一員,把總二員,轄水師。”⑥該年平土賊后,沈文奎將率師討伐膠州叛將海時行,為增強水兵實際作戰(zhàn)能力,漕撫率兵于狼山水域進行實戰(zhàn)演習,李漁與通州諸詩人觀摩了演練盛況。士氣軒昂,鼙鼓震天,旌旗蔽日,將帥雄才大略,指揮得當,調(diào)度嫻熟,怒濤駭浪中士兵配合默契,陣行多變,游刃有余,諸位詩人嘆為觀止,聯(lián)句紀盛。
二是通州地方文獻《五山耆舊今集》“范國祿”條目下李漁之評價:
李笠翁曰:“小范為人沖夷而不流于俗,矯亢而不詭于時,交盡天下士而門無雜賓。括發(fā)著書,恒有欿然不自滿之色。李青蓮詩云‘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可以移贈。”⑦
范國祿,字汝受,一名灊,字平淵,號十山,又號秋墅。其父范鳳翼,雄才經(jīng)國,清德居鄉(xiāng),雖終身不合于奸邪小人,然海內(nèi)君子皆尊其品目。《通州直隸州志·文苑傳》言范國祿曰:“家多藏書,竭十年力,通貫大義,以詩文名震一時。過通者,得見祿,則無憂東道主。四方名宿及琴弈篆刻諸藝術(shù)士,莫不愿游五山,以祿在也。”⑧范國祿克紹其父,提倡風雅,慷慨好客,創(chuàng)造了通州山茨詩社彬彬之盛的新景觀。且與當時文壇名流侯方域、冒襄、王士禛、陳維崧、孫枝蔚、吳綺、宗元鼎、鄧漢儀、孔尚任等結(jié)交為友,相互唱酬。品格峻潔,才華橫溢,文名高著。
《五山耆舊集》(含《今集》)是清通州楊廷撰編纂的地方詩集,重視錄入作者事跡和他人的評論,頗具參考價值。《今集》收錄范國祿作品最多,條目下亦有王士禛、陳維崧、項嵋雪、張文峙等名流時賢評語。李漁年長十三,直呼范國祿為“小范”,對其廣結(jié)名流、沖夷拔俗之激賞,溢于言表。范國祿交游遍及天下,達官顯宦、布衣山人,文人名士、高僧大德,雖身份多元、兼收并蓄,卻是一定原則下的過往相從。李漁云其交盡天下士,門庭無雜賓,可謂對范國祿交友之深刻洞察,二人彼此默契、深度相知,由此可見。
三是《南通范氏詩文世家·范國祿卷》中的七律《次韻答李漁》,詩曰:
何用骯髒六尺為?文章自古傲須眉。一帆煙雨三吳道,孤劍風霜只影隨。青海卻憐長舌在,白狼相訂舉家移。平生尚有經(jīng)心事,旗鼓中原肯讓誰?⑨
范國祿著述頗豐,卷帙浩繁⑩,《南通范氏詩文世家·范國祿卷》收錄詩作3464首,以體相從,雖未加以嚴格編年,但詩作前后時間關(guān)聯(lián)還是依稀可見。范國祿《次韻答李漁》前有《夏日》、《丹桂》、《浴鷺》、《贈止上人》、《謂離上人》等,后為《人日和社》、《贈陳四丈》(有“玳瑁春深青鳥案,醁醽香泛紫鸞笙”語)、《哭童三兄》、《晴》(有“風卷殘煙斷雨簾,晴絲澹蕩景初奩”語)、《沙邊》(有“春光老去壯心寬,蓑雨灘頭把釣竿”語)、《次韻方太史拱乾贈葉光祿鳳歧》、《即席贈光祿公孫》、《贈原丈人》(有“開到榴花向北枝,南塘蓮子又香時”語)、《芙蓉池上同李漁、羅休、楊麓拿舟觀荷》、《朱甥元子始自延令來》、《日長如小年》、《新秋同吳彥國東山漫興》、《送雪上人返邗上兼訂來春之約》諸篇。通過詩題或者詩歌內(nèi)容,上年夏日至次年秋冬的時序脈絡隱然其間。范國祿順治十年作《芙蓉池上同李漁、羅休、楊麓拿舟觀荷》詩,按照上列詩題排列順序推斷,《次韻答李漁》當系于順治九年秋冬之際。
值得注意的是,范國祿《次韻答李漁》一詩,細加揣摩,其中透露了李漁順治十年前后生平事跡的若干重要線索。首聯(lián)突兀而出:“何用骯髒六尺為?文章自古傲須眉。”“骯髒”乃剛直倔強之貌。以此形容李漁,說明此時的李漁有一股抑郁不平之氣。抑郁何從而來?李漁原詩中當有所見,或過于直露,后來李漁編詩集時棄而不納。所幸范氏此聯(lián)留下一筆,與頸聯(lián)對讀,頓知由來。由頷聯(lián)“一帆煙雨三吳道,孤劍風霜只影隨”可知,李漁當時孤身流落,困窘無依,避居蘇州。頸聯(lián)“青海卻憐長舌在,白狼相訂舉家移”最值得推敲:“白狼”即通州狼山,傳說曾有白狼出沒,故有此名。宋劉弇《狼山記》曰:“白狼五山距通州城南十里,率不百步,則嶄然迭起。”通州東臨黃海,范國祿筆端屢現(xiàn)“青海”一詞,與“白狼”相類,均以指稱通州獨特山川風物。詩句所涉毋庸置疑的是,當時李漁飽受外界流言蜚語之中傷,淪落異鄉(xiāng),遠避是非之地、長舌之人,無怪乎其骯髒六尺,有抑郁不平之氣。他正考慮舉家搬遷,并有移居通州之念。其中緣由,一是通州與如皋相鄰,同有故土之親,二是與范國祿的交往,范氏對其文藝修養(yǎng)頗多仰慕。頸聯(lián)是對頷聯(lián)的轉(zhuǎn)折,“卻憐”二字,生動地體現(xiàn)了以范國祿為核心的通州友人接納淪落困境中的李漁的善意情懷。尾聯(lián)為“平生尚有經(jīng)心事,旗鼓中原肯讓誰”,可知李漁與范國祿交往中坦陳自己平生尚有“經(jīng)心事”。順治九年,李漁除了詩文以外,還有何更著意留心之事?毫無疑問,是指小說和戲曲創(chuàng)作,誠如其所云:“吾于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終不敢以小說為末技。”“漁自解覓梨棗以來,謬以作者自許。鴻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詩歌詞曲以及稗官野史,則實有微長。不效美婦一顰,不拾名流一唾,當世耳目,為我一新。”(李漁《與陳學山少宰》)其時已經(jīng)問世的《憐香伴》、《風箏誤》傳奇不過是李漁在戲曲創(chuàng)作方面初露鋒芒,他正處在一生中小說、戲曲創(chuàng)作的顛峰期,話本小說集《無聲戲》初集與二集即將在順治十一或十二年問世,傳奇《意中緣》、《蜃中樓》、《玉搔頭》、話本小說集《十二樓》也將次第而出。李漁向知己袒露“平生尚有經(jīng)心事”時,躊躇滿志、自信滿懷,讓范國祿對之熱切期待、大加贊賞。后來李漁果然不負眾望。若“經(jīng)心事”所指非小說、戲曲創(chuàng)作,李漁如此自命不凡,豈非咄咄怪事?此詩家語也,須結(jié)合事實燭隱探幽。范國祿對李漁文學創(chuàng)獲亦甚是期待,可謂藝文同調(diào)。李漁身陷困境之時賦詩范國祿,以訴衷腸,范氏答詩惺惺相惜,深情寬慰,傾心贊賞,相期碧海之濱,白狼山下,摯友相聚,共領(lǐng)江山勝跡,可謂患難之交。
此詩意義既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順治九年間,李漁飽受長舌交構(gòu)中傷的具體情事為何?其時他是在家鄉(xiāng)蘭溪或金華,還是已經(jīng)移家杭州?這條材料的發(fā)現(xiàn)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據(jù)1935年重修的《龍門李氏宗譜》卷一《水利》中記載:李漁欲使所在村的田畝得到自流灌溉,企圖開掘一條堰坑,但“后因拆生塘胡枏木廳欲建祠中饗堂,胡姓刁詐,事不如愿,結(jié)訟終止,此堰坑亦未開掘完局”,李漁因此不得不遠走他方。但《宗譜》并未記此事發(fā)生于何年,故不能認定此事即順治九年李漁企圖移家通州的原因,況且結(jié)訟與長舌交構(gòu)中傷不是一回事。
順治八年,李漁極可能已經(jīng)由家鄉(xiāng)移家杭州。細加玩味,范國祿此詩中言及其遭長舌中傷之事,很可能是因作品文字惹禍。李漁往往因此而遇到麻煩,其第一部傳奇刻印時,特地在卷首附《曲部誓詞》一篇,賭咒發(fā)誓宣告自己的作品不含影射諷刺。《柬滄園主人》則云:“弟之見怒于惡少,以前所撰拙劇,其間刻畫花面情形,酷肖此輩,后來盡遭慘戮,故生狐兔之悲是已。”文人健筆如刀,李漁作品更是窮形極相,稍不留意,不免觸忌,順治十七年的“《無聲戲》案”幾乎令李漁百口莫辯。順治九年間李漁飽受詆毀,遂有移家通州之念,其原因應與之如出一轍,筆端掀起波瀾,招致詬病。
二、順治十年李漁蘇北之行活動考察
通過以上材料可見,李漁順治十年的蘇北之行乃是應范國祿之約,此行以通州、如皋為中心。在通州,李漁與當?shù)毓偌潯⑽娜藦V泛交往,詩酒流連。交游活動除了上文所述觀摩水操外,現(xiàn)今可考的另有兩次:
一是盛夏觀荷。順治十年,李漁訪通,范國祿招游芙蓉池。此次賞游正為李漁一生酷愛之荷花。《閑情偶寄》中對荷花推崇備至:“無一時一刻,不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一絲,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谷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于此者乎?予四命之中,此命為最。”歡愛之情,溢于言表。范國祿置酒高會,儕輩同游,甚合客意,賓主盡歡,所作紀事詩為《芙蓉池上同李漁、羅休、楊麓拿舟觀荷》:“倚山池館就涼開,香泛荷花水半隈。欲向中流操楫去,卻從陸地蕩舟來。美人笑解江皋珮,醉客吟登澤畔臺。日暮風光青渺渺,蒲菰楊柳一濚洄。”
池水澄澈,微波蕩漾,楊柳依依,藤蘿掩映,田田蓮葉碧無窮,亭亭芙蓉暗香浮。賢人雅士畢集,蕩舟池中,蔚為一時勝景。芙蓉池位于通州范氏河上丈人垞旁,“河垞”始營于范鳳翼,其宦歸,“五被朝命,高臥不出”,順治五年十月筑于城東北隅,臨清河,肘古剎,舊為百客堂,后改建靜寄軒、問天閣、摩朅庵、竺子亭、小山道二堂、洗耳處。范鳳翼偃息其中,日惟讀書飲酒賦詩。其后,“國祿構(gòu)十山樓、奈何齋、小松廣、高光閣於其側(cè)”。遠離塵囂,悠然世外,四時綠蔭,水木清華,一幅天然畫卷。與李漁伊山別業(yè)相似,河垞是范氏家族數(shù)代精心營造的歸隱林泉、吟賞煙霞之所,成為明清時期通州地區(qū)重要的文化活動場所。對于熱衷置造園亭、獨具建筑藝術(shù)稟賦的李漁來說,范國祿芙蓉池招游,深具魅力,賓主流連山水,留意亭臺,飽含園林藝術(shù)的細致審美與品鑒。
二是隆冬賞桂。范國祿有《姚咸招同吳彥國、李漁、詹瑤、凌錄賞臘月桂花》,詩曰:“搖落霜林后,驚秋渺一園。玉煙依葉凈,金雪壓枝繁。瘦欲紉云影,幽宜淡月痕。歲寒情不盡,招隱荷香溫。”李漁對桂花亦是如癡如醉,《閑情偶寄》中曰:“秋花之香者,莫能如桂。樹乃月中之樹,香亦天上之香也。”此次與通州文士賞桂是由姚咸招至寓所,名為蕪原,園林歷史悠久,幽雅恬靜,林木蔥郁,四時風景各異,尤以桂花遠近聞名,是該地文人雅集的重要觀賞場所。順治十年隆冬時節(jié),李漁與通州諸文士徜徉古園,百花絕跡,唯臘月晚桂傲然綻放,風景這邊獨好,綴滿枝頭,云蒸霞蔚,真有梅之風骨。“歲寒情不盡,招隱荷香溫”,天地嚴寒,香在無尋處,清逸幽雅。處處皆成風景,漫步其間,暢敘情話,其樂融融,雅盡風流。數(shù)年之后,范國祿對往昔游賞感念不已,《蕪原賞桂有懷前主人姚咸先生》言:“秋老西園古桂林,客交歡伯坐清陰。日長不覺香盈體,夜靜渾忘露滿襟。好待月分燈火焰,更教風弄管弦音。小山種樹人何在,幾度臨樽問素心。”盛會不常,良朋星散,此景只可成追憶。
上文所述李漁順治十年通州交游,以往大都無考,現(xiàn)將除上文已述漕撫沈文奎、文士范國祿二人以外者考述如下:
范國祐,字汝申,號寒泉,齋號天庸,范國祿兄,諸生,著《天庸齋集》。其詩如秋水芙蓉,亭亭自遠。
凌錄,字水木,一字木道,通州人,諸生,著《冰雪攜集》、《竹灰集》、《愁課集》、《古文選》。保汜《哭凌水木》言:“未肯論交順物情,著書歷歲掩柴荊。客非犬熟門堅壁,談入雞元腹倒傾。過耳忽無揚子吃,比肩頓失晏嬰身。長驅(qū)不必相依戀,天地浮漚總寄生。”詩注:“水木口吃而身短。”凌錄遭時不遇,胸臆抑郁,盡發(fā)之于詩。詩主性靈,自然變化。
楊麓,字屵云,號不周山人,通州人,著《竹柳堂詩草》、《云社草》、《西林社草》、《自怡集》。楊廷撰《一經(jīng)堂詩話》言:“屵云少棄經(jīng)生業(yè),遍游吳越山水,歸與里中范十山、孫皆山、胡麟兮結(jié)社山茨。”
姚咸,字秋濤,號紉秋,通州人,諸生,山茨詩社成員,詞賦稱宗,丹青擅國,著《蕪原集》。
楊時暹,字赤文,號介亭,又號酒生,通州人。居北山之側(cè),吟嘯自娛,著《云山集》。
楊喜越,字太素,故籍鎮(zhèn)江,徙通,與范國祿輩結(jié)秋墅吟社,同編《狼五詩存》。
殷國鼎,通州人,有《孑庵集》。
吳彥國,字長文,徽州人。“善畫山水,尤精堪輿之學。故其足跡半天下,名山勝景莫不入其阿堵中。況披閱宋元墨跡更多,既豐于胸又富于目,落筆靈妙,置布得宜,名重當時”。
詹瑤,字號不詳,順治十年與吳彥國同寓通州,范國祿《送吳彥國》、《送詹瑤》中指稱彼此“同道”。
寂光、吳生,前者為僧,后系道士,是范國祿通州翕集歡會、風雅唱和的積極參與者,順治六年冬月,范國祿宴集,勝流如云,詩文樽酒,極一時之盛,其中有“道士吳生,森牧、映空、寂光、智融四上人”。
通過李漁順治十年通州交游活動及對象考察,可見其以文會友,友人中既有顯赫英武、叱咤風云的一方武官,亦有安貧守節(jié)、雅愛詩文的江湖文人,興趣相投,詩酒酬唱,是李漁一生廣泛交游的典型代表。
此行李漁的另一重要目的地是通州以西的如皋,他的出生之地。其必為之事是祭奠亡兄,有七律《過雉皋憶先大兄》,小序云:“大兄歿于此地,旅櫬在焉。”后二聯(lián)云:“在日塤篪無可樂,別來急難有誰驚。明朝謁墓愁風雨,一哭能教地有聲。”手足之情,真摯感人。詩中亦可見少年李漁在如皋的生活并不快樂。重返故土,或許能見到兒時游伴,李漁又有《詠綠燭和雉皋諸友》。
同時,由上述材料可見,順治十年李漁蘇北之行,從夏至冬,淹留時間至少八、九個月之長,而且在通州觀荷的夏日并非其來到蘇北的起始時間,如果其系本年年初由“三吳道”轉(zhuǎn)赴蘇北的話,淹留時間就更長了。一為躲避流言蜚語之中傷,二為考察舉家遷移之地點,如此則時日不可能短。其行跡并不局限于通州、如皋兩地,與之相鄰的泰州、揚州等蘇北諸地均可見其行蹤。過泰州有《清明日海陵道中》,前一首為《姑蘇雪泊》,后第三首為《過雉皋憶先大兄》,可見順治九年冬日李漁猶在蘇州,次年清明過泰州,赴雉皋祭先大兄。《清明日海陵道中》末二句為“欲飽妻孥因作客,為家何必更思家”,正符合李漁此時孤身流落、困窘無依的情境。
來泰州必然經(jīng)過揚州。李漁詩文中涉及揚州者不勝枚舉,直接以廣陵入題者亦多多,如《訂友同赴廣陵》、《廣陵歸日示諸兒女》、《廣陵肆中書所見》等等。《渡揚子》有云:“目在妙高猶未轉(zhuǎn),人煙稠處已瓜洲。”于此可見李漁往往由鎮(zhèn)江金山渡江,經(jīng)瓜洲赴揚州,然后有蘇北之行。《薄命歌》為李漁詩集中七古第一首,小序云:“有揚州女,適杭人為妾,厄于悍婦,懨懨待斃,似為小青之續(xù)者。何廣陵不少名花而武林之多妒雨也?因賦長歌,代為寫怨。”以閨怨寫失意,乃古代文人的傳統(tǒng),“何廣陵不少名花而武林之多妒雨”之問,或許包含已移家杭州的李漁受長舌中傷后的憤懣。
至于李漁最終為何沒有選擇移居通州,筆者推測原因,其一是李漁飽經(jīng)戰(zhàn)亂,心有余悸,對舉家移遷之地的選擇首先是安定,其時通州并非世外桃源,順治十年李漁親聞土賊暴亂,且海邊寇盜不斷,漕撫沈文奎順治十一年仍用兵該地,“遣兵捕朱周祺,清通、泰濱海逋寇”;其二是李漁熱愛小說、戲曲創(chuàng)作,有沒有接受流播通俗文化的地域氛圍,也是其移家目的地選擇考量的題中應有之義,在這一方面通州自然無法與金陵、杭州相提并論。
三、李漁蘇北之行與小說創(chuàng)作
清初,揚州乃揚州府府治所在地,泰州、如皋、通州皆在管轄之中。揚州或廣陵獨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歷史淵源,豐厚的文化底蘊,使之成為蘇北的代名詞,李漁詩文中亦往往以揚州或廣陵之行代稱蘇北之行。如前所述,李漁幼時寓居如皋,生斯長斯,返回蘭溪后直至順治十年前,其間有蘇北之游,對揚州自不陌生。然而順治十年蘇北之行格外特殊,年過不惑,故地重游,往來通州、如皋、泰州、揚州之間,與摯友涸轍之鮒,相濡以沫,飽受創(chuàng)傷、流離失所之際的故土回歸、友人接納刻骨銘心。其逗留遷延,遲遲未去,流連蘇北各地市井街巷,飽覽山川風物,結(jié)交官紳同好,一切皆打并入他的“揚州情結(jié)”之中,導致緊隨其后結(jié)撰的小說《無聲戲》(后改名為《連城璧》)中以揚州作為故事敘述背景的作品屢有出現(xiàn),揚州的市井風情、社會眾生相頻現(xiàn)筆端,主要表現(xiàn)于以下方面:
坊街廛市。蘇北州縣、廣陵街市,李漁頗為熟悉,小說多處提及,如《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jié)》中馬麟如,在揚州人潮涌動的瓊花觀前租間店面行醫(yī),頗有聲名,其后萬子淵頂替行醫(yī),又怕露出破綻,隨即搬至小東門外。不幸沾染時氣,害病身死,以前積聚的東西,盡為雇工人與地方所得,“同到江都縣遞一張報呈,知縣批著地方收殮”,最終,“抬去丟在新城腳下”。《寡婦設(shè)計贅新郎 眾美齊心奪才子》中的呂哉生祖籍福建,父親呂春陽曾于揚州小東門外開了個雜貨鋪子,在此安家置業(yè)。《人宿妓窮鬼訴嫖冤》中王四原是小東門外篦頭的待詔,雪娘翻臉后自知人財兩空,于是趕到江都縣擊鼓。運官設(shè)計為王四討回銀兩,收了老鴇一百二十兩銀子,不還票約,老鴇恐遺后患,雇船跟從,追到高郵州。這三篇小說中瓊花觀、小東門、新城腳下、江都縣、高郵州等,涉及揚州諸多地名,往來穿梭,轉(zhuǎn)換自然,頗為真實,若非較長時間的實地生活經(jīng)驗,恐不能俯拾即是,如數(shù)道來。揚州街頭俗尚奢華,女子尤為講究裝扮,修冶容,斗巧妝,戴金玉為首飾,雜以明珠翠羽,服飾華麗新穎。時風所及,影響士流,《改八字苦盡甘來》中的刑廳堪稱代表。該官為青年進士,“是揚州人,極喜穿著”。如此好尚不免以貌取人,“凡是各役中衣帽齊整、模樣干凈的就看顧他,見了那襤褸齷齪的,不是罵,就是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時衙門大小,“都穿綢著絹起來,頭上簪了茉莉花,袖中燒了安息香,到官面前乞憐邀寵”。作家敏銳捕捉到了揚州街頭青年熱衷時尚、追攀效仿的典型風貌,外表妝飾,衣著穿戴,頗為詳盡。小說甚至不惜渲染衣飾對于貴賤窮通的決定作用,刑廳對蔣成之襤褸頗為憐惜,取出十兩銀子,教他換身裝束前來聽差。蔣成“隨往典鋪買了幾件時興衣服,又結(jié)了一頂瓦楞帽子”,頓時改頭換面,諸人黯然失色,自此與刑廳時刻不離,終做了腹心耳目。蔣成前窮后通,天淵之隔,其中改變命運的重要因素竟是十兩銀子換來的衣帽裝束,揚州人極喜穿著的緣由于此可見一斑。
災異時變。順治十年,蘇北平原遭遇歷史罕見之干旱,災情持續(xù),赤地千里。《重修揚州府志·事略》引《高郵州志》曰:“大旱,饑。”《東皋詩存》收余庚的五律《月蝕》,亦述及是年大旱情形,題序曰:“歲癸巳亢旱,蕎麥種每石銀三十兩,從來所罕聞見者。占驗書云:‘中秋無月則蕎麥不實。’是夜月蝕殆盡,憂而賦此。”李漁詩集中五古《月蝕》應作于該時。小說《失千金福因禍至》中也描寫了這場自然災害:“不想那一年淮揚兩府饑饉異常,家家戶戶做種的稻子都舂米吃了,等到播種之際,一粒也無,稻子竟賣到五兩一擔。”秦世芳米貨一到,“千人萬人爭買,就是珍珠也沒有這等值錢”。這里李漁是將順治十年置身淮揚的耳聞目見寫到了作品中,小說形象地刻畫了揚州一帶饑荒遍地、米價騰飛、民不聊生的社會現(xiàn)象,表現(xiàn)出對惡劣自然環(huán)境中下層民眾的關(guān)注。
青樓風月。揚州川澤秀媚,淑靈之氣浸潤下女子面容姣好,性情溫柔,舉止婉轉(zhuǎn),聲名遠播,也滋生出該地特有的青樓文化,李漁《無聲戲》小說中亦不免涉及。《寡婦設(shè)計贅新郎 眾美齊心奪才子》中言:“從來女色出在揚州,男色出在福建,這兩件土產(chǎn)是天下聞名的。”李漁筆下對該地粉黛綺羅之盛大加渲染,贊不絕口,不無艷羨之意。廣陵姬妾,芳菲麗質(zhì),風情萬種,謝肇淛《五雜組》卷八曰:“揚人習以此為奇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屬,以徼厚直,謂之‘瘦馬。’”富家子弟納寵揚州,蔚然成風,李漁甚至代江南顯貴到揚州選妾擇姬。其小說亦見該地蓄“瘦馬”的風習,上篇呂春陽在揚腳跟立穩(wěn),娶的那位妻子即是個極美麗的“瘦馬”,標致齊整,風姿綽約。揚州十里春風路,秦樓楚館,鱗次櫛比,歌弦絲管,不絕于耳。高樓紅袖客紛紛,文人墨客、豪商富賈追芳逐艷,恣意漁獵。李漁亦屬風流才子,出入揚州花街柳巷,對風月女性自不陌生。同時,在小說中關(guān)注了這一特殊社會階層,塑造了揚州青樓女子形象,通過人物事件傳達出特定內(nèi)涵,如《人宿妓窮鬼訴嫖冤》中的揚州妓婦雪娘,“生得態(tài)似輕云,腰同細柳,雖不是朵無賽的瓊花,鈔關(guān)上的姊妹,也要數(shù)他第一”。雪娘美艷非凡,然而唯利是圖,滿口答應王生贖身從良之約,私下卻伙同老鴇坑蒙拐騙,導致王生愿望落空,一貧如洗,甚至險遭性命之虞,最終因漕糧運官主持公道,化險為夷。李漁通過沾染惡習、靈魂扭曲之揚州青樓女子形象的塑造,耳提面命,勸世人及早回頭,不可貪戀風流。
科考行醫(yī)。李漁傳奇《玉搔頭》卷首黃鶴山農(nóng)序曰:“笠翁髫歲即著神穎之稱,于詩賦古文詞罔不優(yōu)贍。”崇禎八年李漁于金華應童子試,以五經(jīng)見拔,為主試官、浙江提學副使許豸賞識,刊刻李漁試卷,另為一帙,每按一部,輒以告人曰:“吾于婺州得一五經(jīng)童子,詎非僅事!”(《〈春及堂詩〉跋》)李漁對其獎譽之舉、知遇之恩感激不盡。學界對李漁離開如皋之時間、原因尚有爭議,各執(zhí)一詞。《寡婦設(shè)計贅新郎 眾美齊心奪才子》中人物遭際或可提供李漁生平行跡的若干信息。呂哉生為風流才子,一意功名,十四歲赴考,縣尊取為第一。“揚州的人見他不是本處籍貫,就攻起冒籍來。寫了知單,各處粘貼,要等府試院試之日,一起攻打,不容他進場。”呂為家中獨子,其父豈肯易性命換功名,“就丟了揚州不考,竟領(lǐng)他回到故鄉(xiāng),復還本籍”。回到家鄉(xiāng)福建,由縣而府,由府而道,一路領(lǐng)先。據(jù)此情節(jié),或可推測少年李漁也曾有過在揚州府如皋縣赴縣試的經(jīng)歷,離開如皋返回蘭溪主要是因參加科舉之便。
李漁世代布衣,父輩流寓如皋經(jīng)營醫(yī)藥之業(yè),伯父李如椿為冠帶醫(yī)生,李漁乳發(fā)未燥之時常隨其游于官宦之門。《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jié)》中馬麟如的形象值得關(guān)注。馬麟如自垂髫之年,就入了學,“人都以神童目之,道是兩榜中人物。怎奈他自恃聰明,不肯專心舉業(yè),不但詩詞歌賦件件俱能,就是琴棋書畫的技藝,星相醫(yī)卜的術(shù)數(shù),沒有一般不會”。麟如聰慧異常,各類醫(yī)書觸類旁通,鄰里鄉(xiāng)黨患疑難雜癥者,前來就診,把脈定方,病不無治。因此荒疏了舉業(yè),歲試失意,隨即外出行醫(yī)。到了揚州,“就在瓊花觀前租間店面,掛了‘儒醫(yī)馬麟如’的招牌。不多幾時,就有知府請他看病”。知府患疾多時,病榻之前醫(yī)者走馬換燈,人各一方,元氣消磨殆盡,危在旦夕。“麟如走到,只用一帖清理的藥,以后就補元氣,不上數(shù)帖,知府病勢退完,依舊升堂理事,道他有活命之功,十分優(yōu)待。”從馬麟如形象的塑造中可明顯看到李漁對舉業(yè)的態(tài)度及其父祖輩如皋行醫(yī)的身影,讀來尤為熟悉,倍感親切。
經(jīng)商治生。自隋煬帝開鑿京杭大運河,揚州逐漸形成南北交通的樞紐和全國財貨的集散地,四方舟車,冠蓋往來,商賈萃集,奔競財富。李漁筆下呈現(xiàn)了揚州民間商人的社會生活,如《失千金福因禍至》中秦世芳,偶遇商機,平地登仙。“在揚州買了一宗岕茶,裝到京師去賣,京師一向只吃松蘿,不吃岕茶的,那一年疫病大作,發(fā)熱口干的人吃了岕茶,即便止渴,世芳的茶葉竟當了藥賣。不上數(shù)月,又是一本十利。”隨后思家心切,“就在京師搭了便船,路上又置些北貨,帶到揚州發(fā)賣。雖然不及以前的利息,也有個四五分錢。此時連本算來,將有三萬之數(shù)”。李漁以日常生活為視角,刻畫了秦世芳機遇致富的過程,四處奔波,長途販運,努力經(jīng)營,終獲豐厚利潤。揚州繁華以鹽盛,明清時期,鹽商輻輳,富甲天下,推動了城市商業(yè)與文化的興盛。鹽商中間不乏貪得無厭、為富不仁之徒,如《變女為兒菩薩巧》中揚州府泰州鹽場灶戶施達卿,腰纏萬貫,“原以燒鹽起家,后來發(fā)了財,也還不離本業(yè),但只是發(fā)本錢與別人燒,自己坐收其利。家資雖不上半萬,每年的出息倒也有數(shù)千”。灶戶赤貧者仰仗其借銀燒鹽,施達卿利心太重,刻薄窮民,燒出鹽來,“除使用之外,他得七分,燒的只得三分。家中又有田產(chǎn)屋業(yè),利上盤起利來,一日富似一日”。該人年屆六十,膝下無子,夢得神明,指點迷津,于是散盡家財,扶危濟困,廣施眾舍,終得子嗣。因果報應支配下的情節(jié)安排中,顯然滲透了作者對揚州鹽商中貪婪刻薄者的批判和揭露。
縱觀李漁小說,揚州元素如此頻繁密集地出現(xiàn),在清初話本小說作家中可謂獨樹一幟,營構(gòu)了獨具特色的城市敘述空間。據(jù)現(xiàn)有材料,順治十年蘇北之行是李漁離開出生地后為數(shù)不多、時間最長的返鄉(xiāng)經(jīng)歷。生活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泉,順治十年,李漁往來蘇北諸地,履步街巷,追憶往昔,注目當下,激活、豐富并深化了自己的揚州記憶,此地成為其熟悉且寄寓深情之地。緊隨其后,順治十一年、十二年他的《無聲戲》一集、二集成書,其中現(xiàn)存擬話本小說18篇,以揚州作為故事發(fā)生地點或者小說情節(jié)與揚州緊密關(guān)聯(lián)的作品多達6篇,占1/3。筆觸如此廣泛深入地伸向一座城市,在李漁小說中絕無僅有。熱鬧繁華的街巷、聲色斑斕的市井、悲歡離合的情感……城市圖景、人事風情、災異時變,包括其寄寓在人物形象中的生平行跡得到藝術(shù)再現(xiàn),對該地的眷念可見一斑,足以說明順治十年李漁蘇北之行對于小說《無聲戲》構(gòu)思、創(chuàng)作的深刻影響,其中一些篇目可能就誕生于此期間。對于小說故事發(fā)生地點的設(shè)置存在虛構(gòu)和親歷兩種情況,前者難免顯得浮光掠影、語焉不詳,后者則必定細致真切、如置其間,李漁小說中的揚州無疑屬于后者。城市文化、社會百態(tài)與作家當?shù)厣罱?jīng)歷緊密結(jié)合,沉淀為李漁內(nèi)心深處的“揚州情結(jié)”,啟迪了創(chuàng)作靈感,提煉為創(chuàng)作素材,豐富了小說內(nèi)容。
注:
① 清雍正二年通州升為直隸縣,如皋劃歸通州管轄,此前如皋長期隸屬泰州。
②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54頁。
④ [清]王宜亨等撰《(康熙)通州志》卷十五,南通市圖書館1962年油印本。
⑤ [清]趙弘恩等撰《(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五,《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0冊第131頁。
⑦ [清]楊廷撰編《五山耆舊今集》卷二,道光四年一經(jīng)堂刻本。
⑩ 康熙十七年,范國祿將自著詩文加以整理,有《十山樓稿》六十卷、《紉香集》、《掃雪集》、《聽濤集》、《江湖游集》、《古學一斑》、《深秋聲》、《漫煙集》、《浪游集》、《山茨社詩品》、《賦玉詞》等。
責任編輯:胡蓮玉
*本文為江蘇省南通市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13CNT008)、南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項目編號:12W73)階段性研究成果。
揚州大學文學院、南通大學范曾藝術(shù)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