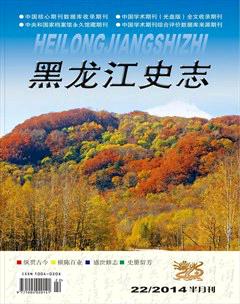崔述與夏史研究
朱思遠+胡曉文
[摘 要]崔述的《考信錄》內容廣泛,其中對夏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夏考信錄》中。崔述對歷代文獻典籍中,關于夏的記載都頗有微詞。在《夏考信錄》中,他對清朝以前的文獻中,所記載的關于夏的部分進行考證,本文聯系當代夏史研究的結果對崔述的考證結果進行探討。
[關鍵詞]崔述;夏史;考信錄
崔述,乾隆五年生于直隸大名府魏縣,字武承,號東壁,卒于嘉慶二十一年。他一生嘔心瀝血寫得一部《考信錄》,全書共三十二卷。崔述繼承家學,攻讀史書極其勤奮,涉獵廣泛,音韻訓詁、天文數歷、地理皆懂。他一生只任過福建省羅源縣知縣,用畢生精力來治學。《考信錄》對后世研究中國古史有很大影響,奠定了他在考信辨偽學上的地位,堪稱這一領域的泰斗。崔述上承宋儒的辨偽思想,下啟民國時期的辨偽思想,對“古史辨”派的形成有很大影響。關于研究崔述的著作有顧頡剛的《崔東壁遺書》、吳量愷的《崔述評傳》、邵東方的《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研究崔述的文章還比較多。但這些成果大多是研究崔述的治學思想、學術源流、崔述生平、崔述與顧頡剛及古史辨派的關系及在中國疑古辨偽史上的地位。對他僅有的著作《考信錄》的研究,也只是研究《考信錄》所體現的崔述的思想體系及其在考證方法上的局限性,并沒有對《考信錄》的內容進行研究。關于研究夏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但多是研究夏的文化遺址,夏族的起源,夏的文化源流及其區系,對夏的史實研究的較少。所以,本文以《夏考信錄》為基礎,研究崔述對歷代史書中關于夏朝歷史記載的考證,并結合現代人對夏的認識,就以下幾個方面對崔述與夏史研究進行探討。
一、崔述有關夏史的考證
由于崔述在《考信錄》中以《六經》、孔孟之言為標準,對其它史書的價值來了個大否定。他說:“周道既衰,異端并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不造言設事以誣圣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為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1),“自戰國以來,邪說并作,皆托圣人之言以取信于世,亦有圣人之徒傳而失其真者。漢、晉諸儒罔能辨識。至唐、宋時尊信日久,益莫敢以為非”(2),“《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之屬,率皆旁采卮言,真偽相淆”(3)。所以最終他的考證原則就是,不敢把成書于戰國、秦漢、魏晉時期的著作中,所敘述的夏朝時期的事情當做史實。但是,這不免有些偏頗。邵東方在《崔述學術中的幾個問題》中說:“崔述在承認經書中材料的可靠性的前提下從事考證的,然而以經書為標準去懷疑古書、古史并判斷其可靠性,必然會使崔述的考證工作受到極大的約束。”(4)崔述懷疑后世之書、偽書傳說,但是不能一概否定,它們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比如偽書和傳說,徐旭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說到:“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他歷史方面的素質、核心,并不是向壁虛造的。”(5)
就崔述《夏考信錄》,筆者認為并不是全都是考證的有理有據的,有些確系用書籍互證,文風文體等方法綜合起來一起考證的,很嚴謹。但是有些不是,只是憑崔述的一己之見就下定論,這未免有些唐突。吳量愷在《崔述評傳》中就提到:“崔述的考證有不夠全面和絕對化的毛病。因為古人的學識未必都比后代人好,他們也受到時代的限制,如科學發展水平、人的認識能力、資料的局限等因素的制約,后代距古時較遠,對古代了解較少,辨識有困難,但也有后代的有利條件,如科學水平的進步,對客觀事物認識能力的提高以及新資料的不斷發現,前代深信不疑的后代未必全信,前代認識不周或有意造偽之處,后人未必都不能覺察……崔述能對史書、經書進行考證辨析,寫成《考信錄》,是在清朝的乾、嘉時期,而不是在清之前。這有力地證明了后人的學識、能力不一定都比前人差。”(6)尤其是在后代,由于地下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甲骨文、金文、竹簡的出土,馬王堆的帛書,云夢睡虎地的秦簡,周原發現的青銅器物等,更使人開闊眼界,看到了過去前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文字和實物資料,這應當補充于歷史之中。
崔述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作為人的理想化、標準化、規范化的楷模。他認為“圣人”和“圣君”不會做不合禮法的事情,否則就不能被稱為“圣人”、“圣君”了。就因為這樣他否定了湯曾為桀臣的事實,以免因為“湯放桀”而毀了圣人的形象。這未免有些有失標準。
崔述在《夏考信錄》中通過論述《論語集注》和近世的人關于禹“躬稼”、“教稼”不同看法,沒有通過相關論證,就直接用“語意不倫”的理由下了定論,他認為“躬稼非教稼”,不可混為一談,而且認為禹沒有“教稼”、“躬稼”。但是禹在鯀死后被貶為庶人,曾經親歷畎畝,怎么說是沒有“躬稼”過呢。
崔述的《夏考信錄》提出了“家天下不始于禹”(7)的說法。世之論者都說:“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8)。后世有人解釋說:“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后世爭之之亂也。”(9)還有的人說:“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10)。崔述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益的功德未必就遜于禹,益與禹都在九官之列,都有大功,都能輔佐舜成大事。益視禹就像當時禹視舜一樣,不能說益非其人不應得天下。禹如果考慮到后人爭位,那就更不會傳給自己的兒子了。如果傳給兒子,天下人必會議論其私心。虞舜時天下就非一姓,傳給自己的兒子也可能會發生爭亂,怎么能說禹擔心會發生爭亂而傳子?所以,傳子是不可能會避免戰亂的。崔述認為:禹未曾傳啟,也未曾傳益。堯舜及以前的時候,天下之人均擇有德之人而歸之,不存在傳子和傳賢的差別。禹死后天下是歸于啟還是歸于益,禹是不可能過問的,也是不能夠決定的。他最后提出來三代時期的家天下之制,萌生于啟,后經歷少康、杼等各個王的繼承和演變,最后形成定制是在商朝,與禹無關,即“夏之世守天下,至少康、杼之后始然”(11),故家天下不是從禹開始的。
關于禹、益、啟之間即位之事,孫淼認為:“禹和益之間不是什么禪讓,而是一場你爭我奪的激烈的斗爭。首先是益篡奪了禹的職位,啟又殺益而奪回了領袖的職位,這就是《竹書紀年》所說的:‘益干啟位啟殺之。”(12)他列出來證明:“《晉書·束皙傳》引《竹書紀年》云:‘益干啟位啟殺之。《史通·疑古篇》引《竹書紀年》云:‘益為啟所誅。《史通·雜說篇》云:‘《竹書紀年》出于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韓非子·外主說右下》云:‘古者禹死,將傳天下于益,啟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啟。《戰國策·燕策一》云:‘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史記·燕召公世家》云:‘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人為不足任天下,傳之于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13)這些記載,推翻了一直流傳的禹和益之間禪讓的傳說。沈長云對這個問題也有所看法,他認為:禹“打算著按老規矩要將國君的位置轉授給來自東夷的部落首領皋陶和伯益,但他同時卻又很自然的將自己兒子啟為首的本家族勢力引入夏朝廷中的各級權力機構。即如戰國時文獻所說:‘禹愛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啟人即禹子啟家族之人。禹以自己家族之人掌管各權力部門,無異已在營造自己‘家天下的勢力了。”(14)所以,這種權利結構的組成已經使得禹不想再將國君的位置交給他人,禹雖然還是做出了傳賢的姿態,其實命令啟去謀得君位。最終,“家天下的制度是奠基于禹統治的時期,而體現在啟最終繼承禹的國君位置這件事情上。”(15)
后羿射掉空中十個太陽中九個的事情,廣為流傳。崔述認為,后羿非射中十中之九日,而是一日之射中九鳥,三、五、九在古代是很多的意思。他糾正了世人的錯誤的看法,敢于質疑亙久的傳說。他還總結道:秦漢時一些不合經義的說法,都是誤會古人的原意,誤讀原句、又轉加復述、曲解附會造成的。后人誦讀,以為由來已久,遂不敢輕易議論,而以誤傳誤。
二、當前對崔述夏史研究的有關探討及啟示
《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16)此處,崔述在《夏考信錄》中做按,認為“貢金九牧”應為“九州之牧貢金”,因為這樣才文義通順,況且九州又不是都產金,怎么會都進貢金,他認為這段話應該以六字為句,“遠方之國圖物貢金,而九州之牧鑄鼎象物”(17),這樣與文理較順。崔述只是猜測九州肯定不是都產金的,所以不可能九州都要貢金。在九州的貢品的問題上,邵望平在《<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一文中指出:“考古資料已經證明荊、揚二州進貢象犀孔翠,豫、兗二州盛產漆竹蠶桑是真實可信的。此外,‘降丘宅土可能是龍山時代至商代黃河下游地區先民生活的特點;‘淮夷蠙珠及魚可能是指當時‘徐州特產的厚殼蚌制品及鱷魚皮;‘島夷卉服是亞熱帶氣候條件下舟山島民的風土記錄等等。”(18)這些映證了崔述九州不可能都貢金的觀點。
在“九州”這個問題上,崔述認為九州是存在的,但禹時九州與后代的九州的范圍是不一樣的,而且對《禹貢》的成書年代,沒有給出答案。當代人對“九州”這個問題還是有爭議的,有人認為“九州”在當時是存在的,有人認為是后人杜撰的。關于“九州”的問題,邵望平先生在《<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一文中,通過對黃河長江流域古代文化區系的研究,來證明《禹貢》“九州”的真實性。同時《禹貢》書中所記載的對黃河、長江流域九個區系山川、土壤、植被、物產、手工特產、人文等情況以及中央王國對各州田畝、賦稅、貢品的規定和貢道的記錄,也應是可信的。但是也應注意到,作者的地理知識僅限于商朝末年周朝初年中央所知的“天下”,還遠遠沒有達到戰國時的水平。“九州”并不是戰國時代的托古假設,而是有三代的史實依據(19)。關于《禹貢》的成書年代,鄭杰祥有不同看法,“《禹貢》所述九州的規模,不僅夏王朝不能實現,就是在商代……除了在畿內,還無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九州地域組織以進行統治……只有到了戰國時期,隨著鐵器的普遍應用,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各地交往的頻繁,才能為《禹貢》的創作奠定物質和思想上的基礎。適應著經濟發展的需要,人們要求政治上統一的愿望愈加強烈起來,而《禹貢》正是當時思想家們為未來的統一設想出來的一種政治方案。”(20)
《史記·夏本紀》云:“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臾洛汭,作五子之歌。”(21)太康失國的具體情況,《史記》里沒有記載,但是在《左傳·襄公四年》有所記載:“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鋤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22)崔述對太康失國、少康中興之事中的細節問題有所疑問,如:“仲康既在故國,相何以又在帝丘”(23),但是對其基本大事沒有疑問。徐中舒在《夏代的歷史與夏商之際夏民族的遷徙》中指出:“窮石地區就是鬲的所在地,也就是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交會之地區。羿在這個地方,把夏滅掉了。但是,他自恃善射,不理政事,不用賢人,而用寒浞。寒浞滅了羿,奪其妻,生澆及豷,封澆于過,封豷于戈。過在掖縣,戈在宋鄭之間,都是黑陶文化區。夏的失國,表示了東方黑陶文化區與西方彩陶文化區的斗爭,這種斗爭的前提,必須是黑陶文化進入低地區域。雖然最初是夷戰勝了夏,但是,這一次最終還是夏戰勝了。所以,《左傳·哀公元年》說,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而‘復禹之績。這也就是所謂的少康中興。”(24)可見在地下發掘出的遺址中所發現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因素與史籍中所記載的相一致,這就證明了史實的少康中興的真實性。
《國語·魯語》云:“桀奔南巢。”(25)“湯伐桀,桀奔南巢”見于《尚書·仲虺》、《國語·魯語上》、《古本竹書紀年》、《呂氏春秋·論威》及《說苑·權謀》等周代秦漢時期典籍。這一事件,崔述沒有質疑,但是關于南巢的地望,前人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杜金鵬在《夏商文化斷代探索》指出:“關于南巢之地望,學者多以為即春秋時吳、楚間之巢國、秦漢西晉時之廬江郡居巢縣、唐宋之廬州巢縣。此外,還有南巢在宋代舒州桐城縣說。關于春秋巢國,杜預認為即六縣東之居巢城,羅泌亦云‘故巢城在皖北六東,六縣即今安徽六安縣,皖即合肥,桐城亦即今桐城。又據在巢湖市郊發現的唐代伍鈞墓志銘云,墓之所在南燾鄉紫薇里即古南巢之地,距伍鈞墓不遠的王喬洞石窟中,有北宋紹圣年間的石刻曰‘居巢紫薇洞天,則居巢括有巢湖東岸,今巢湖市一帶古亦有南巢之名。總之,古人所說的南巢地望,大體說來,在安徽江淮之間,以巢湖為中心的一帶地方。”(26)桀奔南巢的地望,北過合肥,南過桐城,東過巢湖,西界當為大別山。在當代,這些地方先后發掘出了一些文化遺存,很多學者指出這些是與二里頭文化相似的文化遺存,比如:有含山大城墩、肥東吳大墩、肥西大墩孜、壽縣斗雞臺與青蓮寺、以及六安西古城等。而二里頭文化因素在江淮地區的大量涌現,與相鄰文化的慢慢影響已經不相適應,只能用人群的遷徙來解釋才最為妥當。因此,也恰好證明了古文獻記載中的“桀奔南巢”。
崔述所著的《夏考信錄》,把自己懷疑的先秦、秦漢間所記載的有關夏的事跡進行了考辨。他秉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對古文獻中所記載的夏進行考辨,對缺乏證據的歷史事件,寧可以“不可考”為考辯結果,也不隨便下結論。崔述不宗門戶,不囿家法,求真求實,又不拘泥于考據。梁啟超就曾稱贊崔述為“名聲很大的辨偽學家”。崔述在疑古辨偽史上有很大的成就,對顧頡剛等古史辨派人員有很大影響,并為他們所看重,他們發展崔述之學,推動了史學的發展。當然,每個學者都不能避免在學術中出現的局限性。崔述學術中所出現的問題,有思想上與學術方法上的原因,由于他固守儒家道統之說,他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所以,盡管他能指出許多歷史文獻中出現的錯誤,但是一到最后防線,他就在圣人、圣王面前斂手了。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這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不能苛求。崔述的巨大功績就是他用獨特的視角,實事求是的態度在一片暗淡的古史研究中開辟出一條光明之路,為后世史學家研究中國古史打開了缺口,讓后代的學者能夠在他的基礎上,另辟研究的新路。崔述給后代的啟示應該是,不拘泥于文獻,不囿于門派,不隨便下結論,以負責任的態度來研究古史,要注重地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的結合,正確對待它們的結合,不能用地上材料去附會地下材料。就如顧頡剛先生說的:“因為古代的文獻可征的已很少,我們要否認偽史是可以比較各書而判定的,但要承認信史便沒有實際的證明了。”(27)
注釋:
(1)崔述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頁。
(2)崔述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頁。
(3)崔述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頁。
(4)邵東方:《崔述學術中的幾個問題》,《中國文化》,1994年第1期。
(5)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頁。
(6)吳量愷:《崔述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2頁。
(7)[清]崔述:《夏考信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9頁。
(8)[清]崔述:《夏考信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9頁。
(9)[清]崔述:《夏考信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9頁。
(10)[清]崔述:《夏考信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0頁。
(11)[清]崔述:《夏考信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9頁。
(12)孫淼:《夏商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94頁。
(13)孫淼:《夏商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93頁。
(14)沈長云:《先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頁。
(15)沈長云:《先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頁。
(16)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669頁。
(17)[清]崔述:《夏考信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1頁。
(18)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鄭杰祥編,《夏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18頁。
(19)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鄭杰祥編,《夏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02—510頁。
(20)鄭杰祥:《夏史初探》,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3頁。
(21)[漢]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5頁。
(2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936頁。
(23)[清]崔述:《夏考信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5頁。
(24)徐中舒:《夏代的歷史與夏商之際夏民族的遷徙》,鄭杰祥編,《夏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01頁。
(25)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周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8頁。
(26)杜金鵬:《夏商文化斷代探索》,鄭杰祥編,《夏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10頁。
(27)顧頡剛:《古史辨自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頁。
作者簡介:朱思遠(1989-),女,保定博野人,河北大學宋史中心研究生三年級學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經濟史;胡曉文(1990-),男,滄州中捷人,河北大學宋史中心研究生三年級學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