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說中藥(三) 中獸醫方劑的概念、組方原則及應用
王留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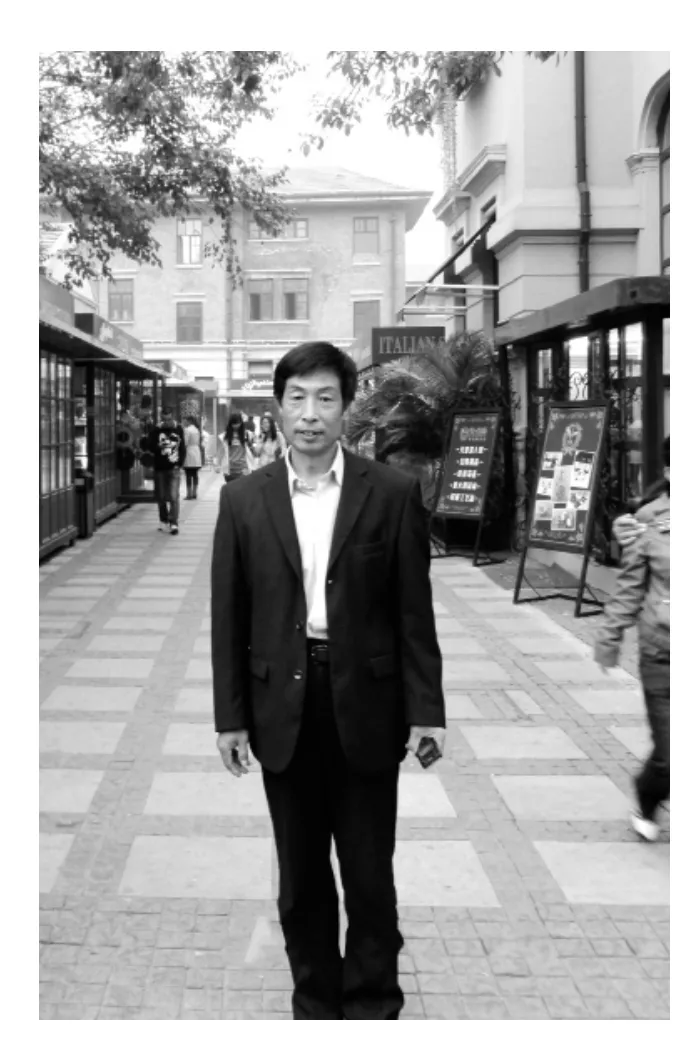
方劑是中醫醫療最終的手段,體現了中醫理法方藥的治療思維。每一首方劑都是根據中醫辨證而有目的、有依據地組設,而不是隨意地藥物排隊或堆砌。常言道,“有是證用是藥”,這也同時說明了方與證是密不可分的,一方一證便是中醫方劑的很好說明。方劑不但有嚴格的組方原則,而且在臨床應用上,根據臨證八法也可大概分為八大類別,分別是:解表劑、涌吐劑、瀉下劑、和解劑、清熱劑、溫里劑、消導劑、補益劑。但是,在具體臨床中又可相互結合,或者一方多法地應用。正如程鐘齡在《醫學心悟》中所說:“論病之原,以內傷外感四字括之。論病之情,則以寒熱虛實表里陰陽八字統之。而論治病之方,則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盡之。”
一、什么是方劑
方,即醫方、藥方。劑,在古代做“齊”,有調劑的意思。方劑就是由單味藥或若干味藥配合組成,是在辨證審因確定治法后,在該治法的指導下,按照一定的組方原則配伍而成的藥方。它也同時體現了對當前疾病的治法,以及藥物的合理使用等的工具性意義。因此,方劑的定義又可概括為:是由藥物組成的,是在辨證審因、決定治法之后,選擇適宜的藥物,按照組方原則,酌定用量、用法,妥善配伍而成。
既然方劑是在中醫理法方藥的指導下、合理選擇藥物組配而成,那就不代表有任何的隨意性。那些隨意組配,或者脫離開中醫理論的組合不叫方劑,只能是藥物的堆砌,其治療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這在禽病臨床中也是很常見的。
二、方劑的目的
簡單地說,方劑的目的既是治病,是充分利用或提高藥物的治療作用,并減低或消除副作用的醫療手段。每一種藥物都有自身特有的性能,其中包括寒熱性質、辛甘酸苦咸五味和歸經等。就歸經而言,大部分藥物可歸多經,同時可以針對幾個經或臟的治療。但疾病從初感到傳經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寒熱性質也是如此),因此藥物的取舍就只能是有用有棄。用的自然是治療意義,可棄的也許就是副作用。鑒于此,就需要配合其它藥物,一是增強藥物的治療作用,二是減低或削弱藥物的副作用,這是其一。其二,由于疾病的復雜性,往往會出現主證以外的其它證侯表現,而任何單味藥物是不可能涵蓋全面的,所以就需要有除了幫助主藥治療主證,同時也可治療兼證的藥物配伍使用,以此增強全方的療效,擴大治療范圍。比如麻黃,可歸肺經,其性辛溫,有發汗解表,宣肺平喘之功。當肺熱熾盛,邪在氣分之發熱咳喘的時候,宣肺平喘是其有利的一面,溫熱之性就成了不利的因素。因此配合石膏,一可以助麻黃辛散宣肺,二可以石膏之寒制麻黃之熱,達到清肺平喘的目的。再者,當君藥在方劑中是主藥,也是對疾病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臣藥次之,它的作用一是幫助主藥驅邪,提高主藥的治療作用,二是治療主證以外的兼證。佐藥有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佐助,二是佐制,三是反佐。佐助即輔佐之意,可以輔助君臣藥物的治療作用。佐制是通過配伍其它藥物而達到減低或制約某些有毒藥物的毒副反應。反佐則是應用與君臣藥性相反的藥物,以防藥物隔拒的出現。使藥,顧名思義有信使之意,也就是引經報使的意思,可引諸藥直達病所。另外,使藥還有一個調和諸藥的作用,可使全方平和不悖。寒邪襲肺,肺失宣肅,則又需配合杏仁,以麻黃之宣配杏仁之降,達到溫散寒邪,宣降肺氣的作用。此即為方劑的目的之一。
二是增強單味藥物的療效,也是方劑的重要目的。比如麻黃與桂枝、銀花與連翹等等既是如此。另外,方劑還有一個減毒的目的,就是通過配伍,使方劑中的有毒成分減弱或消失。某些情況下必須要使用具有毒性的藥物,但為了治療的安全,就需要配合可以制約此種藥物毒性的其它藥物,以此來達到安全有效。比如:半夏、南星配生姜,甘遂、大戟配大棗等等。
三、組方原則
即成方劑,就自然具備組方原則,否則的話就是藥物濫用,輕者無效,重者出現毒副作用,對病體有害無益。一般地說,方劑是由多味藥物組成,具體到每一味藥也是有主有次、有輕有重的(用量)。沒有用量上的輕重之別,就沒有主次之分,沒有主次之分,對疾病的治療就缺乏針對性。因此,好的方劑都是主次分明,方證清晰,藥專而力宏。

中醫方劑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最基本的理論就是“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君藥在方劑中是主藥,也是對疾病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臣藥次之,它的作用一是幫助主藥驅邪,提高主藥的治療作用,二是治療主證以外的兼證。佐藥有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佐助,二是佐制,三是反佐。佐助即輔佐之意,可以輔助君臣藥物的治療作用。佐制是通過配伍其它藥物而達到減低或制約某些有毒藥物的毒副反應,比如半夏配生姜,生姜可制約半夏的毒性等。反佐則是應用與君臣藥性相反的藥物,以防藥物隔拒的出現(藥物隔拒就是機體對藥物的抗拒,比如大熱之體使用寒涼藥入口即吐就是藥物隔拒,此時可稍加溫熱藥為佐,此現象即可消失)。使藥,顧名思義有信使之意,也就是引經報使的意思,可引諸藥直達病所。另外,使藥還有一個調和諸藥的作用,可使全方平和不悖,比如甘草。除了單味藥應用以外,一般地講,每一首方劑的君藥和臣藥不可少,佐使藥可根據具體情況可有可無,不必機械地追求。在全方中,君藥的量最大,臣藥次之,佐使藥再次之,以達到層次分明,治證專一。
方劑在藥味的選定上,也應本照著“急則治其小,緩則治其大”的做法。也就是說,病有新舊、急慢之別,新病、急病制方宜小不宜大,舊病、緩病制方宜大不宜小。這是因為,對于方藥來說,藥少則功專而速,藥多則雜而效緩;對于疾病來說,新病多實多急,證侯特點相對來說也沒那么復雜,治療不益大方,需“藥專而力宏”。舊病多虛多緩,證侯特點相對比較復雜,治療益大方緩圖。因此說,“治急者不可大,治緩者不可小”。另外,古代方書尚有奇偶之說,如《內經》云“近者奇之,遠者偶之后;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素問-至真要大論篇第七十四),但因沒有明確的實際驗證,所以未被重視。
四、方劑的分類
方劑的分類方法,歷代不一,根據醫籍特點,各有偏重,概括起來有五種:以病證分類,以病因分類,以臟腑分類,以組成分類,以功用分類。但是,方劑與治法是分不開的,“而論治病之方,則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盡之”,因此,也可以八劑概括,即:解表劑、涌吐劑、瀉下劑、和解劑、清熱劑、溫里劑、消導劑、補益劑。其中,解表劑可包括汗法和清法——發汗解表、清解表熱;涌吐劑主要就是吐法;瀉下劑是下法,但有寒下、熱下、潤下、逐水等之別;和解劑主要是和法,但根據證侯的不同可包括補法、清法、溫法等。其它清、溫、消、補也是如此,同樣可根據證侯的需要而包括多種治法。
雖然方劑的分類各有說法,但在禽病的應用中常用的并不多,常用的主要有清熱劑、解表劑、補益劑和溫里劑幾種。這是因為禽與人的物種上、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很多病癥在人有的在禽就很少發生甚至沒有。
五、方劑的變化及臨床應用
方劑的變化主要是針對經方或成方的使用,常言道,有成方無成病。意思就是說,現成的、固定的方劑可以有,但疾病是千變萬化的,一成不變的疾病是沒有的,因此需要證變方變,靈活掌握。《醫學源流論· 執方治病論》中也說:“欲用古方,必先審病者所患之證相合,然后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因此,臨床中使用成方要切合當前證侯,一定要做到”師其法而不泥其方,師其方而不泥其藥“。
方劑的變化主要有兩種情況,其一是藥味的增減。在許多情況下,疾病的主證雖然與經方(或成方)相符,但其它兼證或病體體況有所不同,這樣就需要對方劑的藥物進行增減,以達到切合病機的治療目的。但是,在加減的過程中,主藥不能變,主藥變則主證也會變,主證變了那就不是加減而是另擬新方了。比如雛雞群由于氣候或管理的不當,經常會有受風寒所侵而出現的發熱、惡寒、喘咳等癥狀,而”發熱、惡寒、無汗,麻黃湯主之“。可又因為雞與人不同,人可一汗而解,雞卻無汗腺所發。而麻黃與桂枝相須為用,其主要目的是開泄腠理,發汗解表。麻黃為其主,除發汗解表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宣肺平喘;桂枝在這里主要是解肌,與麻黃相配一個解肌一個發表,共奏開泄腠理,發汗解表。因而,桂枝可減。又由于雞被風寒所侵,傷的主要是肺衛。肺衛被傷則肺失宣肅而喘咳,是次要證或者是兼證,所以又可加蘇子。它一有辛溫發散之性,可助麻黃發散寒邪;二有止咳之功,與麻黃為伍共治喘咳,正是經方加減應用與禽病的案例。
其二是藥量的增減。方劑中如果某一味或幾味藥的藥量發生了改變,那么其配伍關系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方劑的功效和主治方向也會跟著改變。比如半夏瀉心湯和甘草瀉心湯,兩方都是由半夏、黃芩、干姜、人參、甘草、黃連、大棗組成。半夏瀉心湯的甘草用量為9g,功效和胃降逆,開結除痞。主治寒熱互結,胃氣不和證。而甘草瀉心湯的甘草用量增大到12g,功效益氣和胃,消痞止嘔,主治胃氣虛弱證。可見,當甘草的用量增大以后,由于甘草味甘歸脾經,功可益氣和胃為君,因此,整方的功效也發生了改變。再比如,禽病防治中經常使用的清瘟敗毒散,它是由白虎湯、黃連解毒湯和犀角地黃湯三方組合而成,功效針對高熱之氣血兩燔。但如果增大其中一方的用量比例,那這個方的方證也會隨之改變。比如增大黃連解毒湯的用量比例,那么此方又會增強燥濕的功效,可針對于熱病夾濕之證。

總的來說,方劑的目的是準確地切合病機,有效地治療疾病。無論是從理、從法、從方、從藥上都是一個嚴肅的過程。而且,就法與方來說,它們存在著主從關系,任何情況下都是法為主,方為從,正所謂“以法統方,以方統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