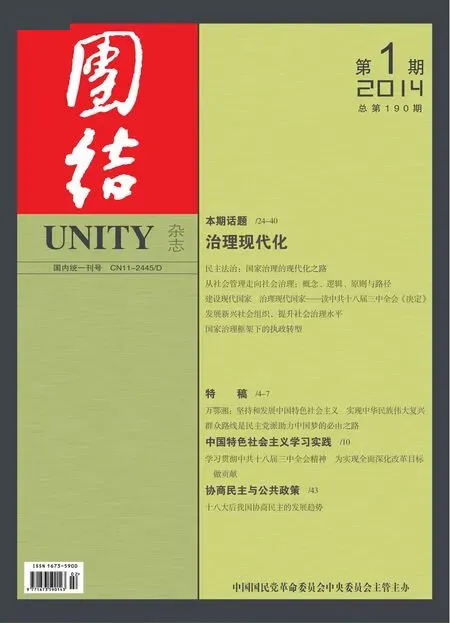國家治理框架下的執(zhí)政轉(zhuǎn)型
◎陳家喜
(陳家喜,深圳大學(xué)當(dāng)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教授/責(zé)編 劉玉霞)
一、國家治理標(biāo)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轉(zhuǎn)型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 “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biāo)。這不僅為中國未來發(fā)展設(shè)定了方向指引,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思維的重大轉(zhuǎn)變。在新社會背景和執(zhí)政環(huán)境下,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更加注重從現(xiàn)代治理理念出發(fā)重構(gòu)黨的執(zhí)政思維,注重從一元執(zhí)政到一元主導(dǎo)和多元參與;從一黨治國理政到社會協(xié)同參與的執(zhí)政機制轉(zhuǎn)變。因此,國家治理不僅是中國全面改革的目標(biāo)定位,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的思維轉(zhuǎn)型。
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具有三個鮮明特點:革命鍛造執(zhí)政地位,改革鞏固執(zhí)政基礎(chǔ),一黨長期執(zhí)政。一直以來,黨的執(zhí)政集中體現(xiàn)在實施領(lǐng)導(dǎo)和直接參與兩個方面,即黨領(lǐng)導(dǎo)人民當(dāng)家作主,黨委在各級政權(quán)組織中發(fā)揮 “總攬全局,協(xié)調(diào)各方”的核心作用;黨還直接參與國家政權(quán),參與重大決策和政策實施,黨的各級組織是黨執(zhí)政的政治依托。國家治理的提出,實際上是將黨的執(zhí)政納入到國家治理的框架之下,而非高于其上。換言之,在國家治理的體系和范疇下,黨發(fā)揮領(lǐng)導(dǎo)作用但非唯一的治理主體,黨的領(lǐng)導(dǎo)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要適應(yīng)國家治理的需要而進(jìn)行調(diào)適和轉(zhuǎn)變,要與時俱進(jìn),根據(jù)社會結(jié)構(gòu)的變化、信息技術(shù)的更新以及觀念思潮的發(fā)展,進(jìn)行治理理念、體制、機制和方式的調(diào)整。
二、黨的執(zhí)政經(jīng)歷三次重大轉(zhuǎn)型
建國以來,隨著社會政治情勢的變化,中國共產(chǎn)黨及時調(diào)整了執(zhí)政思維和執(zhí)政方式,至少經(jīng)歷了三次重大轉(zhuǎn)變。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從局部執(zhí)政到全面執(zhí)政,標(biāo)志著第一次執(zhí)政轉(zhuǎn)型。這一轉(zhuǎn)型的意義在于中國共產(chǎn)黨從居于反對地位的政黨,成為走向執(zhí)政地位的政黨;從在革命根據(jù)地執(zhí)政到全面領(lǐng)導(dǎo)國家政權(quán)。中國共產(chǎn)黨接掌國家政權(quán),黨內(nèi)精英成為國家精英,黨的綱領(lǐng)主張也轉(zhuǎn)化為國家意志。執(zhí)政后的中國共產(chǎn)黨按照自己的執(zhí)政理念不僅改造了國家政權(quán),也改造了階級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體制和觀念形態(tài),構(gòu)建了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鄧小平對此高度評價:“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xiàn)。”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標(biāo)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從革命黨轉(zhuǎn)向執(zhí)政黨,是黨的第二次執(zhí)政轉(zhuǎn)型。2001年江澤民同志提出 “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 “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jìn)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jìn)文化的前進(jìn)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進(jìn)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執(zhí)政黨的角色定位,進(jìn)一步擴大了黨的階級基礎(chǔ)和社會基礎(chǔ)。因為只有革命黨才會只代表一個國家部分人或少數(shù)階級的利益,對另外一部分社會成員進(jìn)行專政;而執(zhí)政黨必須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爭取盡可能多的社會民眾支持。因此,處于執(zhí)政地位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還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可以發(fā)現(xiàn),“三個代表”提出之后,新社會階層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而原先 “社會屬性”模糊的私營企業(yè)主不僅允許入黨,而且還被大量地吸收進(jìn)入各級人大、政協(xié)乃至黨代會。黨執(zhí)政的社會基礎(chǔ)得到進(jìn)一步的拓展和夯實。
國家治理的提出,蘊含一黨執(zhí)政和多元參與,標(biāo)志著黨的第三次執(zhí)政轉(zhuǎn)型。一直以來,黨的執(zhí)政被片面地理解為黨要包攬所有國家事務(wù)和公共事務(wù),其他政治力量如民主黨派只是發(fā)揮協(xié)商和議政作用,社會主體的參與熱情和智慧沒有得到充分發(fā)掘。從治理的詞源意義看,多元主體參與、協(xié)商、談判、互動,共同治理公共事務(wù)是其核心涵義。國家治理在堅持執(zhí)政黨領(lǐng)導(dǎo)地位的同時,也提高了社會多元主體和公民參與國家事務(wù)的重要性。特別是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公眾對于社會公共事務(wù)的參與愿望、熱情和能力不斷增強,并在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中得到充分展示。面對公民參與激增的趨勢以及由此形成的局部治理危機,國家治理的提出,意味著執(zhí)政黨以更為開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心態(tài),積極回應(yīng)社會的訴求和參與的愿望。
三、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前提是黨的執(zhí)政能力現(xiàn)代化
中國共產(chǎn)黨是國家治理的領(lǐng)導(dǎo)者和實施者,國家治理體系與社會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首先要求黨的執(zhí)政能力現(xiàn)代化。只有走在時代前列,能夠引領(lǐng)社會潮流的政黨,才能夠推進(jìn)和實現(xiàn)國家治理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為此,在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目標(biāo)框架下,當(dāng)前應(yīng)當(dāng)著重提升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能力和執(zhí)政水平,特別是制度適應(yīng)能力、決策包容能力、精英吸納能力以及腐敗治理能力。
提升制度適應(yīng)能力。中國共產(chǎn)黨一黨長期執(zhí)政,較少面臨反對力量的競爭與挑戰(zhàn),因此自身調(diào)適能力尤為重要。美國學(xué)者本杰明·斯密斯曾提出,一個政黨的執(zhí)政生命力取決于反對派勢力的強弱和尋租的難易程度。那些建黨初期即面臨群眾性政黨、外部殖民勢力等強力干預(yù)、并且租源有限的政黨,會更加重視選民的動員和自身建設(shè),生命力也更為持久。這一點,從蘇東等國家的共產(chǎn)黨垮臺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結(jié)論。因此,在一黨執(zhí)政條件下,尤其要注重自身的制度建設(shè)與制度適應(yīng)能力。這就要求執(zhí)政黨既注重制度體系建設(shè)、發(fā)揮制度對政黨能力的促進(jìn)作用,同時又能夠根據(jù)執(zhí)政環(huán)境的變化,主動進(jìn)行組織目標(biāo)、制度與觀念的革新,強化組織目標(biāo)對社會的感召力,組織制度對自身的約束力,以及意識形態(tài)對現(xiàn)實的回應(yīng)性。
強化決策包容能力。社會結(jié)構(gòu)的分化、利益觀念的覺醒以及社會沖突的增加,形成了局部性和群體性的治理危機,要求執(zhí)政黨決策能夠包容這些高度分化、異質(zhì)化甚至沖突性的利益訴求。馬克思曾經(jīng)深刻地指出,“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雙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獨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換。一般利益就是各種自私利益的一般性”。要妥善處理大局觀和個體觀的關(guān)系,尊重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正當(dāng)權(quán)益,謹(jǐn)慎以大局、全體、整體的名義要求個體社會成員犧牲自身的合法權(quán)益。要樹立利益相關(guān)者的觀念,在土地、稅收、養(yǎng)老、醫(yī)療、就業(yè)、教育及戶籍等涉及千家萬戶的政策制定時,更需要讓政策利益相關(guān)者參與進(jìn)來,通過構(gòu)建利益表達(dá)和綜合的制度通道,讓社會各主體將利益訴求有序反映到?jīng)Q策環(huán)節(jié)中來,形成各種社會利益的協(xié)商與平衡。
提高精英吸納能力。政黨的興衰存亡還有賴于不斷進(jìn)行精英的更替、循環(huán)和流動。保持精英吸納機制的暢通是保持政黨活力的關(guān)鍵。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組織,也將組織的先進(jìn)性和精英屬性寫入自己的綱領(lǐng)。因此,執(zhí)政黨要暢通內(nèi)部精英上升的通道,選拔和培養(yǎng)富有能力和聲望的執(zhí)政骨干,對其賦予重任和機會;開放社會精英進(jìn)入通道,清除社會精英進(jìn)入政黨權(quán)力階梯的制度屏障,形成優(yōu)秀人才不斷輩出的選拔氛圍。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如何在堅持現(xiàn)有干部選拔制度規(guī)范基礎(chǔ)上,構(gòu)建優(yōu)秀人才進(jìn)入的綠色通道和成長機制,十分重要和緊迫。同時,也要注意防范執(zhí)政精英內(nèi)部的分裂與沖突,確保領(lǐng)導(dǎo)層的團結(jié)與和諧。
強化腐敗治理能力。腐敗是危及政黨生命的毒瘤,治理腐敗狀況也直接決定著執(zhí)政黨其他能力的實現(xiàn)與否。清除腐敗關(guān)鍵是制度建設(shè)與制度實施。要構(gòu)建嚴(yán)密可操作的權(quán)力監(jiān)督制度,不留真空、縫隙和死角,避免投機性腐敗行為的發(fā)生。從黨員干部的日常行為規(guī)范開始,如接受禮品、禮金、吃請等,規(guī)定細(xì)致入微、不留彈性。實行輕罪重罰,“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讓腐敗者在經(jīng)濟上傾家蕩產(chǎn)”,形成強大的制度嚇阻功能,有效打消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提高制度的執(zhí)行力,對貪污腐敗行為實行 “零容忍”,在法律面前,黨員與非黨員,領(lǐng)導(dǎo)與非領(lǐng)導(dǎo)一視同仁,一條標(biāo)準(zhǔn),一條準(zhǔn)繩,做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quán)、制度約束沒有例外”,做到 “有腐必懲、有案必查”,“老虎”和“蒼蠅”一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