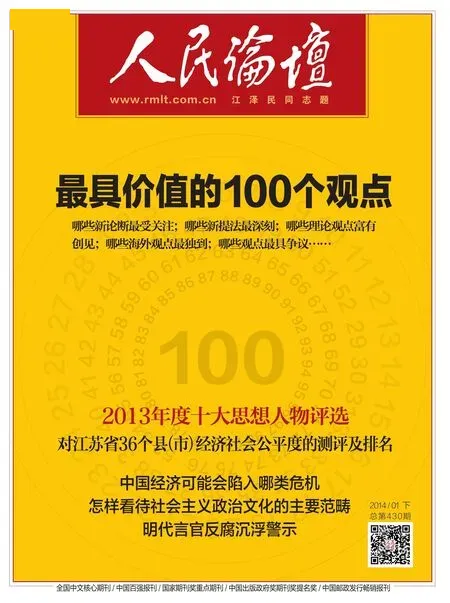論《史記》對黃老學的貢獻
陳金霞
黃老學是托黃帝、老子之言,以老子道家學說為主旨,同時兼采儒、法、名、墨眾家之長而形成的一套治國理論體系。它興起于戰國中期,經二百余年,至秦漢時發展到頂峰,黃老學不僅是對后世產生重大影響的一種重要學術思想,而且全面滲透到當時的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實踐。這樣一種重要和顯赫的學說,長期以來卻缺乏重視。《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不及道家,更不言黃老。這種忽視,直到司馬遷父子著《史記》時才有改觀,可以說《史記》對黃老學的貢獻極大。
《史記》為黃老學命名
黃老學是從戰國中期以來的客觀存在。它有自己的學者,如慎到、尹文;有自己的著作,如《管子·心術》上下、《慎子》、《淮南子》;更有效績顯著的治理實踐,如曹參用蓋公之言治理齊國。但在歷史上首先對黃老學從學術的角度予以關注的是司馬遷父子,首先對黃老學予以命名的是《史記》。
在《史記》之前的文獻中沒有出現過黃、老合稱,更沒有黃老學的名稱。關于黃帝的傳說,最早見于《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左傳》昭公十七年、《國語·魯語上》、《國語·晉語四》等史料,另外《逸周書·嘗麥》記載了黃帝戰勝蚩尤的傳說,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記載了黃帝“已勝四帝,大有天下”的傳說。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春秋戰國以來,黃帝這類傳說中的“帝王”逐漸脫離了神的身份,開始進入人間的帝王世系,黃帝還成為了姬姓氏族也就是周的始祖。在這些歷史傳說中,黃帝與老子沒有任何關聯。
黃帝在被歷史化的同時,也被學術化。在諸子著作中是否出現黃、老連用或者二人共同出現呢?首先看道家和黃老學派著作。道家《老子》不提黃帝。《莊子》內篇中《大宗師》黃帝兩見,都是夾雜在許多傳說帝王中被提及,沒有特殊地位,沒有具備學術特征。《莊子》的外篇和雜篇中有關黃帝的事跡較多,但老子和黃帝都是體道者或大道的宣傳者,有老子言黃帝的例子,卻沒有黃帝和老子并列提起。《鹖冠子》提到一次黃帝,與老子無關。法家著作《管子》多次提到黃帝治理天下,但都不提老子。《商君書》中《畫策》提到一次黃帝。《呂氏春秋》中《應同》、《去私》等篇中多次提到黃帝,與老子無干。《韓非子》有《解老》、《喻老》對老子言論進行解釋和生發,與黃帝無關。其他篇章如《揚權》引黃帝的話又與老子無關。儒家著作幾乎不提老子和黃帝,《論語》、《孟子》找不到關于黃帝、老子的痕跡。《荀子·天論》是儒家很少的幾次提到老子的例證之一。另外,《易·系辭傳》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黃帝。
總之,通過考察發現,在《史記》之前的著作中,沒有黃老連用的例證。只有到了《史記》中,開始大量出現“黃老”、“黃老之言”、“黃老術”等說法。如《樂毅列傳》說:“樂臣公學黃帝、老子”;“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老子韓非列傳》說:“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田叔列傳》說:田叔“學黃老術于樂巨公所”。《袁盎晁錯列傳》說:鄧章“以修黃老言顯于諸公間”。《陳丞相世家》說:“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等等,在這些敘述中,司馬遷有多種不同但是類似的說法:“黃帝、老子之言”、“黃老言”、“黃老之言”、“黃帝、老子之術”等等。“言”,言論,學說。“術”,學術。在《史記》的語言系統中,“言”和“術”是同義的。例如《外戚世家》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這里的“言”和“術”同時出現,都是指黃帝、老子的學說。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司馬遷是把黃老視為一種獨立的學說而一再申說的。
對于這一學說,司馬遷有時稱作“黃老”,有時稱作“黃帝、老子”,可見黃老學說的名稱還沒有完全固定。而司馬遷稱“黃老”的時候遠遠多于稱“黃帝、老子”,則可見他更趨向于命名為簡潔的“黃老”。正是這將定未定之間,更說明這一名稱確實是司馬遷的偉大創造。此后,“黃老”一詞才盛行于漢。把“黃、老”并稱或合稱,使之成為一種學術的名稱,是司馬遷對這種客觀存在的社會學術文化現象的真實記錄與概括總結。這個命名不僅僅是賦予一個名稱,而具有辯明學術的意義。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雖然各家著述中沒有“黃老”的名稱,但是在口耳相傳中有人使用了“黃老”或者“黃帝、老子”的說法。可是從目前存世的材料看,這種可能性不大。漢初習黃老的陳平曾自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①比他稍晚一點的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把“黃老”之實冠以“道家”之名。這說明在當時以“道家”稱“黃老”是比較普遍的。大概和司馬遷同時期的淮南王劉安召集門客集體創作了《淮南鴻烈》,這本被現在學者普遍認為是黃老學集大成之作的集體著作中也沒有任何一處指明自己所宣揚的是黃老學說。另外,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大量道家及與道家相關的文獻,這些文獻的入土時間是漢文帝時,其中也沒有黃老一類的說法。這些都佐證,在司馬遷之前和同時代,沒有學者使用“黃老”的說法。
《史記》記述黃老學發展史
《史記》作為紀傳體通史,它通過為黃老人物立傳而記載了黃老學發展史。《史記》雖然沒有明確說明黃老學起源于何時,但司馬遷通過記錄太公、管仲、范蠡等人的事跡,表明黃老學具有雄厚的實踐基礎,其思想萌芽可能相當早。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司馬遷向人們揭示出,在戰國中期,黃老學主要通過齊國稷下學者發展起來。關于黃老思想何時形成,現代各家學者還有不同意見,但一致同意的是,稷下學宮是黃老學發展壯大的重要階段。《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司馬遷以非凡的學術眼光記錄了稷下學宮的繁榮和蕭條,記述了稷下學宮中眾多學者的學術活動。
稷下諸子的思想對稍后的儒家荀子、法家申不害、韓非都有深刻影響。《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揭示,黃老思想以老子道家學說為理論源頭,法家申不害、韓非都是吸收黃老思想的營養成就自己學說的。曹元忠說:“太史公之傳老子、韓非,傳其學,非傳其人也。”②確實,司馬遷作這樣的人物列傳就是為了記錄學術發展史,保存先秦學術的面貌。如今,后人也確實憑著司馬遷的記錄才能尋繹出一條黃老學發展的線索。在《史記·樂毅列傳》中,司馬遷還記載了黃老學在齊地流傳的情況:“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這條線索彌足珍貴。在當代的道家和黃老學研究中,雖然說出土文獻《黃帝四經》等材料擴展了學術研究的視野,但學者依然需要借助《史記》等傳世文獻的記載來研究《黃帝四經》等材料。
隨著漢王朝的建立,黃老學迎來應用于實踐的黃金時期。在經歷了戰國時期的社會動蕩和楚漢戰爭的連綿戰火之后,經濟凋敝,人民貧困,國家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生產,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而黃老學的基本思想是實行無為而治,提倡寬簡的統治政策,主張統治者省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這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更適合漢初社會發展的需要,即“施于極亂思治之后”,因此大為興盛。漢初朝野上下彌漫著黃老學的氣氛,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人,都是黃老學的熱衷學習者和實踐者。也因為他們把黃老學應用于治國實踐,才取得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在《史記·曹相國世家》、《史記·蕭相國世家》、《史記·陳丞相世家》等漢代人物傳記中,司馬遷記載了黃老思想在漢初七十年的應用情況。漢初七十年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家富足,這是我國封建歷史上第一個盛世,為漢武帝時期的強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其后,由于漢武帝崇儒,也由于黃老學不再適應社會發展,黃老學在武帝時期逐漸衰歇,退出政治舞臺。
《史記》以史實詮釋黃老學理論
黃老學理論著作存世的并不多,如《管子·心術》上下等,又比較抽象,這給黃老學研究帶來很多困難。《史記》刻畫了許多活生生的黃老人物,通過記述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活動,詮釋了許多黃老理論,使黃老學研究相對豐滿許多。
例如,無為而治是黃老學的核心學說之一,以往的黃老著作中對其論述主要在于理論構架和設想,是司馬遷第一次在《史記·蕭相國世家》、《史記·曹相國世家》、《史記·汲鄭列傳》、《史記·田叔列傳》等篇章中通過生動的史實向人們展示了無為而治的方方面面。漢高祖劉邦時期,采取了去除秦朝苛法、開關梁馳山澤之禁、十五稅一等措施,使社會生產得以恢復,與黃老思想暗合。曹參在齊國向蓋公學習黃老之術,用以治理齊國,齊國大治。他入朝為相后,在全國推廣,成效顯著。呂后、孝惠帝時期,“復弛商賈之律,”③對于匈奴的挑釁,實行和親政策,所以能夠“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④。漢文帝時期,去除了收奴相坐律令和肉刑,史稱,“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⑤并且發展生產,“勸趣農桑,減省租賦。”⑥景帝時期,有“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⑦等惠民政策。
又如,把黃老哲學思想中有關謙退處下的內容結合現實政治形勢發展成為一種人生哲學,這是漢初對黃老學的重要發展,司馬遷通過《史記·留侯世家》、《史記·陳丞相世家》等傳記展示了這種以明哲保身為目標的人生哲學的應用情況。在老子思想中,那些所謂“權謀”思想和“謙退”思想并不是直接相關的,是漢初張良、陳平、蕭何這群黃老人物的實踐把二者緊密聯系起來,發展成為人臣的保命術。這種明哲保身之術,其總體特征是識時務,知進退,守分際,臨急能變,知機善謀。其表現形式是在避禍的前提下,不居功,在功利面前謙退自下;自污,授人以柄;藏其鋒芒,遠離政治漩渦等。對于這些處世的學問,《淮南子·人間訓》說:“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這可視為對漢初人物實踐的總結。
司馬遷創造性地發展了黃老學
司馬遷博采各家思想,加以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其中,他有選擇地接受了黃老思想的若干方面,并有所發展,成為他“一家之言”的組成部分,這里只著重強調如下幾點。
其一,在政治上,司馬遷特別贊賞“清靜無為”的治國方略,賦予其新內涵。老子首先提出用清靜無為治國。黃老思想通過因循理論把老子消極的無為改造成積極的有為。無為理論,應用在治國上就是不妄為,不干擾百姓的生產生活。應用在君臣關系方面,就是君無為而臣有為。司馬遷對于君主馭臣之術不感興趣,而對清靜無為的治國方略表現出由衷的贊賞。司馬遷給清靜無為賦予了兩種內涵:一是統治階層對人民要寬簡行政,約法省禁,不干擾百姓的生產生活;二是要求統治者少欲、節儉,不為私欲擾民。黃老理論要求人主“漠然無為”⑧,主要是從養生和治國理論出發,而司馬遷以民眾的需求為依據,發展了“清靜無為”理論。
其二,在經濟上,把“因民之欲”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黃老思想“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⑨,對于治國來說,最大的因循就是因民之欲。司馬遷對黃老學說最大的貢獻是根據“因民之欲”的理論,在經濟領域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司馬遷指出人求利的欲望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動力,從欲望動力的觀點出發,他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⑩,認為最好的政策就是遵循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順應和聽任各種經濟活動自由發展,最壞的政策是國家和政府與民爭利。在兩者之間,他還提出用經濟政策和教育手段來規范市場和民眾經濟行為,來補充“善者因之”的理論。在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司馬遷就提出了以遵循經濟規律和順應民眾求利欲望為基礎的一套宏觀經濟政策,這是十分寶貴的。
其三,在吏治上,把“循名責實”發展為各司其職。黃老主張在名正法備的前提下施行君無為而臣有為。要求君主運用刑名理論,循名責實,以獎懲為手段督責臣下。黃老學說以循名責實為手段達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這暗含著君臣分職而治的傾向。司馬遷把這種傾向更進一步發展為各司其職,要求統治階層的每一個角色都嚴守自己的職責。在《史記·陳丞相世家》、《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等篇章中,司馬遷通過對曹參、陳平、張釋之言行的記錄表達了這一觀點。也就是管理系統內部的上下不同層級應該依據各自的角色分工來實施管理行為,以此為基礎,不僅實現了君無為而臣有為,更要實現“上無為而下有為”,每一層的上級都應該給下級一定自由度,讓下級更有為。君主與丞相之間是上無為而下有為的關系,丞相與執事的卿大夫之間則是又一重上無為而下有為的關系,依此類推,就可以使每個人都明確自己的職責,各自在合理的范圍內作為。
我們以往對司馬遷和《史記》的研究較少從黃老學術角度考慮,研究黃老學也經常忽視《史記》的地位。事實上,它們是緊密結合的,司馬遷以及《史記》應該在黃老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釋】
①(西漢)司馬遷:《史記·陳丞相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63頁。
②(晚晴)曹元忠:《箋經堂遺集》,轉引自韓兆琦《史記箋證》,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781頁。
③(西漢)司馬遷:《史記·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18頁。
④(西漢)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12頁。
⑤⑥(東漢)班固:《漢書·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097頁。
⑦(東漢)班固:《漢書·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35頁。
⑧(西漢)劉安等:《淮南子》,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8頁。
⑨(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0頁。
⑩(西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53頁。
?高流水,林恒森:《慎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