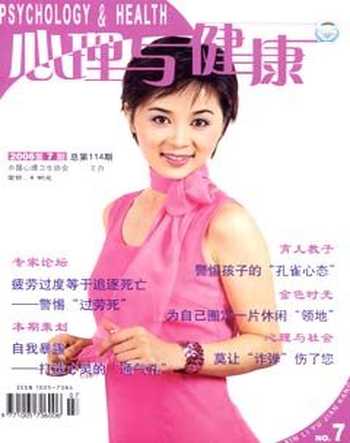心中的影子束縛了什么?
李雅文
姝紫和阿遠的故事,在我們的身邊并不少見,有很多和他們一樣的年輕人由于種種原因,雖然彼此愛慕但誰也不愿意去捅破這層窗戶紙,以至于事隔多年,當女為人婦、男為人夫時方才說出那句憋了多年的話:我曾深深地愛過你……然而滄海桑田,時過境遷,往事不堪回首。當自己的愛人成了別人的新娘時,后悔晚矣!
妹紫和阿遠的故事,是在“影子”的一手導演下演出的一場悲劇。
阿遠很容易地敗在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影子”門下。他不想做別人的影子,而姝紫的玩笑和初次見面時的那件“前男友”的上衣,使阿遠在心里給自己定了位,而在此之前他在北京這個城市已經給自己定了位。這一定位在他后來與妹紫的交往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阿遠懷著一顆尋夢的心來到北京,卻沒有一家單位愿意聘用他,他們對他那張中師文憑,簡直不屑一顧。晚秋的街道,空空的行囊,盤纏用盡,事業無成。在這種情境下,阿遠對自身的評價降低了,壞心情讓周圍的一切都染上了陰暗的色彩。天是灰的,心情也是灰色的,不良情緒像一股寒流在阿遠的心頭彌漫著。妹紫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阿遠很幸運地得到了姝紫的幫助。然而,在得到幫助的同時阿遠卻產生了一種“嗟來之食”的感覺:“制衣廠一定人手很少吧,要不,為啥這么快就搞定了?”
為什么阿遠得到了幫助之后,不僅沒有感激之情卻說出了這么傷人的話呢?這是因為人在心境低落時對事物的評價會出現一種凡事都往壞處想的傾向。從現代認知心理的觀點來看,這是不合理信念的一種,稱為“災難化”,也稱為“糟糕至極”。阿遠想自己不可能有這么好的運氣,之所以能這樣輕易地得到這份工作,肯定是別人不屑一顧的。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影子”的出現無疑進一步強化了他的這種“糟糕至極”的心理。于是,在這個心理背景下,阿遠很輕易地就被“影子”打敗了。
用現代存在主義的觀點來看,對“影子”的認識束縛了阿遠的行為,限制了他的自由,使他不能由衷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在很多時候都欲言又止,徘徊不前。對“影子”的認識,令他在處理和妹紫的感情時猶如頑石,雖然他不只一次地想“要是妹紫不把我當做他前男友的影子該多好”,但是“影子”一次一次地堵住了他的嘴。
姝紫在對待與阿遠的感情上也陷入了同一個誤區。或許是出于東方女性特有的矜持,妹紫沒有勇氣向阿遠直接表達愛意;或許她僅僅是為了浪漫,希望有一天,自己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會手捧鮮花向自己俯首稱臣;亦或許她想故意制造一些波折,讓自己的愛情充滿懸念……于是,“影子”在此刻橫空出世,這個“影子”的存在讓她可以瀟灑自如地向阿遠表達自己的愛意,卻也使妹紫對阿遠的愛猶如鏡花水月,撲朔迷離。
這種不確定感使得本來已不自信的阿遠既渴望愛又不敢去愛,而姝紫也一直躲在影子下,不愿意捅破這層虛榮的面紗,正如她在信中所寫:“臨走那天,我多么希望你對我說,我愛你,留下來吧!可是你沒有,如果你說了,我真的會不顧一切為你留下的啊!”反過來想一想,既然你愛他,為何不再勇敢一些,將信中所說的事實向他坦言,何苦要等到回到家中,事情無可挽回時空留遺憾!
希望妹紫和阿遠的經歷能給讀者以啟迪,幸福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要想獲得幸福就要積極地去爭取。要善于調節自己的情緒,要經常問問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勇敢地去爭取。人的命運有很大一部分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扔出去讓別人去選擇是一種于人于己都不負責任的做法,戀愛是這樣,做其他事情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