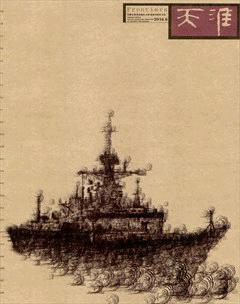箍桶匠的苦難美學
2014-12-17 02:28:42蔣藍
天涯
2014年6期
悖論的葡萄酒桶
箍桶匠是熱帶與雨季的寵兒,但酒桶呱呱墜地,卻像鼴鼠一門心思向往地窖。曾做過箍桶匠的詩人皮埃爾·布瑞說,葡萄酒桶是“一種怪誕、可笑、違反潮流、違反理性、違反實用價值的發明。我們怎么能想象,把這么結實而難以組合的木頭組裝成一個東西,還把液體裝在里面”。他的說法道出的悖論在于:如此嚴密、理性、集體主義的器皿,恰是出自浪漫之人的妙想!這是否暗示了暴力起事總是狂人們策動的呢?而且,利用這一逆向思維的,恰是高盧人。皮埃爾·布瑞就認為希臘人和羅馬人都較為嚴肅,冰結的思維者無法異想天開。雙耳尖底甕、羊皮酒袋、小酒壺,這些都是實用、適度、大眾、理性的!只有成天做夢、隨興所至的民眾才會發明細木條嚴絲合縫的酒桶。也許,凱爾特人都是詩人吧。盡管這是關于法國葡萄酒酒桶的一個起源個案,似難以放之四海——因為人們從古畫里得知,古希臘的酒桶造型已與后來葡萄酒桶甚為近似。這個充滿魔力的拓撲學空間容器,作為個人夢田的大本營,以一種貪欲、肥碩、笨重、欲望膨脹的造像,盡管與中土的陶質大酒缸有點相像,但開關自如、涓滴而下的高腳杯紅酒,與我們身邊大碗喝酒的江湖粗豪,造就了完全不同的美學風范。
箍桶匠的使命
大力者,多殘酷。手藝依靠對木桶的緬懷而活著,木桶則依戀手藝而延年益壽。箍桶匠通過對木片的反復纏繞與緊束,用密不透風的精湛功力來實現超級現實主義的剩余價值——這容易讓我們聯想起葛朗臺第一次見到未來的妻子時那務實而直搗本質的行家目光。……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