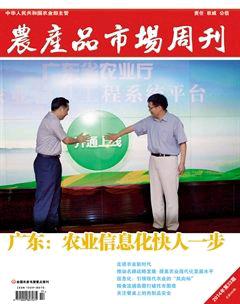糧食流通亟需打破托市困境
李平

糧食價格漲跌并不固定,托市價格卻一路上升,結果扭曲了糧食市場價格,國有企業包袱越來越重,當下的小麥“托市困局”具有標本意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亟待升級。
針對夏糧“十一連增”后的收儲情況,筆者在山東、河南、安徽、陜西、湖北等糧食主產省進行了調研采訪。多年來的托市政策穩定了農民收益,是國內糧食連年增產的重要推動力。但一些地方出現的共性問題不容忽視:連續的政策性收儲使得大量糧源進入國家庫存,造成局部地區倉容緊張;一路上漲的托市價引發“天花板”效應,形成多重“糧價倒掛”現象。
農業專家表示,某種程度上說,當下小麥“托市困局”具有標本意義,有關部門應統籌考慮,以構建目標價格體系為切入點,更好地發揮市場作用,推動糧食流通體制改革。
倉容緊張日益凸顯
在小麥主產區安徽宿州市埇橋區,區糧食局副局長宋長生告訴筆者,“自5月30日安徽啟動小麥托市收購以來,前期還有部分糧食加工企業零星收購,然后就大都是國家糧食收儲企業的托市收購。截至目前,90%的小麥收購都是政策性托市收購。”他表示,在面粉行業不景氣的背景下,不少糧食加工企業處于停產狀態,由此導致大量糧源進入國有糧食庫存,給倉容帶來很大壓力,一些農民未來可能出現賣糧難。
豐收帶來的類似“煩惱”在湖北省同樣存在。該省糧食局副局長費仁平表示,當前全省國有糧食倉庫爆滿,倉容緊張,如果不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不久后秋糧上市將很可能無處安放。
據了解,目前湖北省正在加緊維修危倉老庫,預計新增11億斤倉容,加上促銷騰倉部分,總計可以騰出倉容20億斤左右。但按照秋糧托市收購60億斤的規模,仍將有三四十億斤的缺口。
在傳統產糧大省河南,小麥購銷工作正在平穩進行。筆者從多部門獲悉,盡管目前該省尚未出現倉容緊張局面,但隨著糧食生產能力的增強,未來倉容缺口隱憂猶存。
中儲糧河南公司有關負責人介紹,河南糧食總產已連續8年超過1000億斤,2014年預計將穩定在1100億斤以上。按照《河南糧食生產核心區建設規劃目標》,到2020年該省糧食總產將達到1300億斤,商品糧將突破900億斤,需要有效倉容1000億斤。
“從收儲能力看,目前全省地方糧食企業有效倉容僅有421億斤,中儲糧企業倉容254億斤,倉容缺口高達325億斤。按照當前的政策性收儲勢頭,勢必對將來的儲糧安全帶來不利影響,并有可能出現賣糧難問題。”這位負責人說。
托市收購越來越“走不動”
除了大量收儲造成庫容緊張外,長期實行的托市政策在其他方面也遭遇了“天花板效應”,使得這一惠農政策的執行日漸陷入困局。
一是糧食經紀人“截留”托市政策紅利。在宿州市一處國有糧食收購點,筆者遇到了前來售糧的當地農民劉紅軍。他告訴記筆者,自己當天銷售小麥1.7萬斤,拿到了2萬多元現款。
然而,和普通農民不同的是,劉紅軍此時的身份是糧食經紀人。自從托市收購啟動以來,他就和家人一起開始在周邊鄉鎮收購糧食,平均每天收購4萬多斤。總計收購約100萬斤小麥。按照比托市價低3分錢的收購價,除去油錢、路費等各種成本,每斤賺1分錢左右。
筆者在安徽多個糧食收購點看到,類似劉紅軍這樣的糧食經紀人還有很多。中儲糧宿州直屬庫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該市有1000多個糧食經紀人,大的有2-3輛農用汽車,小的用三輪車運輸,收購量占糧食收購總量的百分之六七十,農戶自己來收購點售糧的僅占3成左右。
筆者了解到,糧食經紀人的大量出現,與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短缺,不少農村流行賣“地頭糧”息息相關。在小麥大省河南,中儲糧安陽直屬庫黨委副書記尚社民介紹,當地老百姓目前賣“地頭糧”的在40%左右,近年來這一比例還在增長。
河南滑縣王莊鎮種糧大戶張登云表示,國家啟動托市價的初衷,本來是保證農民種糧收益,現在因為種種原因,糧販子鎖定了農戶到國有糧庫的“最后一公里”,做起了旱澇保收的生意。“國家的錢沒少花,種糧農民卻并沒有完全享受到應有的實惠。”
二是糧價長期倒掛影響糧食市場健康發展。包括糧食加工企業在內的多方市場主體提出,自2006年托市政策實行以來,小麥托市收購價格一路上漲,頭幾年甚至以每年0.1元的價格走高。這種單方面的只漲不跌行情,扭曲了正常的價格形成機制,形成了國內與國際、產區與銷區、原糧與成品糧等多重“價格倒掛”現象。據悉,從2012年起,國內麥價就開始高于國際麥價。截至目前,進口小麥價格在2100元/噸至2300元/噸,而國內小麥到達南方港口價格為2600元/噸,每噸高出進口小麥超過300元。
湖北省糧食局一位負責人表示,現在的托市價,長期下去肯定行不通。“按理說,糧食價格漲跌并不固定,托市價格卻一直在上升。這種辦法把糧食市場扭曲了,國有企業背上了大包袱,越來越難以為繼。”
三是大量糧源“滯留”國有糧庫,帶來國家資金浪費。中華糧網分析師焦善偉表示,隨著政策收儲量的逐年增加,糧食倉儲也產生了大量成本。“以河南為例,最高時的收購率達71%,從糧食入庫到出庫,中間產生的收購補貼、保管費用、農發行貸款利息等,加起來每斤小麥有2角多錢的‘沉默成本。如果能把這些錢補給農民該多好。”
構建糧食目標價格體系要過三道關
業內人士表示,多年來執行的托市收購政策,有力推動了國內糧食產量連年增加,切實保護了種糧農民收益。尤其是在國際糧價波動期間,充裕的國內糧食庫存保障了市場供應,穩定了市場糧價,為國家糧食安全做出重要貢獻。但與此同時,隨著托市價格的日益走高,這一政策也逐漸逼近“天花板”,未來恐將難以為繼。
鄭州糧食批發市場董事長劉文進表示,按照目前的形勢判斷,托市收購政策越來越走不動了。“繼續走下去,托市價只能遭遇‘天花板,產生倉容緊、收儲難、賣糧難等一系列問題。”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中國農科院農經所所長秦富等專家認為,我國夏糧實現了“十一連增”,如果在部分地區適時在更大范圍內出臺目標價格政策,完善農產品價格和市場調控機制,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農產品價格的大起大落,有助于穩定物價;另一方面可以確保農業從業者有穩定的收入,實現對農民利益的保護。
多位專家認為,未來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以構建目標價格體系為依托,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充分發揮市場價格形成機制,讓政府實現從無微不至地“糧保姆”向抓大放小的“糧司令”轉變。但就作為口糧主要品種的小麥而言,要實現這一過程,至少要邁過三道“門檻”。
一是以什么標準制定小麥目標價格,以怎樣的形式進行補貼。從技術操作的角度而言,此間的許多環節都需要認真研究,而這也是基層種糧農民和有關市場主體最為關注的話題。
二是如何防止價格的大起大落。實行目標價格制度后,對政府部門的調控手段和能力都會提出更高要求,對于可能存在的市場失靈風險,需要提前做好預案。
三是市場行情漲跌的合理區間如何界定。一個正常的市場應該是在波動中維持動態平衡,而類似波動的上下區間容忍度在哪里,需要在實踐中摸索。
中儲糧河南公司有關負責人建議,在目標價格尚未建立和托市收購政策沒有退出前,今后應適當放緩托市收購價格漲幅,為目標價格改革留出空間;同時為確保農民利益,可嘗試將托市收購價少漲的部分通過其他渠道直接補給農民。
糧豐之下亟須破解共性難題
即使今年夏糧產量創了“十一連增”的歷史新高,但一些制約糧食生產進一步發展的因素在糧食主產區已經成為共性難題。走訪中,山東、安徽、陜西等糧食主產區干部群眾建議,多措并舉、綜合施策,破解難題。
首先,降低或取消產糧大縣涉農項目配套比例。由于發展糧食生產沒有稅收,全國的產糧大縣基本上是“財政窮縣”,縣財政幾乎是“吃飯財政”甚至“喝粥財政”,每年幾千萬元的財政資金對于許多種糧大縣十分寶貴。基層建議,逐漸降低或者取消產糧大縣在農業項目中的資金配套比例,減輕產糧大縣在發展糧食生產過程中的負擔。
其次,進一步加大對產糧大縣轉移支付力度。建議按“地方糧食生產總量”或者“糧食貢獻量”等指標,加大對產糧大縣的轉移支付力度。
具體來看,如果按“地方糧食生產總量”進行獎勵,生產一斤糧食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0.1元,即可真正調動起地方產糧積極性;如果按“糧食貢獻量”進行獎勵,那么轉移支付的金額還需提高,比如若一個縣糧食總產量為10億斤、總人口為100萬人,如果按人均年消耗400斤糧食計算,這個地方每年可為國家貢獻糧食6億斤,可按0.15元/斤進行轉移支付。
第三,借鑒試點地區做法,整合相關涉農資金。近年來,我國部分地區均進行了涉農資金整合試點。比如從2013年開始,山東萊蕪開展了涉農資金整合試點,在“資金性質不變、管理渠道不變”的前提下,將37項涉農資金整合起來,統籌安排使用,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有關部門可以在總結相關試點地區經驗的基礎上,逐漸摸索、形成和推行整合涉農資金的成功做法,形成支農合力,改變目前“撒芝麻鹽”的狀況。
第四,對老舊水利設施及時修繕并完善后續管理。制定好長遠規劃逐年、逐級落實,改變水利設施老舊局面。在后續管理問題上,可以借鑒我國部分地區進行的小農水管理體制改革試點經驗,緊抓市場化“牛鼻子”,力破“重建輕管”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