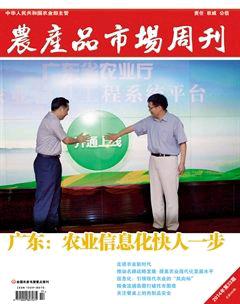食品安全法如何修改才“管用”
王金勇
破解“貓鼠游戲”監管迷局
針對全社會高度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將實行最嚴格的全過程監管制度,建立最嚴格的各方法律責任制度,對違法生產經營者實行最嚴厲的處罰,對失職瀆職的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實行最嚴肅的問責,對違法作業的檢驗機構等實行最嚴格的追責,五個“最”字讓人感到政府“重典治亂”的決心。的確,面對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問題,人們最直接的反應往往是,那么多的監管部門都干什么去了?
監管部門究竟在做什么呢?他們也是一肚子的苦水。一些基層食品衛生監督機關跟媒體訴苦,說有的消費者即使在食物中發現一只蒼蠅,都會要求查處,按程序,這往往需要兩到三個執法人員忙上幾天。數據顯示,我國約有45萬家食品生產加工企業,有2億多家農戶提供食品原材料,5萬多家企業從事食品零售,僅北京就至少有3萬家餐廳以及數不清的小餐館。
面對如此龐大的監管對象,若一味強調“最嚴格”的政府監管,將著眼點放在提高罰款數額、加大處罰力度上,可能導致食品安全監管在某種程度上淪為貓鼠游戲,逮著與否全憑幾率;有的監管部門甚至被相關企業“俘獲”,成為有毒有害食品的“幫兇”。
破解“貓鼠游戲”的監管迷局,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是,消費者發現自己食物中有蒼蠅時,為何不直接要求廠商賠償,或通過調解、仲裁、訴訟途徑維權,反而輾轉求助監管部門呢?自動放棄權利、被動等待監管部門維權的背后,凸顯的恰恰是民眾的私權保護缺失、維權渠道不暢的現實。
讓上帝的歸上帝,讓愷撒的歸愷撒。對食品廠商與消費者之間因食品質量或服務引發的“私”糾紛,完全可以通過完善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制度,暢通調解、仲裁、訴訟等小額維權渠道,鼓勵消費者積極主張、行使、保護自己的權利,一方面倒逼一些黑心廠商采取切實措施維護食品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讓飽受“案多人少”困擾的監管部門從大量“私務”中解脫出來。
至于組織制定食品安全技術標準和管理規范、公布食品安全信息、查處食品安全重大隱患等屬于“公”領域的社會公共事務,也應走出監管部門單兵突進的傳統模式,積極吸納社會和公民的力量參與食品安全治理。如規范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程序,確保程序能便利行業和社會公眾表達訴求、吸納意見。對食品召回后的“回流”問題,在堅持企業食品安全員內部監管的同時,可以探索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外聘專業人士擔任食品安全員,加強社會力量對企業的外部監管。建立有獎舉報制度,鼓勵社會各界和公眾參與食品安全監督。
從字面到桌面,配套落實是關鍵
法律是一種規則,而適用是規則的生命。本次食品安全法修改面廣、懲罰力度大、針對性強,但“造法易、執法難”,食品安全法修訂后,如何確保食品安全從字面走向桌面,不僅是百姓最大的期盼,也是保障食品安全關鍵所在。
從執法體系而言,本次立法修改對風險分級管理制度,對各方法律責任制度的確認,能夠權責到位、有效督促、跟進管理。然而原本多部門共管又不管的“九龍治水”格局尚未完全打破,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的上下關系、平級關系也未完全厘清,延伸到鄉鎮一級的支脈力量和專業整治能力更顯羸弱。不僅如此,如何明確執法權限、如何確保執法產生聚力作用,這些顯然都還需要細致的配套措施。
配套法規、檢疫標準需完善并體系化。食品安全的鑒定與判斷、肉品檢疫與檢測、食用添加劑的不斷創新和涌現等等,這些都給現存的食品安全監管提出了新要求。例如近期玉林狗肉節所暴露的狗肉食品檢疫“短板”,就其標準而言只有幾年前農業部的“產地檢疫”,這就導致在執法中本應針對犬只的個體檢疫,變成了對車輛附帶的產地檢疫,即從“逐只檢疫、一犬一證”,異變為“一車一證”,這種由于檢疫標準缺失產生的安全風險顯然成倍增加。
公益訴訟的配套保障不應缺失。食品生產的規模化、網絡化及產品的多元化帶來的跨區域性,必然導致食品安全的結果危害面越來越大。在出現食品安全事故后,除公權介入并按照法規對企業和生產經營者予以雙責雙罰外,公眾損失也不應忽略,如何確保個體消費者能有效、及時獲得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中的救濟和賠償?難道還是繼續要求弱勢的消費者個體進行取證?面對技術門檻,消費者維權顯然乏力。從此層面而言,“社會共治”還需進行制度化分解。
除此以外,第三方食品安全鑒定機構、一定程度下的舉證責任倒置、食品安全責任險的險種范圍等問題,均是完善食品安全鏈、實現食品安全法“落地”的關鍵。
將預防貫穿各個監管環節
預防為主原則是國際上最重要的食品安全監管理念。筆者建議將預防為主的原則精神貫徹到食品監管的各個環節與流程,須在立法上明確以下事項:
明確食品安全監管由財政兜底,繼續強化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等基礎性工作。草案完善了一系列基礎性制度,如增加風險監測計劃調整、監測行為規范、監測結果通報等規定,明確應當開展風險評估的情形,補充風險信息交流制度,提出加快標準整合、跟蹤評價標準實施情況等要求,值得肯定。但縱觀以往風險監測等工作,部分地區經費不足的問題較為突出,成為監管活動有效開展的制約因素。尤其是較偏遠地區,相關監測、檢驗經費、設施購置費更難以獲得足額財政保障。建議將食品安全工作納入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作為針對各級政府的硬性要求,監管經費列入財政預算,明確國家對欠發達地區開展食品安全監管基礎性工作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確定企業自查和責任約談的法律效力,增強預防制度的威懾作用。草案增設了生產經營者自查制度和責任約談制度:要求企業定期自查食品安全狀況,發現有發生食品安全事故潛在風險的,立即停止生產經營并向監管部門報告;食品生產經營者未及時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隱患的,監管部門可對其負責人進行責任約談,監管部門未及時發現系統性風險、未及時消除監管區域內的食品安全隱患的,本級政府可對其主要負責人進行責任約談。但草案未明確企業自查和責任約談的法律效力和后果,且可能成為相關主體逃避法律責任的借口和托辭。企業自查和責任約談制度的實行,不代表監管執法可以存在任何的懈怠和寬松空間。出現食品違法或瀆職情形,該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和實施行政問責的,應當依法進行,而且應明確,既然在自查和約談后依然出現問題,應在法定界限內從重處罰處分,提升預防制度的潛在威懾力。
對食品安全違法犯罪行為的懲處,亦可以適當引入預防原則精神。食品安全違法犯罪行為與傳統違法犯罪行為不同,一旦發生就會造成巨大損害后果,有必要以預防為主作為規制原則,將違法和犯罪預備行為明確作為執法打擊的對象。如有些食品生產經營者,大量購入變質或有毒有害原料,無法說明合法正當用途的,則可認定其生產劣質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違法犯罪嫌疑極大,通過食品安全法與刑法相關條文規范的銜接和完善,完全可以追究其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