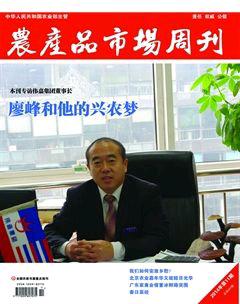澳大利亞低碳農業考察報告
根據2012-2013年度中澳農業交流團組計劃,去年11月,由農業部科技教育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農業部環境保護科研檢測所、農業部國際交流中心組成的低碳農業考察團一行5人,赴澳大利亞進行了考察。根據澳方安排,考察團走訪了墨爾本市的莫納什大學和梅爾基金會、悉尼市議會、瑙拉市馬尼拉生物乙醇廠、多爾比市生物乙醇有限公司、昆士蘭科技大學等單位,圍繞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相關議題與澳方有關單位進行了深入座談,對澳大利亞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進行了系統總結。現將有關情況匯報如下。
澳大利亞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經驗
(一)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澳大利亞十分重視農業資源的利用與保護,從農業布局到具體技術措施都圍繞著合理利用農業資源、保護農業環境進行。一是努力提高耕地質量。近10年來,該國政府每年投入5000萬澳元,支持耕地質量提升技術研發。以保護性耕作技術為例,政府對購買免耕播種機的農民補助10%的購機費,對改傳統播種機為免耕播種機的農民補貼50%的技術改造費用。經過十余年的發展,澳大利亞實施保護性耕作技術的耕地面積已占80%。據澳大利亞農業部協調員Colleen女士介紹,實施保護性耕作技術,在改善耕地土壤結構、提升有機質含量的同時,能夠節水30%-40%,促進糧食增產20%-30%。二是有效節約水資源。在農業用水方面,澳大利亞規定灌區內的農戶對灌溉和畜牧用水擁有的使用權與其擁有的土地面積相掛鉤。同時,在灌區內建設和完善用水信息計量監測系統。例如,在新南威爾士州部分重點監控的農業灌區內,地表水用水計量設施普及率達94%,地下水用水計量設施普及率達34%。三是推行適宜的耕作方法。許多農場在麥茬地放羊,以羊糞肥田,并利用豆科植物,實行麥豆輪作,促進耕地資源合理利用。四是平衡土壤營養成分。澳大利亞土壤缺乏活性的硼、銅、鋅、錳等微量元素,影響作物的生長和羊毛的產量與質量,通過增施微量元素肥料,提高耕地產出率,效果顯著。
(二)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基金。澳大利亞建立了保護生態環境用途的公共基金,各級政府可以從中獲得資金支持。例如,為了恢復和保護生態環境、減少地方政府在事權和財權上的相互推諉,1997年澳大利亞環境部和農牧業部共同成立了預算總額為15億澳元的自然遺產保護信托基金會。該基金會通過對項目提供資金幫助,帶動了其他資金的投入,促進了聯邦和州兩級政府在自然資源管理、環境保護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相關政策的協調和統一。在農業方面,該基金近年來的最重要貢獻是改善了澳大利亞農業主產區——墨累·達令盆地主要河流的生態系統和水體質量。在這個區域,信托基金會提供1.63億澳元,以鼓勵農民使用生物防治、天然農藥、低氮低磷化肥等環境友好型技術,同時為農民從事生態恢復的投工投勞支付報酬。經過10年的努力,盆地內土地鹽堿化趨勢得到遏制,河流局部藍藻爆發事件大大減少,墨累·達令流域河岸生態系統基本恢復。
(三)開展農業生態補償。澳大利亞向潛在排放污染或破壞生態的農業生產者征收一定的稅收,用來補償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例如,澳大利亞針對畜牧業的溫室氣體排放,向畜牧業生產者征收一定的稅收。近年來,政府還探索實施“押金—返還”制度,實現對生態的補償。例如,規模化畜禽養殖企業生產之前必須繳納一定的押金,保證將其畜禽糞便轉化為有機肥,并合理施用到田間。這樣,企業在某一地區生產,就必須租用一定面積的耕地來消納糞肥。而且,押金是否返還給企業必須通過驗收來決定,通常是將土壤質量同鄰近未遭破壞的相似區域進行比較。如果企業未能通過驗收,那么保證金就會被罰沒,充實到農業可持續發展基金中。為了避免加重企業負擔,澳大利亞政府并不要求用現金支付保證金,而是通過銀行或其他經認可的財政機構采用全額擔保的方式實現保證金的財務擔保。
(四)建立農業生態產權交易市場。由于大面積墾荒和過度放牧,澳大利亞的森林草原覆蓋面積一度萎縮。為解決這個問題,澳大利亞政府探索開展市場化的生態產權交易。考察團拜訪的新南威爾士州就在碳匯產權交易方面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成效。該州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碳匯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二氧化碳排放較多的造紙、鋼鐵等企業既可花錢購買其他企業的指標,也可以購買森林、草原等農業資源所有者的碳匯產權。配合碳匯市場,該州通過立法賦予碳匯產權法律地位,對超標碳排放者加重處罰力度。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將新南威爾士州的經驗推廣至全國,國會于2011年通過農業碳匯首次授信法案,規定農民和其他土地經營者可以通過保護森林、草原甚至合理耕種農作物而獲取碳匯信用額度,其他碳排放者可以通過市場從農民手中購買碳排放額度。這樣,農業的生態價值就通過市場化的產權交易方式得以實現。
(五)發展生物質能源產業促進溫室氣體減排。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澳大利亞政府通過制定稅收減免和生物燃料配額制消費等政策,大力推進生物質能源發展。澳大利亞生物質能主要以非糧農作物和畜禽廢棄物、林產品及廢棄木材,以及藻類、水黃皮、短期輪作的灌木桉樹等新型能源作物為原料,生物質能源的種類主要包括生物燃料、燃氣、生物發電等。澳大利亞政府明確規定,消費者使用含有燃料乙醇的汽油,每升免稅36澳分。新南威爾士州要求所有的交通燃料中必須加入6%的生物乙醇燃料。目前,生物質燃料已經占整個澳大利亞交通運輸燃料的0.5%,通過對廢棄木材等生物質熱化學轉化產生的生物電已接近澳大利亞年電力消費的1%。盡管比例不是很高,但澳大利亞各級農業部門都對生物質產能特別是新型能源作物的規模化持樂觀態度。例如,藻類每年可生產3.96億升生物柴油,水黃皮每年可生產0.9億升生物柴油,二者相加可以替代4.2億升化學柴油,約占目前澳大利亞化學柴油使用量的23%;生長周期較短的灌木桉樹每年可以生產4.3億升乙醇,可折合2.9億升汽油,占目前澳大利亞汽油年使用量的15%,或者可用于生產20.2億千瓦電能,約占目前該國年發電量的9%。與玉米、甘蔗等傳統生物質能源原料不同,新型能源作物可以種植在比較貧瘠的土地上甚至污水當中,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可以穩定生態系統。例如,水黃皮可以種植在沿海的鹽堿地上,藻類可以直接在污水中生長,二者都可以清潔土壤和水質,提高土壤質量。灌木桉樹可以種植在沙漠鄰近地區,既可以防風固沙,又能夠改造局部小氣候,甚至能夠改造沙漠。
(六)加強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科技創新。首先,澳大利亞加大資金投入,鼓勵節水農業、循環農業方面的科技創新。近年來,澳大利亞每年投入3000萬澳元研發地面灌溉技術、滴灌和微噴技術,以提高農業用水效率。同時,大力研發生活廢水的處理和再利用技術,促進水資源循環利用和環境保護。其次,澳大利亞積極選育栽培非糧能源作物。考察團獲悉,在農業部門支持下,澳大利亞已經成功培育了一種“能源甘蔗”,其乙醇轉化效率大大高于普通甘蔗,而其水土保持的生態效益也遠遠高于普通甘蔗。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為了防止能源作物與糧食作物爭地,澳大利亞政府重點支持畜禽養殖糞便的能源化利用。通過收集畜禽養殖糞便等廢棄物來生產沼氣,將偏遠地區生產的沼氣集中到氣網進行再分配,送到大中城市,能源利用率提高近80%。
(七)完善政府治理機制。澳大利亞在農業可持續發展上取得的成就,不僅取決于其豐富的農業資源條件,更重要的是與完善的政府治理機制分不開。1996年,澳大利亞將初級產業與能源部調整為農漁林業部,并賦予農漁林業部資源管理的職能,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護和改進了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自然資源基礎。改革后的農業管理體制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注意形成農業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管理體制,避免管理職能的交叉、分散、重疊,從體制上確保農業的競爭力;二是強化農產品的質量管理,建立可追溯體系和法規,加強過程監控,從制度上確保農業安全。近年來,加強對農民的生產經營銷售服務,減少政府對農業的干預,大力保護生態環境和生物安全,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成為澳大利亞農業部門關注的焦點。
(八)發動社會廣泛參與。在澳大利亞,農業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公眾的廣泛參與。目前,澳大利亞全國有4000多個“土地保護小組”和2000多個“海岸保護小組”,其最重要的職能之一就是促進農業資源的節約利用和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的采納。只要想為環境資源保護貢獻一份力量,居住在社區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資源保護小組的組員。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為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動力。
澳大利亞農業可持續發展對我國的啟示
澳大利亞是外向度很高的農業發達國家,其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始終十分重視農業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考察中我們在這方面的感受頗深:
(一)事權和財權統一,完善農業資源環境管理制度。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一是在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和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方面,建立事權和財權相適應的制度。一般來說,中央主要負責農村跨區域、跨流域、影響較大的生態環境保護項目和工作,比如長江上游和黃河上游的生態保護工程、基礎性農業環保科技研究、重要農業生態示范工程建設、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大范圍自然災害的防災減災等;而對于地區性的農業環保設施、小流域環境治理、地區性農業環保應用科研等則由地方政府負責。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職責并分擔財政支出責任,逐步實現農林水資源環境事務責任與財政支出責任的統一。二是探索將我國農業灌溉用水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相結合,強化相關監測、管控等配套設施建設,為農業可持續發展體制奠定基礎。
(二)國家和地方協調,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管理體制。主要有兩方面啟示:一是政府部門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方式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基金,直接進行生態補償。二是以信托投資的方式,籌措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資金,實現農業面源污染第三方治理。農業可持續發展基金需要根據自然資源的規模進行相應的層級劃分,初步可以分為國家級公共基金和省級公共基金兩個層次。國家級可持續發展公共基金的資金主要由中央財政負擔,用于跨省行政區域的耕地、水域污染和環境友好產品和技術推廣應用等生態補償;在中央層面,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協調機制,辦公室設在農業部,協調各部門定期召開聯席會議;省級可持續發展公共基金主要由省級財政負擔,用于開展縣市行政區域的生態補償;在地方層面,相應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協調機制,辦公室設在農業廳或者農委。由于可持續發展基金采用以政府為主體的運作方式,因此要建立嚴格的基金使用管理制度,特別要在資金用途和項目成效的評估方面做出嚴格規定,嚴防資金被挪用和浪費。
(三)稅費和擔保共用,探索建立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堅持使用資源付費和誰污染環境、誰破壞生態、誰付費的原則,逐步將資源稅擴展到耕地等農業資源。堅持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完善對糧食主產區等重點農業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機制,推動地區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建立并完善農業資源環境稅收制度,對農業面源污染者征收環境整治費用,對農業資源節約利用進行以獎代補。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擔保押金制度,由銀行或財政出面為企業復墾、減少面源污染提供信用擔保,要求種養企業完成資源開發之后恢復農業產地環境和植被覆蓋。穩定和擴大退耕還林、退牧還草范圍,調整嚴重污染和地下水嚴重超采區耕地用途,實現耕地、河湖、地下水等適度休養生息。
(四)管制和市場結合,健全農業污染排放控制手段。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建立農業污染排放產權交易市場,用于污染排放權的收購交易,甚至可以探索拓展農業資本市場,鼓勵企業從事節能減排的投資活動。首先,建立并發展農業資源環境產權市場,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及質量交易制度,建立市場化機制,吸引社會資本投入農業資源,節約利用和農業面源污染防控。先期可主要面對國內污染大戶,如農藥、化肥等企業進行交易,逐步融入國際污染排放產權交易市場。其次,以清潔發展機制為核心,在國內逐步引入農業碳匯產權交易機制,帶動農業碳匯項目實施,減少碳排放,發揮農業的碳匯功能,額外增加農民的碳匯收入。
(五)創新和推廣同步,大力發展環境友好農業技術。發展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是一項創新性工程,需要大力加強頂層設計和協調落實。要積極探索和完善我國生物質能源發展扶持政策,創新可持續的商業運營模式,實現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與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統一;要進一步完善農業可持續發展政策,發揮政策在解決環境和資源外部性問題中的重要作用,激勵環境友好農業技術的創新和應用;要積極探索和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和產品的市場信息引導機制,促進環境產品市場的外部收益內部化;要適應農業產業化、標準化、規模化、信息化發展需要,重新認識和頂層設計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推動農業發展模式的根本轉型。
(六)公眾和政府共謀,發動社會廣泛參與可持續發展。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充分發動社會力量來積極參與和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要在政策的制定、規劃執行、績效評估和過程監控等各個環節中,發動公眾廣泛參與,并創新體制機制,擴大農民直接參與。要在退耕還林、退牧還草、休耕輪作、生態涵養等政策實施過程中,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尊重農民的創造精神和參與意愿。要探索開展志愿者活動,適當利用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參與和監督農業可持續發展,疏通社會公眾利益訴求的渠道,彌補管理和法規中的漏洞,使農業可持續發展建立堅實的社會基礎。
(考察團成員:李少華、朱信凱、 汪誠文、楊鵬、李熙)